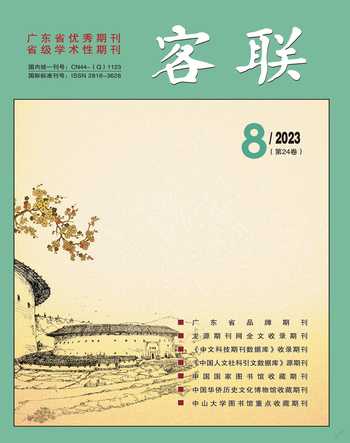昨夜星辰今夜风
2023-12-08望京
我喜欢老家的夜晚,特别是春天,和风拂面,繁星满天,银河又低又亮,硷畔下面的拦水坝里,春意盎然,蛙声乱成一片。坐在院子里数着星星,听着虫鸣,闻着草香,便随意猜想,那遥远的宇宙深处,会不会还有一个地球,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正在看着我呢?这样的天马行空,虚实相间的情形,倒也十分得惬意了。
一
进城生活多年的父母,一直放不下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村庄。
刚进城那会儿,母亲牵挂那颗刚刚挂果的苹果树,这些果树和她所预料的一样,由于没人管理,很快就枯死了,母亲因此心疼了好多年。我很理解,这些果树和我们一样,都是她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大的。后来,母亲总是念叨老家的那几眼窑洞,认为城里的楼房不如村里的老院子住着舒坦。是啊!人都恋土,觉着熟悉的地方住着轻松、自在、快乐、不压抑。就像我们去外地住酒店一样,总喜欢住同一家。何况老家里的山洼,沟壑,一草一木,她老人家那双自己勤劳的手都不止一次地抚摸过的呀。
二零一三年七月,百年不遇的大雨突然而至。老家的那院地方变得面目全非,院子和墙外种菜的圐圙(kūlǜe土石围起来的地方)被洪水冲出了几个大坑,硷畔倒塌,原以为牢靠的千年以上的石窑招架不住四十多天连续降下的雨水侵袭,五孔窑洞变形、裂缝,泥皮脱落,看上去已经弱不禁风,树上掉下来几片叶子就能把它压跨。父母看到后,只能无奈地哀叹水火无情。
原本每年夏天父母都要回老家住上幾天,但一场大雨,让他们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我们兄弟一合计,准备再动土木,花大力气改造一下老院子。但父亲不同意,说:“你们都在外边工作,我们上山以后你们又不回来住,往后的子孙们更不用说了,更不会回来。再说我们年岁已高,修好也住不了几年,实在划不来了”。不过,父母拗不过我们。
二零一七年春天,弟弟一番劳神费力,终于把老家的旧地方收拾好了,窑口重新接好,院子地面硬化,大门口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又逢上政府给家家户户打水井,新地方的整体条件比原来好了许多。
从此后,一到春天父母就回老家住,打理着自己的菜园子,早早就使得“一畦春韭绿”,和留守在村里同年等岁的一二十个老年人一起给村庄添加了生机与烟火气息。母亲和他们话题很多,每天说说笑笑,有了自己交流的圈子,心情好,精神也好。
但是,再怎么说乡下也比不上城里,难免尘土多,出行不便,父母热爱这片土地,从不在乎这些。我们姊妹几个也认为父母的事让父母做主,愿意住哪里就住哪里,想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就让他们干吧,不能因为我们所谓的面子惹二老不高兴,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晚年。
近几年父母除了冬天回县城居住,其他时间都在老家里生活,弟弟下班后十来分钟就回到家里,陪着老人,如果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都回去,应该是父母最开心的时候。孩子们在院子里嬉闹奔跑,大人们围着老人聊天,树上的喜鹊也会兴奋不已,争抢着叫上几声。
二
弟弟专门让人在窑脑畔上推出来半亩地,老两口把种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父亲是一名地质工人,一辈子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在母亲的指导下打理起菜园子倒是得心应手。进入菜地好像进入了一座艺术宝库,辣子、茄子、水萝卜、西红柿、豆角、菠菜、黄瓜、金针等,应有尽有。因为水美肥好,菜长得葱绿茂密,特别馋人,除了给满足儿女所需,还有多余的能送人。村里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会送过来。村里人就这样,纯朴敦实,互补有无,你来我往,关系都处的热热络络。有一家人做的芝麻辣子酱特好,母亲舍不得吃都留给了我。一家人香得没有了吃相,辣的呲牙咧嘴、鼻子冒汗,还不由得再香一小口。
三
父母回老家后,我回老家的次数自然而然多了起来。
每次快进村时,我都想把车停远点多走两步,想亲自踩着属于自己的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是通向初心的路,通向血脉的路,通向真情的路,是我安放灵魂的路,唯一能倒背如流、闭着眼睛走也走不错的路!
我多次给儿子讲,原来的小路沿着河湾走,又窄又陡,弯弯曲曲,在河水里淌过来淌过去,到沟口大路上足足有十公里之远,经过多次改造才有了现在的一马平川,路程也缩短的不足原来的一半。不知道儿子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们当年没有人给铺路,要从村里走出来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曲折,我的少年时光最远走到沟口那所乡镇中学。
每次回到老家,父母听见有车回来,就赶快出来到硷畔上接应,总要帮我把东西从车上提回家,有时父亲不在家里我就直奔他的菜园子,肯定能第一时间看见父亲,看见被他侍弄得像帅哥靓妹一样的菜品,我多次发朋友圈展示,点赞的人比我发任何作品点赞的人都多。看来,父亲的菜品才是上乘之作!
我爱听父亲说他的菜,品种好,上来得早;南瓜结上多少,西瓜什么时间能吃;茄子怎么摘叶强枝,黄瓜、西红柿如何打顶增果。父亲俨然成了经验丰富的菜农,分享他的这份投入、充实、收获的喜悦很高兴。我明白父亲积极种菜是为了让我们都吃上无公害蔬菜,因为他看到村里几家务菜的人隔三差五地给菜上打药,他说买的菜根本不敢吃。春上他就让弟弟买了羊粪,所有菜没有农药化肥。经常让熟人给我们捎菜来,也嘱咐让我们一有时间就回来拿。
我沉浸在做孩子的快乐中,这种“啃爹”的福分,不是所有五六十岁人都会有机会享受的。
四
我周末下午一定要回老家去看望父母,得空去村子老柳树下走一走。以前老柳树下好似村里的一个小戏台,人们常年习惯在这里的聚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递搭着,说谁家小子闹下婆姨了,谁家儿包下工程了,谁家孙子考上好大学了。我去了话题变了,但主题不变,每次都能听到他们为我准备的“三套车”。哑巴媳妇,比比划划,意思是我比她掌柜的大两岁,但看起来小够十岁,话没有说完,马上就有人张牙“你怎么敢和人家比?”高家大嫂爱说母亲当年在村里受了多大的苦,虽然我听了很难受,恨不得穿越到过去帮母亲多干点活,也没办法让母亲当年能穿越到现在,少受点罪,我很感激这位大嫂,一定要好好孝敬母亲,把原来受的罪用现在的好生活找补回来,老村长常常当着众人的面说他们那代人的辛酸史,感叹我父母命最好,现在享福了。
五
去年清明节,我陪父亲和族人给老刘家祖上几代人上坟,都说老祖宗的五座坟坍塌得不成样子了。五座坟现在位于村子中心,一簇茂密的次生林增加了几分神秘,坟前一棵杜梨树粗到两个人都搂不住,树冠能遮风挡雨,是我们刘氏家族的“老槐树”。现在家族分布在县域好几个村子,一线城市和国外都有我们五服之内的刘氏后人。“五座坟”慢慢也就成了村里的一处地名,就像北京的公主坟、陕西的乾陵一样。我们添土上香后,想立碑不知道最上边的祖宗名讳,我提议立一个地标性碑石,书上“身在全世界,根在五座坟”。
记得小时候,有老汉老婆们不认识村里那些毛孩子,一看貌相就知道是谁家的后人,我感到很好奇。现在我年过半百突然也有了这种特异功能,遇到小孩子,一看就知道是村里谁家的孩子,孩子眼里闪着亮光和惊奇,我好像看到当年的自己。村里和我年龄上下差不多的人有三四十个,同年等岁的就有十三个,一起上学、砍柴、拔猪草、游泳、搧纸宝。自从我考学走了,四十年再没有见面,他们都抱上几个孙子了,过得很幸福,我真替他们高兴。
记得儿子上小学时,和学校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准备干仗,互相责骂:“你是哪里这么个毛小子?”结果都是一个村里的,两个孩子瞬间烟消云散,成了好朋友。亲戚、本家、老鄉、一个村的这些根文化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血脉传承,在孩子们身上能体现的更为明显。
有一次,小我二十多岁的晚辈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打小就没有受过苦(劳动),不像他大受了一辈子。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说村里那架山上长什么草,那个沟里长什么树,在座的都说我说得对对的,他一下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原来也和他们一样,马上没有了距离感。我想告诉他,我爱村子对面山头上的柏树林,家家户户一出门就能看到它坚韧不拔地屹立在正前方,这是全村刘高两大家族兴旺发达的风水树,我爱村前塔沟石厂(音ǎn,指石崖横向内凹进去的部分)路边的泛水窖,以前无数的路人到此畅饮歇脚,它是故乡人古道热肠的见证,我爱天空中的鸽子群,他们用优雅的姿势飞出了温暖的声音,那是先人们放飞的善念,我更爱这里高家刘家每座山上下来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村子的未来和希望。
几天前,和一个朋友探讨石厂(an)这个词时,我坚持认为这个词是最为形象最为准确的,不能变通或使用别的词。我的理由是:一方面变通后就没有原来的味道,另一方面方言是作者给自己出具的身份证明,那里人说那里话,这是一种文化自信。朋友问我哪个村的,说村名也许他不知道,分不清楚沟里紧挨着的几个村子,但一听说塔沟石厂(an)路边的泛水窖,立马就说出我们村叫什么名字,还一口气说了许多当年的故事。
朋友说很早以前延川人去山西的走的就是我村里的这条大路。南来北往的路人都要石厂底下喝水歇脚,许多人在这里做起了买卖。遇大暴雨,农民从山上跑下来避雨,多少人都能容下。特别是伏天中午,周围几个村子拦羊的人都要把羊群赶在这里歇晌午,羊群喝足泉水后卧下休息,眯着眼,悠闲地反刍食物,让人奇怪的是几群羊混在一起,再出发时,不要拦羊人分辨,他们自己开始组群跟着头羊,跟着羊倌出发,一个也错不了,这是不是喝了你村里的神水让羊也变得聪明了呢?朋友还说,在那里喝完水,有一个讲究,孩子们要把脚下的小石头捡起来扔在石厂(an)里边一个三米高台阶上,再开始走路脚就不会疼。朋友问我知道不,我哈哈大笑,知道,知道。
六
大概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个冬天的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一个人从外婆家往回走,走到刘高山下面的深沟里,突然头顶几只鸭儿盘旋尖叫,立刻营造出阴森可怕的气氛,不一会几只喜鹊加入盘旋队伍,叽叽喳喳,我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又过一会两只乌鸦加入盘旋,比他们飞的还高,虽然叫声低沉,“哇啊—哇啊—哇”,但穿透力很强,空谷回音,好似魔鬼的二重唱,瘆得我后背跟着这叫声一阵一阵发麻、紧缩,浑身忽洒洒起来一层鸡皮疙瘩,我不由得小跑起来。突然鸭儿和喜鹊轮流俯冲下来,又直上云霄。在它们往下俯冲了几个回合后我看见了真相,三只很大的黄腰正从侧沟里朝我跑来,在三只黄腰快要和我相遇时,它们不顾一切地冲下来啄这些该死的野兽,我没敢细看它们之间的较量,趁机快速爬上山逃之夭夭。
黄腰,一种群居动物,智商很高,性情凶狠,动作敏捷,一般体长六十公分左右,鼬身豹头,四肢短健,有黑色长尾,平衡性极好,有摔不坏骨头的说法;腰背部成黄色,故叫黄腰或黄瑶。人能套住狼,炸死狐狸,捉住猯,但没有人能直接伤害到黄腰。传说雨点能下哪里他们就能爬到哪里,经常偷吃鸡和蜜蜂,在饿极了时会向人下手,听说曾经三只黄腰吃过一个婆姨。陕北大人们哄孩子睡觉,不说狼来了,说的是黄腰来了。
可惜我当时并不明白,它们高空尖叫是给我发出危险预警,给野兽发出严厉警告。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这些精灵们自觉组织起来保护我。可我竟然一无所知,反而害怕他们。
鸭儿,喜鹊,乌鸦是三种不同的鸟,叫声也不同,他们能统一行动明显不是靠语言组织起来的,那它们靠的是什么呢?是心灵感应,还是出于本能的反应?我觉得都不是。是它们天生对人类有一种偏爱与友善,所以,当我遇到危险时它们才会出手相救。只不过是人类渐渐失去了这种心灵感应,而变得不懂它们。
作者简介:望京,男,陕西延川人,用握过枪的手开始握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