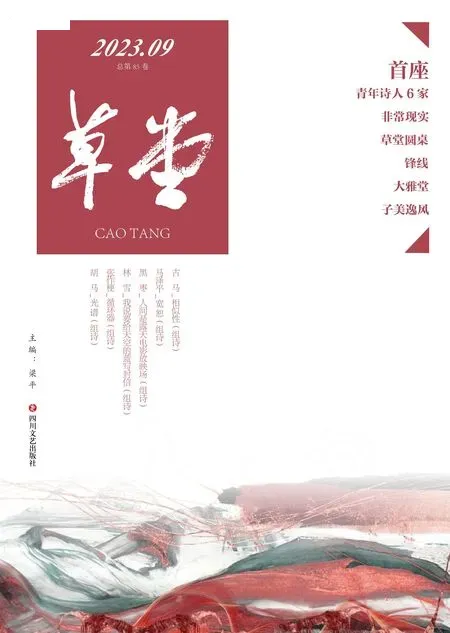乡土意识的觉醒与诗意的演进
2023-12-08袁锦钰
◎袁锦钰

袁锦钰
伴随着乡土作家的散失与乡土文学的日渐凋零,文学和乡土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乡土文学已经面临拐点。诗人作家们和乡土的血缘纽带日渐疏离。曾出身农民的作家们多年难回故土,关于乡土创作的激情也日益减退,难以写出真正反映乡土命运、乡土伦理、乡土情结的作品。
诗人林雪的作品给人以最直接印象与冲击的莫过于——“乡土”。从早期的“朦胧诗”到如今深入生活的乡土关怀,林雪的转变是飞跃式的,是一种诞生去旧存新式的“蜕变”。抛弃细碎缱绻的闺阁情愫,诗人将更多的关注投注于更加深沉辽阔的乡土大地。
乡土诗意中的诗人主体性确立
当我们谈论起诗歌与诗歌文本,诗人主体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点。诗人作为诗歌的主宰者,以一己之力构建一个精神的王国、一个思想的乌托邦。因此,在很多诗人的诗歌之中,诗人主体性是外显且无法撼动的。在诗人主体性的具体表现上,除了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批判,诗人们还在更多追求着诗歌的更高境界——对于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与救赎。当我们谈到林雪的诗歌:“我要在石头里坐好/成为石膏洞里/一簇气泡”(《我的马车带走了哪些词?》),“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人/我们/把握不住的事物/在对我们的/回忆中撤离”(《诗意秧苗》)。在《大地葵花》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林雪的诗歌中运用了大量“我”“我们”等第一人称代词,以第一人称对所见之人事物进行叙述,对个人情感也是直接地进行抒发,诗人主体外显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得以不断强化。同时,林雪也善于从旁观者的角度、以第三人称视角观察生活,“村庄睡在自己的经验里/河流向右转身/那些避难的人还未返回/被死亡截留的人/还没入睡”(《睡吧,木底》),看似是在讲述他人的事件与故事,但在细致叙述中流露出的上帝视角则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叙述者的存在感,并没有刻意地规避与隐藏,使得进行叙述的诗人虽未以第一人称视角直接亮相,诗人主体性却在诗行叙述之中自然得以展露,不断巩固加深,可谓“未谋其面已知其人”。
除此之外,林雪诗歌中的诗人主体性有着与其乡土情结相适应的独特特征。广泛来说,在文本中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使得诗歌主体成为主宰,这是诗人们建构诗人主体性的常用手法。该手法的特征便是以强烈道德感、崇高感凸显存在和自我矛盾斗争,并且使诗人主体符号化。而在林雪的诗歌中,诗人主体性并非通过拔高自身而突兀显现,究其原因便是因为诗人独特的乡土意识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其诗人主体性与乡土意识紧密融合,于乡土意识之中显现。林雪在创作中以“赫图阿拉”这一乡土意识的精神标杆作为关切人类命运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诗人主体与乡土情结自然融合,从而使得自身的创作既具有崇高普世情怀,同时又以扎根大地的乡土意识持续为这种“悲悯”与“救赎”输送精神给养,使得诗人无论是抒怀或悲叹都显得丰满踏实而不轻飘。诗人主体性也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建构,同时也成为诗人的乡土意识向着更深远层次进化的途径之一。
乡土诗歌中女性诗格的转变
当我们谈及林雪,“诗人”是她的第一标签,但在此基础上另外一个重要标签也不容忽视——“女性”,这是无论谈及其本人或其作品时都无法规避的一点。在这里“女性”不仅仅是指其生理属性,在涉及其作品时则指向“女性主义”。而林雪在其至今为止的诗歌创作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转型与蜕变,其中女性诗格的转变则贯穿了整个过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诗人林雪就以《夜步三首》入选了当时轰动一时的选本《朦胧诗选》,这本诗选在当时的地位是历史性的。可以说,林雪在当时以一种使人惊艳的诗人身份于中国文坛隆重登场。尽管林雪在极其年轻的年纪迅速取得了文坛承认,但是在当时百花齐放的“朦胧诗”流派中,相比舒婷、北岛等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诗人,林雪所处的位置仍相对边缘。不可否认,受年龄所限,林雪当时的阅历与技巧还带有青年诗人身上常见的对于自我的过度关注和视野上的狭窄。但这时其作品中特有的女性的细腻与敏感已经成为林雪重要个人特色,同时也为其之后女性主义觉醒做好了铺垫。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自我精神的深度探索,林雪创作中的女性诗格已然萌发。正如其自述一般:“到了20 世纪90 年代,我觉得我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写诗的语言和语气:即女性经验、意识与角色,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理想、心灵、命运和情感。比如我在那个时代的工作、爱情或阅读,一次轻易的离别带来的永诀,在无数夜晚写下的诗篇,忍受过同样的孤独悲伤。这一切都曾经是我心中的诗歌素材,像《微火》《紫色》等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时写出,并被称为是女性主义写作代表诗人的代表作。”(林雪、许维萍:《诗歌:对大地和人民的热爱与低吟》)此时的诗人经历了情感的洗礼进而蜕变,与自己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在这一阶段,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已经有所调整,并且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诗歌中描写的对象也开始有了平凡的人和事。如果说前一个阶段诗人仍飘浮于朦胧诗意的“虚化的”诗情之中,到了这一阶段,诗人因内心精神的扩充与丰满开始向下沉,逐渐开始生长出向大地扎根的根须,女性主义不断成长和完善,同时乡土意识开始觉醒并且日益占据重要的篇幅与位置。
终于,沉浸于“淡蓝色的星”的诗人终于找到了通向诗歌更深处的道路,沉潜多年,诗人林雪迎来了又一次转型,而此次转型也可以看作林雪诗人品格的一次质变。2006 年,《大地葵花》集结出版,第二年便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一个寻找词语/并被诗歌寻找的女人/正在接近/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有生之日》)。《大地葵花》中这些超越了纯粹个人情感经验的诗篇,强有力地证明了诗人林雪已经完成了生命与哲学的伟大相遇,实现了从小我走向大我甚至无我的精神转变。
通过对其女性主义觉醒与女性诗格转变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林雪因生命体验的丰富使得女性主义觉醒的程度不断加深,而丰富的生命体验与不断觉醒的女性主义共同作用,促使林雪诗歌创作的核心日益下沉,最终触及深层的乡土意识内核——诗人的乡土情结。在诗人的乡土情结被触发之后,又反过来与已趋向成熟的女性主义相互融合进行补完,而二者补完的成果便是林雪女性诗格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以其独有的生命体验对女性主义的多元性、复杂性进行探索与思考,而这一生命体验的精神内核便是诗人的乡土情结。以女性的主体意识融入乡土文学创作,最终实现个人女性主义的真正成熟,同时也从另一角度对诗人乡土意识进行补充与支撑,是对于原本女性诗格的系统升级。在这次转变之后,林雪开始以细腻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广博的乡土故事,实现了女性主义与乡土诗意的完美融合。
“乡村客车”与博尔赫斯式的“小说”图式
博尔赫斯,其存在与作品是公认的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分水岭。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自不必赘述,且博尔赫斯的作品在中国一经登陆,就立刻在文坛上散播开来,掀起一股巨大的博尔赫斯潮流,引得无数中国文学创作者学习与模仿,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尔赫斯的出现使得传统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博尔赫斯从一个全新角度打破了文学种类的界限,其短篇小说总是带有诗化倾向与诗意色彩。这已成为博尔赫斯极具辨识度的个人标签。而作为在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创作者之一,诗人林雪在精神原乡和伟大思想的影响下,孕育出了与博尔赫斯的小说诗化相对应的具有乡土意识的诗歌的小说化。
“东州街到五龙30 公里/出城的路啊越走越摇晃/生活啊越来越荒凉” (《乡村客车》),这首诗里仅通过不长的篇幅就生动描绘了挤坐在乡村客车里的人们,诗人基于乘客们的身形与装扮,对他们日常的乡村生活进行了想象性描写。生锈的车体、原乡人的喉音、荆条叶子、晒干的毡靴和乌拉草……几乎没有丝毫多余笔墨,仅通过浑北大地上原生的些许意象,就使得乡村大地上人们生活的烟火气升腾于读者眼前心间,并且在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上更胜于冗长小说的铺排叙述,点线成面,于诗行中呈现出博尔赫斯式的精致的小说化。
“诗歌的小说化是一个概括性定义,总体来说,是诗歌从普遍抒情转向后现代普遍叙事的过程”(刘成康《论博尔赫斯小说中的“嵌套”艺术》)。在博尔赫斯小说哲学的影响下,林雪的诗歌创作中也蕴含着乡土化了的博尔赫斯式的“小说”图式。首先从林雪诗歌的语言上来看,诗歌语言的小说化通常被认为是诗歌的禁忌,但诗人却能用其卓越技巧和细腻感知,敏锐地寻找到二者之间的临界点,使其诗歌语言在诗与小说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自然流露出“博尔赫斯倾向”。其次,林雪善于在诗歌中构建一个沉浸式“小说场”,而这个“小说场”又通常以乡村为背景,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语言的组织上摆脱小说的松散叙述,使得诗歌结构更为紧密和富有“原乡”质感。同时,在有限诗句中承载丰富内容,也要求诗人必须从遣词造句上精心雕琢,使得每一行诗句都蕴藏着巨大信息量,为诗歌在意义上扩容。可以说,林雪的诗歌以赫图阿拉为精神原乡的大地为创作的根基与背景,融合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手法,共同构建出一幅“乡土小说式”的诗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