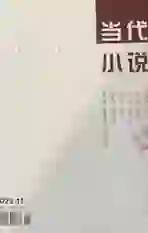我家的电视机
2023-12-03乔洪涛
乔洪涛
祖父把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打开,把声音开到最大。
深冬的北方,树叶尽落,院子里月光白冷,照在西厢房里那副硕大的黑漆棺材上,棺材前部朱红毛笔写就的“福”字隐约可见。寒风吹动东厢房的窗纸,那盘土炕渐渐变凉,祖父穿着毛皮大袄,窝在藤椅里看电视。
那把和他一样老旧的破罗圈椅,距离电视已不到一米。他已是望九之年,耳朵聋得厉害,眼睛也花了,看电视得趴在上面,才能听清声音。这个时候,常常已是午夜时分,整个村庄寂静无声,只有我家老宅子里发出轰隆隆吱啦啦的声音。大家都知道,那是祖父在看电视。
他傍晚六七点钟上炕睡觉,午夜时分已经醒来。他像一只老鼠,昼伏夜出,睡得早起得早。空旷的老院子,空荡荡的老房子,一个行将就木的身影,在深夜里与一台电视机为伴。此时,电视的大多数频道已经成了“雪花”,呼应着窗外的天气。不管什么频道,只要有节目,祖父都来者不拒。最爱看的是戏曲频道,咿咿呀呀,黑白舞台上的演员哭哭啼啼地演绎着人生命运,诅咒着世道人心,让祖父忍不住反复回忆一生所经历的各色人等,并作出总结告诫儿孙。
这台黑白电视是我家淘汰的。二十多年前,跨新世纪,我父亲买回了一台彩色的,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就搬到了祖父家里。祖父以前似乎并不爱看电视,那时候祖母还在,祖母爱看,每个夜晚都要到我家来看到半夜,然后拄着拐棍回家。祖父爱听戏,家里有一台老式留声机,有几张红红绿绿的戏片,诸如《刘墉下南京》《对花枪》《苏三起解》什么的,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反复唱下去。直到祖母去世,父亲把老电视送给他,他才成了深夜电视观众。
白天的他,爱打盹,往那里一坐,断断续续就是一天。父亲央他搬到新家里来和我们一起住,他却发脾气。“我还能动弹,我去你家里干啥!”祖父脾气不好,一辈子在黄河里开船,摆渡、捕鱼、捞尸,是根硬骨头。
老宅子胡同的邻居找父亲告状,说老头子电视声音开得太大,半夜聒得整个胡同睡不好觉。父亲让他把电视声音开小点,他不仅不听,反而在晚上把窗户打开,弄得半条街都睡不好了。直到那年腊月底,一场大雪下来,天寒地冻,祖父卧在罗圈椅里看着电视死去,这事才算了结。第二天父亲照常去探看,喊门不应,心觉不好,翻墙头进去一看,老爷子坐卧在藤椅里已经驾鹤西游,面前的电视正以最大音量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播报早间新闻。那一天是腊月三十,全国人民正喜气洋洋地迎接新年到来。
我父亲啪的一声关了电视,把他老子轻轻抱到炕上,整理好衣冠,给他盖好被子,用一块白毛巾搭在了他脸上。然后,父亲拽了拽自己的衣角,弹了弹衣服上的褶皱,依次把屋门和大门打开,用他做了半辈子小学教师的大嗓门拖着长音冲着胡同喊了一嗓子:
“愚子不孝,我父驾鹤西游了——”
足足有一年多,我家的电视没有打开了。张如在她卧室里刷手机,我在我卧室里看手机。去年儿子考上大学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家里就剩下了我们俩。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除饭在一个锅里吃之外,每人一间卧室,房门一关是深山,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家这台电视价格不菲。液晶曲屏,55寸,刚搬来新房时,我俩和儿子一块儿去电器商场选的。那时候手机网络还不发达,电视似乎也还可看,电视剧还能吸引女人,新纪录片还显得真实,综艺节目也还没这么无聊,电影频道还算丰富庞杂。张如看宫廷戏,儿子看球赛,我看纪实和电影,每当夜深人静,他俩看完回房,客厅就成了我的王国。我半躺在沙发上“一览世界”,连茶几上咖啡飘出的微苦的香气,我闻起来都会感觉到一些莫名的幸福。
直到后来,网络发达,智能手机攻克了我。
手机功能强大,各种照片、微视频铺天盖地,躺在床上划拉手机,美女、美食,包括一些刻意制造的感动源源不断,让人欲罢不能。初始我以意志力抗衡,最终溃不成军,双手投降,片刻不刷手机便觉心慌气短,坐卧不宁。
只不过看电视和看手机感觉不同,电视看后能让人生出些许幸福感,且会持续伴人入眠;而手机看罢,却总会叫人有莫名的空虚。
我把这些和张如交流,张如嗤之以鼻:“无聊!”
最近,她痴迷于一个因为生意失败被迫转型网络直播带货的“鸡汤王”,每天的直播一场不落,“鸡汤王”卖什么,什么就会变成包裹源源不断地被快递小哥送到家里来。有时候来得太多,她心虚理亏,也会悄悄把包裹藏在储藏室角落里。这般年纪,我自然掩耳盗铃,装作看不见,不把眼光瞄向那些地方。有时无意到她房间造访,会发现她的床头柜、梳妆台上总是频率很快地更换着不同的瓶瓶罐罐,那大概是用来涂抹脸部的化妆品或者饮用以养颜健体之类的滋补品,像面膜、虫草、枸杞、参片……我有时候趁她不在,也会捏一把枸杞放在茶杯里摇晃几下,但似乎也未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便也嗤之以鼻,冷笑一声:“无聊!”
这个年纪的女人,往往对自己的男人失望透顶,而对遥远的男人还抱有最后一点期望。身为有经验的中年男人,我自然明白此时万万不可随便干涉、劝阻、吃醋、心疼……如果定力不足,胆敢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加学识替她们分析一二,那一定是自取其辱,不仅起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被骂个狗血喷头,甚至引发一场海啸。当然,反之,如果你有胆量去对别人家的女人“循循善诱”,或许会有出乎意料的效果……但是切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老房子失火,后果很是严重。
电视成了摆设。推门回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休息,喝茶,刷手机,一抬头就会看见那个巨大的屏幕,它静静地立在电视墙前面。它已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只剩下机顶盒的指示灯一闪一闪。据说现在的宽带已经提速到了一千兆,炎炎夏季是各种火热的电视选秀节目的热播季,可以想見,无数资讯在纤细而庞大的网络线里拥挤着想要变成画面跳出来,向每一个观众展示,可是,电视机前面的沙发上或坐或躺的这个中年男人或者女人无动于衷,要么埋头看手机,要么躺着打盹。
我把眼睛闭上,世界便和我无关。喧嚣的世界以及火热的生活,像疾驰的高铁一样在眼前和耳边呼啸而过,我感受到了那种风驰电掣的速度。有几次,看手机累了,望向对面硕大的黑蓝色屏幕,我便想打开它,看看今天的“那个世界”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遥控器找不到了,也就作罢。有一次,我拉开三个抽屉,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两个发黄的遥控器,但拿在手里,面对无数按键,却忘了怎么打开。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半天终于想起来,狠狠地摁下电源键和网络选择键,屏幕却毫无动静,指示灯发出一点一闪即逝的红,即刻消失成一片漆黑。我掀开遥控器的后盖,发现里面的七号电池已经变软、变黏了。
“去超市时买几节七号电池回来。”我提醒张如,我懒得动。
“我半年不去超市了,我不用去超市。”她懒洋洋地回答说。
她的确是用不着去超市,她所需要的东西都在那个“鸡汤王”那里呢。她只需在手机上一选,一点,自会有身穿职业马甲的快递小哥服务上门,礼貌地轻轻叩响门环:“喂,您好。您的快递请签收。”
小伙往往瘦而精神,眼睛里可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张如这个时候会面带少见的微笑,优雅而有教养地对快递小哥报以微笑。
这个时候,我发现张如还是挺漂亮的。哦,这么多年,我几乎都忘了,当年我对她也是一见钟情的,她两颊有两个小酒窝,面貌端庄,皮肤白皙,笑靥如花。
快递小哥回以礼貌的微笑,收回签字夹,转身,把门轻轻带上,消失在门外楼道里。然后,张如转身,脸上的微笑会瞬间消失殆尽。她还给生活,还给我,还给这个家一张僵硬而冷峻的脸,似乎不这样便对不起这个家以及面前的这个中年男人的品位。
“砰!”关卧室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轻了,她略有愧疚地把快递藏在胸前,用日渐发福的身体遮挡住我的视线,开门,关门……可以想见,她手持剪刀划开快递外包装,掏出里面物品时的满足感、幸福感。
有幸福感和满足感就够了,不管是谁给予的。感谢电线那头的那个熟悉而陌生的男人,谢谢。
我曾想着把客厅改成书房,把电视墙改成书柜,张如不同意,说是看见书就头疼,电视虽然不常看,但是每个家庭所必备的电器,在那里摆着,也算合情合理。
“谁家不是这样?谁家没台电视机呢?”她说,“做人不要总是那么任性,这是家,家里要有电视才是家,你买的那些书你看过吗?”
我有些心虚脸红。
“你要想离婚你就明说,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她说,“你适合单身,你单身的话你把这里变成书库是你的自由,但是还没有离婚,你不能这样为所欲为。”
“好吧,按你说的办。”我懒得讨论,急忙转身进了卧室。
我知道,买书是我的恶习。我买了太多的书,这些年,这几十年,我总是源源不断地把书买回来,虽然读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慢。好多书买回来,书封或包裹都没有打开过,但我依然控制不住地要去买新书。遇到好的书,我甚至会几本、十几本地往家买,不同版本的,不同出版社的。买回来的书,有时候我会接着送人。但我自己写的书,我从不送人。
倒也不是因为谦虚或自卑,似乎是源于对自己书写的尊重。这话不好理解,此处我也懒得解释,解释给谁听呢?
于是電视机依然保留着,就像我父母家里的那台二十多年的老彩电,依然保留着一样。
我小时候,很少见到可读的书。那时整个乡村只有土地、山林、河流、庄稼这些“大地之书”,可以用镰刀、锄头、犁耙等等,一遍一遍地“翻读”。艰苦的劳动能把人累到虚脱,不到十岁的我跟着父母下地耕种、打药、割草、放羊……上学上到五年级,我家买了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
那几年,我家在黄河滩地种西瓜,一年能有五六千元的收入,但买一台电视机还是不舍得。没有电视看没有书看,夜晚就显得格外漫长,格外无聊,尤其是冬天。我常去祖父家听他讲老故事,讲鬼故事,听得晚了,天又冷,我就和他挤在炕上睡。后来,我们村养鸡的万元户红林家买回来一台电视机,才让我们的夜晚变得丰富起来。那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谁见过这是啥呀,我顶多只在村头看过几次拉银幕的电影,电视从来没看过。这电视比电影好,啥节目也有,啥时候看都行。红林的爹留福说,黑白电视机吧,就是黑天白天都能看,彩电不行,彩电只能黑了天看。我们就都觉得黑白电视好,要买就买黑白电视。但电视上长长的电视剧一集接着一集,好看是好看,一个月也演不完,真熬人啊。《射雕英雄传》一天只演一集,能把人急死。天不黑我们就往红林家跑,去一趟电视黑着还没打开;去一趟在演《新闻联播》;再去一趟,开演了,人家却把大门插上了——不插不行,人太多,全村的人都往那里跑,屋子里人挤不动。男人都是老烟枪,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屋里像着了火似的能把人呛死;女人爱嗑瓜子,兜里都揣着半兜瓜子,一把一把嗑得满屋都是瓜子皮。看电视也不老实,老是说话,一会儿说这个演员好看,一会儿说那个演员难看,聒得我们小孩子都听不清。大家只要来了,都不舍得走,一直到电视屏幕成了“雪花”,还恋恋不舍。
红林骄傲得像个王子,一会儿熊这个,一会儿嚷那个,一会儿故意把电视关了治人,一会儿又往外撵人。红林爹笑眯眯地不说话,坐在床头抽烟。来看电视的男人都带着烟,他抽一支就有人再递一支,红林爹一晚上能抽两盒,抽得咳嗽不止。红林娘好清静,人多了就烦,挂着的脸像个苦瓜。所以,等终于忍辱负重巴巴结结看完了《射雕英雄传》,到了播出《血疑》和《星星知我心》的时候,我们村上又悄悄添了几台电视机,那大都是赌气买的,他们嘴里“哼哼”着,放出了再去红林家看一回电视就猪狗不如的毒誓。那个冬天过去,过新年的时候,终于有几家花光所有积蓄或者借钱买了电视机回来。
我去红林家看电视,也被红林骂过。那是因为我们在“郭靖与欧阳克谁厉害”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我一时激动,没有顺着他。他受到挑战,气得大声骂我:“不要脸,自己家买不起,天天赖在别人家看电视!”他骂完,我就蒙了。我俩是好朋友,也是同桌,我学习好,他学习差,他总是抄我的作业。在学校里他对我很恭敬,没想到在他家里看会儿电视他能那样骂我。我又气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想转身就走,却被小军偷偷拉住,只好忍着看到最后一集播完,才恋恋不舍又愤恨地回家去了。我脸皮薄,从小没挨过骂,那天晚上回去,我蒙头在被窝里哭了半夜,醒了哭哭了醒,心里想着一辈子再也不搭理红林了。我娘听见了,跑过来问我,我不想说,只哭得浑身颤抖。我娘看我不想说,叹口气走了。躺在床上,想想自己平时是怎么对他的,他现在却这么对我……我越想越委屈难受,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爹我娘知道了原由,都不停地唉声叹气。后来,我爹和我娘商量了一下,开着农用三轮车就走了。我问我娘我爹干啥去了,我娘说去县城买肥料去了。我问大冬天买啥肥料,我娘说,冬天肥料便宜,过了年就得施肥,买了预备着。
那天下午天快黑了我爹才回来,三轮车上没见化肥,却拉回来了一个大纸箱子和一个大锅盖。我看见纸箱子上印的字了:熊猫牌……
“啊,电视机!”
我高兴地跳起来。我娘从屋里出来,既心疼又高兴地说:“真买回来了?”
我爹有些兴奋,说:“买回来了!你快去喊喊他三叔,让他来帮忙安电视。”
我三叔家前不久也买了一台电视机,他是村上的电工,知道电视机怎么安装。我一听,急忙说:“我去喊我三叔,我跑得快!”说完,便一溜烟跑走了。
我三叔正在吃饭,一家人围着煤球炉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推门进去,喊:“三叔,三叔,快点跟我走,去我家!”
我三叔一惊,说:“咋了?咋了?是不是你娘的羊角风又犯了?”
我说:“不是。是电视机,买了电视机,你快去给我们安上吧!”
我三叔把碗放下,吃惊地说:“你爹买了电视了?
真买回来了?”
我说:“那还有假,快走吧!”我拽着他的袖子,拉着他往我家跑。
趁他给我家安装电视和天线的工夫,我又跑去喊我祖父和祖母,让他们来看电视。“咱家有电视了,咱家有电视了!”还没进大门我就喊上了。
我奶奶比我还激动,放下饭碗就拿上拐棍跟我来了。我爷爷倒是没看出啥激动来,继续喝他的烧酒,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那得花多少钱?那得花多少钱?”
有了电视,整个日子一下子都变了。很多没见过的人,没见过的事,把我们震惊得一愣一愣的。我爹喜欢看新闻,喜欢关心世界上的事,一边看,一边啧啧称叹,一会儿说这个国家不好,一会儿说那个国家不孬。我娘看不懂,也跟着点评,说这人咋这么黑?说这些草原上的大羊没人要,要是逮一只杀了剁馅子包水饺,那多好。我们就笑,哈哈地笑,嫌我娘光知道剁馅子包饺子,不知道那是非洲大草原。我奶奶很准时,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过来看电视,她爱听戏,可戏曲频道不好找,有时候得碰巧才行。另外,我们都不爱听戏,一听我就犯困,我爹也不爱听,我们很少看戏曲频道。我奶奶在她家当家,说啥就是啥,在我家里却不争,我们看啥她就看啥,我们笑她就笑,看完了,大半夜深一脚浅一脚,我爹或者我送她回家。阴天的时候,天乌黑,有一回奶奶差点崴了脚,我爹就买了一个手电筒,打着手电送我奶奶。有时候我爷爷也跟着来玩一会儿,那就不用送了,他俩趿趿拉拉地慢慢走就行了。
这台电视一直撑了十多年,跨世纪之后,我家买了彩色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就送给了我爷爷。只可惜那时候,我奶奶已经去世。但我爷爷却慢慢地喜欢上了看电视,直到那一天看着看着驾鹤西游。
后来,我爹外出打工去了,我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到外地工作了,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娘自己了,那台彩色电视机与她作伴。我娘说,她一个人在家,睡觉也要开着电视,这样有个动静才能睡得着,如果把电视关了上床休息,反而要失眠,睡不着觉。这样,我家的电视几乎天天都开着,只要我娘在家,电视就不休息。
我问她:“看电视有啥意思?”
娘说:“电视才有意思呢。电视比你们都强,你们都不在家,只有电视天天陪着我。电视演啥我就看啥,咱也知道那些事儿不一定是真的。我这一辈子没出过门,心里想着只有看电视,才能知道人家咋过日子的。看看人家咋过日子,心里就敞亮些,要不,天天这样圈着,像圈里的猪,不是更没意思?”
我叹口气,不知道说啥好。
娘也叹口气,说:“要是你爹在家也还好点,可在家上哪里混个钱花去?”
那天半夜,张如突然推门进来,钻进我被窝,把我推醒,心惊胆战地说:“你刚才在客厅看电视了?”
我说:“我没有。我睡得正香,看什么电视?你不知道咱家一年不开电视了?”
她往床里侧缩,说:“那电视怎么自己开着呢?”
我说:“那怎么可能?”
她说好几天了,半夜时分都听见电视在响着,她还以为我半夜发神经起来看球赛呢。
我说:“我从来不看球赛,你不知道?”
她说:“我也觉得奇怪呢,还寻思你咋又看起球赛来了。”
我说:“别吓唬自己,我去看看。”我起床推门,客厅里一团漆黑,电视像一堵黑墙立在那里,安安静静,哪里有什么球赛。
我回到床上,说:“你做梦了吧?电视关着,一点动静也没有。”
她说:“我明明听见了,不是一天了。”
我说:“可能是你太累了,出现了幻觉。没事了,别自己吓唬自己,今晚就在这屋睡吧。”
她不说话,躺在那里,睁着眼睛想事情。我把灯关了,房间里一团漆黑,我们能彼此听见对方的呼吸,呼吸带着中年男女沉重的心思,在暗夜里持续着。
这样躺了半天,睡不着。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手,她轻轻地拿开了。
“你睡着没?”我问。
“你呢?”她说。
我笑起来,说:“失眠了。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不习惯了。”
她哼哼着,说:“别扭呢。我还是回去,回我那屋。”
她摸索著起床。我把灯打开,她打开门,快速地溜回大卧室,我接着听到锁门的声音。
看看手表,才三点多。我躺下,眼睛睁着,睡意全无。我把手机打开,点开老家的无线摄像头。老家院子里黑魆魆的,堂屋里却有微黄的灯光,一闪一闪。我有些吃惊,把镜头拉近,隔着窗户看到堂屋客厅里的电视在闪亮着。
这个时候还看电视?一定是忘关电视了。我想。
我把镜头再拉近一些,隐约看见母亲在沙发上坐着,电视一闪一亮的。
难道我娘还没睡觉?心头突然一凛,我想起来我爷爷半夜看电视的事,忍不住有些害怕。窗玻璃上映出一个苍老的身影,我眼睛有些潮湿。
我曾下决心把母亲接来城里住,再也不能让她自己那样生活了。可是她却住不惯,每次来不到一周就像病了似的,一门心思要回老家去。
母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有些担心,我想打开摄像头声音喊一嗓子,又怕大半夜的吓着她;想打个电话给她,看看时间还不到四点,也作罢了。
说来奇怪,这天之后,我家的电视又自动打开过许多次。张如有了心病,每天半夜焦灼得无法入眠,心惊胆战地等着电视自播。
她在卧室给我打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好好听听客厅里是啥声音。果然,仔细听听,客厅里仿佛真有人在说话。嗯,是电视里的声音。我侧耳倾听,各种声音交替传来,一会儿像早晨热闹的菜市场,一会儿像家庭里的剧烈争吵,一会儿还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枪响的声音……
我鼓足勇气,猛地推开门走进客厅——客厅里一切如旧,安静寂寞,月色弥漫。抬头看,阳台外月亮高悬。小区里寂静得可怕,一点动静也没有。
真是奇也怪哉。
我决定在客厅安装摄像头,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些声音来自哪里。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人间烟火,那些每天上演着的一幕幕戏剧,真的是在我家电视里藏着吗?
我躺在床上,放下手机,把窗帘拉开。月光钻进来,偌大的双人床,空空荡荡。我睡在一侧,另一侧堆满了我睡前随手翻看的书籍。书籍里全是汉字,它们也静静地躺着,仿佛一只又一只睁着的眼睛。
突然,在天花板的最顶端,我发现了一个红点。
它闪烁着,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可现在,它明显地在闪烁着。我腾地从床上爬起来,站着盯着它看了半天。哦,那里面也有一只盯着我的眼睛。
哈哈!我笑了一下,躺下了,像一摊烂泥一般躺在床上,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是谁安的摄像头,也许是建筑商,也许是前房主,也许是张如……但我想,也很有可能是一台电视在搜集故事,那些人间的故事。我们每天看着别人的故事,渴望看到新奇的生活,但同理,无可避免,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生活在别人的电视里呢?正如我们都想从电视里面看到别人的生活一样,别人大概也很想知道我们的生活。
这样说来,我既是观众,也是主角了。
“哗!”一阵掌声从客厅的电视里传来,不知道谁又获得了众生的赞赏。我笑了一下,关上手机,闭上眼睛,一阵困意袭来,我要继续我的梦中之旅了。
我梦见我们家的电视机从墙上跳了下来,面带微笑,缓缓朝我的房间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