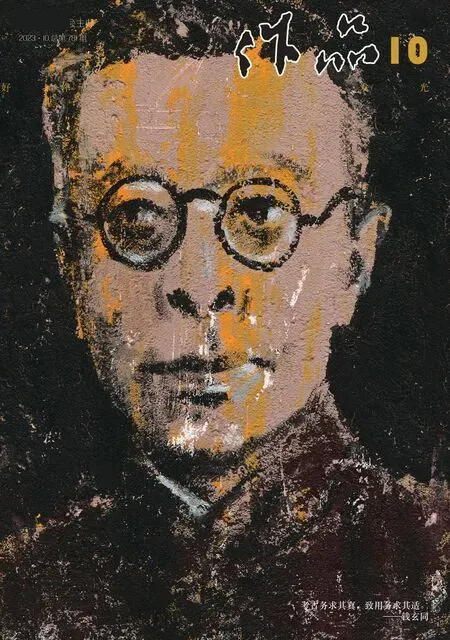沉入湖心(短篇小说)
2023-12-03陆铭晖上海外国语大学
陆铭晖(上海外国语大学)
推荐语:张群(上海外国语大学)
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经指出,“陌生化“不断更新人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过时感受,摆脱惯常化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通过创造性的独特方式,从习以为常中发掘出不同寻常的东西来,从而感验到事物的异乎寻常性。
小说《沉入湖心》便是这样一篇“陌生化”的小说,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体验,既熟悉,又陌生。小说以“湖”为中心意象,以故事套故事的嵌套结构,表现当下在校大学生的情感世界和对环境、对人与人关系的认知。在大故事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性别的模糊、美与丑的转换、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着力再现了一种焦虑处境;而在小故事中,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了,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意象:湖。一个浓缩的丰饶之海。湖心的夏娃恰如其名所喻,是原初的纯粹。大故事中对陌生女子的追寻是这种回归纯粹渴望的一种隐喻,也是对小故事主题与结构的呼应。大小故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且随时间发展逐渐交织、相互影响、合二为一,构成了一种完美的结构形式。故事展现了存在的焦虑、认识的焦虑这一深刻的主题思想,是一种成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手法,精准把握了当下盛行于年青人中的碎片化阅读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青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方式:完整性和全面性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小说是对年青人精神世界、心理处境的一种艺术再现。
无论是从叙事结构、叙事形式、叙事语言的视域,还是从主题思想、人物刻画的角度,该小说都是一篇非常值得一读的(后)现代主义佳作,完好地体现了这位在校大学生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娴熟的文学创作技巧。
大学毕业前一阵,赵曼说要拍一部毕设,作品名字叫《沉入湖心》,里头有两个女角色,一个短头发,一个长头发,个都不用很高,文静就行,长发那个出镜三次,短发那个出镜一次。我们有一个月时间去筹备并拍摄,立冬刚过的第二天,我们就跑遍大学城去招女演员,我们就是在那时见到的她,自始至终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称她为徐荷。
赵曼是在一年里最冷的时节找到我的,同往年一样,上海没有下雪。我们聚在琴房的窗边,赵曼、葛志文还有我,看着外头淅淅沥沥飘着雨。这部片子的剧本出自葛志文之手。十分钟的片子,最牛逼的地方在于要把演员两次扔进一个湖里,而现在是冬天,那个湖就在我们的正对面。我看着窗外,玻璃透出我自己的影子。
葛志文背靠着墙抽烟。
把演员扔进湖里的那一场需要用到一处浅滩,水没过脚踝,人躺下时一半在水里,一半朝着天空;还有一处稍微深一点的,水得没过腰身,女一号得身穿灰色长裙站在水里,吹笛子。那个镜头里,她将变成一只天鹅。
赵曼找了三个人,有扛摄影机的,有举灯光的还有打场记板的,一人一天五十块钱,不到开机绝对不来。我能感觉到情境很窘迫,“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个演员也没有。”
我花十分钟看完了葛志文的剧本,故事大体讲的是:有一个男的在湖边割草。有一个女的在湖心吹陶笛,那种陶土做的笛子,拿在手里像一块光滑的石头。另一个男的骑着一台破旧电瓶车,赶往一个地方见一个人。
见到她之前的那个上午,我们淘的二手电瓶车就到了,它的上一任车主是一个戴贝雷帽的女生,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第一眼把我认成了一个男孩。我们都不知道这台电瓶车这辈子都经历过什么,总之它旧得恰到好处,少一处划痕都不行。同剧本里构思的一样,这车的提速有问题,稍微开快一点就会发出嘀嘀的报警声,碾过减速带的时候,坐垫下边还会嘎吱嘎吱地响。葛志文为之花了三百块。
大学城附近最繁华的地段是一座商场,霓虹灯灯管和巨幅广告拼成的方形建筑,我这辈子见过最丑的人造物之一,大学生无处可去,扎堆往商场跑。大门顶头挂着一排大红灯笼,我们三个站在灯笼下边,赵曼对着手心呵气,葛志文的打火机点不着烟,我把半张脸埋在衣领里。
剧本是个双线发展的故事,一个故事有关镰刀,一个故事有关电瓶车。我们有了适合于长发姑娘的人选,赵曼的室友,她花了一个上午在寝室谈下来的,南方女孩,普通话说得不好。南方不缺长得漂亮普通话又不好的女孩,所幸这部片子里她不用说话,连近景都没有。我一定听她介绍过自己的名字,我也一定不记得了。后来我们都管她叫人物的名字,陈子夜,还有个希伯来语名字叫夏娃。
夏娃一共就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里,她站在湖心的柳树下吹陶笛,是不是柳树都无所谓,于志阳从湖的这一面看见她,她拿脚尖点过水面。于志阳是男主角的名字,赵曼说想让我来演。我说,“你确定要让我来演一个男的吗?”尽管我承认,除了想得很多,我的性格其实挺像一个男人的。
第二个镜头里,我跟夏娃同框,不过仍隔着半座湖的距离,那时夏娃得从岸上缓步走向湖心,越走越低,直至水面没过头发。“人物设置上来说,于志阳个子不高,所以你也可以。”
然后我站在这边的岸上,用鞋底搅和着浮萍往下探。
第三个镜头里,我浑身湿漉漉,刚从水里爬起来,水面没到我的腰间,镜头越过我的右肩看见远处水里的夏娃,然后朝左摇动,划过我的身后,再次照到对面时,水中央已是一匹白颈长项的天鹅。
天鹅是在电瓶车之后到的,葛志文骑着电瓶车带回了装天鹅的笼子,美中不足的是这是一只灰天鹅,样子不够优雅。我们管隔壁视觉学院借到了这只天鹅,暂时安顿在琴房,每天傍晚定时打扫它拉了一地的屎。整个房间里都臭气熏天。
因为种种不确定因素,最后我们没有用到那只天鹅,但是否极泰来,我们在琴房遇到了王瀚,一个突如其来还愿意照顾天鹅的人,那是后来的事了。
遇到徐荷之前,我们走遍了商场的每一个角落,从一层到五层,又从五层到地下车库,拦下了三十多个女孩,得到的答复都是,“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每隔一个钟头,我们就走到商场大门口去吸烟,看着正对面太阳一点一点投入建筑的夹缝。直到墙壁逐渐泛黄的时候,我们仍旧一无所获,有两个女孩愿意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赵曼让她们明早来东方政法大学找她。我们都知道她们不会来。
很难想象东方政法大学里能有一个艺术学院,有那么一帮人在学广播电视编导,也很难想象这帮人真的会扛起摄影机在大学城里拍电影。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遇到徐荷以前,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着这么一件事,一件我愿意称之为等待的事。
一
于志阳这个人很有意思,骑电瓶车的王浩见到他的时候,他总穿一件大一码的格子衬衫,把自己埋藏在衣领里。他们跑去操场上空无一人的看台喝最便宜的啤酒,于志阳总是随身在包里放着一次性杯子。这一天他告诉王浩,他在等一个人。
早在王浩骑着他的电瓶车到达以前,在静月湖边于志阳就发觉自己在等待一个人,那个湖就叫静月湖,取景地就是教学楼对面,水边的立牌上印着三个宋体大字“静月湖”,湖的名字比湖本身更美。那个他要等的人在湖中央的堤岸上站立,那是一座由陆地延伸向水中央的堤岸,堤的另一面连向树林,杂草长过膝盖。
“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夏娃在柳树下吹笛子。
夏娃就是陈子夜,陈子夜就是夏娃。
我一直无法理解赵曼的是,她总能把最丑的东西看出美来,对我而言那是一种虚伪。丑的就是丑的,比如静月湖,浅处污泥堆积,鸭子和水鸟的排泄物同腐烂的浮萍挤成一团,我们后来花了很大工夫才从中清理出一片空间,东边是我校引以为豪的图书馆大楼,远看像一朵朝天开放的菊花。
葛志文说,“对。”
于志阳在这样一个极丑的地方遇见夏娃,她穿着一件廉价到不能再廉价的灰色长裙,这时候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
所以他说,“浩哥,你觉得她是怎么走到湖堤上去的?”
王浩有自己的心事,他说,“谁知道呢?”
在商场进门处的大厅,见到她的时候我对葛志文说,“老葛,我好像看见徐荷了。”他说,“谁?”
他妈的,这个故事里的名字太多了。
徐荷是个坏女人。要说明的是,葛志文的人物塑造很烂,在他的概念里,这个世界上只有好坏两种女性,还有一种捉摸不透,难以定义,他称之为夏娃。对这个故事而言,这已经够了。当然,还有一种像我,假小子。
王浩和坏女人徐荷的故事是这样的,徐荷耍了他。
于志阳问,“怎么耍的?”
“她说她是外语学院希伯来语系的,其实不是,我特意跑去问过了,他们说从来没有过一个叫徐荷的女生,学希伯来语的全他妈是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年半以来,我对她一无所知。”
于志阳说,“一无所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看着她在跳舞,穿着一件说不上有多诡异的衣服,像是马戏团里那种,紫色条纹的塑胶紧身衣,头顶着粉色假发,她们一排女孩全穿着那样的衣服,墙角站着一台音响和一个瘦小着西服的男人。
“流动剧团。”
“什么?”
葛志文说,“流动剧团。”
我们想等她,可是我们等不到的,因为这是个流动剧团,演完这一出还得赶往下一个商场。
人们停下脚步来看着她们,从四面八方来的人,穿越大门口的塑料帘子然后驻足。我们也看着她们,葛志文的手里始终捧着记录本,我们的打扮一看就是三个有正事的人,在寻找什么东西。
她在所有舞者里,站的是最中间的位置。只有她在微笑。当我们议论她时她一定也注意到了我们。葛志文断定她的名字里一定有一个“徐”或者一个“荷”,我信。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徐荷,徐荷一定是她,现在我们必须等她跳完这支舞,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王浩也在等待徐荷,或者于志阳在等待夏娃。她的眼睛里具备戏弄人的潜质。
葛志文想给她写一部戏,一个不太一样的风尘女子。赵曼说得了吧。
王浩不相信夏娃的存在,“你总是在做梦,老于,除非我们再去湖边一次,你让她明明白白站在我面前,我才信。我劝你现实一点。”
然后他们坐在湖边的水泥台阶上,两个人中间放着一瓶酒,夏娃当然没有出现。王浩在等着夜晚与徐荷在富林桥下的会面,那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桥,富林河是一条时常有人在里面钓虾的臭水沟。他和徐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夏天,现在他已经不能确认她是否叫徐荷了(我们还能确认,是的)。坏女人总是有意无意地主动靠近,说,“我以前在哪见过你。”地铁列车经过水畔的时候,阳光折过来美极了。他们拥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拥抱接吻然后做爱,她说她爱他,把沉重的词挂在嘴边就显得不那么沉重了。她侧躺在床上看手心里发光的网络小说,他不感兴趣。他瞥到她放在床头柜上的身份证想拿过来看,她不让,说照片太丑了。
王浩感到悲伤,他可以确定她的名字不叫徐荷,所以他感到悲伤。他无法确认自己认识的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有一回在北仑,他们约好在酒店会面,他跟前台报了徐荷这个名字,前台说查无此人,后来她就从电梯里出来了,说自己刚刚睡醒就接到了电话,“烦死了”。他就把前一回事忘了。
我们站在那里等她跳完这支舞,跳的时候发现她并不只是徐荷,如果可能的话,她甚至能胜任陈子夜这个角色,至少比赵曼的南方室友要好。讨论剧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埋藏着一个问题——在各种程度上,陈子夜应该是一个好女人还是一个坏女人?我的答案是都可以,最好的处理是,让她不那么像一个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那样于志阳之后的行动才显得合理,这年头,浪漫是专属于妖魔鬼怪的。
于志阳对王浩说,“你太过依赖真实,所以你疲惫不堪。”
他捡起镰刀开始割湖边的草,我们知道他是怎样到对岸去的,到陈子夜一定曾经站过的地方,每逢夏天到来地上的草便疯长。王浩说,“你真的打算把时间浪费在这一件事上吗?”草割了还会长出来,再割了再长,整个夏天都是这样。指腹大的小蛤蟆在树下跳来跳去,更深的草丛里有更大的蛤蟆,夜晚降临之前,王浩就要走了。
据葛志文说,于志阳的有关等大的哲学是这样的——在等待之前使自己相信这场等待没有结果。他做的不是等待,而是一种习惯。葛志文不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人,他也不会使自己笔下的人物具有骑士精神。浪漫离我们都太远。
他坐在水边听着蛙声,蚊子在他的四肢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吻痕,王浩的电瓶车有时从对面缓缓飞过,有时绕到这边来,车上的人带着啤酒和开瓶器问他有没有等到夏娃。“我帮你打听了一下,真的有这个姑娘,就在管理学院,大三三班。”“谢了。”“我是说,你真的想找她的话可以去管理学院,在这等着也是白等。”
“你可以走了。”
“走吧。”
有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眼镜就是一台摄像机,这样我能把看到的一切存成一部纪录片。为此赵曼说,咱们都是这样,害怕失去。认识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她把使用过的一切物件都留了下来,大学前三年里囤积着整整三大箱东西。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总和别的学生不太一样,我们又和别的编导专业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忙着学习的时候,我们在保持忧愁,他们忙着挣钱与恋爱的时候,我们还在保持忧愁。
赵曼拿着手机,只身冲过去赶上正在离场的流动剧团。我紧跟在后面,奔跑的时候眼前的世界在晃,镜头在晃,有节奏的脚步一如鼓点。葛志文跟在我们后面,他总是跑得最慢的那一个。
紫色的女孩们排成一列穿过人群。那个穿西服的矮个男人推着音箱。赵曼直接走到徐荷的边上,如果她真的叫徐荷,跟着她们的节奏前进,我没听见她们都说了些什么,只知道徐荷在倾听时会保持微笑,眼睛看着前方的路,她身后那个戴紫色假发的女人拉开了赵曼,对我们说她们正在工作,闲人莫扰。
赵曼停下了,我也停下了,然后葛志文也停下了。流动剧团的队伍远去,我们停下的地方大厅中央有一架白色的钢琴,我走过去把手指放在C1 键上。葛志文问,“她还会回来吗?”
二
我不是非常明白剧本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对它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样的。回去的路上,葛志文还在反复念叨那句话,“她还会回来吗?”我不知道流动剧团的日程会是什么样的,或许再过几个月她们又会回到这座商场,或许不会。
短片最长的一个镜头是,于志阳用镰刀割着草,湖堤上的草。赵曼还没想好用什么方法表现这一情节:草割了又长,割了又长。事实上,现在这个季节湖边本来就没多少草。这个镜头预估得持续两分钟。
冬天傍晚的松阳冷得不像一座南方城市,直到我们坐上缓慢行驶的橙黄色电车,唯一一样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身处松阳的事物,邻座有几个男大学生说,这车比他老奶奶的骨灰盒跑得还慢。成群结队的电瓶车从玻璃外划过把我们甩在身后,前方是臭水沟般的富林河,河边没有灯光,有一小块空地是属于东方政法大学的地界,据说那里曾经有一间小木屋,吸引如饥似渴的青年男女前往幽会。我们没能见证它的辉煌,但见证过它的覆灭。大二下半学期,一架明黄色的铲车挥舞抓斗将它轻而易举地夷为平地,尘土掩盖的碎木板下覆盖着不计其数使用过的安全套,后来我们的电影放映社团在那片废墟之上支起了一面小小幕布、一台放映机和几张凳子。是的,这个地下小社团是赵曼、葛志文和我一手操持起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那放库布里克,后来是黑泽明,再后来是伯格曼,再后来社团联派了两个代表来把空地上寥寥十几个人遣散了,散的时候投影里还放着寺山修寺的片子。
我们可以想象于志阳在湖边度过的那些傍晚,就像我们在河边守着几张凳子等待有人来参加社团活动一样,也并不一样,湖的对岸灯火通明,此处却蝉虫嘶叫,黑得密不透风。蚊蚋声声作响。那时,葛志文用旧书报点燃了一团火,却未能下定决心把投影幕布扔进去,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短暂燃烧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
回琴房之前,我们在快递站取了两个包裹,分别是短柄镰刀和陶笛,拍摄最重要的两样道具,往琴房走的路上我试着吹了几个音符,Re,Mi,So,不知道该失落还是该高兴。
王瀚就是在随后出现的,早在我们回到琴房以前,他就已经在那里了。屋内正传出天鹅的叫声和钢琴音符,我们推开琴房的门,赵曼问他是谁,他问我们为什么琴房会有一只天鹅。
我看着他愣了好一会,说,“同学,有兴趣演电影吗?”
他说,悉听尊便。
秋天就要过去,杂草就要停止生长。
寒潮到来的前一天,赵曼带着我们喝了很多酒,我没有喝,因为适逢月事,葛志文给我煮了姜茶,总在这种时候我才想起自己是个女孩。
演员的人选就是在那天敲定的,我演坏女孩徐荷,得化一个很浓的妆,穿露肩的衣服,赵曼她室友演陈子夜,葛志文自己演王浩,王瀚同意演于志阳。后来我问过赵曼,“你给了王瀚多少钱,他愿意帮这个忙?”她说,“他没要钱。”
“真的?”
“真的。
“一分钱都没要。”
我有小半年没化过妆了。
拍摄用到的设备很少,一台摄影机,一个三脚架,一个云台,一截手持灯管,没了。第一场拍的是富林桥,凌晨五点半,拿日出模拟日落,镜头对着栏杆与河水的交界处,一半是水,一半是路灯的光。王浩骑车入画,镜头在他身后跟了五秒,那辆年事已高的电瓶车歇在了上坡处,镜头也随之停下,又摇到河岸的方向,徐荷站在那块空地上将一块白布投入火中。
下一个镜头对准我的脚边,那块燃烧着飘动的白布,我,徐荷一动不动,感受着火焰的温度在不远不近处,燃烧并不完美,烧到一半就灭了。结束的时候我问葛志文,那块白布的含义是什么?他说,没有含义。
三十秒,王浩推着电瓶车走过桥面,镜头定在那里,人和车消失在路面以下。
陈子夜本该在下午来,可是没有,她忽然说要去找男朋友,就没有来,所有人在湖边待了半个钟头,葛志文去食堂给我们打了饭。我们暂时回到了琴房,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王瀚给那只天鹅喂食,我说,“吉娜疯起来的时候,见人就啄,能让它这么安静的,你还是头一个。”
事情其实再简单不过,它在视觉学院门前的大水坑里呆久了,忘了自己是一只天鹅。“它的名字叫吉娜?”“叫吉娜。”
“小时候在乡下,养过一只鹅,看着它缓慢长大,后来过年的时候,家里人把它炖了。你知道吗,杀鹅之前得给它灌烧酒,它的毛就会竖起来?”
赵曼对我说,“临时决定,你来演夏娃。”
“夏娃也可以是短发吗?”
王瀚和葛志文走出去,留下赵曼、我和吉娜在屋里,赵曼给我改妆,换上那条二十块买来的灰色裙子,我已忘了自己有多少年没穿过裙子,吉娜伸长脖子看着我,镜子里的人忽然让我陌生。
拍摄从湖的浅处开始,堤岸、浅滩,最后是没至腰身的水,我想象一只天鹅浮在水面上是什么感觉,也许就是这样,水面托起羽毛,唯一的区别是,我的脚下是拥有难以言喻的触感的泥。他们特意准备了防水的靴子,拿塑料胶布把鞋口一圈又一圈地封死,固定在我的小腿上,事实上无济于事。
水总会渗进来。
赵曼说,裙子只有这么一条,不能沾上泥了。
这句话她是喊出来的,因为这时她离我很远,剧组的其他人员都离我很远,他们站在另一头的岸上,摄影机也架在那里,我的周围空无一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距离下,镜头不会暴露我其实冷得瑟瑟发抖。
第一个镜头,我拿着石块一样的陶笛在嘴边吹出三个音符,Re,Mi,So。
第二个镜头,我缓慢地朝湖的中心挪动,让水位沿着我的皮肤上升,直到赵曼宣布这一镜结束,我还在往前走,因为事实上我一句话也听不清。他们围着相机狭小的屏幕回看方才的镜头的时候,我反应过来往岸边走,王瀚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根竹子伸到我面前,我冲他笑一笑,他把我拉上岸,然后我才注意到他的衣服也都湿透了。
透过身后这片林子,可以看见外边车来车往的马路,黄昏逼近。赵曼似乎有些喜悦过头,反复说着太好了,太好了。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演了个啥,王瀚的意思是,他也不知道。我站在那里,晃动靴子听着里面咣咣咣的水声,浅灰色长裙已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泥,我们坐下。他把手放在我的小腿上,帮我摘下被水泡烂了的塑料胶布,脱下靴子,倒出里面的湖水。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到这的?”
他说,“什么?”
我说,“没什么。”
我说,“赵曼本来想让我来演男生,没想到碰到了你,你出现以前,我们在商场等一个戴粉色假发的女孩,她跳舞很好看,她就是以跳舞为生的。”
他说,“她叫什么名字?”
我说,“徐荷。”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徐一一。”
他说,“徐一一,我会记住这个名字。”
我快冷死了,我说,“我不打算在我快冷死的时候发生爱情。”
三
吉娜不见了。
葛志文带回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已在准备拍下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必须用到吉娜,陈子夜已经准备好变成一只天鹅了。
那时我还在想象粉色头发的徐荷当下在做着什么,在这座城市某条街道某辆大巴上,她在等待抵达下一个演出场地,重复先前的动作先前的微笑,我很想问问她,是否喜欢自己这份工作。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一行人围着教学楼和静月湖盲目地寻找一只走失的天鹅,黑色的天鹅在逐渐转黑的天空下变得愈发难以寻找。第二十一分钟时所有人再次会面,无言相对。
赵曼决定说,“不用天鹅了。”
葛志文点了一支烟,把剧本改了,删去了原定的那个镜头,又加了两个。
第一个镜头讲述于志阳是如何落到水里的:他原想往浮萍上走。
赵曼对王瀚说,“你得真的走,往浮萍上走,然后真的掉进水里。”打板员会在边上拿手机录下落水的声音。镜头将在第一脚踩到浮萍上的瞬间转为黑场,只留下那段落水的声音,哗啦啦啦。
紧接着下一个画面是,于志阳站在水里,我从湖心径直朝他的方向走过去,镜头里是背朝夕阳的侧影,两个人擦肩而过。
赵曼站在岸上喊,“别看对方!别看对方!别看对方!”
后来葛志文告诉我,画面里看着,我的表情就像是要哭一样。我说真的吗?
于志阳等到了夏娃了,这事他从没预想过,夏天过去了,杂草不再生长,不再需要他挥舞镰刀证明自己还在等待,夏娃在那一刻之后便不再美丽——镜头风格转向写实,定格在岸边,我的面部被放大,置于画面左侧,右侧是模模糊糊的水,水里是模模糊糊的于志阳,我转过身去对着他,最后一句台词是:“快上岸吧。”
与此同时,在湖的另一边,王浩正把自己的电瓶车推入湖中,苇草丛遮住本应激起的水花,落水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大。我忽然感到一股真实的寒冷,于是裹紧手臂,我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尾
吉娜没有丢,吉娜回到了视觉学院门前的大水坑里,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独自找到回去的路的。毕设拍完了,赵曼请我们吃了一顿散伙饭,只有她、葛志文、王瀚和我,在大学城唯一也是最丑的那座商场的二楼,站在二楼的玻璃扶手边可以看到一楼中庭的样子。
葛志文很喜欢我对最后那个镜头的提议,就是王浩把电瓶车扔进了苇草丛里,一点水花都没有溅起来,但是有“咚”的一声猛响,我冲他笑一笑,说失陪,独自起身往卫生间走。走到玻璃扶手边的时候,我看见一楼某个角落的椅子上坐着一行穿着脏兮兮芭蕾舞裙的女人,好像在歇息或是在等待,中间那一个我还能认出她,现在她的头发是亮黑色的,像夜晚没有星星的湖水一样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