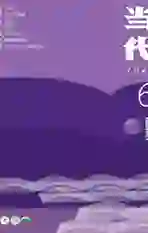焰火
2023-11-28杨小凡
空中是没有风的,青白的海浪还是一波推着一波,向沙滩上涌。
也许是天气太冷,平日金黄的沙滩泛上一层灰白,是从海面上飘来的雾气吗,似乎又不是。这淡淡的白色是从哪里来的呢?沙滩上的人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口罩,或两三个或五六个站在一块儿,指指点点的,在说着什么。他们是在讨论沙滩为什么变白吗?恐怕,他们还是没弄明白,不然就不会一直这么热烈地讨论着。
望着窗外远处的大海、近处的沙滩,以及沙滩上的人们,我在想:她应该快来了吧?
昨天,在海边的教堂门前偶遇她时,我俩都很惊奇。毕竟有四年多没见面了,本来应该多聊一会儿的,可刚刚说几句话,我的手机就响了。彭先生急急地催我去他家吃饭,说另外两个朋友都已经喝完了两杯茶。
她见我接电话,尽管脸上罩着微笑,眼神里还是透出些许的失望。
我挂了手机。她说:“一家人来过年的吗?”
“不是。就我一个人!”我向海的远处望一眼,那里有一艘孤零零的轮船。
“啊!”她很吃惊。
“你怎么也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家人呢?”我有些不解地问。
她也把目光投向远处那艘孤零零的轮船,平静地说:“我也是一个人。”
“你也一个人?”我感到很意外。
停了有几秒钟,她开口说:“这几天,”迟疑了一下,才又接着说,“要是方便的话,我想到你住的地方坐一会儿。”
“可以啊。明天,明天下午吧!”她提出这个想法,我想也没有理由拒绝,况且,这几天我一个人也挺孤独的,便立即答应下来。
她显然十分高兴,又不想让我看出来,就说了两个字:“好啊!”
“一言为定!”
我走出十几步远,突然想起并没有告诉她我的住处,赶紧转过身,大声地说:“哎,我在隐庐一号楼,1330房间!”
她向我扬了扬手,是告诉我她听到了,还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没有多想。
此刻,我在想,她这个点还没有来,是没记清我住的地方吗?也许,她就要来了。那现在该不该先把茶泡上呢?
我从窗前回到沙发上坐下,又点上一支烟。最终决定,还是等她来后再泡吧。当着客人的面泡茶,不会让人产生喝剩茶的怀疑,也是对她的尊重。尊重朋友是一个人起码的修养。何况,我俩也说不上是真正的朋友,这之前才见过两次面。
现在想起来,昨天的奇遇,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决定到这里来过春节,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廬州的春节虽然热闹,那是别人家的,我依然还是一个人孤单单地过。还不如到这里来,只“阿兰若”这三个字,就让我的心安静下来。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就被这特殊的气质吸引住。这个由梵语aranya演变命名的海边社区,濒秦皇岛海岸营建,处处透着简朴的品质,洋溢着丰盛的节制,形成一个独立的逃离城市的静谧空间。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人间寂静处,可以找回本我的地方。
昨天是正月初四,我一个人在公寓里窝了五天,确实很寂寞。傍晚时分,我裹上羽绒大衣,走出公寓。公寓外面就是空空的海滩,平日飞动的海鸥也不见了踪影。我决定,到远处的图书馆和教堂那边走一走。
图书馆独自矗立在空旷无际的海滩上,面朝大海,低调而高雅。外观是简约的灰色,在大海和沙滩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寂静,像一座遗世独立的雕像,凝视着大海的波涛和时光的斗转星移。图书馆分为两层,全是阶梯式座位,临海的一面是一块巨大的透明玻璃墙,阳光、沙滩、大海,扑面而来。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正是初夏,我在一层的靠椅上坐下,要了杯咖啡,放下手中的《庄子》,看着大海上迎面涌起的浪花游弋翻腾,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图书馆没有开放,我在入口处站了一会儿,便向左边的阿兰若教堂走去。教堂的两座建筑一灰一白,像两个锐角三角形,没有任何多余装饰,极简地矗立着。蓝的天,蓝的海,白的云,白的台阶,淳静悠远的钟声,让我生出无限的遐想。
海面上吹来的风凛冽冰冷,我站在这里却久久不想离去。我在想,在这里的每一句誓言和承诺,哪怕是虚浮的,也会变得神圣。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问话,“前面可是楚老师?楚筱白老师!”
这声音似乎熟悉,我一时竟想不起是谁。转过身子,几米处站着一个穿黑羽绒服的女人。这女人有一米六五的样子,脖子上一条白色的纱巾飘动着,让她显得高挑而灵动。她是谁呢?她肯定是认识我的,而我确实叫不上她的名字了。
“请问,你……你是……”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
“哦,记不起来了吗?我们是在之意书社认识的!”她微笑着提醒道。
这时,想起五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和出版社的编辑在之意书社做新书《左岸》的分享会。分享会最后是互动环节。她并没有提问,但她那专注的神情,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互动结束后,不少人挤着要我签名。我签了不少书,手都有些累了,就在要起身离开时,她从人群外走过来,把书递给我,“请楚老师也给我签个名吧!我叫童雪,童年的童,小雪的雪。”那是我当天签的最后一本书,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她接过书,感激地说:“楚老师,我读完后可以向您请教吗?”我顺口说了句:“当然可以。欢迎赐教!”
想到这里,我赶紧抱歉地说:“噢,你是童雪!真巧。”
见我叫出了她的名字,她显然很高兴。
现在,我又想起来了,第二年的秋天,我们在“锅庐”喝过茶的。
那个秋天,庐州老城大街上银杏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起来,煞是迷人。
一天早上,我接到她的短信,她想请我到“锅庐”喝茶,请教几个问题。其实,那时我对她并没有太深的印象,甚至都想不起她长什么样子。她说已认真读完了我的《左岸》,正好我那天下午也没有提前约好的事,就答应下来。
她给我发的定位,距离并不远,就在老城区的宣城路旁。这样的老城区里,应该是陈旧和喧嚣的,在这里喝茶,能有清净吗?我是有些怀疑的,不过,答应了下来,就不能不赴约。我叫了出租车,半个小时就到了。
临街的黑漆大铁门紧关着,我确认一下门旁上白色的标记“锅庐SPACE”,按了两下门铃,铁门就从里面打开,迎面站着的是一个帅气的服务生。
这是一座独院,院子里有一个高高的红砖烟囱,烟囱下一片镜水,里面有十几条青色的鱼,悠然地游动着。水面直抵西面红色的两层建筑,临水的墙体是阔大的透明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楼大厅,以及大厅里高大的棕色木书柜、吧台,还有吧台后站着的小姑娘。我收住目光,看着脚下木石相间的小径,突然想起来这个地方我是知道的。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破烂的栅栏里面,有几堆垃圾和废物,野草和杂乱的小灌木几乎掩盖了院子。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老的建筑物的时光肌理,与洁净的玻璃、水面、花木和谐一体,俨然是一处闹中取静的怀旧处。
我在服务生的引导下,穿过庭院路,刚到大厅门前,她正好从黑色的楼梯拐弯处向下走。她在二楼,应该是看到了我进来,就下来迎接的。
我随她到了二楼。她刚才就坐在临窗的桌子前。庭院的一切,都在她的眼底下。
桌子上是一套白瓷茶具,壶、公道杯、品茗杯放在茶盘上,小茶罐放在茶盘左侧,烧水壶在茶盘右侧。
她穿着青色白花的连衣裙,一袭清爽。化了淡妆,并不浓,却恰到好处。看得出,她出门时是精心打扮过的。她一边按了水壶的按钮,一边说:“楚老师,今天冒昧地约你,真有点不好意思。”
“挺好的。这个季节。”我说罢,就习惯性地去拿手包。
“这里可以抽烟的。”她竟看出来我想找烟,就微笑着说。
我自嘲地说:“烟真不好戒!”
“作家一般都抽烟的吧?”她看了一眼茶具,“今天,我给你泡茶!”
谈话自然地从我那本《左岸》展开来。她先说了读这本书的感受,当然少不了恭维和赞扬。这是读者面对作家时肯定要说的话,既是对写作尊重,也是拉近两人感情的通道。面对作家夸他的书,就像面对母亲夸她的孩子一样,听者和说者都是愉快的事儿。
水开了。她从包里掏出一个香烟盒大小的铜色盒子,打开,里面是两小包茶叶。“这是‘群芳最’。”
“啊,这是祁门红茶的‘皇后’,我喝过的。”我没想到,她知道我爱喝祁门红。
她一边打开茶包,一边说:“楚老师,这茶合您的口味吧?”
“你怎么知道的?”
她笑一笑,“作家是没有秘密的。你的爱好都写在书里了!”
“你真是聪明啊!”我不由得赞叹道。
她有些不好意思,“我聽说过,每一个作家,最终写的都是他自己。”
这时,我对她多了些兴趣。这是一个知性的女人,应该没少读书的。
看来,她对茶道是有过研究的,烫杯、投茶、洗茶,之后,才将开水加入壶中,约莫过了一分钟,再洗杯,将水倒掉,右手拿壶将茶水倒入公道杯中,再从公道杯中斟入白瓷茶杯,斟了七分满。这时,鲜甜醇厚的嫩香,便从红艳明亮的茶汤中飘散开来。
我接过她递来的茶杯,放在鼻下深吸一口气,鲜醇的嫩甜味进入鼻腔,像玫瑰花,像苹果,又像蜜糖。香味在鼻腔中走深后,我才下移杯子,啜了一口,又抿了一口,再饮了一口,茶汤入喉时,顺滑润畅,一股扑鼻而来的清新香沁入心肺。“真是好茶!”
我对茶的满意,让她很高兴,“好茶是找人的,要给楚老师这样的人品,才不枉它的一生一世!”
品了两杯,我突然想到美人如茶,她果真是很雅致的女人。可我并不了解她。这是我们第二次相见,确切地说是第一次真正坐在一起。
她又给我续了一杯茶,“我想给你说说自己,这些天,我心里很难受!”
“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淡然表情后面的忧郁,“如果你信任的话,我愿意倾听!”
她叹口气,端起茶杯,“我知道是可以给您说的。”
眼前的这个女人,一定是有故事的。
我也端起茶杯,掩饰着自己的表情,鼓励地说:“但愿,我能给你一些建议。”
于是,她开始了静静地讲述。
她说自己在庐州图书馆工作,自从离婚后就请了病假,快有两个月没去上班了。在庐州图书馆工作之前,她在皖江县图书馆干了十年,在做图书管理员之前在皖江县乡下的一个中学做了快十年的语文老师。按说,她从乡下中学调到县城时,有不少岗位是可以选择的。那时,她丈夫已当了副县长,副县长的夫人在县城基本是可以随便选择工作的,她选择了图书馆。并不是这里特别清闲,主要是她喜欢读书,喜欢与书在一起的感觉。她说:“女人都是感性的,许多时候是靠感觉来决定一切。”
这时,我才认真地注意起她来。她的面相与一般女人不太相同,是典型的长方形脸,丰腴的腮上两个浅浅的酒窝,这让我立即把她与众多的女人区别开来。那次给她签书时,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我正在想,她脸上怎么会有异域的影子呢,莫不是基因里有混血的成分。她显然是注意到了我的走神,就叹了口气,我立即朝她微笑了一下。
她又接着说:“没想到会过成今天这个样子。”
她的丈夫,不,应该是前夫,应该也没想到自己能走到市长这一步。他是她大学同学,一起分到她爸爸当副乡长的农村中学教书,一个农村中学老师二十年后竟当了市长,当时她确实没想到。
她停了几秒钟,“他确实精明,也能干,是那种抓住一根稻草就能上岸的人。我爸只是把他推到了乡团委书记的位子上,他就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了上来。”她苦笑了一下,“他走得太快了,忘了身后的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过去!”
也许是愤恨,也许是鄙视,她显得很激动,声音颤抖着,硬是把下面想说的话咽了回去。这时,我看到她捧着茶杯的手颤动得厉害。她的手指很细,很白,由于握茶杯越来越用力,手指上深蓝色的细血管,像要爆出来一样。
她似乎注意到了自己情绪的异常,赶紧拿起茶杯,试图掩饰。过了会儿,继续说:“我不想提他的名字,甚至不想回忆我们的过往。我心里实在憋屈得难受,胸口有快要爆炸的感觉。说是离婚的人一别两宽,可那一个个历历在目的日子,却无法消失。”
看得出她心里很难受,可我又不好插话。婚姻破裂的处境我是有过的。我的妻子,不,应该是前妻,从加拿大寄来离婚协议时,我也特别绝望。我十分理解,这个时候,所有的劝慰和安抚都是多余的。正所谓不经其苦,莫劝人善。我只好随她自己的意,想说就说,想说多少就说多少,不想说就算了。
她给我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茶,还是接着说了下去。
她说她对这段婚姻是不舍的。为了儿子,也为他们不容易的过去,她最终还是同意离了。“儿子就要大学毕业了,当知道那个女人要挟他,要他离婚,知道我与他一直在争吵,竟与谈了三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儿子说,他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这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他自己。我为儿子担心得要命,只有强装轻松地劝儿子,同意与他协议离婚。我当时只想陪儿子生活一段,让他从绝望中走出来。”
她稍稍平静了一下,也许,觉得跟我说这些有点唐突,不好意思地说:“我把自己心中的不快说给你了,影响你的情绪了吧。”
我立即说:“你多想了,这是对我的信任。如果能让你轻松一些,我就觉得这个下午很有意义。”我抬眼向落地窗外望一眼,又说:“你看,窗外的烟囱和它下面的静水,虽然突兀却很和谐,万事万物只要融在一处、互相依偎,就是一种大美。”
她也抬眼望向窗外。围墙内的小院静谧,外面的街道依然人车喧嚣。她舒了口气,把目光收回到茶桌上。
“一道围墙隔成两个世界,他如愿地当上了市长,换了新妇,真是春风得意啊。我和儿子却被抛弃了。”
“那你為什么要放弃呢?”我有些不解。
她停顿几秒钟,又把脸转向窗外,声音很低地说:“为了他这半生的不容易。当然,更是为了儿子!”说完这句话,又抬眼望向窗外。
我不能完全正视她的眼睛,从侧面观察到她两眼睁得很大,眼珠呆呆地静止着。也许是视线的原因,我见她眼眶很幽深,因了幽深就显得特别空洞,仿佛是两口蒙着一层薄雾的深井,这井里究竟深藏了什么,让人有一种永远猜不透的感觉。
她在想什么呢?是对婚姻和人生的绝望吗,我不知道。
这时,我想起了两年前自己经历的那段日子,心跳的速度突然加快起来。于是,赶紧掏出一支烟。我自己也需要平静一下。
我点着烟,刚吸了几口,她突然惊奇地说:“啊,水上焰火!”
随着她的声音,我也把头扭向窗外。这时,十几朵五颜六色的烟花,从水面上围着高高的烟囱,盘旋着、缠绕着,升起,绽放,如花雨般地跌落,然后,再盘旋着、缠绕着,升起,绽放,戛然跌落……
外面,天已暗下来了。光影焰火开始绽放,这个小院一下子欢欣生动起来。
这时,她幽幽地说:“烟花易冷人易散。日子要像这光影焰火就好了!”
我吸了一口烟,正想着如何接她的话,她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有要起身的意思。
深秋时节,五点半天就快黑了,正到吃饭的时间。她为什么突然有要走的意思呢?她是本来就没打算与我共进晚餐,还是没有了谈话的兴致,我没有猜透。
于是,我也看了一下手表,主动说:“你还有事吧?我晚上还有个饭局,该去了。”
“哦,耽误你的时间了吧。下次,下次,我再请你共用晚餐!”她有些不好意思,站起身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个子高挑,比年轻女孩多了成熟的丰腴,却没有中年女人的臃肿松散,让人怀疑,不可能是一个大四男孩的母亲。她确实亲口说自己快五十了。看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以前生活的优质和对自己形体的严苛。
离开“锅庐”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为什么要跟我聊这些呢?
其实,此前我们只见过一次面,根本说不上是熟人。她主动把自己生活中的暗疾告诉我,完全是对我的信任吗?这显然不太成立。是要找一个倾诉对象吗?也解释不通。难道是心里压抑太重,一时兴起,就是单纯找一个陌生人发泄一下?似乎也不太可能。那天,她就像个谜一样存在了我的脑海里。
时间波涛汹涌,生活斑驳陆离。
过了不久,我就把她和那次约会忘掉了。毕竟,那时以及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生活也一地鸡毛似的杂乱飘飞。
如果不是昨天的偶遇,我真的是把她忘记了。
我再次走到窗前。天已经暗下来了,海滩上星星点点的那些人影,模糊起来,似乎都呆立在那里,并不见活动。我想,外面一定很冷了,海水与沙滩的接合部应该是结了冰的,随着海水的波动,正发着嚓嚓的声响。此时的阿兰若,多少有些北极冰川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叩门声。
她为什么没有按门铃呢?我一边想,一边赶紧向门前走去。
门打开了。我首先看到的是她怀里抱着的一只纯白色小比熊。啊,她怎么抱着一只小狗来访呢?昨天我并没有看见她带小狗。这是一只很漂亮的小比熊,两个黑眼珠忽闪闪地看着我,像婴儿一样,充满好奇、充满亲近,两只前腿向上抬着,要从她的怀里挣脱,似乎想让我去抱它。多可爱的小狗啊!我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涌动,伸手想去把它接过来。
这时,她开口了:“带它来,你不介意吧?”
“很好啊,这毛孩子多可爱!”我又向前伸了伸手,想把它接过来。
她并没有把狗给我,而是抱得更紧了。她肯定觉得一进门就把狗给我,有点不太合适。其实,她并不了解,我家里也养着一只猫呢。
如果没有那只猫,我许多时候的悲伤情绪,是无法平复的。那只叫佛手的猫,呆傻而可爱,我看书或写作的时候,它赖在书房里不走,就在书柜的顶部趴着,有时在上面睡得很香,有种物我两忘荣辱不惊的样子。有几次,它在睡梦中竟从上面掉下来,见我笑它,就懵懂地看了我两眼,然后,不以为意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书房。
离开家快半个月了,佛手一定在寄养的宠物之家急坏了。我为什么没把它带在身边呢?我正这样想着,她开口说:“请原谅,我真的不想离开它!”
“很好啊!我也养着一只可爱的猫。”我说着,又伸出双手去接她怀里的比熊。小比熊显然对我十分信任和喜欢,身子向上一纵,就扑到了我的手上。
她换了拖鞋,开始摘掉口罩。就在口罩从面部摘掉的一瞬间,我看到她那长方形的脸显得更窄了,两边颧骨棱角分明,两只眼也显得比四年前大了不少,长睫毛下面的眼眶更加幽深。她开始脱羽绒大衣,前面的拉链拉开时,我注意到她的身材没有以前丰腴了。
“你瘦了!”我不由自主地竟说了出来。
她定睛看了我两三秒钟,苦笑着说:“这些年,我脱了几层壳。差点把命都丢了。”
我一时不知再接什么话好。这时,小比熊从我手上挣脱下来,扑向了她。我正好摆脱了尴尬,就说:“你先坐。我来泡茶。”
她坐到沙发上。小比熊也想上沙发,从地板向上蹦了一下又蹦了一下,第三次才蹦上去。它似乎为自己的成功很自豪,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然后,才贴进她的怀里。
“这毛孩子太黏人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过后,又沉默了。
客厅里安静下来,连小比熊的喘息声都能听到。
为了打破这寂静氛围,我便想从手中的茶说起。“今天,我也准备了祁门红。”我一边烧水,一边说。
她感激地笑了,“楚老师太用心了!这茶暖胃。”她停了一下,又接着问:“您去过祁门吧?”
“去过。那真是个好地方。”我便想起对祁门的印象来。
祁门依山临水,凤凰山、眉山、祁山、青山环绕四周。城东的阊江之上,并立两座古桥,上桥叫平政桥,下桥名仁济桥,文峰塔立于城南凤凰山上,山光水色、塔桥倒影,尽收在小城怀抱。矮山下河泥沉积而成的平地、小洲,因石质风化,土色各异,或黄,或红黄,或黑沙,或白沙,或黄沙,因山就势遍布茶树。清明前后,层层叠翠,绿海如涛,天地间清香弥漫。
春茶采摘时节来到这里,真是心脾通透,茶香沉醉。
水开了。我打开茶叶盒,用茶匙取出茶叶。今天,我准备的“祁门特茗”,虽没有“群芳最”等级高,但也细嫩挺秀、紧细匀直、乌黑油润,根根如金毫笔直。
洗茶过后,客厅里便飘荡起鲜醇的嫩香,仿佛是春天的芬芳扑面而来。
她端起一杯茶,闻了闻香,然后说:“这些年,你还好吗?”
我本来是要先问她的,她却先问起我来。我该怎么回答呢?想了想,故作轻松地说:“一切照旧。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啊,怎么会一个人呢?”她有些吃惊。
“我也离婚了。”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她显然更吃惊,“什么时候离的?”
我笑了一下,望着她惊奇的眼睛,淡然地说:“其实,四年前那次见面时,已经离了。”
她又端起茶杯,细瘦的手指在微微颤动,茶杯也开始抖动起来。又了喝口茶,才接着说:“为什么?”
我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我想用烟雾遮掩一下自己的表情。
其实,我自己到现在都弄不清楚。女儿去加拿大读书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妻子有什么变化。后来,女儿在她的谋划下拿到了绿卡,我也觉得挺好的,想将来也到那里住一段时间。四年前,她请了假,说是去女儿那里看看,谁知竟一去不再回来。又过了半年,竟把离婚协议寄了过来。她说,她不准备回来了,已经取得了绿卡。
我确实感到很突然。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她早有预谋的。结婚后这二十多年,家里的事全是她管。随着她在银行里的职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忙,我们的交流就越来越少,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甚至渐渐地不知她一直在想什么。她为什么要离开我?她从哪里弄到的那么多钱?为什么她和女儿都一直瞒着我?我是真不明白。
一支烟抽了三分之一,我才开口说:“你不觉得,在婚姻里是没有‘为什么’的嗎?”
她没有回答我,把小比熊抱得更紧了,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我又给她续了一杯茶,看着她怀里的小比熊,问:“它叫什么名字?”
她的思绪被我打断,机械地说:“小熊!”
小比熊听到“小熊”这两个字,以为在叫它,就仰起头,两眼盯着她望。
她与小熊四目对望着,身体突然抖动起来。这抖动先从胸部开始,一波一波向整个身体蔓延开来,以致沙发也随着开始颤动。
“你怎么了?”
她只任身体颤动,像被冰冷的寒风吹着一样。
我端起茶杯递给她,想让她喝一杯热水。
她接过茶杯,又放到茶几上。长舒了一口气,把小熊又向怀里搂了一下,才开口说:“我现在只剩这个毛孩子了!”
“儿子呢?”
“儿子两年前离家出走了。他把小熊留给了我。”
“啊!一直没有消息吗?”
“没有。”
“他没说到哪里去吗?”
“没有。也许,也许……”她抽泣起来,瘦削如刀的肩膀耸动着。
我见她太痛苦了,想走过去,用手抚住她的肩,又觉得不太合适。这个时刻应该让她心里的憋屈发泄出来。
小熊见她一直在抽泣,伸出两个前爪,不停地扒她的前胸。好像孩子看见母亲难受,自己心里也很不安,它不愿看到她这样抽泣。
我为了安慰她,也是为了平抑自己的情绪,就说:“别过样,人生就这个样子,许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
她显然知道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就开始尽力调整。经过努力后,最后慢慢平静起来。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长吐一口气:“对不起,请原谅!”
“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又点上了一支烟。
她又用手抚了抚小熊的头,然后问我:“你听说他的事了吗?”
“谁啊?”我说过这句话,突然又感觉后悔,这个他,肯定是她的前夫啊。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对社会上的八卦是不太关心的。
她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觉得我肯定知道,“他已经进去了!”
我这时才明白,于是就问:“他进去了?”
她冷笑一下,没有说话。我有点蒙。
她看到我表情的变化,端起一杯茶,大口喝下去,“儿子出走了,他毁掉了儿子对婚姻和生活的信心!”
“上个月,我好像在朋友圈里看到市长被调查的消息,我并没在意。”我说。
她冷笑一声,“你不知道是他吧?”
“不知道。”我向来对官场上的事不太关注。
“他进去了!”她说过以后,好像比原来轻松了一些,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唉,也是报应!”
我在想,也许是被谁举报了。不会是她做的吧?
毕竟,举报自己的丈夫,一定是鱼死网破后才能做到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凭着这些年的社会经验,我知道,如果不是真有证据在手,想扳倒一个市长也是不容易的。
“应该是被举报了。”我猜测地说。
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又冷笑一声,“上天不会放过谁的!”
“啊!”我真的有些不理解。
这时,我突然想到我的前妻。她这么绝情地离我而去,是早有预谋的。我只是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她挪用公款做投资,赚到挺多的钱。好像她离开时补上了公款的亏空,但是,银行一直在追查她。
刚离婚时,我也想过举报她。但是,又一想,她毕竟与女儿在一起。最终,我就没有了勇气。
这时,她突然说:“我儿子没了,一切都没了,走着、走着,走进了死胡同!”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显然是充满愤恨的。
“你现在怎么想?”我不解地问她。
她似乎从刚才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深情地说:“我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是为了小熊,我真的想走了!”
她说到小熊,小熊显然是听懂了,抬眼张望,两个墨黑的眼珠,扑闪闪地与她对视着,有惊恐,更是信任。
她一边抚着小熊的头,一边喃喃地说:“小狗是要命的生灵,你养了它,它就拿你当父母或朋友,即使为了生存甚至死都不会背叛,与人正好相反。”
突然,我看到窗外的高空中,炸开一朵巨大的烟花,紧接着一片金色的流星雨,四散开来。
“有人放焰火了!”我惊奇地站起来。
她也看到了正在向下散落的流星,站起身来。
我们走到落地窗前,剛才那朵烟花已经散尽,海滩又回归黑蓝的寂静。
突然,十几条金色鱼尾般的焰火,游弋着向上攀升,夜幕被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高。我压抑的心在这突然开阔的夜空中舒展多了。这时,一朵又一朵烟花相继绽放,红色的、橙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青色的、蓝色的、金色的火花,从高空中倾泻下来,瞬间把整个天空照亮。海滩、海滩上的人群、海面、海面远处那艘孤零零的轮船,尽收眼底。
海滩上的焰火再次升起,夜幕被五颜六色盛开的花朵,照得流光溢彩、热烈绚丽。
她、小熊和我,都被窗外的焰火惊艳了……
十几分钟后,焰火停了。海滩顿时沉寂下来,远处的天穹中,现出几颗明亮的星子。
她从窗前走开,黯然地说:“烟花绽放后,留下的就是碎屑与空虚,正如我的人生。”
我掐灭了烟,笑着安慰道:“曾经绚烂过,便不枉此生!”
这时,窗外的高空中,突然间又炸开一朵巨大的烟花。紧接着,十几条金色鱼尾般的焰火,游弋着向上攀升,夜幕再次被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高……
责任编辑 石一枫 徐晨亮
作者简介:杨小凡,现居安徽。出版有长篇小说《酒殇》《楼市》《天命》《窄门》。已在《当代》《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钟山》等刊发表小说四百多万字。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山花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