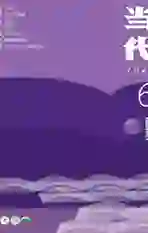亲爱的母亲
2023-11-28韩东
一
大姑妈葬在德贤公墓,那儿草木茂盛,空气阴凉,的确是个长眠的好地方。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块刻着“亲爱的母亲”的石碑,碑身的颜色发暗,文字边缘也已经圆润了。
全文如下:
亲爱的母亲杜家英之墓
儿 钟淮
女 钟河 敬立
我问妈妈,“谁是亲爱的母亲呀?”
“你大姑。”妈妈说。
“她不是大姑姑吗?”
“她是小淮、小河的母亲,”妈妈说,“就像我是你的母亲。”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母亲因病去世,在我的坚持下她老人家的墓碑上也刻上了“亲爱的母亲万晓岚”。就这么光秃秃的几个字,没有“之墓”,也没说明碑是谁立的。我终于也有了“亲爱的母亲”,我在想,虽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然是这个人的孩子。
这里的时空似乎有点紊乱,让我们稍稍梳理一下。大姑妈病逝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大姑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而母亲领着我去德贤公墓扫墓是“文革”期间,我大概六七岁的样子。我从没见过小淮、小河,只知道他们生活在安徽淮南,和大姑爹钟仁发住在一起。
每次去德贤公墓,母亲都会对我说一点有关大姑家的事。德贤公墓我大概去过三四次,母亲闲谈的内容串联起来就有了如下脉络:大姑、大姑爹是自由恋爱,两人都是国家干部,在治淮指挥部工作,因此才会将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钟淮”“钟河”的。在河工现场大姑突然生了怪病,一天下班后洗脚觉得脚疼,然后就病倒了,还没来得及诊断出病因大姑就去世了。之后钟仁发再婚,后面的老婆也生了孩子,但后妈对小淮、小河一直都很好。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妈妈。
“听你爷爷说的。”
“那爷爷是怎么知道的?”
“钟仁发和你爷爷一向都有联系,寄过小淮、小河的照片。”妈妈说,“你爷爷也会从天津寄小人书或者学习用品到淮南,有时候还会在信封里夹钱和粮票。”
这时我们已经走出了公墓大门,一阵风刮着几片落叶在路上跑,那些叶子显然是从墓园内的大树上落下来的。
二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扫墓活动便停止了。三年以后我爷爷去世,父亲只身前往天津奔丧。据说爷爷死得还算安详,只是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大姑的两个孩子。以前爷爷在世,大姑家的事自有他老人家做主,他这一去责任就落在我父亲身上。父亲又是个急性子,因此不顾当时的处境(我们全家下放是某种发配,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回苏北途中绕道去了淮南。
对钟仁发而言我父亲绝对是不速之客,搞突然袭击,父亲虽然不是故意的,却因此获悉了小淮、小河生存的真实状况。实际上父亲只见到了大姑的一个孩子,小淮作为知青此时已下乡到淮南郊县,没有见到。小河,怎么说呢,按我父亲后来的转述,由于长期受到后母虐待人已经完全变傻了。见到舅舅也就是我父亲时,小河嘻嘻而笑,穿着一件男人的衬衫,所有的扣子竟然都扣错了,是错位的。平时小河和钟仁发住一个房间,钟仁发的床头放了一根竹竿,专门用来每天叫小河起床。不用语言,二话不说,自己也不用起身,抓起那竹竿就捅另一张床上的小河,或者在她的被子上抽打。那根竹竿我父亲亲眼所见,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开裂的地方用胶布缠住也已发黑了,可见有年头了。挨打的细节想必是小河提供的,或者我父亲套话套出来的。总之父亲当即爆发,折断竹竿怒斥钟仁发夫妇后没等见着小淮就连夜将小河领回了苏北。于是我就见到了我的表姐。
小河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骤然从逼仄的城市来到农村广阔天地,高兴坏了。不用再去上学,也没人再用竹竿揍她,可她还是忘不了竹竿之类的东西,经常跨着我们家扫园子的竹扫帚或者一根大树枝,在家前屋后来往奔突,嘴里同时发出“驾!驾!”的吆喝声。分明是个傻子,难怪初中还没毕业呢。我父母也从没想过让小河就地转学,就这么放在家里养着,只要她不出桥口即可。小河乐得快活,每天在园子里追鸡撵狗,要不“骑马”,直到饭点。早中晚三顿,快到吃饭的时候小河这才大汗淋漓地停下,问做饭的外婆:“怎么还没有开饭啊?”
开始时大家都觉得有趣,后来就有点吃不消了。但想到小河遭遇的不幸,也就只好由着她。我母亲说:“这孩子怎么就不知道忧愁呢?”大概算是某种表态。
小河无忧无虑,精力无限,的确不像是后妈养大的。“这只是事情的表象。”父亲说,“她的智力大概只有八岁,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她的智力只有八岁?”
当年我已经十二岁了,也就是说小河的智力发育还不及我。我从来没叫过小河一声“姐姐”或者“表姐”,向来是直呼其名,“小河,小河,芦花鸡要下蛋了,不準你再欺负它!”
然而在生理上,小河的确已经是一个少女,个子比我高出一个头,胸部也开始隆起,尤其是她的皮肤,生来就白,到我们家后由于油水充足小河吃得白里透红。她一向衣衫不整,身体露出衣服的部分就像奶油做的,泛着一层令人恶心的光泽。她的白脚丫子上长了好几根黑毛,我向母亲报告说:“就像猪脚爪没挦干净一样!”
“胡说八道。”母亲说,“不准说你表姐坏话。”
“反正我再也不吃猪脚爪了。”
那年夏天,表哥也就是小淮终于出现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小淮”,就像没有叫过小河“表姐”一样,他从下乡的淮南郊县来到我们家下放的苏北。表哥的表现的确就是一个大哥哥。他比小河只大两岁,但非常沉静,甚至是不怒自威,当然这是针对小学生的我来说的。在大人面前表哥十分柔顺,按我父亲的说法就是“懂事”;父亲说表哥懂事自然暗示了我不懂事,或者小河不懂事,这些就不说了。
表哥帮我母亲洗被单,那可是一项需要体力和技巧的劳动,在一个大木盆里用搓衣板搓洗,之后走到小河边上站在“跳板”上过水。表哥将母亲搓好的被单或者床单,像撒渔网一样撒向碧清的河面,看着它们逐渐下沉,然后再捞上来像拧麻花一样拧去里面的河水。表哥有的是力气,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以前拧被单的时候母亲总要叫上父亲),母亲和我都看愣了。正值学校放暑假,我不用去上学,整天跟在表哥屁股后面,无论他去小锅屋里帮外婆择菜还是去自留地上挑粪协助父亲给玉米追肥,我都跟着。
外公喜欢绕着我们家的园子散步,有时候也走出园子来到村道上,甚至一直走到村外的河堤上。而且外公不喜欢说话,表哥也不喜欢说话,就这么沉默无语地跟着他。这一老一少之间并无尴尬。表哥跟着外公,而我跟着表哥,小黄(我们家养的狗)则跟着我,由高到低地(外公是我们家里最高的人)在灌溉渠的河堤上站定。如果是黄昏时分,晚霞满天的西天上就会映出这一队奇怪人马的剪影……
小河也很听哥哥也就是表哥的话,他总能让她安静,虽然管用的时间不长。但有表哥在到底好多了,小河不再那么疯疯癫癫难以禁止。也没见表哥责骂小河,只要他一出现,小河马上就蔫儿了,跨着扫把竟然会装出扫地的样子。这说明小河的智力也不是那么不堪的。现在小河的衣服扣子也都能扣齐了,不再错位,露出不该露出的白肉。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表哥的“懂事”,而是他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
白日将尽,我们在草房前面的泥地上泼上水,搬出竹床准备当成饭桌在上面吃晚饭。锅碗瓢勺运出来以前有一个时段,气温已经下降,但天光依然很亮,竹床也空着,一天辛苦的劳作也告一段落。在小河里游泳并洗过澡的表哥,赤裸上身,肩膀上搭一块毛巾,盘腿坐在竹床上。他手上拿着一本我父亲的藏书《西游记》,挺直腰背,右手(拿着书的手)前伸,左手则捏着下巴颏。读到兴奋的地方表哥会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笑声不免肆无忌惮,向四周扩散。我觉得表哥的笑声潜入了我们家的自留地,在玉米秆播散的阴影里穿插,一直飘到了小河对岸。成年以后,我算是有了一点见识,回想起表哥阅读《西游记》的情形,那姿势包括风度像极了关公秉烛读《春秋》。只是关云长手抚美髯,表哥的下巴颏光溜溜的,他大概边读书边在揪那根刚冒出来的“鼠须”吧。也许表哥读的不是《西游记》,而是《三国演义》。
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表哥回知青点去了,就像他来我们家就是陪我过暑假一样。
不久以后,表哥又来了一次,这次是专门领小河回淮南,只住了两个晚上。
小河目前的状况待在我们家也非长久之计,即使是办了转学她也永远不会毕业。再加上“形势”的变化,我父母自身难保,竟然有人检举他们到了农村也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而是大兴土木整饬园子,妄图过上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我父亲的党籍因此被开除。送小河回去,父亲不方便亲身前往,只好叫来表哥,千叮咛万嘱咐,并拿出了钟仁发寄来的保证书,展示给这对兄妹。父亲说,如果再发生虐待小河的事就立刻和他联系,如果他死了,我母亲也会负责到底的。
他说得悲壮,表哥的回答却风轻云淡,“舅舅、舅妈放心,还有我呢。”
正是这句话让父亲感慨了半年,他的意思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表哥是真正的男子汉,让我好好学习。
“今后,这一辈子,”我父亲说,“无论碰到什么事,你们都要和我商量,知会我们,你们是有舅舅的人。”
我在旁边插话:“什么事啊?”
“比如结婚嫁人、上学工作。”父亲说。
表哥始终在点头,但他没掉一滴眼泪,倒是小河哭得稀里哗啦,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哭。
两年以后,我父母奇迹般地恢复了工作,当然不是回南京原单位,而是被抽调到当地的县里。父亲被安排到县文化馆,母亲去了县副食品公司当秘书,食品公司分了两间平房给我们家。于是举家搬迁,我也进入县中读初一了。
一天放学回家,院子里很热闹,邻居们都在伸头伸脑地窥探,走近才发现骚动的根源是我们家——家里来客人了。由表哥“押送”,小河和她的未婚夫上门拜望舅舅,自然也是接受审查请求批准的意思。
由于房子窄小,吃饭的人多,我们吃饭时房门是大开着的。未婚夫背光坐在门口,左手始终垂在下面,大概是怕桌上的人看见吧,但也有可能是一种习惯。射入室内的阳光正好照着那只手,不仅是我,邻居们也都看得分明,那手上只有三根手指,食指和中指齐根没有了,残手的截面光溜溜的一片。也就是说小河的未婚夫是个残疾人。而且那人并不年轻,长得干巴巴的,一脸的褶子,比我父亲也小不了多少。小河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竟然出现了害羞的表情。表哥端坐在他俩中间,依然十分沉着。
由于家里住不下,当晚表哥他们住进了县委招待所,父亲找关系开了两个房间,表哥和未婚夫一间,小河一间。可小河哭着闹着要和未婚夫睡一起。表哥坚决不答应,他也说服不了小河,只好站在房间外面守了一夜(不让小河进去)。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去送行,表哥脸色发灰,直打哈欠,问起来他才說自己通宵没睡。当时我父亲说:“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机敏的表哥立刻抓住了这句话,听出了舅舅的意思,也就是说同意了这门婚事。因为他回答我父亲:“我知道了。”
“人才是比较一般,”父亲说,“只要你妹妹满意就可以了,她的情况我们都知道……”
父亲反过来安慰表哥,但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必要。“舅舅、舅妈说行,那就行。”表哥说。
“那手看来也是因为工伤,”父亲说,“说明至少也是个熟练工,有手艺的。”
“六级车工,我了解过了。”
“是啊是啊,不影响生活和工作就足矣。”
在送表哥他们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我父亲和表哥一路交谈。因为专心和父亲讲话,表哥没机会搭理我。他牵着我的手,手上不时地使劲儿,一会儿放松一会儿使劲,意思是没有忽略我。我回头看落在后面的小河和未婚夫,两人是抱在一起走路的。准确地说,不是未婚夫抱小河,是小河用手箍着未婚夫的脖子,整个人几乎都猴在他身上。小河把未婚夫当竹马骑了。总之她高兴得不得了,路人不免侧目而视,我发现不少人都是从食品公司跟过来的。
这一次小河没有哭。倒是父亲和我回到家,母亲落泪了,她说:“小河真可怜。”大概想到了未婚夫的那只残手。
父亲说:“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他告诉母亲,表哥准备去当兵。“妹妹有了着落,这才考虑自己的前途,这孩子真是好样的!”
“表哥要当兵,我怎么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我说。
“你知道什么,从小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哪里知道人间疾苦!将来有出息也不会大!”父亲莫名其妙把我骂了一顿。
四
表哥真的参军当兵了,并且当的是侦察兵。他从部队寄来照片,一身戎装,趴卧在雪地里,肩膀上扛着火箭筒,两只眼睛一睁一闭,和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照片里的珍宝岛上的战士一模一样。
表哥自然不会在珍宝岛,那场著名的战斗也是前几年的事情了,但他当兵的地方肯定是北方,冰天雪地,表哥英勇坚毅的表情也非常标准。我向父亲要了这张照片,貼在床边的墙上,和从《解放军画报》上撕下来的某页并置在一起。至此,我对表哥的崇拜已达顶点。
也有关于小河的消息,她和未婚夫生了个大头儿子。当然,未婚夫现在已经不是未婚夫了,而是小河的丈夫,那大头儿子和其他的婴幼儿也很相似,看不出什么差别。在信中表哥特地强调孩子一切正常,智力发育比同龄孩子似乎还要强一些。总之他絮絮叨叨,就像他是那大头儿子的父亲。表哥告诉我父母,这张照片是小河送给舅舅、舅妈的,他那还有一张。我对小河的儿子并无兴趣,照片被母亲收藏了。
时间过得飞快。我初中毕业继续读高中,仍然在同一所中学里,因此也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如果硬要说有变化,那也是心理上的吧?我将亲爱的表哥逐渐置之脑后,甚至他那张卧雪的照片也从床边的墙上撤下了。当然不是故意撤的,我有了自己的房间,睡觉的床搬过去的时候照片和画报都没有“搬”。
时不时地仍有表哥和小河的消息传来,我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除了是特别重大或者惊悚之事,比如说小河失踪了。她留下三岁不到的孩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小河的丈夫还特地来我们家找过。由于我整天不着家,所以没有见到。表哥也从部队转业回了淮南,他倒是没有再来我们家。两件事串在一起,似乎表哥转业是为了小河。他在部队一向表现优秀,已经当上了排长,置大好前程于不顾只是为回乡寻找妹妹;之所以没来我们家也是因为此事刻不容缓,或者他认为,不找到小河就没脸再上门。
父亲为表哥惋惜之余,又开始夸赞他这个外甥。他恨不能亲身前往,也去淮南寻找小河,但那时他已经身患重病,体重不足九十斤,早已不是当年跨省怒斥钟仁发时的精神气了。由于身不能至,父亲的思维特别活跃,竟然一口咬定小河的丈夫谋害了小河。“当年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善类,贼眉鼠眼的,这人都是相由心生。”父亲一边挂着吊瓶一边说,“再说他有作案的条件,六级车工,能把自己的手指切掉,就能切割人体其他部分……”
父亲暗示小河的丈夫作案后分尸,继而分析道:“因此他才会来苏北找人的。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会藏匿小河吗?这充分证明了他做贼心虚、转移视线,至少也是推卸责任。这个混账东西!畜生!”
父亲怒不可遏,母亲向周边的人解释说,他肝火太旺了,县医院的初步诊断也是我父亲的肝脏出了问题。至于到底是什么问题,院方建议去南京的大医院里做进一步检查。父亲对此置若罔闻,那段时间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小河的事情上。
“告诉小淮,小河丈夫是重点怀疑对象,其次是钟仁发和他老婆!一定要找到你妹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耳提面命,让母亲代笔给表哥去信。自然,写信时具体的措辞母亲是会推敲斟酌的。
实际上,父亲所有的家信都是我母亲写的,也不能算是代笔,母亲只是代表,代表我们全家。当年和我爷爷通信,后来和表哥通信,以及和我二姑、小姑通信,一概都是我母亲写的。母亲的温柔、婉转、通情达理是一贯的,在这些信中亦不能读到我父亲身体的真实状况。
五
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我一九七八年中学毕业,从县中以应届生的身份考取了山东大学,去济南读书。我前脚刚走,后脚落实有关政策,父母被调回到南京的原单位。又是举家搬迁。我们原来在南京住的房子早就被别人占据,外公外婆只好借住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我父母则被安排进一家宾馆。实际上那宾馆房间只是我母亲一个人住,父亲直接从县医院搬进了南京军区总院的病房。终于有可能做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来日无多。因为怕打搅我的学习,并没有人告知我。等得到消息,我父亲已经病逝。
我从济南回南京奔丧,坐了一夜火车,清晨时分来到一个陌生的大杂院里去一扇木门前敲门。门开后,传出一片女人的哭声,从床沿上方伸过八九条手臂拉住我,告诉我,我父亲去世了。一概都是女人的手。后来我才知道前来奔丧的亲戚男女分开住,女性都住在这间借住的平房里,包括我母亲和外婆,两张大床上竟然睡了六七个人。男宾则挤在那间宾馆房间里,外公加上四五个至亲,表哥也在其中。
父亲的丧事和追悼仪式就不说了,因为这篇小说的主角是表哥。这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见到他,也是表哥第一次见到除我们家人之外他母亲娘家的亲戚,我二姑、小姑、二姑爹、小姑爹和姑姑家的孩子们,对表哥而言就是二姨、小姨以及表弟、表妹。大家无条件地接纳了表哥。哭声震天,悲欣交集,或者说悲中有喜。悲的自然是我父亲的离去,喜则是终于见到了这个一表人才的大外甥,就像白捡的一样。表哥也非常争气,不仅在第一时间厘清了复杂的亲戚关系,姨妈、姨爹没有叫错,没叫成舅妈、舅舅,他的表现也异常“懂事”,该哭的时候哭,该劝的时候劝,该干活的时候干活。
表哥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卷起袖子领着我负责这一堆人的一日三餐。买菜、做饭是小事,要在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进行排布却需要智慧。表哥指挥若定,并亲自动手,和我抬起两张大床将其面对面放置,中间放上大桌子,如此一来床沿上也可以坐人了。方桌的两头再放一些椅凳,十几个人坐下后竟不觉得拥挤,尚有走动的余地。房子的另一头放着煤炉,煎炒的刺啦声不绝于耳,不断有做好的菜端上桌子。每次吃饭都会摆满一桌。
表哥掌勺,我跑堂,不在桌上吃饭,这样又可以节省出两个座位。
人人都夸赞表哥的手艺好,在治丧期间每餐都做到了盘空碗净,大家不免有点不好意思。“谁让小淮做得这么可口,”我母亲说,“我也是第一次品尝他的厨艺,可惜舅舅吃不到了。”
说着母亲的眼眶不禁又红了。于是吃喝的速度稍减。
小姑爹说:“还是部队锻炼人。”
立于一侧的表哥笑了笑,未置可否。
我在想,如果我父亲在世,并品尝了表哥的手艺,肯定又会感慨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在饭桌上,他们谈到了小河,表哥表示,自己一定会把妹妹找回来的。如此承诺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我父亲的遗像,无色的镜框,黑白照片,顶端饰有一大朵白花,两股黑色的丝绸沿镜框两侧披垂下来。二姑爹问起表哥的婚事,有没有满意的对象,以及什么时候办喜事之类。表哥把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意思是,不找到小河他是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
“一码归一码。”二姑爹说。
“我答应过舅舅。”
说着表哥又看了一眼我父亲的遗像。
我突然意识到,表哥崇拜我父亲,就像我崇拜他一样。只不过,我的崇拜出自一个少年的情怀,表哥则不同,那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表哥把我父亲当成他的父亲了吧?
六
父亲去世时我十八岁,刚好是法定的成人年龄。不知道是因为父亲去世还是因为已经成年,这以后的时光恰如风驰电掣。
先说我们家。父亲病逝后不久,我外公也逝世了,然后是外婆,五年之内家里死了三个人,原本的五口之家就剩下两口,母亲和我。为照顾寡母,大学毕业后经本人要求我被分回南京工作。
除了死亡和减员,也有相反的好事。由于这篇小说写表哥,他们家的事自然需要记录在案。
你怎么也想不到,小河被找到了,表哥多年来的明察暗访终于有了结果。小河被拐骗到东北农村,卖给一户人家,已经又结婚并且生了两个孩子。表哥千里迢迢跑去接小河回淮南,小河竟然不从。两个丈夫,两个家庭以及和不同的丈夫生的小孩,小河坚定地选择了“后面的”。表哥在小河现在的家里住了一周,经观察比较,觉得小河目前的日子过得不错,至少丈夫不是一个残疾。也就是说,表哥找到了小河等于没有找到,他独自一人回了淮南。
这之后,表哥开始着手处理小河的遗留问题。第一个丈夫此时已病入膏肓,小河和他所生的孩子其实表哥早已经带在身边,这会儿去办理了正式的领养手续。第一个丈夫终于可以闭眼,也真的闭眼了,一命呜呼。这些都是表哥在信中告诉我母亲的。父亲去世后表哥并没有中断和我母亲通信,就像我父亲也就是他舅舅还活着一样。
表哥结婚了。实际上他早就有一个对象,因为小河的事,两人始终没有谈婚论嫁。漫长而无尽头(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小河)的拖延也是对对方的考验,表嫂通过了考验,当真不易。其间表哥领着表嫂(她还不是我表嫂的时候)来过南京,面见我母亲,当时我也已经结婚,和妻子搬出去住了,回去看望母亲时见过那女人。由于表嫂相貌平常、人很安静,加上我对表哥的关注已今非昔比,所以几乎没有留下印象。表哥领着对象来看母亲,很可能那次也带来了小河的孩子,我就更没有印象了。
母亲老了以后尤其喜欢说话,按南京人的说法就是“韶”,她已经是一个韶老太了。母亲说话的时候并不需要对方的反应,你没有反应她也可以一直说下去。比如你已经走进里面的房间,仍然会听见她老人家在客厅里唠叨。我则养成了听而不闻的习惯。但也幸亏母亲一遍遍地说起表哥,说起他们家的事,有关的情况我才有了大致了解。
总之小河的事情已了(有了结论),表哥也结婚了,不久表嫂也生了孩子,也就是说表哥有了自己的小孩。那个小婴儿两口子也曾抱来让我母亲看过,我被叫回母亲那儿吃饭,匆匆一见。倒是表哥的厨艺没变,每次来看望母亲都是他掌勺。表哥做的饭依然好吃,令人回味,我甚至专门叫上妻子跟我回去吃表哥做的饭。
母亲说:“小淮现在已经是副厂长了,你爸爸要是知道肯定会高兴,嘴巴都要笑歪。他最喜欢这个外甥了,我也喜欢,自立自强,做事从来有头有尾……”
什么厂的副厂长?工厂的规模有多大?是国营的,还是私人企业?抑或是中外合资?这些我都没敢追问,因为母亲一旦说开去就会没完没了。但至少我表哥事业有成,收入稳定,一家四口过着正常甚至不无富裕的生活那是一定的。发了大财似乎也不像,因为我听表哥对我母亲说过:“舅妈,您现在住的七楼没有电梯,现在还能对付,年纪再大一些爬上爬下就不方便了。争取在您七十岁以前我和弟弟一起,孝敬您一套有电梯的房子。”
这完全不像一个大老板说的话,给我母亲买房还需要和我一起负担。
七
表哥经常来南京,当然也因为大姑妈也就是他和小河母亲的墓在南京,就是德贤公墓里那个“亲爱的母亲”的墓。我竟然一次也没有陪表哥去扫过墓。可这次不同,我们不是去扫墓,而是去迁坟。
本世纪初,基建狂潮开始,城市向周边扩张,到处都在修路架桥,于是死者不得安宁。不仅我父亲、外公、外婆的墓被迁到了更远的地方,德贤公墓这样的老牌墓地也保不住了,一条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将从此穿过。实际上德贤公墓早已经满员,近二十年来增加的不是墓碑,而是越长越密的林木,整个公墓俨然成了一座森林。林间无空地,只有绿石头——老旧的石碑上裹着厚厚的青苔绿衣。德贤公墓存在少说也有六十年了吧。
扫墓我可以不去,迁坟我则非去不可,因为需要人手。大姑妈的墓不像我父亲或者外公、外婆的墓,下葬的是骨灰盒,她病逝那会儿都是土葬,墓碑下面是棺木,因此不知道会有何异变。尸身肯定已经腐烂,尸骨恐怕也得一堆,也许棺材里还会有积水……因此我不仅去了,还叫上了两个有见识胆略的朋友,加上我妻子、表哥、表嫂和我母亲,一行七人。准备了红布、鞭炮、铁锨以及一只用来盛放骸骨的板条箱(里层钉了塑料布)。最后一次祭扫完大姑妈,放完鞭炮,在硝烟弥漫之中推倒了“亲爱的母亲”,然后开挖。
表哥和我的分工是这样的,我领着三位女性各执那块大幅红布的一角,站在挖开的土坑四周;下面的坑穴里,表哥领着两个哥们手持铁锨挖掘不止。罩一块红布自然是因为迷信,据说入土安息的死者不可见到白光,否则便是大大的不吉。这套说法和安排均來自表哥,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和习得的。就像他不是第一次领着众人迁坟,或者他就是一个殡葬工,干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工作。表哥沉着镇定,指挥得当,流程的衔接也如行云流水。那块红布透下暖暗的红光,加上四周林木茂密、头顶枝繁叶茂,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阳光进入土坑内。
挖至半人来深,表哥示意两个哥们上去,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下面挖了。挖出的新土堆积在土坑周边,那坑看上去更深了,表哥只露一个脑袋,不断地将铁锨里的土举送上来。那土黄黑色,散发出一股土味,但干干净净,里面并无任何杂物。之后,表哥送上来一件圆乎乎的东西,平置在铁锨前部,我还以为是一大块土垡。目睹表哥郑重的态度后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颗头颅,也就是颅骨。那颅骨和泥土一样的颜色,又圆又小(比想象中的骷髅小了太多),但完整无缺。换了一个角度,我看见了颅骨上的牙齿,竟然如此整齐。
我接过表哥双手平举过头顶的铁锨,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还是表嫂拿了一块红布(小幅的)过来,隔着那红布包起大姑妈的颅骨拿走了。表哥埋下头去继续挖,越发小心翼翼。
这之后,分别送上来两根大约是大腿骨的骨头,另有三四块疑似骨头的土块,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没有棺材板,没有衣物碎片,没有手骨或者脚骨之类的小骨头,只有泥土,而且是那种非常细腻、略微潮湿“匀质”的泥土。一切,都已经化作了泥土。
“真干净啊,太干净了。”我母亲说。她的意思是除了颅骨和大腿骨什么都没有了,听上去又像是对大姑妈的赞美。老人家少有地言简意赅,没有多说一句。
表哥一直挖到土坑底部渗水。他穿着那双军用皮靴站在泥水里挖个不停,送上来的稀泥也很干净,没有异味只有水味。母亲说:“上来吧,没有东西了,你都快把自己埋进去了。”表哥这才分别拉着我和一个哥们的手,借力爬出了土坑。
头顶的红布撤去,阳光透过枝叶斑斑点点地洒下,汗水淋淋的表哥冲我母亲笑了笑。
由于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装,准备的板条箱没有用上。表哥就是表哥,是有第二套方案的。他从淮南带过来一只土陶罐,比泡菜坛子大,比腌菜缸小,很难看出那罐子原来的用途,几乎就像是一件古物。大姑妈的骨殖被放进去,表嫂又拿出一块红布,比包裹颅骨的红布大,比那块大红布小,不大不小的红布此刻包上了那只罐子,而罐子被我表哥搂在怀中。他就像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似的,离开土坑,走出德贤公墓的大门,向停放在路边的中巴走过去。那辆中巴是表哥从淮南开过来的,我们也是乘坐它来到此地的,现在,它将带着大姑妈的遗骨开回去火化并安葬。
其他人跟在表哥身后,天高云淡,秋风习习,真是人生难得的好时光。表哥为照顾我母亲,走得也不快,步履沉稳,几乎是慢条斯理,自有一番韵律。一段不长的路走了有十分钟。于是我就想,“亲爱的母亲”在她孩子的怀中待了十分钟。
责任编辑 孟小书
作者简介:韩东,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及思想随笔集四十部。近年出版有诗集《奇迹》《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中短篇小說集《狼踪》《幽暗》等。近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中篇小说、凤凰出版集团金凤凰奖章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