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李庄
2023-11-23黄卫
黄卫

在人民大会堂遇见老朋友,李庄喜笑颜开。 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每次听到有人说她出身“新闻世家”,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总是感到有些惶恐。父亲李庄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报总编辑。李东东进入新闻行业以来当然时时能感受到父亲的声望,但又不愿被笼罩在这荫庇之下。
李庄主持人民日报社夜班工作二十余年,李东东则3岁开始上全托幼儿园、寄宿小學,17岁上山下乡,与父母一直聚少离多。等她退居二线后真正静下心来,想要深入去了解父亲,却早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今年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73年前,李庄是第一个入朝采访的中国记者。李东东一直想要彻底捋清父亲三次入朝的经历,惜父亲在世时没有当面请问,现在只能凭着一股“轴劲”不懈地考证、追寻,并将所得所感陆续发表于报刊或结集成书。
作为新闻二代,她总想努力完成父亲报人生涯的拼图。因为这不仅关乎父亲个人,也关乎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那一代人,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心路历程,以及背后的时代印迹。
2006年,李庄辞世后不久,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叠泛黄的活页纸,是他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在朝鲜战场采访期间的日记。
李东东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年年底调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根据这叠半个世纪前的珍贵手稿,她主持编辑了《李庄朝鲜战地日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左手页为影印的李庄战地日记手迹,右手页为铅排文字,装帧精美。但编辑中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出版前言中写道,日记是李庄“第二次赴朝采访时所记”,但这一点其实并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当时只能暂时放下,结果一放就是十年。
2018年适逢李庄百岁诞辰,李东东计划将他的朝鲜战地报道完整结集出版。这次,她决心上天入地都要把父亲三次入朝的脉络厘清。
李庄首次入朝的时间是确定无疑的。那是1950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刚爆发十多天。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突然把他找去,告知中央决定派他担任团长,与法共党员、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和英共党员、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组成一个国际记者团,入朝采访。
李庄在新闻界是出了名的笔头硬、写稿快。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当记者时,总是被编辑部派去找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审阅重要稿件。邓小平很重视向延安的发稿,总是放下手边事情立即处理。他边看稿子边谈意图,李庄能够边听边迅速组织语言,现场改完,邓小平直接就在“花脸稿”上签字,一次过。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只有两个文字记者获准到会场主席台区采访,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李普,另一个就是《人民日报》首席记者李庄。李庄每天赶写一篇通讯特写,八天会议,八篇通讯,记录了新中国诞生的新闻现场。
第一次入朝,李庄在朝鲜停留了50多天。他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抵达了大邱、釜山最前线,写了12篇战地通讯。李东东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的报纸合订本中一一找到了这12篇文章,拍摄了当年的竖排版面。
但另两次入朝,脉络就不那么分明了。李东东巨细无遗地查阅了那段时期的《人民日报》,又仔细重读了父亲的战地报道和日记,终于有所发现。
日记起自1950年12月2日:“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培蓝即李庄的妻子赵培蓝,当时她已怀孕,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次年夏天出生的小女儿李东东。这一次,李庄是率《人民日报》记者入朝采访。
12月3日的日记非常关键。从记载可知,当夜他们在沈阳见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泗淇告诉他们,现在汽车被美机打坏很多,交通困难,建议他们“先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看情况再到前边去。大家讨论后同意这个方案。
那问题来了。“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到底过江了没有呢?
不巧的是,9日至18日的日记空缺,只知道8日李庄还“站在鸭绿江北岸”看积满白雪的河床,19日已“从临江出发回北京了”。那这10天他究竟在哪里呢?
李庄曾在回忆录《难得清醒》中提到,自己曾三次到过朝鲜新义州,第二次是在1950年11月底。这说明,他第二次也是过了鸭绿江的,但11月底这个时间又对不上。
李东东追问母亲。母亲也是人民日报社老编辑,当时94岁了,依然思维敏捷。她有印象李庄去了三次朝鲜,但记不准具体时间。面对李东东的执着劲头,她大声说:可以了,不要再查了!你爸爸也不见得就记得那么准。他完成了任务,留下了作品,这就行了!
李东东还是不甘心,她继续查找,终于在父亲离休后写的一篇文章《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中发现了新线索。文中提到,第二次访问新义州是在1950年12月,这个整洁美丽的江城已被彻底夷平。李东东推断,父亲的回忆录中说11月是笔误了。
这样,一切就都能说通了。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期间,李庄等正是为此而来。12月6日中朝联军收复了平壤,他们可能即于此时过江去采访得胜之师。战地采访很艰苦,这段时间的日记很可能因此空缺。
12月31日中朝联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于是李庄日记从30日起又开始了(19日回京后即中断),这天黄昏他再次渡过鸭绿江入朝。这次他在朝鲜连续待了两个多月,经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日记一天也没有中断。
1951年3月10日,李庄前往位于平壤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与相熟的临时代办柴成文畅叙了一番。四次战役李庄亲历了三次,对得失颇有一些观感。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整不了我们,我们一时也整不了它”,但敌军的“技术条件比我们好”,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防御之势,以争取准备时间。他和柴成文等人对此都有共识,但国内一些人却不了解实际困难,李庄认为,“这是要不得的”。
日记到此戛然而止,谜底也昭然若揭:日记跨越了李庄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入朝,而不是此前以为的第二次。李东东总算能放下这个心结了。
父亲在世时,李东东其实并没有来得及真正去了解他。
从她记事起,父亲就长年累月上夜班,从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到后来担任副总编辑,“文革”之前几乎天天如此。那是一种被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戏称为“穷凶极恶”的马拉松式夜班,通常从下午一直到次日清晨5点。
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李东东和哥哥姐姐才能从学校回家住。通常他们起床时,父亲刚下夜班正在睡觉;等他们下午游泳、滑冰回来,父亲又已經开会、上夜班去了。
外人都觉得李庄随和、好脾气,但李东东兄妹有时却有点儿怵他。李东东的童年总的来说阳光灿烂,但家里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来讲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这时候,母亲就会带着他们兄妹走开,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父亲消气。
直到李东东长大,才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父亲的处事原则是对人宽、责己严,而家人显然是属于“己”这个范围里的。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持夜班的最后把关人,他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被称为人民日报向上级写检讨最多、也最善于写检讨的人。心力交瘁的他难免有时情绪失控。幸亏母亲性格温婉、通情达理,像一座港湾,在风雨中承托起家庭这艘小船。
不过,父亲虽然永远工作繁忙,有时在家里发发脾气,但他的“不教即是教”的教育方式总的来说是十分文明的。有一次正值小学放暑假,李东东夜里睡不着,悄悄起来,见父亲还在工作,她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她的头,笑着答应了。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父亲俯身写字台,时而沉思,时而疾书,时而起身踱步。这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和绿色台灯罩前父亲伏案写作的背影,一直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但岁月静好的天空,一夜之间变了。
那是1966年5月,《人民日报》奉命转载一篇重要社论。这篇社论比较长,报纸一版上半版排不下。李庄时任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他的意见是要么全文发一版,要么一版转二版,但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不同意。其时,山雨欲来,空气紧张,李庄怕值班编辑删出纰漏,决定亲自动手,与编辑一起“抠着”删掉了五百多字。没想到,就此闯下大祸。人民日报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李庄本人则在“文革”前夜第一批“靠边站”了。
这年李东东15岁,正在北京市最好的女中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二。父亲出了事,她没资格当兵或当工人了,1968年底被分到陕北延安插队。她从小以为全中国都和北京一样,天南海北的人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至此总算见识了真实的世界。
时至1970年秋,形势渐渐有了一些变化,党内特别是军队一些老干部对“文革”不满,开始向“落难老战友的落难子女”伸出援手。靠着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也凭着自己的绘画特长,李东东以“文艺兵”的名额被招进了位于石家庄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
她成了政治部宣传处一名资料员,管理着一间资料室。资料室背阴,也就十来平方米,密密排列着几个书架。“文革”初期,学院图书馆、阅览室一度被废弃,随着形势的变化,宣传处这间资料室的书架上先是有了《史记》和《汉书》,很快又有了《辞海》和《词源》。随着内部发行渠道的日益畅通,《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的其他史籍也源源不断登上了书架。这些书多是淡黄色封皮,被称为“黄皮书”。再往后,苏联文学作品《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一批“灰皮书”也上架了。

1982年十二大期间,李庄向夜班编辑布置版面安排。
有了《辞海》《词源》,李东东捡起了小时候父母灌输的查工具书的习惯,恶补古汉语。这间小小资料室给了她无穷乐趣,工作之余,她静静徜徉在书海里,逐渐看淡了身边时有发生的飞短流长。
遇到疑难,她就写信向父亲求教。有次碰到一个生僻字“(劦/口)”(甲骨文中的“协”字),她怎么也查不到,父亲回信说,这个怪字《康熙字典》 《中华大字典》《说文》《辞纂》以及日本编的《大汉和辞典》中都没有,但“我总可以找到此字的”。
“文革”期间,李庄一直是“另册”上的人。他先是在报社印刷厂搬运组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搬运每卷重达半吨重的卷筒新闻纸,一年多下来,已能达到组中体力最差的工人的水平。之后被派到报社图书馆打扫卫生,可以进“参考阅览室”,他如饥似渴地看书,上厕所也捎上一本。再之后他三进干校,被誉为“研究生”。有人曾找他,说只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就解脱他,他坚决不肯。有一次,在河南叶县的干校中,秋收后闲来无事,他心中苦涩,在旷野中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李东东受铁道兵学院政治部领导之命,回京打听消息。离京回部队前一晚,她和父母关起门来,挤在一张床上谈心。暖气不足的冬夜很冷,三人都披着被子。
那些日子里,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忧心忡忡的氛围,他们一家也在密切关注着。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担心:周恩来身后,老干部的日子会更难过,命运难测。
她的入党问题终于在前一年解决了,不出意外的话,她将很快成为“四个兜”的干部,既体面又稳定。但是,如果父母受到新的冲击甚至被发配外地,谁来陪伴、照顾他们呢?
李东东和父母彻夜长谈,从她的坎坷动荡的青春,谈到父母波澜壮阔的青春。父母都是三八式干部,抗战开始后,“一声炮响上太行”。而现在,她也离家八年,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铁道兵扛枪。父辈所经历过的,除了战争,她几乎都经历了。这一刻,她感到与父母是那样心意相通。
天亮前,她说服了父母,他们终于同意她复员回家,一家人患难与共。三人压低声音,一同唱起了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在这寒夜和黎明之间,都有一种悲壮之感。
在李东东的记忆里,这是她唯一一次与父亲的深入交谈。
李东东不止一次发现,很多时候真的是物极必反。就在他们做好全家一道“流放”出京的最坏准备时,“四人帮”被粉碎了,李庄官复原职。
李东东依然没能在父母身边生活。1976年3月她复员回京,第二年就结婚搬出去了。1983年,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创刊不久的经济日报社,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踏着父亲的足迹走上新闻之路。她先在农村部当记者,然后当编辑,再当总编室副主任、特刊部主任,一干十年。
入行后,她在和同行的交往中,在与“新闻二代”们的聚会中,常常听到父亲的逸闻趣事。人民日报几乎没人讲不出几个关于李庄的段子。
李庄恢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职后,依然天天上夜班,大家还是叫他“老李”。他常常自己到排版车间去取大样,排字车间的工人还是亲热地称他“老李头”。他夏天值夜班时爱穿一件老头衫,见人总是乐呵呵,没一点儿架子。
老友们发现,复出后“胆小怕事的李庄胆子变大了”。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做着工作,看似平淡繁琐,却目标明确。他在报社是一位通才,能写能编,能倚马可待地写评论。报纸上出彩的标题,不论新闻、通讯还是言论,很多出自他手。

1973年冬,李东东从部队回家探亲,与父母合影。

左图:李庄致女儿书信。右图:《李庄文集》出版,父母在2005年李东东生日那天为她题字留念。
1976年至1978年这两年,在党史上被称为“在徘徊中前进”时期。李庄回忆,北京各大报负责人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形成了一条反对“两个凡是”的战线。一种办法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交来东西,我不能不登;我组织文章,也不送你点头。
1977年10月6日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李庄在编前会上宣布,准备刊登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如有错误,自己一人检讨。大家都说不要他一人检讨,编前会集体负责。《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個多月之前,他就在《人民日报》“思想评论”栏内组织登载了署名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当年6月24日
《解放军报》发表重磅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打破惯例,不是第二天而是当天转载。这是此前李庄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三次电话商定的,连版面位置、字体字号、标题大小都经过仔细斟酌。

李庄在人民日报办公室上夜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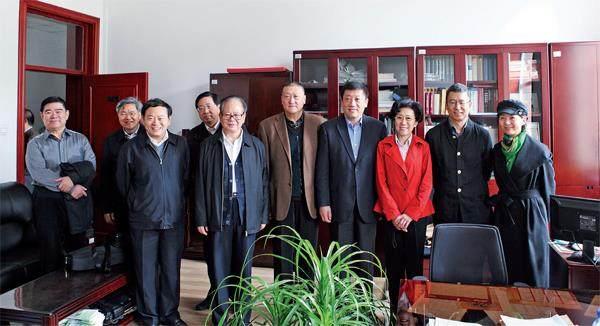
李庄感慨,大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但也学到许多东西,对什么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什么是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把握时机的宣传艺术,确实懂得多了一些。这种变化,在他的同辈新闻人中很普遍。
1983年,李庄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说,这是一个欣欣向荣、说真话的时代,战战兢兢的心情消失了。他依然一丝不苟,上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夜班。多年来他养成了一种“单干”的习惯,一直没有专职秘书,凡事自己动手,常说的一句话是“笨鸟长飞”。
1986年春,中央批准他退居二线,老朋友们都祝贺他“平安着陆”。离休后,他开始放下红笔,重拾蓝笔,寄情于写“小文章”。
他感叹,毛泽东有句名言,凡事要问个“为什么”,但自己直到离休之年才懂得它的真谛。他以朝鲜战地报道而成名,但他在《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中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报道也许只能得六七十分,“可见坚持真实性原则,既需要‘水平’,也需要‘勇气’”。他在1988年为《<人民日报>历届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集》所写的序言中写道:“独立思考是新闻记者最宝贵的品质之一。”
这些文章随写随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上刊载,1990年集成《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出版。一些老同事看后建议,书名不好,选材也嫌狭窄,应该尽可能写写报社这期间的各种大事,不要局限于个人直接处理的事情。他觉得这些意见很好,又加以增补、扩展,写成《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但这本书仍然只是单篇文章的集结。
他下决心要写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他是参与创办三张《人民日报》(分别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三朝元老”,而且始终参与编委会工作。这样的老兵,当年就剩他一个人了。人民日报那时还没有一本报史,甚至没有一本正式的大事记,这让他有一种深重的责任感。
让他痛心的是,早年不懂积累资料,等终于有这意识了,近10年的工作笔记却在“文革”抄家时全部散失。手头没有参考资料,他只能采取笨办法:一张一张翻报纸,以唤起记忆。
李东东听家人说,那些日子父亲每天一大早就起床,自己带着饭,来到位于金台路的人民日报图书馆,一坐一天。很多同事回忆,每次去图书馆,总是看见他在伏案查资料。有时候,偌大的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就这样苦干了三年。他在人民日报40年,一万几千张报纸,他一张不漏全部看过。其后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点就在台灯下开始伏案写作,一直写了15个月。
1999年,李庄回忆录出版,分为启蒙、探索、追求、苦斗、攀登、考验、困惑、沉思八章,书名就叫《难得清醒》。
这是他的收山之作。他说,书名概括了他相当长时间的精神状态:不清醒。他们这一代三八式老干部,从大处说生很逢时,从小处说有人历经坎坷。幸运的是,经过种种磨砺,他们的头脑比以前清醒,是非观比以前明确,斗争勇气和工作方法也有长进,有些事情开始清醒,有些事情还未完全清醒,有生之年还想求得进一步清醒。
“东东爱女一阅” “东东爱女一读”
“东东暇时一读”……由于不像哥哥姐姐常伴父母身边,李东东不忘在父亲出书时请父亲题赠给她,反倒难得地拥有了一套签名本。但要静下心来细读,却苦于没有时间。
那时她正忙于打拼事业,一程接着新的一程。1994年她离开经济日报,赴任湖南省张家界,挂职市委副书记。后调任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此后又担任《中国改革报》社长兼总编辑。2002年奉调西北,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直到2004年春,她才偶然获得了一段意外的“暇时”。那时她做了腰椎手术,只能卧床静养一段时间。这期间,她仰面朝天地举着书本、杂志,认真读了父亲的大部分文章,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文字这么从容、凝练、深邃。她敬佩而又自责,同时想要为父亲做一点事:为他一生心血凝成的文字完整出一套文集。
2004年10月,《李庄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共四本,分别为《新闻作品编》 《散文论文编》 和《回忆录编》(上下册)。这套书很有质感,同时又是自费出版,没给组织上添麻烦,父母和她都觉得这件事办得很好。
那时父亲长住北京医院,头脑尚清醒,但已不能说话了。他抚摸着这套书,只是流泪。母亲后来告诉李东东,每提起一次女儿为他出书的事,他就要流一次泪。
一年半之后,父亲就去世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不是通常的哀乐而是《在太行山上》,上千人为他送行。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被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年,后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位的迟浩田写来挽幛:“德高望重的新闻工作者李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题写了挽联:“平平常常朴朴素素宽厚作风贯一生,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耀眼光环照晚年。”
友人纷纷撰文回忆他。责己严待人宽,是他在报社的口碑。
共事40年的老同事何燕凌曾赠他一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何燕凌觉得,老友应该无憾了,因为他是在清醒状态下安息的。

李东东到北京医院看望父亲。
父親生前,李东东几乎没听他直接表扬过自己,他只是说,女儿很认真,很努力。但是长辈和同辈中的很多人都曾告诉她:“你爸爸可为你骄傲了!”
2018年父亲百年诞辰之前,她编辑撰写的《红蓝文稿》出版,分为四册:《岁月痕》《山河笔》《红蓝韵》《风云辑》。前两册主要是对父母的回忆和父亲的作品,后两册是她本人的作品。其中,《红蓝韵》收录了她2011年在人民网开设的“讲传统谈新闻”专栏文章,第一篇就是《真实,不能触碰的新闻底线》。
整套书之所以命名“红蓝文稿”,是因为红笔与蓝笔象征着两代新闻人一辈子编与写的两种角色,也如同父女间一段隔空相和、余音不断的二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