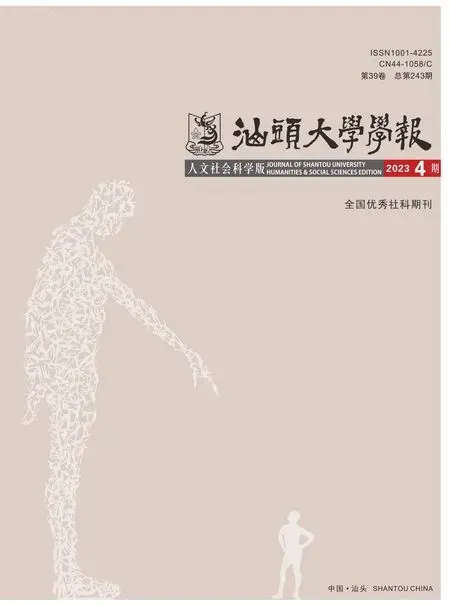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2023-11-21陈祎满
陈祎满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吉姆爷》(Lord Jim,1900)讲述了海员吉姆在一次航行中,遇到海难置乘客于不顾弃船逃跑,随后独自接受审判,继而被西方社会抛弃,前往东方成为英雄的故事。在《吉姆爷》中,“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是小说的中心事件。在“帕特纳号沉船事件”中吉姆因违背了水手的职业准则接受审判,在“布朗事件”中,吉姆以自我牺牲获得了他所重视的荣誉,他的行为被叙述者反复评价,伴随叙事进程的展开,读者对吉姆产生了多维反应。学界倾向于对《吉姆爷》进行伦理阐释,揭示小说伦理道德的复杂性。有学者指出吉姆在东方世界进行精神忏悔[1]100,认为“吉姆的灵魂只有在偏远山区才能得到拯救。”[2]120也有研究者认为《吉姆爷》讲述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梦,肯定了友情和互惠的价值[3]33,表现出康拉德普遍伟大的道德愿景[1]102。若执着于对《吉姆爷》的中心事件进行伦理评价,则难以窥见小说的审美价值,援引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可以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厘清文本极具阐释价值的多义性,审视小说在叙事伦理、叙事形式上的交融。
当代叙事学理论的重要学者詹姆斯·费伦认为,叙事会建立自发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这一进程邀请读者参与其中[4]147。费伦据此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判断:“阐释判断(将某事视为X而不是Y 的决定),伦理判断(关于构成人物活动价值、叙述者活动价值以及作者活动价值的决定),美学判断(关于叙事总体质量和具体质量的决定)。”[5]28其中,阐释判断是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伦理判断是从道德角度进行的判断,而美学判断是对叙事质量作出判断。这三种判断存在于小说故事层面与小说的叙事交流之间,且这三种叙事判断或是互相影响,或是相互交融。康拉德在小说中使主人公、叙述者以及读者围绕吉姆行为做出诸种叙事判断,在赋予文本多义性的同时,也构成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动力。此外,费伦指出文本中存在四种“伦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s),可简单概括为:人物的“伦理取位”、叙述者的“伦理取位”、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以及“有血有肉的真实读者”的“伦理取位”[6]23。《吉姆爷》中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与理想读者,真实作者与读者之间在涉及到知识、判断、价值、信仰上均有所分歧。主人公、叙述者围绕“帕特纳号”和“布朗事件”的不同判断使小说充满不确定性,故事的不确定性和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在文本中构成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推动小说叙事进程,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和叙事伦理上的交融和暗和,构成具有丰富意蕴的叙事美学。
一、主人公的阐释判断:被迫逃逸与直面死亡
《吉姆爷》以主人公吉姆对朋友马洛的讲述复现小说的中心事件,吉姆通过回忆性讲述阐释自己的举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吉姆是帕特纳号船上的大副,拥有成为航海英雄的理想,在帕特纳号的一次航行中,船只发生大面积漏水现象,危机之时,船员们置乘客于不顾弃船逃生,在事后的审判中,只有吉姆出席了庭审,被吊销了航海执照。吉姆只得前往东方重新开始生活,成为备受尊崇的“吉姆爷”。海难发生时吉姆看到船上的铁板即将被破开,整条船将被淹没,船上的救生船数量也根本不够所有的乘客逃生,这种情况下叫醒乘客只能是增加更大的恐慌。此时的吉姆六神无主,正在他眩晕苦恼之际看到其他船员准备逃生,随着船长的喊叫声,他懵里懵懂地跳上了救生船。
吉姆在对马洛的讲述中,不断强调自己跳船时无意识的状态和跳船之后的懊悔。吉姆多次重复跳船的细节,指出自己颤抖着站在甲板上,满脑子都在想着“八百个人,七条小船”[7]117。混沌的他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选择了逃跑,是当时情况的危急和其他水手的引诱与迫使让他最终做出了跳船的选择。他也反复强调自己醒悟过来后内心的煎熬与懊悔:“我当时但愿能死掉……我仿佛跳进了一个无敌深洞……”[7]198吉姆竭力想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出当时那种混乱而又真实的场面,试图重现那一刻他内心的煎熬,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企图得到倾听者的理解和宽容,以消解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吉姆在对马洛的讲述中,反复强调自己跳船时和跳船后的心理状态,强调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费伦指出:“同一行为会引起多种判断,人物行为本身包含人物对自己的判断。”[8]9吉姆将自己跳船的行为解释为无意识的和被迫的,消解了弃船逃生行为的不道德性。
如果说吉姆在“帕特纳号”事件中展现出了人性的软弱,那么在“布朗事件”中直面困境,慷慨赴死则是他修复创伤的重要行为。吉姆被西方世界抛弃后,来到斯坦因在土著部落帕图森的贸易站工作,他因斯坦的推荐获得了头人多拉明的信任,凭借自己的智慧摧毁了恶棍警察长的军事营地,建立了自己的营地,受到当地人的认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吉姆爷。白人海盗布朗入侵后打破了他理想的生活状态。起初入侵的海盗布朗被头人的儿子丹·瓦利斯制伏关押起来,吉姆在与布朗交谈后出于对受难白人的同情释放了布朗。但布朗脱困后对部落进行了反击,攻击并枪杀了丹·瓦利斯。吉姆失信于帕图森人民,面对自己给部落带来的重大伤害,吉姆没有逃避,他来到头人多拉明面前,没有任何的犹豫与迟疑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面对与吉姆有相似遭遇的布朗,吉姆选择给布朗一次机会。反观吉姆在西方世界的遭遇,即便他接受了惩罚也未曾得到任何人的原谅,导致他只能来到帕图森重新开始。吉姆对布朗的释放是与过去自己的和解,第一次面临生命的选择时,他被迫逃生后饱受精神的折磨,当再次选择时他坚定地维护生命。他也并未因自己被白人社会抛弃就心生怨怼,而是以自己的生命为布朗做担保。最后在面对自己的决策失误时,他也坚定地选择了放弃一切奋不顾身地履行责任,直面死亡以弥补自己在帕特纳号事件中的软弱,他也从一个逃避责任的海员变成了一个拥有坚定刚毅气质的英雄,修复创伤后的吉姆成为了大英帝国的英雄。
吉姆的行为包含对其理想信念的阐释。吉姆的弃船逃跑是无奈之举,之后作为船员代表出席庭审并被吊销执照,是他对自己罪责的承担,从而使他弃船逃跑的罪行减轻甚至变得可以理解。吉姆在布朗受困时呈现的友好善良以及在布朗反击后承担责任的勇敢坚毅,吉姆最终为自己信仰的英雄主义和普遍性伦理法则而死,成长为道德意识极强,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男子气概的英雄。
二、叙述者的伦理判断:社会弃儿与土著英雄
叙述者是小说重要的叙事动力,康拉德擅长通过不同的叙述声音使作者以及读者的道德立场复杂化。在叙事活动中,人物的言语行为参与叙事话语的建构[9]150,《吉姆爷》中叙事者的多声音对话呈现出不同的伦理取位。热奈特指出所有承担叙述职能[10]180的人物都可以称为叙述者,同时将叙述者的职能分为五类:讲述故事、讲述话语结构、叙述情境功能,回忆证实功能,以及叙述思想。依照热奈特的分类,将《吉姆爷》中叙述者的功能进行区分,以更清晰地辨别叙述者的伦理取位。《吉姆爷》中马洛是承担讲述故事职能的叙述者,与此同时小说中诸多人物担任了叙述者的不同职能,对主人公吉姆进行评判,在小说中形成了多声部、复调式的对话结构,以丰富小说的叙事判断。小说中叙述者的判断与吉姆对自己的评判产生分离,多种人物的不同立场的互相交织,形成了故事层上的不稳定性,而多种叙事声音的不确定性推进了小说的叙事进程。
马洛是小说主要的叙述者,康拉德以其对吉姆的不确定性判断建构了不可靠叙述话语。布斯指出,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表意不一致时,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马洛对吉姆事件的叙述,是通过转述吉姆的回忆性讲述和他对事件的评判构成,但他的判断充满不确定性。在法庭中关注吉姆是因为他想看一个罪犯被逮个正着的后果,马洛一开始认为帕特纳号案件船员违反职责是不道德的,将吉姆视为罪犯。但他见过吉姆后发现吉姆身上的气质明显与另外两个海员的气质不同:“吉姆在外表上是那种给人良好印象的傻瓜。”[7]146从这里他开始对这个罪犯有了好感。之后吉姆讲述了自己痛苦迷惑的经历后,马洛将吉姆视为同类并理解他的行为,导致他对吉姆做出不同的伦理判断,认为吉姆善良且看起来不像是罪犯。正如他指出:“吉姆想尽办法使我摇摆不定,我承认这一点……那原因很模糊,很没意义。”[7]184马洛对吉姆行为做出的阐释判断使其认为吉姆从道德上可以被接受,但马洛又在之后与吉姆的交谈中对其道德品行进行质疑。马洛对吉姆的伦理判断不断反复,吉姆对自己内心的反复忏悔最终使马洛接受了吉姆的行为,将其视为可怜的迷失青年,并帮他推荐工作重新开始生活。马洛在知道吉姆在帕图森成神又因布朗事件被消解神性后感慨道:“吉姆是一个无名的征服了名声的人,在他崇高的自我主义的示意和召唤下挣脱了一份妒忌的爱的臂膀。”[7]445马洛指出吉姆虽以生命践行了承诺获得了名声,但他的死亡终是自私的,自我的出于对名誉的追求,吉姆最终也未能逃脱浪漫主义的束缚。马洛的判断在叙述中不断变得模糊和不可靠。
马洛对吉姆的判断始终是含混的,康拉德以此消解了马洛作为小说的重要讲述者所代表着的绝对权威。叙述者马洛对吉姆进行报道、阐释和评价,读者根据马洛的报道认定马洛是最能理解吉姆的人,然而“马洛在探索关于吉姆的真相时,消解了二元对立,暗示了他解释的不确定性”[11]202,但是马洛对吉姆的阐释和评价都是不确定的。直至小说的最后,吉姆死亡时马洛也对此发出了疑问:“他满意了没有——相当满意了没有,现在,我想知道。”[7]445主要叙述者马洛的不可靠叙述增加了小说的叙述张力。
布斯指出,在戏剧化的叙述者中,除了叙述代言人外,还有旁观者[12]172,康拉德借助叙述者马洛之口传递小说中旁观者的判断,在人物参与情节进程的同时形成对吉姆的多元伦理判断。首先在船员的世界中,吉姆被认为是一个在危急关头弃船逃跑的背信弃义的人。水手们对吉姆的阐释判断依据的是吉姆作为水手的实则行为,大部分水手没见过吉姆不了解他,但他们听说帕特纳号事件后,便在茶余饭后指责他们行为的不道德。与此相对,也有可以理解吉姆行为的白人叙述者。作为吉姆案件陪审员之一的布莱利尔船长认为对吉姆的审判是一种折磨,他认为那些有道德瑕疵的审判者批判吉姆的行为极度虚伪,他想要出钱资助吉姆逃跑。布莱利尔认为当自己处在吉姆那样的绝境,也不一定会做的比他好。布莱利尔深知作为一个船长必须要对船只负责,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有着对生的渴望,这是个体对生命的本能欲望。布莱利尔认为吉姆的选择是对生命的渴望,可以被理解,所以他对吉姆的行为做出了正面的伦理判断。马洛的朋友斯坦因在听说吉姆的经历后表示:“我非常理解,他很浪漫。”[7]278斯坦因认为吉姆是一个浪漫的人,这种浪漫正好与斯坦因的追求相契合,于是他推荐吉姆去他在帕图森的贸易站工作,给了吉姆重新开始的机会。
叙述者马洛指出“帕图森以传说赋予吉姆以超自然的力量”[7]324,吉姆被帕图森人视为神一般的人物。吉姆来到帕图森后,他的事迹总是被神化,他一个人能背两门炮上山,在与阿里警长斗争中的胜利奠定了他在帕图森人心目中的地位,村民们非常信赖他,将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帕图森人对吉姆的判断是从神话他的行为开始,他们将吉姆利用滑轮运送炮弹的行为解释成他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头人多拉明和他的儿子丹·瓦利斯也对这种力量深信不疑。海盗布朗在见到吉姆时就指出他是一个因为犯了错而藏匿在这里的人,称他和自己一样都是侵略者,并且他在这里捞到了不少的好处,而吉姆嘴上所提到的责任与村民们无辜的生命都是借口,布朗认为吉姆跟自己是一路人,只是他运气好,先到了这里,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吉姆的妻子珠宝与忠实的仆人唐·伊塔姆,在吉姆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而坚决赴死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不理解。珠宝在得知布朗的血腥复仇后,想让吉姆立马逃跑,但是吉姆并没有听她的,甚至吉姆在做决定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过珠宝的想法,对于唐·伊塔姆来说更是这样。珠宝和唐·伊塔姆对吉姆是带着怨恨的,在吉姆死后,被斯坦因收养的珠宝指责吉姆虚伪[7]393以传达自己的怨气。珠宝无法理解吉姆的行为,只能看到他的自私与无情。
叙述者马洛在对吉姆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也承担了转述者的职能,转述了其他旁观者的看法,康拉德以此使叙述者的讲述变成不可靠叙述,进而影响读者的判断。读者通过叙述者对吉姆的判断后对吉姆的认识是愈发模糊与不确定的。对于吉姆的弃船逃生,马洛与白人世界都对他进行了不道德的伦理判断,但同时马洛、布莱利尔以及斯坦因又从对其行为的阐释判断上理解了他,正是这些不一致的叙事判断影响了读者在对吉姆的判断。除此之外,布朗、珠儿、唐·伊塔姆对吉姆在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上的否定,也使读者陷入了对吉姆的复杂的思考,读者在理解叙事时,首先要判断人物的判断究竟是否合理,在这阐释判断的基础上做出伦理判断,最终做出对小说叙事的审美判断。
三、读者的审美判断:单向接受与双向对话
《吉姆爷》的命名使读者以对吉姆进行笃定认知的接受预期进入文本,作者康拉德借助主人公、叙述者、旁观者对吉姆的多种评价混淆读者的判断,文本的不可靠叙述使读者的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错综复杂,从而突显文本的审美艺术功能。费伦认为一部叙事作品中至少有两个平行的叙述层次,即叙述者主导的故事层面和隐含作者主导的讲述层面,援引费伦的叙述层次有利于厘清读者的叙事判断。《吉姆爷》的叙述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由叙述者马洛讲述关于吉姆与帕特纳号和帕图森故事的被讲述层面,另一个是由康拉德作为隐含作者所建构和构想的层面,即讲述马洛讲述的故事。《吉姆爷》的读者在叙述者的讲述中对吉姆进行单向的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在与康拉德的互动中对作品进行审美判断。
在叙述者的讲述中,吉姆的复述使读者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判断中。吉姆认为自己弃船而逃是无奈之举,并且叙述者马洛从阐释判断的基础上对吉姆做出了可以谅解的伦理判断,同时其他人物的议论分错也使弃船的不道德变得不确定,本来是一件吉姆失责的事件,因为吉姆出于对生命原始欲望的冲动而陷入迷茫,读者在此陷入了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现代伦理[13]157的困惑中,查尔斯·泰勒指出现代性带来了极端个人主义[14]1-10的隐忧。20 世纪末的英国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使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平等现象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滋生个人主义,康拉德以吉姆弃船逃生的失责行为喻指英国社会迭出的不道德现象。此外,康拉德还通过多重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判断,从叙述艺术的层面指出吉姆并非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在个人主义和英国伟大传统道德间踟蹰的徘徊者,以引导读者做出不同的伦理判断。
康拉德在讲述“帕特纳号”的故事中消解了吉姆道德上的失误,呈现出人性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赢得读者的同情与理解。小说中吉姆以及多位叙述者对吉姆行为进行的伦理判断和阐释判断,影响了读者对吉姆的判断,正如费伦所说:“人物的阐释判断与伦理判断相交织,读者不同种类的判断也自然会相互交融。”[15]27事实上,人物的阐释判断涉及的是吉姆的行为所涉及的道德责任,读者需要对人物的判断做出阐释性的判断,也就是说,读者需要判断吉姆对自我行动的辩护是否合理。
在这一事件中,康拉德在小说中有意引导读者消解吉姆行为的不道德。首先,康拉德抹黑谴责吉姆跳船行为的事件评论者。指责吉姆弃船跳海行为的评论者是虚伪的法官和道听途说的水手,康拉德在庭审现场使法官的无理与虚伪暴露无遗,而那些将此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胡诌乱说。其次,康拉德借助马洛将吉姆形象与其它两个船员的形象比较,指出吉姆的长相并不像罪犯。读者在对事件并未完全了解后,就被吉姆重复的话语迷惑认为他的弃船之举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最后,在读者了解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和吉姆被诱惑的无意识行为后,康拉德再指出其实帕特纳号最终并未沉没,恐怖的海难与八百朝圣者命丧大海的局面并未出现,吉姆的行为并未造成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与独自站在审判席上可怜又无辜的吉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吉姆与罪犯的格格不入,引发了读者的同情与怜悯,使读者对吉姆的行为做出可以理解的阐释判断。
在“布朗事件”中,康拉德暗示读者对吉姆慷慨赴死的崇高性产生怀疑。吉姆直面承诺死在多拉明枪下,他认为这是自己取得非凡成功的时刻。但康拉德通过马洛之口消解吉姆为诺言而死的英雄性,马洛在吉姆英勇赴死后说道:“吉姆是在他崇高的自我主义的示意和召唤下挣脱了一份妒忌的爱的臂膀。”[7]445这句话直指吉姆的个人主义。吉姆的妻子珠宝和他忠实的仆人唐·伊塔姆面对吉姆丝毫不顾及他们感受的自私感到无尽的痛苦,帕图森百姓也对他生出无尽的失望,吉姆爷的神性光辉逐渐暗淡,康拉斯似乎有意在消解吉姆为承诺赴死的崇高性,暗示是吉姆的精神失落使他最终走向直面死亡。此时对吉姆来讲是唯一可行的路,而这条路无关道德的崇高性与英雄主义的实现。吉姆直面死亡并不是为民族或群体做出的巨大牺牲,而是以牺牲的姿态践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个人主义英雄,吉姆试图以此去弥补自己在道德的缺陷,以实现精神世界的完满。
康拉德通过马洛对吉姆的不确定判断,引导读者参与文本的接受,在对中心事件进行阐释判断、伦理判断,感受20 世纪末英国社会道德困境的同时,接受小说由不确定性带来的艺术张力的审美召唤。康拉德似乎在向读者暗示,吉姆既不是一个道德上完满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他身上的缺陷具有普遍性。吉姆认为自己的慷慨赴死能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拯救,实现人生价值,但马洛对此提出了疑惑,这也是康拉德在小说中提出的疑问。康拉德在小说中借斯坦因之口说道:“人很神奇,但不是杰作。”可以说,康拉德无意塑造一个英雄形象,而是通过彰显人性的弱点,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及道德的相对性。这种复杂性在“吉姆爷”的命名上就有所体现,有学者指出,“神”隐喻着一种神性的光环[16]163,代表着英雄和浪漫主义,而“吉姆”隐喻了一个普通人。实际上这种复杂性也与康拉德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质疑有关,在19 世纪理性与科学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同时康拉德也继承了浪漫主义精神传统,因此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总是呈现出理性主义与浪漫理想的矛盾交织,这种交织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正是康拉德对19 世纪盛行的理性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则戕害了人性的自由,强者和完人的社会理想毒害了像吉姆这样看重名誉的年轻人,使他们无法正视自己的道德缺陷。正是出于这样的叙述目的,康拉德通过多位叙述者的不同讲述,使读者陷入了多维关系网,以此展现了生活世界的多层次性,利用吉姆对自己行为的判断与各位叙述者站在不同伦理取位上对吉姆做出的判断,使读者对吉姆的伦理判断陷入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彰显,使读者更关注吉姆对人生的体验。正像昆德拉曾提到的:“小说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的力量。”[13]160正是小说中这种伟大的力量引导读者去关注人物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价值,体会人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13]4,触摸个人的生命感觉,而不是去寻求一种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这也是小说书写的重要取向。
结语
康拉德在《吉姆爷》中通过多种叙事声音进行繁复的叙事判断,完成了小说叙事对伦理、形式和审美的要求,实现了自己和叙述者的双重目的。在故事层面让读者陷入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张力与活力中,完成对文本的接受,同时在讲述层面读者可以充分参与文本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马洛对吉姆的判断,影响了读者对康拉德叙述目的的判断,读者由此对吉姆的行为进行反思,做出自己的伦理判断,这样康拉德与读者建立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单向、简单直接的给予和判断关系,而是读者在马洛的讲述中不断对吉姆的行动进行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康拉德邀请读者与他合作理解马洛的讲述,读者只有在做出阐释、伦理判断之后才能实现对小说的审美判断。由此,读者会反思康拉德对整部小说的设计,重审叙述者和小说中诸人物对吉姆的判断,进而对小说的叙事质量做出积极的审美判断,正如费伦指出:“同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相比较,使读者参与同解决叙事形式问题紧密相连的复杂的伦理判断,是更大的成功。”[15]30同时“吉姆以充满负罪感的反英雄形象,使《吉姆爷》成为现代小说的诞生之作。”[17]29康拉德以多种叙事声音的参与充分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思考人性的同时实现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詹姆斯·费伦提出叙事判断后,并未指出明确的实践路径,研究者在应用的过程中,常将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的阐释、伦理、审美判断融为一体。本文尝试分开论述《吉姆爷》中人物的阐释判断以及叙述者的伦理判断,同时在读者的审美判断中论述诸种叙事判断的关系,以更好地厘清《吉姆爷》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为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