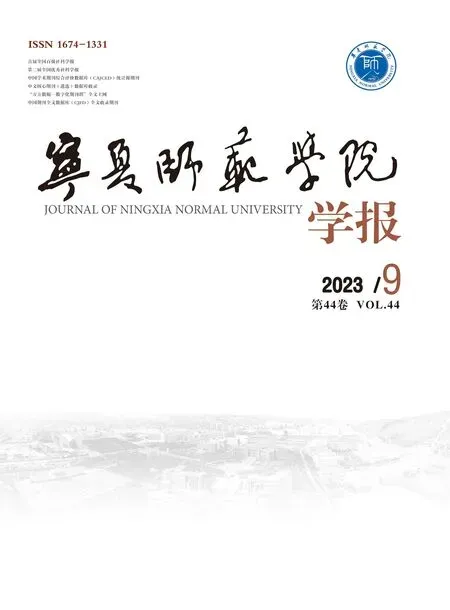1919年商务印书馆美国教科书版权纠纷案与中国版权法国际化
2023-11-21梁甜甜
梁甜甜,马 艾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近代以降,中国封建社会固有体系被资本主义摧残的同时,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亦产生猛烈的冲击,晚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因而变得岌岌可危。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为救亡图存,纷纷在出版物中提出各自的见解,由此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在中西文化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之下,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被国内外出版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概念正是在此时传入国内知识界,版权文化的传入和兴起必然伴随着版权纠纷,近代中国的版权法在层出不穷的版权纠纷中逐渐成熟。前人对中国版权史已进行系统研究(1)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版权法,并参照西方版权法对中国版权的立法工作进行探讨。周林与李明山《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是研究中国版权史的第一部专著,开拓挖掘版权史料的全新领域。李明山《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阐述近代中国版权发展的历史,再现中国近代版权史复杂多变的演进脉络。,但鲜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商务印书馆的版权官司。而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巨擘,自建馆以来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版权纠纷。因此,商务印书馆的版权纠纷无疑是近代中国版权立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建立此二者的联系对中国版权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商务印书馆美国教科书版权纠纷案始末
中国版权法的建立和完善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在西方先进版权法传播和帝国主义治外法权侵略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版权立法工作在重重困难中不断发展,尤其在处理涉外版权纠纷过程中,近代中国版权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而1919年商务印书馆与美国商会关于美国教科书的版权纠纷便是其中一例。
商务印书馆与美国商会关于美国教科书的版权纠纷始于1919年4月22日美国商会致上海总商会的一封信函。美国商会指控华商所办印刷所(即商务印书馆)翻印美国教科书的侵权行为:“华商所办印刷所,有翻印美国课本,销售于上海及中国各埠者,侵夺版权,违犯法律,事实昭然,无可掩饰……今此事已呈明美国驻京公使,与北京政府磋商办法,望警告及印刷局。”[1]上海总商会立即将此函转至商务印书馆。继1911年与美国吉恩公司关于《迈尔通史》的版权纠纷之后,商务印书馆再次受到美国出版业的侵权指控。由于上一场与吉恩公司的版权官司经历重重困难才得以胜诉,此次商务印书馆为避免重新陷入版权官司,便以最快反应速度在收函次日4月23日电呈外交、教育、农商三部。电文提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之内容,并强调此纠纷解决之重要性,“此事于学商两界前途,关系甚巨”[2],农商部随即批复,但这场纠纷并未结束。
商务印书馆深感此次版权纠纷若不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对中国的教育和出版事业造成严重阻碍,因此对此案高度重视。1919年5月,商务印书馆再次电呈农商、教育、外交三部。此份电文篇幅较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商务先列举1903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关于版权保护的内容,再回忆吉恩公司《迈尔通史》版权官司的始末,最后就中国是否应当加入国际版权同盟提出见解,欲以此证明自己翻印美国商会美国教科书并未侵害其版权利益。教育部和农商部对商务印书馆的电文及时予以批复,欲等美使提议再行核办。
商务印书馆再次陷入棘手的版权纠纷无疑对整个中国出版市场影响重大,出版同业均密切关注此事。上海书业商会即刻召集全体会员开会并评议查阅翻印书目,于5月随商务印书馆后呈文农商部、教育部和外交部三部。呈文除复述美国商会函文和商务印书馆电文外,进一步为商务印书馆翻印教科书一事进行辩驳。上海书业商会认为,美国教科书并非专备中国人民所使用出版之书籍,不享有中国版权的保护,故商务印书馆此次翻印并未违法。各部门对此案尤为重视,教育部和农商部对呈文作出批复:应转由外交部查核办理。农商部于6月6日发布批文称:“兹准复称,此事尚未准美使来部提及,除俟美使提议,再行核办外,请查照等因。”[3]最终美国商会对商务印书馆的侵权控告被驳回,此次版权纠纷得以解决。
二、商务印书馆美国教科书版权纠纷的解决
商务印书馆美国教科书版权纠纷不是个例,此纠纷的成功解决亦是当时诸多版权纠纷案得以终结的缩影。清末民初,出版商与著作者之间以及各出版商之间的版权纠纷因出版市场的繁荣发展逐渐频繁。例如,北洋官报局盗印文明书局《中国历史新智识读本》而产生的版权纠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广益书局、世界书局、米林公司、吉恩公司、美国商会等国内外出版商均发生过版权纠纷。翻版盗印现象随处可见,“翻版之案,湘、鄂、粤、鲁、川、豫等省最甚,已经发见正在诉讼中者,几于无省不有”[4]。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
西方传教士表面以传播基督教文化为目的,实则进行资本主义侵略。传教士往往会成立出版机构,编辑发行宣传教义的出版物,以达到其文化侵略的目的。此时中国民智初开,欲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注意力并不在宗教之上,因而传教士在宣传基督教时不得不附加国际时事和科学知识来迎合中国知识界以增加销量。此做法取得巨大成效,随之而来的即是书商翻刻盗印售卖行为,这必会引发传教士出版机构和中国书商之间的版权纠纷。广学会出版的《中东战纪本末》和《文学兴国策》是书商翻印的热门书目,其负责人林乐知和李提摩太判定翻印行为侵犯广学会的版权,“西例,凡翻人著作掠卖得资者,视同盗贼之窃夺财产,是以有犯必惩。中华书籍亦有翻刻必究成案”[5]。因此广学会先通过美国总领事致函中国地方官刘道宪请求出示谕禁,后要求上海会审公廨解决版权纠纷。
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既是版权纠纷兴起的导火索,又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出版企业解决版权纠纷的有力工具。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并未满足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美日两国次年欲通过续修通商行船条约扩大在华权益,要求加入版权保护条款。管学大臣张百熙极力反对版权条款,他首先致函日本使臣内田康哉,表示版权公例“施之敝国,则窒碍殊多”[6]。接着致电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们可以影响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和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坚持定见,万勿允许,以塞天下之望”[7]。经历列强意欲扩大侵略范围的谈判,条约将“意在概禁译印”改为“专为我中国特著之书”[8],虽成效甚微,也不得不说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中关于版权保护的条款对中国出版商的翻印行为加大限制,而“西学东渐”浪潮下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版权纠纷则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版权制度的缺失。
中国的版权思想萌芽较早,但未形成制度和法律体系,从而导致“中国之士,终身著述,而书或无资刊印,即数世不出。苟出矣,而坊间翻板同时发卖。殚力于己,而授利于人,或竟以原稿售之坊间,尽归他人”[9]。著作者的劳动成果因盗版翻印被书商窃取。
版权保护文告是中国传统的版权保护方式。传教士出版机构广学会、民营出版机构东文学社、公营出版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等出版机构都曾要求清政府发布版权保护文告,以保护其出版物。然而版权保护文告具有行政权力有限、管辖范围狭小和张贴时间过短的诸多缺点,近代以来这种版权保护方式因其落后性不再适应新兴的中国出版业。
版权纠纷的频发促使清政府和出版界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有的版权保护制度才能稳定出版行业的发展。清政府于1906年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和《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大清报律》,但其在制定以上条律时始终将稳固封建专制统治放在第一位,对出版者和著作者的权利漠不关心,这必会诱发版权纠纷。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虽较为完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的中国,商务印书馆等众多民营出版企业依旧无法避免版权纠纷的发生。
综观商务印书馆的诸多版权纠纷,《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内容和中国未加入国际版权同盟这两个因素对纠纷能否顺利解决起到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由于中国的版权法尚不完备,且中国并未加入国际版权同盟,故原告和被告双方所能依照的法律条文仅有中美之间订立的条约,“惟控案必凭法律,此案可以范围被告之法律,约言之厥维三种。甲 中国本国之法律;乙 万国公法经中国颁发明文认准通行,及虽未经颁发明文而历办有案,已予承认者;丙 中国与外国订立之条约,约明有应守之法律,俾他国人得一体均沾者。”[10]并且,条约中写道:“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2)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光绪条约卷六十八,1903年。,该表述在之后的版权纠纷中成为律师打赢官司的一把利刃,尤其“专备”一词在官司中被灵活使用。美国教科书是美国为本国编印的教科书,显然非专备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必然不应受中国版权的保护。在1911年商务印书馆与吉恩公司《迈尔通史》一案中,商务聘请的礼明律师强调《迈尔通史》并不专备中国人民所用,不能享有版权。经他考察,该书为全英文书写,广销美国,全书800页仅有9页的内容为中国历史,因此可以断定为不专备中国人民所用。1923年美国米林公司《韦氏大学字典》一案中,《韦氏大学字典》虽又称《汉英双解大学字典》,表面看来是专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所编著,实则不是。因为“(米林公司)心中决不想及华人常用此书,此书在华销数亦不敌在美者远甚”[11]。所以《中美商约》签订伊始,美国便不满于此条约。“不论美国人所著何项书籍地图,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3)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光绪条约卷六十八,1903年。,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迫使其屡次提出修约的要求,但中国对此态度强硬,在《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美国的这一诉求也未得偿所愿。在近代中国处于列强侵略的劣势下,商务的官司仍能够胜利,这体现出法律条文的不可侵犯性,中国出版界深刻领悟到版权立法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均未加入国际版权同盟,这一条件使商务在版权官司中可以充分利用《中美商约》关于版权的规定。1886年美国虽然派代表参加了在瑞士伯尔尼举办的万国版权公会,但由于《伯尔尼万国版权公约》与《美国版权法》矛盾重重,美国最终没有加入伯尔尼联盟。中国出版界也曾掀起两场关于是否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的争论,上海书业商会对此持反对态度,并于1913年在《请拒绝参加中美版权同盟呈》中提出九条中国不能加入同盟的理由。梁启超、蔡元培和张元济也提出反对意见。张元济在美国教科书一案中表示:“今吾国教育及工商业之程度,安敢与美国比肩,如此时加入万国版权同盟,窒碍甚多。”[12]《东方杂志》的杨端六和武堉干却对加入同盟持乐观态度,杨端六将版权问题扩大至国际地位:“我国苟欲于世界政治占一地位,对于此等公共事业应积极的干预,不得终世处于消极地位也。”[13]未加入国际版权同盟使得商务版权官司可以不拘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对纠纷的解决大有裨益,但中国版权制度长期与国际社会脱轨必然不利于中国版权立法工作的进程。
三、中国版权法的国际化发展
商务印书馆在解决版权纠纷的同时不断探索国内外的版权制度,大力推进中国版权立法工作,中国版权法逐步实现国际化发展,文教事业的繁荣和祖国主权的捍卫亦贯穿在这一过程中。
其一,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版权法律体系。
近代中国出版市场版权纠纷的频发使社会各界纷纷呼吁版权立法,“然欲办此事,则当移版权制度……保护著述者之权利,以酬其著辑之劳,为最要矣。”[14]中国版权法的修订刻不容缓。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普南和罗白孙合著的《版权考》,详细地介绍各国版权制度并首次翻译刊载《伯尔尼公约》的内容,馆长张元济专门为其作序,强调版权立法对国家进步的重要作用:“而所谓Trade Mark商标,Patent专利,Copy-Right版权之律以成,而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独以版权为最。”[15]商务印书馆的《版权考》使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接触到国际版权法,自此,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并探索中国版权保护的新出路——版权立法。1910年,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和统治危机,以商务印书馆的《版权考》为蓝本颁布中国历史上首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这标志着近代中国版权制度的正式确立。《大清著作权律》是清政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被迫修订的法律,其中无法避免腐朽性和落后性,但西方契约精神和法律文明等先进思想又体现出其进步性。《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更意味着中国已与国际版权法律体系接轨,并且逐步融入国际版权法律体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商务印书馆在诸多版权纠纷中对国际版权法的探索。
在1911年商务印书馆与美国吉恩公司发生《迈尔通史》版权纠纷案之前,张元济便委托前编辑颜惠庆前赴美国,与美国吉恩公司代表乔治·普林顿就在华代理书籍出版一事进行洽谈。在此后商务印书馆版权官司中丁斐章律师的辩词“然则万国版权既不能禁者,尚有何权可以禁之乎?将谓法律可以禁之耶”[16]和礼明律师的辩词“美国法律先已不准华人享受,尚得谓中国以人之施诸我者,还而施诸其人为有乖通商之道德否耶”[17]等均可体现中国对世界版权文明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为融入国际版权法律体系做好准备。
商务印书馆的诸多版权纠纷均是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内解决的。“上海外国租界犹如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会审公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畸形法律审判机关。”[18]上海会审公廨在本质上是列强侵略下产生的一种兼备中国衙门和西方法庭的混合法庭(Mixed Court),由中国政府和领事裁判权国家共同审理租界内的民事与刑事案件。伍廷芳和吕海寰曾言:“洋官于互控之案,大率把持袒护,虽有会审之名,殊失秉公之道。”[19]虽然中国谳员为主审官,外国领事为陪审官,但会审公廨毕竟是西方领事裁判权扩大的产物,是对中国主权尤其是司法权的严重侵害。因此,商务印书馆经上海会审公廨审判而胜诉的版权官司意义深远。首先,法律的本意为公平,但会审公廨是列强统治下明显违背公正性、具有侵略性的审判机关,审判结果必定会倾向于租界内的外国势力。因此,在此背景下商务印书馆的胜诉实属不易,这也体现出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的,从经济到文化无孔不入。其次,商务印书馆的胜诉在敌强我弱的处境下固然令人喜悦,但是商务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其版权纠纷竟然需要在外国势力设立的司法机关中进行审理,并且需要以侵略国的法律作为衡量尺度,既体现列强对我国领土权和司法权等主权的侵犯,又反映我国版权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落后与不完备。最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被传入中国,给晚清中国腐朽封建的统治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推动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进程。
其二,推动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
近代版权纠纷的顺利解决使得出版商可以继续发行出版物,物美价廉的教科书使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民教育事业得以继续发展。版权保护制度的缺失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在近代不断衰落,作者创作积极性的下降和翻译作品的利润微薄使得版权立法的诉求愈加强烈。严复最早与张元济通信交流《原富》版权问题,提出“限以年数”和“二成分利,逐年递减”的抽税标准,要求“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20]。随着近代中国版权法的不断完善,鲁迅在《新小说》《绣像小说》《浙江潮》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作品,林语堂由于著有《开明英文读本》《剪拂集》《大荒集》而获得“版权大王”的称号。版权制度的保护使诸多文人依靠稿酬改善生活条件,从而激发中国众多作家的创作热情,中国学界涌现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可见版权法的建立和完善对文化事业进步产生极大作用。
国民教育在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版权纠纷中贯彻始终,近代中国的落后也深刻体现在教育方面。“夫此等者文明世界所必要之普通智识,而日用不可离之书籍也……偶见一二,则九牛一毛耳。”[21]教育资源的稀缺也异常严重,“国内英文一科缺乏课本,间由外洋供给,价值既贵,又难适合国情。”[22]商务印书馆聘请的律师礼明在《韦氏大学字典》案的辩词中提到:“西方教育在中国现方发达。中国领袖知从各方面提倡此项教育为必要,提倡之一法,在供给国人以低价之书籍;但欲供给国人以低价之书籍,即在不能保存外人版权,否则定价将为外国出版家所挟持而不能从廉矣。”[23]教育的落后导致国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而翻印其他国家的教科书即是改善教育现状的途径之一,故纵使身陷多起版权纠纷,商务印书馆依旧选择“亟宜采有用之书,而以贱价售之务,使尽人能购而后已”[24]。
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民国教科书方面成果颇丰,时全国超过七成的教科书均出自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特设编译所并聘请专家编译教科书,“凡小学、中学、师范、高等专门大学各校应用之教科书、参考书,无不精益求精,各科咸备”[25],经历最新教科书、共和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和新时代教科书四个时代,始终以发扬文化为己任,努力于一般文化之促进。在与国际社会的版权交涉中,商务印书馆不断翻译外国名著,如汉译世界名著、现代教育名著、政法名著、经济名著等。教科书编译工作的成果足以印证张元济与夏端芳、高凤池等人所约定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经营宗旨,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其三,抵御文化侵略和捍卫中国主权。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民族出版企业的代表,和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夹缝中举步维艰,基础薄弱的特征使其难以翻译外国书籍并扩大生产,而肩负民族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发展重任又使其难以抛下民族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催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妥协与革命的双重属性迫使其和外国资本主义始终关系密切,不可避免地对外国资本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不得不依赖资本主义的困境中,商务印书馆在版权纠纷中依旧尽其所能地“以保主权,而宏教育”[26],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
上海书业商会在中国出版界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权纠纷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于1905年由文明书局、开明书局、点石斋书局、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及有正书局等二十二家新办书局共同设立,以“联络商情,维护公益”为宗旨来维护中国出版界的权益。上海书业商会对商务印书馆翻印外国书籍一事大加赞扬,“(商务印书馆)为国民生计及教育进步计,不得不然”[27],如果商务未翻印,则“不惟商业受其影响,教育前途亦将大有阻碍”[28]。在商务印书馆诸多版权纠纷中,上海书业商会无一例外地为商务印书馆发声,在多起版权交涉案中向相关部门呈文维护中国的出版权益。上海书业商会始终笃定商务印书馆“保存主权,维持教育”[29],面对涉外版权官司时尽力反抗列强的文化侵略,与外国出版业家据理力争,使得中国文化不至于落入“外人觊觎不已,得步进步,尝试要挟,效尤日多,后患之巨,尤难胜言”[30]的境地。上海书业商会于1922年呈国务院和内务部关于修正著作权法的请愿书,认为版权立法“于人民事业之奖进,国家文化之振兴”[31]均有益,修正著作权法更是为保护国家文化,“诚以著作物之盛衰,文化首蒙其影响,关系国家,尤隆且巨”[32],故版权立法于国家主权前途的作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