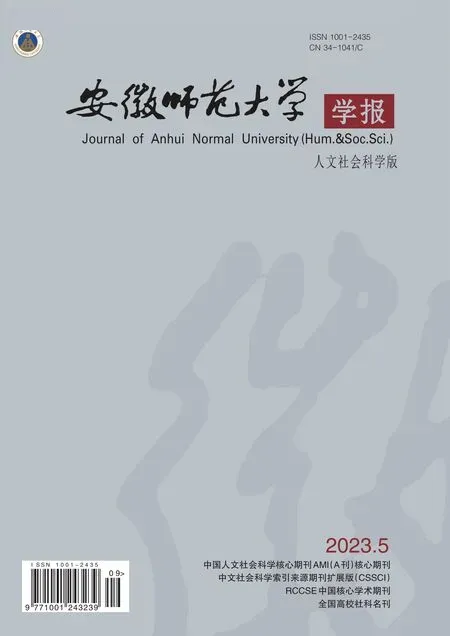历史叙述中的转喻探究*
——以马克思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话语转义为例
2023-11-18牛牧晨
牛牧晨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分析的历史哲学遭遇普遍的理论困境的背景下,西方历史哲学界发生了鲜明的“叙述”转向,将关注重点转向史学文本,考察史学文本的叙述特征,强调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在历史写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对史学客观性的形塑作用。①近年来国外学界的相关代表性论文包括:Kalle Pihlainen,Rereading narrative constructivism,Rethinking History,vol.17,no.4,2013,pp.509-527;Simon,Z.B.&Kuukkanen,Introduction:Assessing Narrativism.History and Theory,vol.54,no.2,2015,pp.153-161;P.A.Roth,Back To The Future:Postnarrativist Historiography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54,no.2,2016,pp,270-281;Zelenak,Eugen,How to cure narrativism with rational evaluation,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11,no.1,2017,pp.22-32;Jansen,H.,Research,Narrative,And Representation:A Postnarrative Approach,History and Theory,vol.58,no.1,2019,pp.67-88;Gangl,Georg,Narrative explanations:The case for causality,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15,no.2,2019,pp.157-181;F.R.Ankersmit,A narrativist revival?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15,no.2,2021,pp.215-239;Lynne Humphrey,The Holocaust and the law:a model of‘good history’?Rethinking History,vol.24,no.1,2020,pp.94-115.历史学家需要以历史叙述为中介来呈现对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的理解,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离不开话语转义方式,正是通过史学家的话语转义,历史事件才能成为历史事实并被构造为历史故事。因此,转喻作为基本的话语转义模式,在历史叙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转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理论领域,史学理论界尚缺乏对转喻的专题式研究。本文在结合认知语言学和文学关于转喻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转喻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机制及其效果。通过分析马克思关于1848—1852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历史叙述,我们将发现:一,历史转喻可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特定的历史事实,呈现超越实在论层面的历史表现;二,历史转喻以事件序列表明历史事件的特定关联,形成深层次的历史解释;三,历史转喻可以将相关历史事件构造为具有一致性形式的故事结构与类型,以表现史学家暗含的审美风格与意识形态立场。由此,对历史转喻在历史叙述中地位、功能和意义的深入思考,将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历史转喻对史学客观性概念的挑战与重塑,更为合理地评价历史叙述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
一、作为话语转义模式的转喻
(一)转喻的语言认知特征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转喻(Metonymy)和隐喻(Metaphor)一样,不仅是人们为增强表达效果而使用的修辞格,更构成了重要的认知工具和普遍的思维方式。②[美]莱考夫、约翰逊著,周世箴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66页。从概念界定上看,转喻通常指使用某一事物去指称另一事物,即通过某一事物来提供可通达另一事物的认知途径。转喻中的两个事物往往属于同一认知范畴,存在邻近共存的紧密联系。③LITTLEMORE J,Metonymy: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20.转喻以显著度高的事物(源域)来转喻显著度低的事物(靶域),以实现最大的认知效率与最小的认知成本。④显著度主要指的是某个事物或概念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程度。参见束定芳编:《转喻与隐喻研究》,上海外教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当说话人所用源域的概念显著度高时,听话人便可以快速从头脑或环境中搜索、分辨出靶域的概念,以达成理解效果。⑤陈禹、萧国政:《事件转喻及其基本类型与篇章限制》,《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3期。根据相关学者⑥RADDEN G,KöVECSES 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9,p.35.对转喻分类的研究,转喻可分为“整体—部分”关系结构和“部分—部分”关系结构。举例而言,以“50只帆”代替“50只船”这一转喻,便是以“帆”(部分)来代替“船”(整体);又如在“壶开了”这一转喻中,便是以“壶”(部分)代替“水”(部分)。
转喻源于人类自身的生活体验,体现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关系,人类经验、感知选择、文化偏好和交际原则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于特定转喻的选择与使用。⑦RADDEN G,KöVECSES 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9,p.35.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以“谷雨”“芒种”等农业概念来指称相应的时间节点,对此,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因为他们早已脱离了这一转喻得以产生的社会生活环境。因此,转喻的语言认知性根源于人类的社会性特征,体现了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替代性思维。
(二)转喻的文学修辞特征
根据叙事学的研究,文学文本至少可区分出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①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3页。文学文本既要呈现故事的内容,又要呈现故事的发生方式。创作文学故事意味着将特定的话语秩序置于文本,“就像自然科学的背后存在着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一样,文学也不是仅由作品杂乱地堆集而成,而是一种词语的秩序”。②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17.因此,文学家为了在故事内部建立话语秩序,便需要编排故事内部的诸多要素,以话语转义③根据海登·怀特的研究,转义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tropikos""tropos",本义为“旋转”,也有“途径”“方式”之意。在古典拉丁语中演变为“修辞格”“隐喻”的意思,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文体(style)这一概念,可以在文学研究中用来描述语词构成的形式,怀特将之称为“话语”(discourse)。参见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2.(tropic)的方式在诸要素之间建立特定关联。
在微观层面,转喻可以通过简洁的概念语词达到最突出的表达效果。④林慧英:《英语文学话语修辞的认知转喻阐释》,《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例如海子的诗歌《五月的麦地》中写道:“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⑤骆一禾、海子著,西川选编:《骆一禾海子兄弟诗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其中“东方”等四个意象便是对全世界兄弟们的转喻,以抽象的空间方位营造宏大的时空感,增强诗歌感染力。在宏观层面,转喻可以在诸事件之间建立内在关联。雅各布森曾强调转喻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重要性⑥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p.52.:叙述者经常在转喻意义上由人物(Character)转向场景(Setting)、从情节转向氛围,以实现不同结构之间的转换。⑦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158.例如《老人与海》的主人公便是通过梦中意象的变换(鸡眼—斗鸡—老人与马林鱼的搏斗)来置换和满足自身的欲望,并通过这些意象不断确证着自我,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深化发展。⑧万曦:《基于〈老人与海〉中隐喻和转喻的变化探索》,《新纪实》2021年第26期。此外,在文论研究中可以发现以转喻方式隐含的心理学与神话学意义的意象与原型⑨[美]维塞尔著,李昀译:《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5-26页。,例如热奈特提出的“转述”概念⑩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吴康茹译:《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⑪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
(三)转喻的历史叙述特征
转喻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仅具有语言认知和文学修辞功能,更发挥着历史叙述的作用。⑫周建漳、王建志:《修辞学的文化蕴含与认知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看来,史学文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特征要远远大于其科学性特征⑬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5,no.2,1966.,史学文本不可避免地蕴含着诗性逻辑与话语。“每一部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产品。”⑭[美]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当克罗齐将编年史⑮克罗齐从观念论的立场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并认为后者的抽象性使其脱离了精神与思想活动,切断了与当下生活的现实联系。参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8页。(Annals)称为“死历史”时,他看到了单纯罗列事件要素并不能达成历史理解。怀特指出,史学家需要通过对历史要素的编排处理,赋予事件可辨认的开端、过程与结局,采取相应的历史解释手段,将编年史塑造为故事。⑯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7-29.
就史学文本作为一种诗性作品而言,可以从类型学视角区分和辨析不同历史学家的历史编纂风格。从比喻理论出发,怀特确立了四种基本的比喻类型:隐喻、转喻、提喻(Synecdoche)和反讽(Irony)。①根据怀特的研究,隐喻主要用来呈现归属于两个不同认知域的对象的相似性,转喻主要用来呈现两个对象的外在因果关系,提喻则主要用来表明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的内在相似性本质,讽喻则主要以辩证方式来进行言辞否定和自我批判。参见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38.与其他类型不同,转喻用于描述事物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常将现象界划分为行为主体与行为本身②例如“电闪雷鸣”,便是在作为行为主体的“闪电”与行为本身的“闪”、作为行为主体的“雷”与行为本身的“鸣”之间建立联系,人们便可以将行为主体与行为特征联系起来。/原因与结果③例如马克思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前者作为后者的原因而发挥决定性作用。,史学家将一种现象还原为另一种现象以形成特定的历史解释。不同于专注于个体性和特殊性描述的一般历史学家,以转喻为手段的史学家主张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与一般规律。作为主要比喻类型的转喻,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得历史学家将冗余的编年史要素转化为简约可辨的事实与故事结构,进行历史解释并赋予特定的历史意义。④赵志义:《历史话语的转义与文学性的衍生——评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因此,在历史写作中,转喻不仅体现着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更是联结表层的历史叙述与深层的历史解释的重要纽带。
二、历史转喻中的事实、序列与结构
(一)历史转喻中的历史事实
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关于某一历史论题争论的焦点往往并非史料层面的事实认定,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方式。当我们面对某一史学文本时,史学家实际上早已完成了以下工作:“与论题相关的对事实的可能陈述,哪些应该进入历史文本,哪些应该被放弃或排斥在外。”⑤彭刚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史学文本中转喻对历史事实的编排和处理方式,本文将首先从微观层面的事件要素出发,以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552页。为主要文本,同时参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⑦[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3-774页。,去分析马克思是如何以转喻去叙述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并分析事件要素在转喻模式下转变为特定的历史事实这一过程。
历史转喻可以运用于历史人物的描写中,以呈现超越个体事实层面的功能与结构。从叙事学的视角看,描述历史人物一般有两种描写方法:心理型描写与功能型描写。⑧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第52-54页。与专注于描绘人物性格特征、心理倾向与人格气质的心理型描写不同,功能型描写基本不考虑人物的性格和思想,而是将其视为服务于故事结构的、在故事中发挥特定功能的抽象符号,其意图并不在于对人物细节的如实刻画,而是以转喻方式来凸显人物身份的整体特征以及其在事件中的地位功能。
在马克思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历史叙述中,其笔下的赖德律·洛兰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502页。,作为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代表,其行为特征不再具有个人色彩,而是通过转喻指代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⑩在转喻式的人物描写中,源域和目标域可以相互替换,例如我们可以直接用“小资产阶级”这个通名替换掉“赖德律·洛兰”这个专名,由此马克思呈现出这样的叙述效果:社会一切中间阶层不是把赖德律·洛兰视为自己的英雄,而是把小资产阶级视为中间阶层的代表。由此,赖德律·洛兰身上体现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特点不能被理解成其个人心理与性格特质,而应当从话语转义的角度理解为整个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在叙述3月10日议会选举的事件时,马克思并没有一一罗列所有当选的议员,而是选取了分别代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的三个人物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盟的阶级”⑪[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4页。,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马克思对这三人背景资料的介绍,可以发现其选取的均是和其代表的各自阶级相关的特点与经历,而非不加选择地堆砌大量历史细节。例如,对于德弗洛特而言,马克思叙述其背景时所选取的象征符号可归结如下:“被放逐者”“谋杀”“布朗基”,这种叙述修辞手法无疑是转喻的,这些符号都共同指向了无产阶级这一本体。因此,马克思笔下的历史人物不是按照心理本质和性格类型来规定的存在者,而是按照阶级属性和社会环境来规定的参与者,其旨在通过转喻来呈现历史事件中的结构关系。
历史转喻可以揭示特殊历史事实的普遍性意义,拓展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广度。马克思对波拿巴当选总统的历史事件也进行了阶级视角下的转喻处理,波拿巴当选不仅代表第二共和国新总统的诞生,也代表了通过普选权支持波拿巴的农民阶级的胜利,更反映出法国社会各阶级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由此,马克思才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2页。这句话便是对波拿巴当选总统的深层原因的转喻式理解,马克思正是要通过转喻修辞来解释波拿巴如何在具体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一步步获得权力、成为独裁者,从情势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的转化②“情势的历史”与“结构的历史”为布罗代尔的历史概念,用来指代不同时段中的历史表征。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通过转喻来完成。作为具体的平庸个人,波拿巴的上台具有历史偶然性;作为法国社会阶级斗争难以调和的产物,波拿巴的上台则具有历史必然性。由此,马克思通过转喻沟通了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
历史转喻可以运用于历史分期,在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之间建立关系。马克思在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进行历史分期时,以转喻的修辞区分了“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die sich konstituierende Bourgeoisrepublik)与“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die konstituierte Bourgeoisrepublik)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2页。,前者从1848 年6 月开始到1849年6月结束,而后者则是以1849年6月为起点。与研究这一时期的其他历史著作相对比,可以发现其他著作中并没有“建立”与“建成”的共和国的区分。此外,从编年史的字面角度看,完全可以将共和国在法律意义上的成立日(1848年2月25日)作为其建立起点,以制宪议会制定宪法(1848年11月4日)作为其建成起点,但这些分期视角都与马克思的视角大相径庭。显然,马克思在此是以历史转喻的方式将“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指代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小资产阶级尚未下台的历史阶段;以“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指代小资产阶级下台、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权的历史阶段,即以第二共和国的各派统治阶级的实际统治时间为标准进行分期,这也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采取的历史分期相一致。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划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二月时期,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1848年5 月28 日到1851 年12 月2 日。可以看出这种历史分期同样是以历史转喻指代法国社会相应阶级的实际统治阶段。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4-755页。由此经过历史转喻的处理,编年史意义上的自然时间也就转变为历史意义上的社会时间。
(二)历史转喻中的事件序列
在历史写作中,史学家不仅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分类标准与概念界定,还决定着不同历史事件在文本整体中的序列关系。历史学家不仅要发现和确立历史事实,更要将这些历史事实编排为有机的整体,通过特定的事件序列来获得相应的关系,以呈现特定的效果和意义。“历史叙事不光是对于它所报道的事件的再造,而且也是一个符号复合体。”⑤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Clio,vol.3,no.3,1974.转喻作为重要的转义方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转喻可以揭示两个表面上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的共性特征,以形成对于两者的总体性理解。马克思在叙述二月革命后的国家政权形式时,将之与七月革命后的政权形式作对比:“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反讽地对比了1830年七月革命与1848年二月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的遭遇,并通过历史转喻揭示了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共性与内在联系,本质上都是不同表象形式下的资产阶级统治。与此类似,当马克思宣称“资产阶级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利(der Februarsieg),而是六月失败(die Juniniederlage)”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6页。时,便赋予了二月革命和六月失败以深层次的转喻意蕴,二月革命与六月失败通过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固与否建立了内在关联,我们也达成了对两次事件的总体把握。最终,表面上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便在历史叙述中形成了特定的事件序列,并呈现出以阶级分析为叙述结构的历史解释效果。
历史转喻可以揭示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通过表面的历史叙述形成深层次的历史解释。②马克思十分重视对范畴的转喻处理,这种转喻决定着对相关对象的叙述顺序与方式。例如他曾说:“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马克思在叙述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的游行失败时,通过历史转喻将1848年六月起义以插叙的形式与之对比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6-508页。,力图呈现巴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仇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恐惧。进而指出:正是由于前一年事件两方结下的恩怨,导致小资产阶级并不能像1793年雅各宾派那样重演历史的辉煌。因此,马克思通过转喻安排的事件序列告诉读者:1848年6月无产阶级的失败预示了1849年6月小资产阶级的失败,前者是后者的深层原因。在对历史事件的转喻式叙述中,马克思也呈现了历史事件序列背后的因果关联,即法兰西阶级斗争关系的动态变化。
历史转喻可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以形成对不同时段历史的一致性理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针对1848—1852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划分了三个历史时期,其中第二个历史时期与第三个历史时期依据统治阶级的不同,又分别划分为三个短时段,它们之间依据先后顺序构成历史转喻关系。④[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4-755页。共和国成立时期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失败)与立宪共和国的第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的失败)构成转喻关系,第二阶段(共和派当政)与第二阶段(秩序党专政)构成转喻关系,第三阶段(共和派的失败)与第三阶段(秩序党失败,波拿巴当权)构成转喻关系。通过事件序列的转喻排列,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建立了有机关系,最终呈现出构成转喻关系的阶级在政治命运上的相似性关联:正如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小资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各个阶段前者的失败都暗示着后者失败的原因,革命的悲剧最终一步步演变成讽刺剧。
(三)历史转喻中的故事结构
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确立历史事实、编排历史事件,还需要将事件类型化以编排成统一的“事件群”。历史叙事不仅反映了历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摹写,更反映了我们施加于历史事件之上的特定的故事类型与意义。因此,对历史的话语转义不仅发生于史学文本的中微观层次,更作用于史学文本整体,对一个历史故事的理解就是对一种特殊类型的理解。⑤Hayden White,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Edited by Robert Doran,JHU Press,2010,p.116.例如,当韦伯从宗教的视角去解读资本主义和加尔文教派的关系时,特雷弗罗伯则从财政精英的流动性视角去解读,二人实际上呈现了不同的历史故事类型。⑥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Routledge,2001;Hugh Trevor-Roper,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eligion,the Reformation,and Social Change,Liberty Fund,Inc.1967.在历史写作中,转喻不仅制造着表层的历史事实,更塑造着深层的故事结构。
历史转喻可以将历史事件放置于阶级关系层面的故事结构,以形成对不同历史主体的关联性理解。面对六月革命,马克思将之转喻为“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⑦[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7页。,并进一步转喻为“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⑧[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同时,马克思对六月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了深入剖析,马克思通过“革命失败—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劳资矛盾并非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逻辑链条进行层层转喻,将六月革命理解为反映法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历史必然性产物。与此类似,马克思在叙述当时法国农民所处的社会地位时,以剥削者(资本家)和被剥削者(农民)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转喻结构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4-526页。,又以此结构来论述农民和无产阶级建立政治同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者共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相似的历史命运。由此,马克思便在阶级关系的转喻结构中建立了对社会各阶级的关联性理解。
历史转喻可以将历史事件放置于社会形态层面的故事结构,以形成对不同政权形式的贯通式理解。马克思在论述1849 年重新恢复的葡萄酒税这一事件时,通过插叙的方式回顾了1789 年、1808 年、1815年、1830年和1848年的各届政府统治政策,指出其共同特征都是对葡萄酒税的保留。②[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2-523页。马克思通过转喻指出:保留葡萄酒税的这些政权本质上体现了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形式,实质上将葡萄酒税的有无还原为衡量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发展程度的标尺。由此,相关历史事件便在这一故事结构中得到安排和解释,历时性历史要素转化为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历史成为了社会性的历史,而社会也成为了历史性的社会。
历史转喻可以将历史事件放置于世界历史层面的故事结构,以形成对地域性历史事件的普遍性理解。马克思在论述波拿巴任命的新任内阁时,特地用大量篇幅去叙述财政部长富尔德上台的意义,不仅指出富尔德代表对波拿巴内阁支持的金融资本家集团,更通过“财政部长—交易所—金融贵族—国家财政—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的关系—法国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状况—法国工业资本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这一逻辑链条,将富尔德上台的个体性事件转化为法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状况的案例表征,由此法国的政治状况便在世界历史层面的故事结构中得到观照。与之类似,马克思对二月革命的历史叙述与对1847年英国工商业危机的叙述紧密相连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9-450页。,马克思对法国新一轮革命可能性的否定与对1849年以来世界性的工商业繁荣的叙述密切相关。④[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8-541页。最终,马克思在法国和以英国为代表的世界市场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形成了自中心向外围的历史解释路径,也塑造了世界各民族通过普遍交往而日益形成的世界历史这一故事结构。⑤[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169页。
三、历史转喻的形式与功能
(一)作为历史解释形式的历史转喻
历史学家的史学文本不仅要讲述“发生了什么”,更要说明“事件何以如此发生”。表面上看,第一个层面专注于历史叙述,第二个层面专注于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但在丹图看来,解释就是对起源和结局之间的变化发生过程的描述⑥[美]阿瑟·丹图著,周建漳译:《叙述与认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怀特也指出:史学家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转变为叙事化的形式与实质,便形成了对相关事件的历史解释。⑦[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中译本前言”第3页。因此在史学文本中,无法直接区分客观意义上指称对象特征的“描述”(Description)与主观意义上历史学家的“解释”(Explanation),事实与虚构往往相互交融,历史学家运用特定的修辞话语与论证形式描述对象时,实质上也是在进行符合其立场与意图的历史解释。⑧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51.
转喻作为基本的话语转义模式,不仅能够呈现事物的特定样貌,表现历史对象,也能建立历史对象之间的因果关联⑨束定芳编:《转喻与隐喻研究》,第421页。,解释历史事实,实现从历史实在向历史知识的转化。马克思在叙述1849年波拿巴内阁的远征罗马事件时,以插叙方式与卡芬雅克在1848年的远征行动做转喻式对比,揭示了两者的深层次关联。马克思首先将卡芬雅克远征行动还原为“教皇—神父—农民—总统”的逻辑,其次将波拿巴内阁的远征行动还原为“罗马—教皇—天主教—法国天主教—农民—资产阶级制度”的逻辑。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4-495页。上述两者的逻辑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既承接着前一个概念、表明自身是前者的结果,又决定着后一个概念、表明自身是后者的原因。由此,两件表面上看似没有深层关联的历史事件在马克思的转喻修辞中得到了有机叙述,同时在一致性的逻辑结构中得到解释和理解。
参照法国史专家乔治·杜比对同类事件的论述,可以更深刻认识到历史转喻在马克思的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在意大利,共和派(马志尼、加里波第)已在罗马取得胜利,教皇庇护九世落荒而逃,一支法国军队首先开往那里,其主要是为了防止奥地利借机牟利。但是,新政府扩展和加重了法国远征军的使命:要求他们夺回共和派手中的罗马,并与教皇一起恢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红衣主教们的统治。②[法]乔治·杜比著,吕一民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74-975页。
很明显,乔治·杜比只是平直地叙述波拿巴的远征事件,并将这一事件起因解释为法国与奥地利的地缘冲突。但这种叙述方式显然无法解释如下关键问题:为何共和制的法兰西要进攻同样是共和派当政的罗马?如果只是与奥地利的地缘冲突导致远征,那么为何还要下大功夫去恢复教皇的统治?然而这些问题通过马克思的历史转喻都可以得到清晰回答,马克思不仅解释了卡芬雅克和波拿巴的远征动机,也解释了这一动机背后的因果关系,揭示了两者共同象征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由此这两件历史事件不仅得到了融贯的历史解释,彼此之间更建立了历史认识上的内在连续性。
同样可以与马克思进行对比的是文学家雨果,雨果因反对波拿巴政变而被驱逐出境,但在其笔下,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事件却被归结为波拿巴个人的权谋作用,“在这个人物及其手段的内里,就只有两个东西——诡计和金钱”③[法]维克多·雨果著,丁世忠等译:《一桩罪行的始末》,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但据此便很难对当时法国历史做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④[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4页。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叙述中,波拿巴作为特殊个体登上历史的舞台,其根本原因是法兰西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斗争。马克思并不否认波拿巴个人的历史作用,但始终强调其个人命运要放置于历史的行程中去把握。正是通过历史转喻才能看到:结构的历史决定着情势的历史。“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⑤[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4页。
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转喻的功能就在于深入到历史现象背后的关系层面,在不同历史现象之间建立关系,发现关系得以成立的一致性形式,并将这一形式运用于历史叙述之中。无论是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论述,还是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都能看到马克思对抽象力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力体现了马克思在超越实证主义和观念论的基础上,实现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内在统一。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Die Abstraktionskraft)的重视与运用。可以说,在历史解释中,转喻就是历史学家的抽象力,历史学家正是凭借历史转喻发现决定着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allgemeine Beleuchtung)⑦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主要的生产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并将这种生产称之为“普照的光”。马克思运用这种历史转喻广泛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诸种社会形态及其主要特征。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发现变化的历史现象背后的不变的历史形式。
(二)作为历史表现整体的历史转喻
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区分诗人与历史学家时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1页。,他没有看到历史中的诗性因素。历史学家不仅需要描述历史实在,更要以戏剧化的情节来表现历史的样貌。历史学家可以运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历史实在。“世界不仅仅是用其字面上所言说的东西构造出来的,而且也包括其言说的隐喻意义。”②[美]古德曼著,姬志闯译:《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历史学家通过转喻不仅构造着历史事实,更塑造着超越历史实在层面的特定历史表现。③此处主要借用安克施密特的历史表现理论,对于安克施密特而言,“表现”理论来自于贡布里希与阿瑟·丹图,表现者与被表现者的关系是非指称性的,前者通过“表现”实现对后者的替代。参见F.R.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9-48.转喻打破和模糊化了历史作品中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联,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进行赋形,从而更直接地触碰现实。④杨梓露:《文学与历史: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及其效应》,《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转喻作为一种拓展和强化历史感知的工具,帮助我们深化了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的理解。
历史转喻可以表现历史事件最典型的意义,拓展人们对历史图景的感知范围。在马克思笔下,六月革命通过“革命死了!——革命万岁!”⑤[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1页。这一表面矛盾的历史叙述,赋予了法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典范性意义。六月革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冲突,因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性意义。由此六月革命既呈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悲剧画面,也蕴含着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喜剧式图景的乐观期望。通过历史转喻,六月革命超越了历史事实层面的实在论图景,在悲剧性的短暂现实与喜剧式的想象空间之间,呈现出最强烈的表现张力与最深邃的历史意义。
历史转喻可以传达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感知视角,表现历史整体的风格类型与美学意蕴。马克思借用悲剧与笑剧的戏剧类型,将波拿巴和拿破仑一世进行转喻对比,表现了作为笑剧小丑的波拿巴对作为悲剧英雄的拿破仑的拙劣模仿,以及1851年政变对1799年雾月政变的拙劣模仿,最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变与1848—1852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变形成了形式类似、实质迥异的两幅画作。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如圣茹斯特、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等人,以罗马共和理想为旗帜,进行着资产阶级的伟大社会变革,直至他们作为英雄人物难以抗拒现实黑暗的阻挠力量而陨落;1848—1852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各派资产阶级,却在现实中不断妥协,法国也从革命的共和国一步步沦落为议会制的、保皇派的乃至帝制的国家。马克思通过历史转喻表明了18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的美学意蕴,前者本质上是舞台主角在现实主义的妥协中粉墨登场的讽刺剧,后者则是舞台主角为了资产阶级自由理想而英勇献身的悲剧。
(三)作为意识形态蕴含的历史转喻
当读者阅读史学文本时,不仅关心历史事件的最终结局,更关心这一文本所要表达的主题(Dianoia)思想。⑥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52.史学家通过特定的主题思想来表现超越了历史事实层面的事物,传播着特定的文化观念、伦理价值等意识形态。⑦Hayden White,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Edited by Robert Doran,JHU Press,2010,pp.136-153.“正是赋予当前社会体制的价值,解释了他们对于历史演进形式和历史知识必须采用的形式的不同概念。”⑧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25.正如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潮流,在形成鲜明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同时更体现出普鲁士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色彩。⑨Antoine Guilland,Modern Germany and her Historians,Jarrold&Sons,1915;Georg G.Iggers,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Wesleyan,1984.因此,如果说政治家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运用是规范性的,那么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运用则是认知性的。⑩F.R.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1.转喻作为历史学家认识和解释历史的重要工具,蕴含着意识形态并体现着特定的价值立场。
历史转喻可以赋予历史对象特定的伦理属性,以表明历史学家对相应历史事件的价值偏好。当马克思认为1849年的山岳党是对1793年的山岳党的拙劣模仿时,认为赖德律·洛兰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拙劣模仿时,借用1793年雅各宾派的成功政变来讽喻1849年山岳党人对局势的无能为力时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490、496、505、668页。,他实际上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嘲讽了小资产阶级荒诞可笑的政治幻想。与马克思表面立场相似但实质取向不同,虽然同样嘲讽了山岳党人②[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3页。,但托克维尔却将阶级斗争理解为现代社会中野蛮群氓与革命恐怖主义对伟大共和理想的侵犯和践踏,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立场上高傲地隐喻法国的政治现实。只有在历史转喻中,山岳党人才能被理解为应当向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坐标系不断靠近的历史主体及其随从,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主体的伦理属性只有转喻为阶级属性才能被判定。
历史转喻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还原为一致性的结构规律,帮助历史学家以激进主义对抗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当马克思将1848年二月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转喻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时,将六月革命转喻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劳动与资本的伟大斗争时,制宪议会的代表奥迪隆·巴罗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将之解读为巴黎工人的非法反叛,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同样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立场对二月革命感到悲伤和悲痛,③[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文集》第4卷,第99页。认为六月革命是“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理论的结合”④[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文集》第4卷,第184页。。在托克维尔那里,他以一种贵族精英式的保守主义和民主式的自由主义相杂糅的气质去体验和叙述社会历史的变革⑤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200.,拒绝以转喻的方式去洞察历史的深层结构和规律⑥[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文集》第4卷,第96页。,最终以一种感伤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讽刺的人类社会。当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洞察到人类衰落的贵族理想与悲剧形式的反讽命运时,马克思却通过历史转喻在19世纪预言了人类社会崛起的无产阶级曙光和颇有喜剧形式的和解结局。
四、结 语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界开启的“叙述”转向表明: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的呈现离不开历史写作,对史学文本的叙述方式、结构与特征的分析能够更清晰揭示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与主体作用。从后现代思想界的进展来看,对于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离不开语言学、符号学与叙事学等理论成果,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研究与阐释也应当突破内容层面的解读,从叙事学视角深入分析其文本写作层面的形式因素和特征。转喻作为基本的比喻类型之一,能够揭示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叙述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的历史转喻融汇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不仅挖掘出历史事实的普遍性意义,也凸显了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呈现出对历史整体的结构性把握,并根据对象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蕴与意识形态。不同于沉浸在冗余多样的史料中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也不同于用思辨逻辑抹杀事物特殊性的观念论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转喻既有对于历史领域的形式描述,又有对于历史过程的叙事性表现,因而超越了传统的实在论与观念论偏执于主客体任意一方的立场。马克思的历史转喻,作为对资产阶级的错误隐喻幻象的破除,指明了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与一般规律,最终成功消解了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及其意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