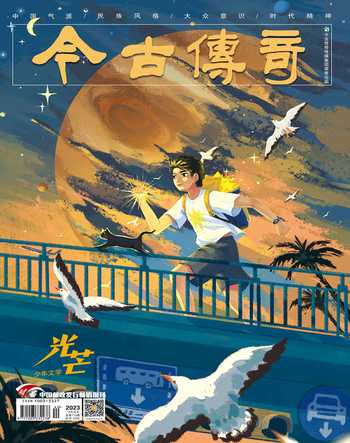书田勤耕溢芬芳
2023-11-11翟英琴
翟英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大山里的音乐会——共产党员邓小岚的故事》《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乘着星光回家》“冒险岛少年励志成长”系列小说和绘本《雨靴》等少儿文学作品50余部,作品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获国家出版基金扶持。荣获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七届“大白鲸”原创图画书金鲸奖、第二届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奖图画书薰衣草奖、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荣誉称号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民谚有言:“光阴有脚当珍惜,书田无税应勤耕。”小时候的夏夜,吃过晚饭的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围在老人周围,听他们讲一些“上了讲究”的民间谚语,尤其喜欢听他们讲故事。是谁为我们留下如此富有哲理的话?是谁创作出如此美妙的故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那该多好啊!我幼小的心灵中时常会产生这样的愿望。
爱听故事的孩子
我出生在冀中平原一个叫李千户的村庄。这里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不发达。但是,洁白的云、湛蓝的天、广袤的黄土地,还有那质朴、憨厚的人,都给了我醇厚的滋养。最重要的是,我很小就被故事的魔力所吸引。
记得有一天,父亲下班带回来一个神秘的大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有着美丽花纹的东西。父亲说,这是收音机。父亲稍加调试,收音机里就传来了唱歌的声音,稍微旋转按钮,马上又传来老爷爷讲故事的声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它的确是个新奇物件。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个收音机对于学龄前的我来说简直太神奇了,因为从它里面传来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
收音机很美,枣红的外壳上有飘逸的花纹,前脸开关上面是镶嵌着金丝线的牡丹花纹,下面是黑色的。妈妈很喜欢这台收音机,总会用花手绢盖住它的顶部,以防灰尘落在上面。
对幼时的我来说,收音机不仅外形美,而且功能强大,它不仅仅会唱戏、讲故事,还会说评书。
白天,妈妈和邻居家的婶子、大妈们坐在我家的大槐树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听刘兰芳讲评书。那时候,刘兰芳讲的《杨家将》和《岳飞传》非常流行,大人们都很爱听,听完之后还会发表各自的评论。
我对收音机充满了好奇,总是不明白唱戏的人、说书的人是怎么钻进去的。收音机那么小,人又那么大,收音机是怎么装下的?所以,收音机像磁铁,而我就如铁钉一样,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
但我常常只能在一旁“蹭听”,大人们听什么,我就听什么。
我黏在妈妈身边,静静地听刘兰芳讲故事。她的声音铿锵有力,讲到悲愤处,似乎整个人都要从收音机里跳出来。那时候,我虽然不知道岳飞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忠良”,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听故事。
飞针走线纳着鞋底的妈妈一遍遍地“吓唬”我:“小心针扎到你!”她一遍遍地提醒我离她远一些。有时候,我只象征性地走远一点儿,依然支棱着耳朵仔细听;有时候,我就假装走开,再悄悄藏到妈妈身后;有时候,我干脆原地不动,因为我已经听得入迷了。不管怎样,我都没被针扎到。久而久之,妈妈也默许了我的“蹭听”行为。
白天,我只是“蹭听”;傍晚时分,收音机就由我完全掌控了。记得当时雷打不动的节目是由曹灿叔叔主持的“小喇叭”节目。“嘀嘀嗒,嘀嘀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每当从收音机里传来这个声音,我就会变得很“专断”,不许年幼的弟弟妹妹发出任何声音,包括爸爸妈妈,他们说话声音大了,我也会毫不留情地制止。这个时间段,我们家只允许曹灿叔叔亲切的声音出现。通过音波,《哪吒闹海》《木偶奇遇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等一些优秀的少儿故事,在我上学前进入了我的脑海。
当然,我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离不开妈妈的启蒙与引导。
妈妈识字、有文化,脑子里装着许多故事。所以晚上睡觉前,我经常缠着妈妈讲故事。妈妈讲的大多是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星光灿烂的夜晚,夜深人静之时,《牛郎织女》《七仙女下凡》《柳毅传书》《白蛇传》等故事从妈妈口中飞出来,在温暖的小屋中盘旋。那时,我常常羡慕七仙女,既可以在天上云间飞来飞去,又可以到人间游览玩耍,多么快活啊!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对培养我的想象力大有裨益。
爱读书的孩子
世界上有许多奇妙的事,未必都能用语言表达清楚。但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缘由,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
文学是有神奇的种子的,它隐藏在文字的一笔一画中,隐藏在一行行生动优美的句子里,隐藏在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后面,隐藏在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顿悟里。文学那神奇的种子,是怎样飘落到我的心田,并且扎根、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我想,这一定跟我小时候爱读书有关。
李千户是我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它坐落于冀中平原,是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村庄。说它普通,是因为它的房屋、街道、树木跟冀中平原其他村庄没有区别;说它不普通,是因为村里住着一些在外面工作的人,他们有学问、有见识,在当时相对闭塞的条件下,常把一些新奇的东西带回来,开阔了小孩子们的眼界,点燃了他们对未来与远方的期待和想象。
跟现在相比,那时候很穷,穷到没有多少书来读,穷到作业本的正面写作业,背面用来演算。当时,如果一张纸只使用一面,那就是浪费。幸运的是,我生活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经常被文学的魔力所吸引。
很小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等我认识了一些字,吸引我的是图画书和小人书。我记得爸爸第一次给我买的是《小猴子吃瓜果》和《小鸟比美丽》。《小猴子吃瓜果》教給我做事要虚心,《小鸟比美丽》是说要注重内心的美丽。这两本图画书做工精美,色彩靓丽,寓意深刻,让我终身受益。那时,我快要上学了,爸爸还给我买了一个森林王国的铁皮铅笔盒。铅笔盒上也是有故事的,我讲给弟弟妹妹听,讲给小伙伴们听。
那个年代,小人书很盛行。上学后,我开始和同学们互换小人书看。爸爸见我如此喜欢,时不时给我买回来一些。有的同学看过的不要了,也送给我。慢慢地,我家的小人书就多了起来,足有三大纸箱。我一遍一遍地翻看它们,被里面精彩的故事和传神的画面所吸引。《西游记》《水浒传》《杨门女将》《董存瑞炸碉堡》《雷锋叔叔的故事》……好多好多的小人书,成了我疯跑玩耍之后的精神食粮。我很爱惜它们,别人送给我的有的已经破旧,我就用油纸和糨糊给它们重新做封面。
我喜欢读书,在街上遇到掉落在地上的半张报纸,也会捡起来看看上面的内容。如果听说谁有一本好书,就会非常羡慕,想尽办法借来读。所有的这些,都是文学的种子,它们像是不着痕迹,又润物有声,日积月累,神奇地在心田中扎下根,并萌发嫩芽。
小学第一次写作文,我的习作就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初中时,我偶然发现一份语文报纸上有个版面是专门刊登学生习作的,于是我抄下报纸的地址,将自己的一篇作文好好润色了一番,一封带着我的梦想的信从邮局出发了。好长时间过去了,在我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编辑部寄来了样报和十二元稿费!这个消息在我们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学时,我读的是中文系,遇到了刘玉凯、韩盼山、尹振华等优秀教授,他们学识渊博,教学严谨认真,爱生如子,我如鱼得水,尽情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课余,我不太喜欢社交,只沉浸于读书,所以,阅览室、图书馆经常出现我的身影。一般情况下,我会跟随文学课程的进度读书。讲中国古代文学时,我读《诗经》《庄子》《西游记》《红楼梦》;讲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我读鲁迅的《呐喊》《彷徨》、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阿城的《棋王》、余华的《活着》等;讲到外国文学时,我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父与子》《罗亭》《前夜》等作品。
大学期间,在学习之余,我开始写诗歌和散文,《中国青年报》《河北日报》《河北青年报》《保定市报》等报刊经常出现我的文章。由于文学创作成绩斐然,我获得了所在大学的“文学作品与论文创作单项奖”。
为孩子们创作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在业余坚持写作,创作的范围比较广,诗歌、散文、短篇小说、评论等都有涉及。我在文学园地徜徉,似乎漫无目的,只是出于喜欢。在我35岁那年,因为给我的孩子讲故事,时光为我推开了儿童文学的一扇门,我被儿童文学的百花园吸引,从此步入儿童文学创作领域。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我起步虽晚,但很快找到了快乐,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大量发表作品、报刊连载、出版童书等。可是,这个年龄的人在工作中也是如日中天,面临着很多机会。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作出选择——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将人生追求的重点放在文学创作上。
业余创作,当然占用了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周一到周五,我基本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写作。晚饭后,别人去遛弯、看电视、跳广场舞,我坐在电脑前打字。创作任务紧的时候,每天晚饭后七点半至十一点半,四个小时的时间,相当于白天的半天,我會全力以赴地在文学园地耕耘,思绪驰骋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有时候,创作惯性让大脑停不下来,就会写到深夜一两点钟。有一回,我写着写着,竟然在电脑前坐着睡着了。可能因为写作劳累,睡觉时我的双臂还在胸前弯着揪在一起,保持着打字的姿势,活像正在吃松果的松鼠。我意识到,长期过度劳累可能会导致颈椎、腰椎、胳膊出现重大问题,我选择以按摩来缓解。按摩时犹如受酷刑,我咬牙坚持。家人劝我加强体育锻炼,不要用按摩代替锻炼。我懂,我听,但我做不到,因为时间太宝贵了。后来,我尽量用走路来代替坐车,这样可以增加锻炼的机会。
双休日、节假日是我创作最为宝贵的时间,因为这是大块的时间。有几年春节,正赶上有创作任务,我打发爱人带孩子回老家过年,自己留下来安心创作。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家家户户辞旧迎新、欢聚一堂,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煮速冻饺子凑合着填饱肚子,空闲时也会心酸,但一投入创作,我就全然忘记了这些。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说过:“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勤奋”一词,对于整天在书堆和文字里摸爬滚打的作者来说至关重要。我认为,文学创作是一辈子的事,在这条路上,只需默默耕耘,尽力探索,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文学的力量和魅力必然显现。
在儿童文学领域,我的创作范围也很宽泛。我不想给自己划范围、贴标签,遇到感兴趣的素材,就会好好打量它,仔细琢磨它适合写成一个什么体裁的作品。十几年过去,我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纪实文学、童话集、绘本等,涉及幻想、冒险、侦探、红色历史、现实生活等各个题材。有朋友建议我在一个方面深挖,这样才有可能挖到富矿。我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但当捕捉到素材时,我就会被创作的激情鼓动,朋友的建议早已抛之脑后。
没有夜以继日的创作,就没有一部部作品的问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倾注了作者的勤奋汗水和心血智慧。我看重每一次创作,也看重每一部作品。今后,我依然会努力耕耘,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有趣有益的作品。我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久耕书田一定会芬芳四溢。
(责任编辑/孙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