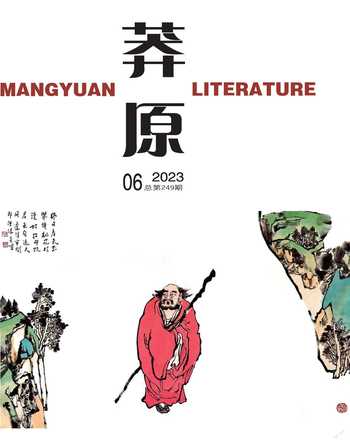食之形而上学
2023-11-08黄扬柳
黄扬柳
修心如习射,初学不瞬,进而学视,视微如著,非物,而境。
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光透过头顶的一片琉璃瓦泻下,正好倾注在铁锅中央。灶台里没有火,锅里却冒着热气。水,以缓慢的速度向上蒸发。我将身体低下来,眼睛恰好与水面平行,紧贴着灶台,那一锅水就开始变得无比崇高和神秘。锅里漂浮着几棵植物,在水中新生,世界最初的生命,植物在这个维度的平静中诞生。水会继续升温,随后便会有其他生命的诞生,世界有了能够察觉的声和象,更显出动态的生命之美。
我们等待。
饭好了,二十分钟,我点起蜡烛。
沉默的慰藉。
酒二两。
从一根葱开始
就一根葱了。有些食材就是过不了夜,香葱就是一种。这几天在做菜这事儿上算是到了瓶颈,原本打算做一个烧豆腐了事,能把那根葱派上用场就万事大吉。可终日寂寞的人,在生龙活虎的菜市场就按捺不住了,伸手就是一棵娃娃菜。
白色。
我灵感的百草园就活起来了。
顺手又买了一袋龙口粉丝。
白色。
很久不做这个了,今天碰碰运气,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是哪根葱。
不知道烟台的粉丝和招远粉丝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煮到位了,它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各显神通,食材本身的缺点也是可以弥补的,况且它是怎么煮都还不赖的粉丝。我心里寻思着,白菜粉丝豆腐,鲜啊。基调奠定了。再加两鲜怎样?遂又买了一点儿平菇和番茄,轻轻掰下来一点儿平菇,凑近闻,潮湿的味道使我想起五月,那是一种怎样的气味呢?其实并不亲近,但是令人心旷神怡。番茄红彤彤的,很饱满,是这些食材里最有怒力的,然而你看它,绷紧了的同时又很节制,你担心它把皮撑破了,可它并没有。色彩有了,白昼的一轮红日,点睛之笔有了。对,还有鸡蛋,我买鸡蛋总是对数量很在意,就像某种仪式,今天买了七个。我从来都是拿单数的,鸡蛋就像眼睛,双数怕它成精。
三鲜,想起来并不是很助兴,我也不怎么喜欢三鲜口味,但我对今天的菜品构思很满意。人在欢喜的时候,智慧就来了,灵感就闪现了。家里不是刚买了一盒咖喱嘛!难不倒我。但转念一想,切记咖喱不能多放,否则就喧宾夺主了,我的菜就会让咖喱囫囵吞了。在做菜的过程中,量、度、火候的把握是尤其重要的,学做菜也就是在学做人,菜料洞明皆学问,刀火练达即文章。
备好菜,平菇、豆腐焯水,下油锅炒鸡蛋,嫩炒,捞出。
油锅下番茄。番茄在火的加持中逐渐变得柔软,在出浆但仍有颗粒的时候下平菇、豆腐,加蒜末、剁辣椒,翻炒出香,只要菜的香气出来了,接下来底味就显神通了。加热水小火熬制,娃娃菜加入这场论辩,热火朝天。过去不吃娃娃菜的秆,当我找到适合的烹饪方法时,甚至觉得它比叶子好吃多了。诀窍就是,切丝,煮到半透明。最后加入泡好的粉丝,小半块儿咖喱,小火煮,加盐、鸡精。最后点缀葱花,完美收官,这菜很适合秋天。
白色的食材经过熬煮之后变得金黄,从冬天开始,到秋天结束,又显得圆满。是我喜欢的口味,又善解人意。
生活的乐趣在于自给自足,自得其乐,来去自如,而且总是在最平淡的地方出其不意,柳暗花明。
柳不改其乐也。
我领受着生活的馈赠,滋养灿烂的灵感。
川味油泼卤牛肉土豆泥沙拉
川味油泼卤牛腩土豆泥沙拉。
如果可以,名字还可以再长一些。
创造始于对重复的厌倦,然而,倘若只有对重复的厌倦,还成不了气候,顶多是一种异常天气。
命运赐予我们川味油泼卤牛肉土豆泥沙拉,就像过去它赐予我们豆豉、薯片、油底肉,赐予这个世界绵绵若存的生命。然而,谁会勇敢地追问那第一次创举呢?“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所有的疑问都固定为一个陈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所有的对存在本身的探求都反射向人类自身。我们仍旧用我们的经验在看,而非用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睛在看。我们的战线拉得和我们对事物的命名一样长。在琢磨了关于起源的问题之后,人们就开始琢磨“啥时候是个头儿”的问题。就像祥林嫂问鲁迅那样: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吃一口吧,吃下去就是明天了。明天,不是今天的一天。
是苦的,我从来没有在我做过的菜中尝到这样的苦味。我却不知道这苦是哪里来的。这多少使人心惊。
那苦是熬出来的,水来熬它,时间来熬它。苦得古老。
忽然想到,母亲做的年夜饭中有一个菜也是苦的。幸而苦得不辣,苦是一种味觉,而辣才是一种异己的痛觉。母亲说:“我自从嫁到这个家,二十多年了,每年过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对一切食物的原味充满了向往,并且坚信我能从中感到一种新的愉悦和安宁。
把菜放在灯下,照出它的静默,就像小时候打着手电筒一颗一颗地照鸡蛋,想看看里面有些什么。拿灯照照还不够,还得等,等它自己从里面打开。
思考了关于起源和死亡的问题后,我们才开始真正探讨关于吃的问题。情感使我们摆向两端,而引力将使我们最终立在这里。
香芋蘸白糖
香芋很少人买,凌乱地散布在货架上,七个,保持旧日秩序,和所有的瓜类摆在一起。
我挑走一个。谈不上挑,没有意识参与,不知道哪个更好,我只是象征性地作出认真的样子,是它挑了我,物自足自得。本事不足,瞎逛有余。
香芋宜蒸,做甜品更佳,蒸的香芋蘸白糖,鲜美到家了。
不知道是哪个想出来的吃法。这是地头的贵族,比洋葱更贵气。紫墨扎染在白练上,霎如闪电昼出。香气使我又想起潮湿的南方,我翻遍地头,才翻出這么个东西。不像是地里自然生长的,倒像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尤物。北方人吃惯了大葱白菜烙饼饺子,吃这些稀奇玩意儿也需要勇气。我是南方的逆子,又是北方的过客,因祸得福,来者不拒。
不拒的人有福了,纵然是口福。
买了一瓶红酒,从冰箱里掏出一根香肠,我妈做的,香极了。我统共只带了两节,先断后不乱,我这牛劲儿一掰,半截落地,冰箱冻过了,脆生生的,下手讲究稳准狠。入水,是个唤醒的过程,那香气只有我妈才熏得出来,这次的香肠是我妈倾心注爱灌来的,不好好吃就是不孝子。松枝的香气和着肉香、酒香缓缓送入,肺腑之间,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的感觉开口就来。
光有香肠还不够,又买了超市旁边熏肉店的熏鸡腿,可谓南北合璧。蒸一下,熏汁有助食之力,若神来之笔。酣畅淋漓,直呼痛快。蒸香芋蘸着熏汁。贵气虽好,但须和光同尘,染这烟火气,又送一个“好”字。
好好儿女。
是孔子的“如好好色”之“好好”。
不可以貌取“圆”
元宵节了,还没有一点儿过节的样子。原本想着一个人,凑合凑合也是一天。得了,今天、昨天和无远弗届的明天有什么不同呢?省了那些讲究人的讲究事儿,底层人没有讲究只有将就。可,没必要每天都过得如此苦大仇深。
在过去买烧鸡的店里买了六个元宵。
元宵是长得有些其貌不扬的,那凹凸不平的球面使人没多大食欲,也仅仅是为了一个仪式,一个惦念。生于忧患。我还很纳闷,这好吃吗,因南方人吃惯了光滑的汤圆。事实证明了:
元宵不是汤圆。
过年不是春节。
放眼看了一下,把元宵当做汤圆的还不止我一个。元宵是一遍一遍地以黑就白滚出来的,汤圆是以白就黑一次性包好的。元宵是需要熬煮的。总之,是决不能以貌取“圆”的。这使我重新思考了关于“圆”的定义。
第一次煮了十分钟,端上来,下口还是硬心,包心更是冥顽不化。煮个元宵还真不简单。我一遍一遍地煮,和它较上劲儿了,就像它当初在粉里无休止地翻滚,雪炼一般。因为第一次煮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熟,每煮一次就吃掉一个尝尝它熟了没有。煮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兑了一大锅水,我也不着急,叫它不化,我倒是要看看它的心究竟有多硬。
杯里的酒尽了,元宵大概也熟了,熟了,也圆满了。圆满了,也还是凹凸不平,不平就是它的本性,本性难移嘛。所谓的圆满是什么呢?也许就在水火之间。
下得了口了。
但那心仍旧是硬的,没有熟到底。大概是食材本身的问题吧,我如是道,我已经尽心了。南方人学吃北方菜,还得从长计议,这不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这不也是一个关于吃的故事吗?
腊肉西兰花
夜里做菜,腊肉西兰花。
虽说是炒,但是此菜对水的要求是极高的。因而,我便有了时机等候水沸。看它如何将外部的力转化为内部的奇遇。看它如何从心中涌起一股敬意,垂直上升,充满热忱地把绿色稳稳托住。因而它又是柔情的,纯洁的。这些半透明的卵,春池之鸣从树的低处爬上来,绿,从鸣声开始的地方爬上来。春来自风,零雨其濛。遂想起傍晚归家路上,风扬起我的头发,然而露在外面的手已经不感到冷了。
融化,然后生发。
锅里的水热了,我将双手浸在蒸汽里,想着,这样就可以让手醒过来。用醒过来的双手趁热去唤醒世界。在这里,不到十平方米的厨房,事无巨细的小世界,赋予它们第二次生命。
刹那生念:大好的生活都被我们枉费了。
漫不经心是你的罪状,傲慢是你的罪状。
烧豆腐
大刀阔斧可以做出大气的饭菜,但不能用在空的地方,要用在生活的琐碎之处才显出一种张力。我时而细致入微,时而激情四射;时而凝聚,时而喷薄欲出;时而体贴这些锅碗瓢盆、瓜果时蔬,时而拿它们当个玩笑;时而聆听它们的旋律,时而感受它们的节奏;那音律时而悠扬婉转,时而荡气回肠,哀转久绝。
这是我的克制与狂妄。
一碗烧豆腐下肚,胸腹间产生一种灼烧感。灼烧即净化。
这碗烧豆腐也是偶然得之,像过去那样,我只是想做豆腐,而不会具体构想要做什么豆腐。我享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以及做菜时的一种游历的心境,让我更能在专注于当下的同时,心游万物,而不必按部就班,精打细算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是人类的幻觉,真理的曲线更富于美感和活力。人生亦如此。太实太直未免患得患失。
手里刚好有小白菜,火锅底料,八角,香菜,加上摧枯拉朽的想象,事儿碰巧就这样成了。毛姆曾写过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
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为了使灵魂更具活性,一个人每天也要创造一点儿新的东西。
笋与虔诚
超市里已经有笋卖了。
在北京,平民百姓所能采购的食材虽说不算丰盛,但有一點是好的,有时令。
元宵节,菜市里有元宵;春天有笋,春笋、冬笋皆备;秋天有板栗;冬天来了,该囤大葱了,大葱就一捆一捆地堆在超市门口,颇解人意。就像这里的四季,比南方总是更分明一些。其余的菜几乎一年四季都在那里,老熟人了。以至于只要你告诉我店铺里都卖了些什么菜,我就知道这是在哪里。每一个货架都填得实实在在,你能看到不管怎么实在,总还会有一个间歇,一个空白,虚席以待。想来也不真是铁板一块,它有可爱玲珑的包容心,有自己的乐感,这些季节的赤子,如同飞鸟赋予天空以精致的旋律。也就是说,一个诗人不可能是纯粹的诗人,他还必须同时是一位教师,一名商人,或是官员。
我仍旧有模有样地练习做菜,好做好吃,好聚好散,善始善终,以此作为与世情和自然亲近的一种方式。
不断地尝试对不同食材甚至调味料的把控力和想象力,练习刚与柔,快与慢,动与静,轻与重的相辅相成。对食材敞开亦是对世界敞开的一种方式。一部食物的进化史即人类文明进化史,对食材驯化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人类文明。
每做好一道菜,心中怀着对至上造物的感念,回想它从准备到完全生成的整个过程,像感知生命那样去感知它的存在。它的第一次生命是造物者赐予的,而又在我们的劳作中重获新生,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存在,我们创造食物,也创造着我们自身,这是与自然直接对话的途径。我把它们都记录下来。
对事物秉持虔敬之心,并在那里凝聚起你此刻的所有爱与心力。菜品自然就成了你自然力量的投射,从造物者之鬼斧神工到人创制之巧夺天工。你守持了那心中的静,在创造性的运动中,你忘我,欢喜,度苦,生慈悲心。我能感知到,这是我本性使然,从我记事起,我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探索,人化自然,自然化人。
驾柚子米糖而归
柚子是两天前买的,还如当初那么饱满,御风如鸟羽,善化如鱼鳞。
我每天吃一点儿,每天可以谛听它与时间的谈判。这种谈判使我焦灼,然而它是自在的。就像面对苏格拉底将逝的生命,他的门徒哀伤不已,而他自己是从容的一样。它此刻发出千年前的一种声音: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哪个好,只有神知道。
天气干燥,裸露风中的部分变得坚硬,就像挨过烈日的老道的谷粒。我仔细剥下一瓣,果实一粒紧挨着一粒,像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它们全活了,在我眼底攒动,有了自己的生命,我只能通过它的运动感觉它微微的呼吸。而每一个单独的生命又作为这整個族群精致秩序的一分子,紧凑地完成自然赋予的使命。
我把眼睛告诉我的同样告诉你们,它们每一粒都是不一样的,它们也有它们的“根”,白色的,如银针,凭借它行走,也凭借它飞行;用它汲取,也用它释放。生命的不二法门。
那么,也许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脊骨,我们找的恰好就是这个东西,踏踏实实,按图索骥。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其实连每片树叶的每一条脉络都是各有千秋的。就是这些独立个体,交会在一起又构成了更大的独特个体。展开柚子瓣中的一粒果肉,越着魔地看,它越不像是所谓“长”出来的,长,太寡淡,太生疏了。那样一个惊人的创造,竟像是天地萃出来或者炼出来的。到这里,我几乎快要惊呼“大哉乾元”了。
最近喜欢吃柚子,而且单爱吃白柚,寂寞如雪,粒粒分明。我去超市买的时候看到柚子上写着“琯溪蜜柚”,那不是我的小学校歌里唱的吗?如今我记得的唯一一句“琯溪蜜柚香”……这样说来,那它和米的结便解开了。“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爷爷奶奶一天天老去,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心扑在庄稼地里,如今,家里种的就只有稻子和柚子。稻子种在屋的西边,柚子种在东边,日出,日落……同一片大地上同一个太阳,恒久如新;同一棵柚子树,同一片稻田,不变应万变。它们没有辜负过谁,也不会多给谁一点儿,只是自己长自己的,应运而生。我们呢,到时候了就摘下来,品尝它,同时品尝着造物者在这片土地留下的痕迹。一年中的雨水,日照,霜天,虫害,一切只是偶然,而果实是必然的。时间秉持其神圣的法则,人类守护其内心的法则。
一切都是关乎我生命的产生,食物酿造的记忆。“粒粒皆辛苦”,苦的是农人,苦的亦是天地。想起奶奶过去常责怪我吃零食不吃饭,说“你硬是把它当饭吃哇”,我想,倘若我吃的是白柚子呢?柚子,米;米,柚子;要是我真能当饭吃,它也就是饭了。
米与柚子粒,以及世上一切的鬼斧神工,完满的果实中容纳的是多么无穷无尽的变与永恒啊。它如同一个大的剧场,世界藏身在这里,天与地,万物与我。过去坐火车的时候,身边坐着一个小女孩在吃柚子,她称之为吃糖。看,米连接了柚子,柚子又和糖联系起来,在生存之上又有了精神,不是吗?本来,生存与精神就是不可分的,就像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叫作“柚子米糖”的东西,有些不同于我们吃的“煎饼果子”“玉带虾仁”“油炸花生米”。
我又好奇它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它们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命运。《江湖行》唱得好:“快也是万水和千山,慢也是千山和万水,沿着一条乡村到城市的路,看到一片光明和飞扬的土。”但是,也许它对何为“无常”知道得比我更透彻,因为过去它完全循着自然的轨迹,生长荣枯,比人类规矩。来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命运,那么此前和此后呢?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想到这里,我不自觉地拿起窗台上一个小的空酒瓶子,又轻轻地一粒一粒地掰下柚子的果肉,把它们装到里面去。正当我专心之时,听到一个声音这样说:
“因为世界不断地创造他们,如同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地创造世界一样。”
烹饪的乐趣从大油大盐,大手大脚,化为一种静谧的,悄悄进行的,每天的祈祷。
我认识一些很会熬粥和煮汤的人。那些独居者从万物中找寻那极具承载力和包容性的事物,遍尝而不至于厌倦。等待,仿若遥远的启示。在烹饪中熟谙这种等待,熬,苦熬出甜美,这是她告诉我的,走一步,再走一步,而非走一步看一步。一改以往紧锣密鼓的参与感,留给事物自行完成的时间,哪怕是漫长的,它和我一样需要那样的独处,让火候和时间去完成它。我学着与它建立起这样的平等关系,不密切,不擅作主张又能遥相呼应。如此,杂感杂感,而已而已。
责任编辑 刘淑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