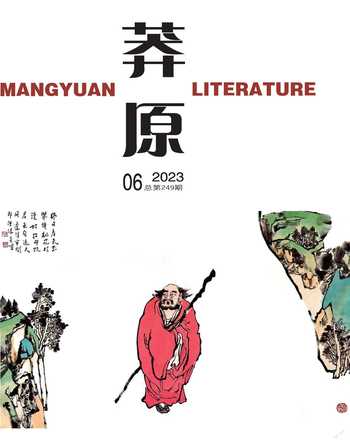大地上的声音
2023-11-08叶剑秀
叶剑秀
一
自小对声音敏感好奇,喜欢琢磨各种声音,但凡哪里有点异动,都会做出下意识的反应。譬如——咯噔咯噔的脚步声从门前走过,就知道是老村长深夜巡街,他的脚跟稳,踏出的声音扎实厚重;哗啦啦一阵儿自行车驶过的声音,一准是村里起早赶往县城打工的女人;一声哀号夹杂着一声怒吼,便是张家二小子和媳妇又打架了……
大人们夸我耳聪心慧,便越发痴迷于捕捉和揣摩声音。这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即便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所以一年四季要靠午休来补觉,要不下午就蔫儿吧唧无精打采。遇到出差或在陌生地方过夜,无论是城市的喧哗躁动,还是山里的风动溪鸣,必然是彻夜难眠。
然而,猝不及防地,我对大地上的声音突然失聪了。
我对各种声音到了痴迷的程度,常神经兮兮地独坐一处,暗自发问:大地上为什么会有各种奇妙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大地深处、还是高远苍穹?它们为什么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它们表达着什么?倾诉着什么?
越想越复杂,越想越离奇,把我折腾得近乎抑郁。书上说生命存活的三大要素为阳光、空气、水分,我总觉得也离不开声音。声音是生命律动的音符,甚至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假若万籁俱寂,生命可能会在凝固中枯萎窒息,便是一息尚存,又何以寄托?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
我对大地上的声音开始重新认识,似乎不弄清声音存在的真谛和意义,便辜负了上天赋予我的神圣责任和使命。
二
村庄依附着大地,大地托举着村庄,人们依偎着大地的怀抱和村庄襁褓,大地的声音鼓动着村庄的气息,灵动着村庄的气象,声音的气味、颜色、韵律,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漫长日子的希冀和守望。
追溯声音的经往和演绎,是件很有情趣的事。
老王家百岁的老太太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宽宅大院里寂落无声。大夫摇摇头,说老人熟透了……家人就听到了时间之镰磨刀霍霍,知道又一茬生命到了收获的季节。殡葬的仪式甚是隆重,素衣孝身,哀乐阵阵,哭声高高低低,有恋恋不舍的无奈,却没有多少悲恸。不同的声音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追思着老人的前世今生,也好像在庆祝老人辞世劳碌,荣归天城。
大地也在发声,风吹草木,放声高歌,顽石点头,旁敲侧击,汇成一部交响乐,铺成人间通往天堂的路,全村的人簇拥着逝者的棺木,把她送到祖坟里,让她得其所在,入土为安。一季庄稼成熟了,该为下一季庄稼腾地儿了。
规律性的合唱是季节的标志,也是农时的启动和更替。一声春雷响过,松动了冰封一冬的大地,万物仿若受到催促和鼓动,睁开了惺忪的睡眼——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新春的声音,给大地和村庄送来了又一个美好的开端。
老李家大门上的喜字还没褪色,欢快的唢呐声还在院子里萦绕,好事就脚跟脚来了。婚房里艰难的呻唤过后,咔嚓一声,接生婆剪断了婴儿的脐带,稚嫩的哇哇啼哭声飞出门楣屋檐,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村里人便知道老李家添了新丁。于是,祝贺声、道喜声盈满宅院,喜乐奏起,杯盏交错,一年前迎娶的喜悦接续为添丁增口的欢庆。
天高地阔,四时吉祥。季节的轮回中,这家添一个,那家生一口,无论男丁女娃,只要这声音延续不断,村子就永远香火兴旺。
此起彼伏的蛙叫和连绵不断的蝉鸣,是村子里每年规定的演奏节目,把季节衔接得天衣无缝,日子无论干涩与温润,耕耘和农事都显得那么的紧凑和流畅,仿佛人世间的光阴总是那么的通达美好。
不和谐的音符也是有的。老天宁静温顺的表情后面,掩藏着另一副面孔,不定哪天就发了脾气,甚至凶悍暴戾,令人恐惧和心惊。一声炸雷,串通发癫的狂风,借助雷电的闪光,挾来倾盆大雨,无情摧残大地和村庄。惨叫声、奔跑声、呼天唤地的哀嚎声,怪异的声音记录了人间的灾难。
然而,天道有常,一声鸡啼,唤醒了大地和村庄。草木依然茂盛,五谷依然丰登,村里的孩子们依然粗枝大叶地疯长。
三
有一种声音,裹着几多乡愁,交织着人间悲欢的情结,难以取舍和褒贬。
传统的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一年一度的团圆,少不了烘托欢乐气氛来庆贺。燃放爆竹,是延续千百年的民俗。可这些年禁放了,就少了浓厚的年味,但过年的声音是掩盖不住的,不但掩盖不住,好像还多了一些,浓烈了一些。
过年的声音,是有滋有味的。时令进入小年以后,村庄沸腾起来,人们开始忙年了。
“二十三,发面火烧夹糖瓜儿;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屁股扭一扭……”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大年从小年开始。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是刺刺啦啦的油煎声,火烧馍出锅了,和糖瓜一起供在灶王老两口像前。火烧馍是他们上天路上的干粮;糖瓜要粘住他们的嘴,防着他们到天庭胡言乱语。
二十四,到处都是扫帚的声音,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地出门,寄托了人们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扫尘既有驱除病疫、祈求新年安康的意思,也有除“陈”(尘)布新的情感寄托。
二十五,磨豆腐,轰隆隆的石磨声中,白花花的豆浆流出来,被人们做成白花花的豆腐。“腐”“福”同音,过年吃豆腐,来年更幸福。
二十六,割年肉,杀猪是过年的重头大戏。路旁或河边支起一口大锅,下面是熊熊燃烧的柴草,锅里是翻滚冒泡的开水,养了一年的肥猪驱赶过来,那猪知道自己大限已到,犟着身子不肯往前走,可终究抵不过几个壮汉,被拉过来摁在案台上。那猪绝望了,挺着脖子拼了一辈子的气力啊。只见专业的屠夫手起刀落,猪脖子那里喷出一股热血,四只蹄子蹬了一会儿,咽下最后一口气息,生命终止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猪叫声是惨烈绝望的,是一头肥猪告别世界的呐喊。可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却好像为人们增加了节日的欢乐。生为猪命,供人享用,人们觉得这种声音很好听,听到这声音就亢奋不已,这大概是生命不平等的法则,是上天早已给出的宿命。于是,人们心安理得地把一头猪变成猪肉,把猪肉拿回家,清洗、剁碎、煮炖、烹饪,色香味俱全的丰盛年饭便呈现出来。当人们大快朵颐的时候,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悲情场景,完全彻底地被忽略和遗忘了。一个生命的结束,满足了另一群生命的欲望需求。人们早已经忘了雷电狂风肆虐的时候,他们骂天骂地的诅咒,仿佛这一切合情合理,这或许就是大自然声音的哲理命题。
……
一头猪还没有吃完,就到了除夕夜。按照老习俗,除夕夜是要安静的,怕的是谁口无遮拦,说出了不吉利的话,惹恼了哪路神仙。现下不一样了,每家的电视里都播放着“春晚”,台上的人疯子一样胡言乱语,台下的人傻子一样大笑不已。但这些声音好像不是声音,反倒衬托了年夜的静。
到了大年初一,人们就放肆了,互相串门,互相拜年,高喉咙大嗓子地说着吉祥话,也不管有用没用,都说了,都收了,每一只耳朵里都装满了祝福,慢慢地供一年享受。
四
村庄是人类的家园,哺育着相互依偎的生灵,丰盈着生命的厚度,不断诞生着梦想和希望。
村庄大多时候是安然的模样,偶有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便生出了纠结的疼痛。
乡下人进城了,看到城里的高楼大厦、广场阔路,回到村里,便想比葫芦画瓢仿着城里的模样改变乡村。拆迁、铺路,绿化、整合。铲车繁忙,在乡村盖起一栋栋楼房;推土机轰鸣,一步步把乡村推向城市化进程。如今的村庄一天天在改变,仿佛逐渐和城市拉近了距离,一下子变得新潮和时尚起来。
热烈壮阔的声音深处,一声声沉闷的叹息不绝于耳。乡村开始与土地剥离,仿若能听到断裂的声响。一座座新房盖起来了,可一个个乡下人却离开土地走进了城里,乡村成了空壳。能走的走了,该回来时也如匆匆过客。老人、儿童和一些走不出去的人,散落在村庄的皱褶里,无奈地守着一个老的传说和新的期盼。距离很远,过去的可忆而不可触碰;将来的可望而不可企及。好在还有一根线,把乡下的失落和城里的欢乐连在一起,也能听见,也能看见。听着听着就泣不成声了,看着看着就泪眼模糊了,老人的眼泪苍凉浑浊,孩子们的呼唤奶声奶气,维系着世间的温暖亲情。
有了新的居家环境,乡村看似舒适安逸了,但赖以生存的土地一遍一遍地流转后,正在被一片片地圈走,然后惨遭遗弃,变得荒芜。狗尾巴草是结不出丰硕果实的,失去土地,乡村就失掉了古老的尊严。乡村变成华而不实的空巢,往日温馨的人间烟火荡然无存,新房舍、新环境,谁来呵护这些弱势群体的心灵?谁来关爱老人孩子?谁来守护他们生存的家园?
土地的叹息声,黯然漂浮,也显得苍白无力……
五
突然有一天,土地发出希望和力量的声音,这声音飽满丰盈,和谐悠扬,充溢乡村的时空——乡下人把城里的钱带了回来,开始重铸乡村的灵魂。
乡村的学校坐落在一面山坡上,十几名朴素的乡村教师,带着百十个孩子,像极了老母鸡带着一群雏鸡。校园,曾经是十几间土坯草房,水井旁的槐树上挂着一节铁轨;后来变成砖瓦结构的教室,铁轨换成了铜钟;现在是高耸矗立的教学楼,铜钟也换成了电铃。不管怎么变化,校园的声音都是清脆明亮的。当鸟儿唤醒村庄的时候,早晨的霞辉铺满校园,朗朗的读书声响彻乡村,在田野上流动,在天空中回旋。这声音带着村庄的希冀和梦想,好像当年那节铁轨活过来了,一寸一寸连接着外面美好的世界。
河岸的柳树冒出嫩芽,唤来了村童的脚步,风一样到处乱窜,在嫩黄和浅绿中,折柳弄笛,长短不一,柳笛声声,高低相间,春天被吹醒了,天地明朗起来。
春光洒满村前的小河,河水清澈透亮。妩媚的村姑端着大盆小筐的衣物,纷纷走向河边,择一块光滑的石头,抖开大包小包,扯出几件衣服,在涓涓的河水里摆动浣洗。叽叽喳喳的家长里短停不下来,抡起的棒槌有节奏地捶打,用声音的力量,敲开春天的希望之门。
夏日黄昏的余晖落在打麦场上,身旁站立着高低不同的布袋子,装满收获的喜悦。一张张褶皱的脸,写满饱经风霜的沧桑,轻轻掸掉身上的浮尘,守着麦秸垛子吧嗒起烟袋,眯起的老眼在青烟缭绕间放射着悠然自得的光亮。一群汉子赤露着壮硕的上身,吼着粗犷浑厚的梆子腔,直奔河里洗澡去了。
秋禾正旺的季节,庄稼长到齐胸深,夜里拔节的声音极具诱惑力。一个雨后的夜里,淡淡的月光像稀薄的轻纱,我约上几个伙伴,躲进茂密的玉米地,屏住呼吸,果然听到了咯吱咯吱的声响——一夜间,玉米棵子疯长了四指高。庄稼拔节的声音令人亢奋,正是这种声音,催发着庄稼的青绿和繁茂,饱满了农人和村庄的殷实与富足。
村庄极富乐感的声音,是一首首流动的歌,现代的节拍和着古老的元素,赓续着二十四节气的韵律。这生动空灵的声音被时代的记忆收录,留给未来的人们深切怀念。
村庄的声音在时光流转中开始丰富。有的消失多年,却似乎并没走远;有的应运而生,却好像似曾相识。
村庄里电喇叭的叫卖声天天都有,忽而飘过,时而停下,打破了难得的清静,令人烦躁不安。留守的几位老人,凑在阳光温暖的花园旁聊天,忽然被这不协调的叫卖声骚扰,郁郁地瞥去几束厌烦的目光,抬手挥动着拐杖无声驱离。但第二天叫卖声照常来招揽生意,乡村的宁静便被异常的喧嚣侵扰不止。
晚阳落幕,街灯亮起来。村庄东边的广场上,秧歌的锣鼓早早敲起来,西边广场的舞曲也不甘其后,村庄恍若城市般繁华。充满活力的秧歌队伍,老少皆宜的广场舞,人影憧憧,欢声雷动。戏剧、歌曲的爱好者加入了热闹的行列,南腔北调地吼起来。一天天过去,几张熟悉的老脸几乎没有更换,也蹦跳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本来就没有观众的自娱自乐,在星光灿烂的村庄里惨淡经营,落叶枯黄的季节里看过去,极似干涸的池塘里风摆残荷,令人心酸叹息。
繁华背后的落寞,留给大地无限的思索和疑问。各种曼妙的声音依然存在,且不断丰富和更新,可没有观众的捧场和喝彩,缺失的或许是大地的接受和欣赏,没有观众的百姓舞台,终归要冷淡萧索地收场。
怀念大自然的声音,接纳华丽悦动的音符,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六
乡村的慢时光,是在大地深处氤氲出的声音里度过的。品赏大地的声音,有味道、有温度、有情怀、有意蕴。
晨曦微露,不知哪家的雄鸡一声啼叫,引来同伴的附和,把暗淡的天光叫亮了。门户洞开,成群的鸡鸭鹅扑棱棱飞出了一个响亮的晴日,人们开启了一天的忙碌。看门护院的狗,不顾夜晚尽职尽责的疲倦,兴致十足地吠几声,仿佛是弥合鸡犬相闻的完整画面,一幅优美的乡村图画重复显现。
狗们过去给人类看家护院,何时成为人们的宠物,已无从考究。不知是狗的心性变了,还是人们故作矫情,冠以爱心的虚名,把狗无节制地娇养,乖啊宝地叫着,穿衣戴帽伺候着,狗也丢了本能和职责,发出嗲声嗲气的声音,再也没有了勇敢和野性,家里进了贼都不敢唧哝一声。这种荒诞的现象,混乱了大自然的法则,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观念。哦,各有所爱,留给时间去评判和矫正吧。
牛依旧是大地的忠臣,更是乡下人的依靠。劳作了一天,暮归的老牛自己能踏着夕阳的余晖,寻到回家的路。村口哞的一声,透着如释重负的舒松,叫出了耕耘和回报的喜悦,似乎自豪地告诉村庄,又是一天完美的收工。
在不出工的休闲时光里,一头头健壮的牛俯卧在树荫或暖阳里,姿态憨厚可爱。慢悠悠地咀嚼着岁月,嘴角泛着白沫,脖颈上的铃铛叮当响,反刍着人世悲欢的悠远和绵长。
牛叫的声音是个谜,大多时候都是温柔驯顺的,愤怒的时候,也只是喘几口粗气,受了委屈也只在喉管里发出几声呼噜,眼里默默流几滴眼泪。很奇怪体身庞大的牛为何叫声低哑沉闷?是命运的束缚?还是岁月的压抑?甚或是低调内敛,不事张扬?
村庄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声音,乡下人称作叫魂儿。体弱的孩童受到惊吓或刺激,恹恹的像患上了疾病,浑身绵软无力,闭目不醒。上点岁数的老者搭眼一看就知道孩子是丢了魂儿,于是赶紧去给孩子叫魂儿。母亲或奶奶抱起孩子,用手做着巫师的动作,伸手一抓,回手抚身,好像要把丢了的魂抓回来;也有手里操着木棍,敲打桌椅或床帮,嘴里不停地呼叫——回来了,回来吧……反复几个来回,奇迹就出现了,魂儿回归,孩子慢慢睁开眼睛,渐渐恢复元气,不消一日,就像没事人一样活蹦乱跳了。这种诡异的现象,在过去的乡村里是很盛行、很常见的,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那些真实而又奇特的记忆,至今仍令人疑惑不解。
在乡村出生或生活过的人,对一种呼唤的声音终生难忘。懵懂的年纪,孩童在村里玩耍,上樹掏鸟,下河摸鱼,或在田野里追兔子、捉蚂蚱,往往会忘了吃饭的时间,母亲就在家门口或村头呼叫。这种声音是母爱的召唤,带着焦虑和不安,带着埋怨和责骂,一声声或悠长或急促,在旷野里嗡声回旋,直到看见孩子平安无恙地归家。这声音带着母爱的温度,像胎记一样伴随孩子们终生。
如今乡村的格局不断变化,更新着蓬勃的气象。打工的游子背起行囊离乡那一刻,母亲的脸上写满了殷殷的牵挂,嘱咐的声音絮叨温婉,叮咛的话语萦萦绕耳,村口挥挥手,母亲的心就伴着儿女一起远行了。
村口耸立着一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树梢上哗哗啦啦舞动的声音,在光阴流逝里迎来送往,记载着每一个村民的悲欢离合。这声音为游子指明回家的方向,迷失的时候能寻到心灵皈依的家园。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失魂落魄,家乡随时都敞开怀抱,迎接归家的游子,把漂泊的灵魂召回故土。
大地上的声音筑就心灵的故园,是落叶归根的最终栖息地。
责任编辑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