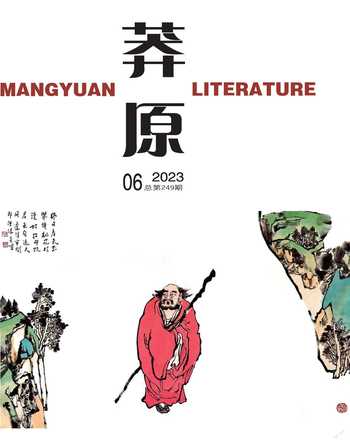行走在黄河岸边
2023-11-08金光
金光
湖边老人
黄河水弯到这儿,被苍龙河汇入时一顶,形成了一个偌大的湖。冬天,有许多白天鹅在湖上栖息,引来很多人观赏;而在夏秋两季,却是孩子们的天堂。放学后割草的、放牛的、摸鱼的,一群一群的少年来到这儿,脱了衣服泥鳅般在湖水里玩耍,把苍龙湖闹腾得鸡飞狗跳。
早时候湖边没有路,来往的人就站在召公岛迎祥阁上往湖里看,一圈粗壮的毛白杨包裹着清水湖,靠岸的地方长着丛丛芦苇,或是有着厚叶子的蒲草,风一吹呼啦啦作响。贪玩的小家伙们就在草丛中扎猛子,有时候因为摸了一条黄河鲤鱼而相互追逐着,那活蹦乱跳的场面像是过电影。
仲夏的一天,暑热难耐,我驱车来到黄河边,将车停在召公岛下的公路上,走到湖边的白杨林漫步。芦苇和蒲叶已经长得很高了,不远处还有人工种植的莲花,几朵刚刚从水里探出头来的荷苞正随风摇曳。野鸭子和鸬鹚听到脚步声,纷纷从岸上跳进水里,弄出“扑通扑通”的声响。我知道打扰到它们了,很不好意思,就将脚步放轻了。
原以为能看到几个小家伙在湖里洗澡或玩耍,那样我会拍一些图片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可转了半圈儿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失望之际,在丁香花丛旁的长椅上坐下来,想小憩片刻,再继续沿着湖堤往前走。微风吹来,顿时清凉了。此时,杨树上掉下一只雏鸟,张着翅膀,挣扎着乱叫,显然落地时受了伤。遂上前捧起小鸟儿,检查了一下,并无大碍。我将它端在手掌上,动了动它的翅膀,它抖了抖身子,尖叫一声,展翅飞走了。
前面树荫下有两头牛在吃草,看我走来,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粗气,又低下头,伸着舌头,将嫩绿细草卷进嘴里,用牙齿咬紧后往上一揪,细草就吞咽了。
一位老者静静地坐在杨树下,应该是牛的主人。他看着牛,也看着我,却一言不发,摆弄着手中的一根长竹竿。我坐在他身旁,无话找话地问道:“放牛都拿鞭子或柳条儿,你咋拿根长竹竿啊?”
老者眉头一展,卖了个关子说:“照你这样说,我就不能拿竹竿啰?”
他这一反问,我竟无言以对了,就转移了话题:“记得往年这儿会有孩子们下水玩,今天怎么没看见?”
“你好久没有来这里了吧?十年了,再也没有孩子到湖里耍水了。”老人说着,挥动了一下他的竹竿。
“为什么?”
“我不允许。”
说这话时,他透出了一种倔强的表情。我有点不理解,孩子们到湖里玩耍是他们的天性,与一个老头儿有何关系,你说不允许就不允许了?
我半开玩笑说:“这你恐怕管不了吧?”
“管得了。”他把长竹竿往空中一提,“哪个不听话就打屁股。”
我终于明白了老人拿竹竿的用意,细细一想,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故事,便挪了挪屁股,向他靠近了,和他拉起家常。
老人姓秦,苍龙村村民。十多年前,他儿子已经上了高一,那年夏天和同学们到苍龙湖边打猪草,下湖游泳,溺水了。老人说,当时他儿子只是在湖边玩,并没有到湖中间游泳,但他们不知道苍龙河上游下了暴雨,河水上涨冲进湖里,将一个孩子从湖边往黄河冲去。他挣扎着,喊叫着,在水里不停地扑腾。老人的儿子稍有点水性,见状就去救人,结果拉到那位同学的时候,求生本能让落水者把他兒子死死地拽住,往水下按,他们都沉到了湖里。后来,他儿子拼着最后的力气,用肩膀托住同学,硬是将那同学顶到了岸边一棵小柳树上,他儿子却被洪水冲进湖心,淹死了。
老秦叙说的时候,阴沉着脸,竟然没有流眼泪,有的只是一声叹息。我知道这是他最伤心的事儿,陪着长叹一声,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允许孩子们来这个地方玩水了。
老秦的孩子是见义勇为。团县委和教育局联合下发了红头文件,表彰了他的儿子,他接到那个红头文件时,看也没看就把它放进了装着他儿子遗物的木箱里。
“被救的那个孩子咋样了?”我问。
“那孩子很有出息,上了大学,后来在一家科研所上班。”老秦说。
“了不起呀……”我又叹了一口气,“不过,可惜你家孩子了。”
老秦说,那个被救的孩子很懂得感恩,每次探家都来看望他,还要给他钱,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也就是从那以后,老秦常来湖边,心里呼唤着儿子,眼睛巡视着湖面,看见有孩子下湖玩水,就吆喝着赶他们上岸。后来,他年纪大了,干脆就养了两头牛,夏天的时候把牛赶到湖边放,为的是不让悲剧在这里重演。
他晃着手中的长竹竿,说:“这个竹竿三种用途,一是吆牛,二是看到有孩子往湖边来就拿它吓唬他们,三是真有人掉进了湖里,就用它捞人。”
我明白了,看着满面沧桑的老秦,看着他手中的竹竿,心里肃然起敬。
一只野鸭在湖里“呱呱呱”叫起来,许是碰见了天敌,引得一群野鸭惊恐地往远处飞去。两头老牛抬头看了看飞起的野鸭,调头往我们这边走来,停在了我们面前。
“走,回家喽。”老秦站起身,拿竹竿在牛背上轻轻敲了两下,赶着它们顺着湖边的小路往远处的村子走去。
我沿湖向停车的方向返回,禁不住又往湖里看了一眼,仿佛看见了一个少年正在湖中拉着挣扎的溺水者,那少年的面部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湖面上似有一声轻轻的叹息。
割草的女人
黄河岸边常有一片一片的滩涂。
每年汛期河水上涨便淹没了滩涂,到了八月以后水位下落,滩涂就裸露出来,人们会在这个空档期里,在滩涂上种些大豆或向日葵之类的作物。滩涂地是不需要施肥的,本就是黄河冲下来的淤泥,黑乎乎的,壮着呢。那些作物一旦种下去,正逢八月三伏天,出苗后疯长,到十月下旬成熟。种地人就去河滩上抢收,能收多少是多少。
我曾在河边捡过豆子。大豆成熟后,庄稼人用收割机收。可机器总不如人细心,常常是豆棵子的上半截儿被割走了,下半截留了四五寸长的茬子,上面结着稠稠的豆荚,留给我这样的闲人捡漏儿。我是带着妻子去看黄河的,黄汤一样的河水已经退到了河心,站在河沿上看了一会儿,就被捡豆荚的人吸引了,便和妻子一起,加入捡豆荚的队伍中。我们两个拿出小时候打猪草的劲头,一薅一把豆荚,不多久就装满了一大袋子。回到家,妻子坐在阳台上把豆荚剥了,上秤一称,竟有七斤多。
河滩上有很多野地,人们根本种不过来,任凭它自个儿荒去。野滩涂断断续续地在河湾处、陡崖下闲置着,由于泥土肥沃,很快便长出各种各样的杂草。我能认识的有夹拉毛、杂苇子、铁秆蒿、猪耳朵草、黏刺秧等。它们比庄稼长得快多了,几天不见就长得掩住人了;再几天不见,那草秆就由筷子粗细变成拇指粗细了。于是,各种鸟儿钻进去,连野兔也藏在里面,滩涂的野草地里便有许多动物的故事发生。
正是八月下旬,眼前这一长溜儿野地,野草足有七八尺高,风一吹“唰唰”作响,一群麻雀钻在草丛里,像我们小时候捉迷藏那样,飞来飞去又咋咋呼呼。我漫步在草地边的沙土路上,看着这一望无际的野草,仿佛置身于遥远的荒野之中。突然,草丛中冲出一只兔子,也许是晕了头,直接撞在了我的腿上。野兔愣了片刻,一折身紧跑两步,又停了下来,两只耳朵高高地竖起,像两根天线不停地在空中摇摆。我拍了下巴掌吓唬它,可兔子好像知道我拿它奈何不得,卧在那儿抽着鼻子不肯离开。我索性挽起袖子向它扑去,结果在腾起的一刹那间,兔子一抖身子便没了踪影。
这家伙分明是来戏弄我的。我自嘲地看着仍在抖动的草棵,摇了摇头。为了释放刚才的尴尬,我又跺了下脚,用手做了个喇叭形对着野兔跑过的草丛,可着嗓门吼叫起来:“喔喔喔——”声音在广袤的黄河滩上并没有传多远,就像一块小石头扔进大海里。
“居然还有人来这儿旅游。”我听到不远处的草丛中有女人的声音,愣了一下,寻着说话声过去看究竟。
大约走了五六十米,眼前豁然开朗,一位中年女人正拿着镰刀在割草。
看见我,女人住了手。她的身后,是一片已经被割光了草的空地,码放着一铺铺刚被她割倒的野草,其中的一铺草上,放着一壶水和一个录放机,录放机里正播放着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唱段。
“你不会是真的来河滩上旅游的吧?”女人半开玩笑地问道。
我随口說道:“如果这样也算旅游的话,我就是来旅游的。”
她哈哈大笑起来。
女人拿起水壶,问我要不要喝水。我摆了摆手,她自己喝了两口,又把水壶扔到了草铺上,准备继续割草。
“这么热的天,割这些杂草干啥?”我问。
“割草喂鱼呀。”女人说,好像我有些少见多怪。
我看了看她割下的那些草,有的软有的硬有的细有的粗,尤其是猪耳朵草和野向日葵,秆子都很粗壮,便不解地问:“鱼,能吃这样的草吗?”
女人拢了一下被汗水浸乱的头发,说:“咋不能,鱼啥草都吃。”
说实话,我见过猪马牛羊兔子吃草,从没见过鱼吃草,便问:“鱼不是吃鱼食吗?”
女人大笑起来:“那是鱼缸里养的,我们家要是养吃鱼食的鱼,那可养不起喽。”
然后又说:“你没听说过吗,草鱼草鱼,就是吃草的鱼。”
她说她家在旁边的土崖下挖了两个鱼塘,有五六亩大,春上放了两万多尾草鱼苗儿,每天光喂草就得几百斤。她和丈夫在农贸市场上开了个鱼店,每天早上在店里卖鱼,下午来黄河滩割草。她在这儿割,她丈夫负责往鱼塘运草、喂鱼,天天如此。
我看到她的手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手指似乎都变形了。
“这么粗的草秆子鱼能吃下去吗?”我指着地上的粗秆子问。
“再粗的秆子也能吃得了,别看鱼那么小,吃起草来比牛还厉害哩。”女人说。她怕我不信,就指着远处的一棵白杨树,“有时候我们来不及割草,就折些杨树枝子扔进鱼塘,它们不仅吃了叶子,连树枝也吃掉了。”
说实话,我只知道牛马嘴大牙尖,除了吃草以外还能吃一些藤子,从来不知道鱼也有这样的本事,它那么小的嘴居然可以将粗壮的草秆子吃掉。
女人怕我不相信,说一会儿她丈夫来拉草,可以去鱼塘里看看她说的话是不是骗人的。
说话间,一个男人开着三轮车三拐两拐来到了跟前。女人告诉他说,这人不信鱼能吃这么大的草。男人笑着说,那好办,一会儿跟着去看看就清楚了。
为了一睹鱼吃草的情景,我也帮他装草。三下五除二把车装满,男人又用绳子煞紧,开着三轮车让我跟着他往鱼塘去。
到了鱼塘,他松了绳子,抱起一捆杂草往塘里扔去。那草刚一落下,就有几百条大鱼从水面跃出,欢快地张嘴去逮去咬那些杂草。鱼是在水里吃的草,看不见它们是怎样吃的,但眼前的一切告诉我,那些鱼肯定能将这些草连叶儿带秆子吃下去,要不,那些粗壮的草秆子早就撑满了池塘。
“这些鱼都是吃野草生长的,没有激素,也没打什么药,需要的话可以放心买。”男人告诉我他在农贸市场的几排几号,如果需要鱼,他也可以送上门。说着,还给我递了张名片。
返回的时候,又经过女人割草的地方,看见她还在挥镰劳作,镰刀所到之处,一丛丛杂草纷纷倒下。在我的眼中,偌大的河滩上,她是那样的渺小,而在杂草面前,她又很高大,像个将军。
女人又停了下来,用手捶了下背,说:“看到了吧,我没骗你,鱼吃野草吃得美着呢。”
我点了点头。
“黄河滩地肥,野草长得太疯了,幸亏我养了那么多鱼,可以割了它喂鱼,要不然它就白长了。看来,大自然的一切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啊。”女人像在自言自语。
我心一震,突然意识到这句富有哲理的话,竟从一位割草养鱼的女人口里说出,便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我问她上过学没有,她的回答更让我吃惊。她说她当年读了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不景气,就和老公自己创业了。
我伸出大拇指,为她的勇敢点赞。末了又说:“这草不割也挺好的,它长在这儿环保。”
“这你就不懂了,十月份水位上涨,野草经水一泡就腐烂了,沤到明年天一热就发臭,污染环境哩。”
女人一板一眼地说,意思是她割草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儿。
天快黑了,我转身往回走,出了滩地,仍能听见女人录放机播放的《朝阳沟》唱段。
落 日
那次,二月河来了陕州,让我带他去古城寻找他儿时常骑的小铁人。我们先在北门的亭子前打听,有人说那铁人四十多年前就被移走了,移到了什么地方却说不清楚。
二月河告诉我,当时,陕州古城的北门是陕县公安局办公的地方,他的母亲就在公安局上班,他当时在宝轮寺塔那边的小学读书,每天放学时母亲还没有下班,他就骑在门口一排小铁人的肩膀上等母亲,他对那些小铁人的印象太深了。我打电话让文旅局的朋友帮着去寻找,便带二月河顺着一条小路往西边行走。
我们走到一处土崖边时,二月河停下了脚步,他凝望着面前的黄河,愣愣地站在那兒,好长时间不说话。我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便不去打扰他。良久,他转过身指着脚下的一处土凹告诉我,这地方叫羊角山,前面的河湾就是古时候有名的黄河太阳渡。
我问:“你对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小时候一定常在这儿玩吧?”
二月河的老家在河对岸的山西,解放初期随父母南下来到这里。当时这里还叫陕州,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说,星期天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羊角山的土坎上看太阳渡,来来往往的船挂着白帆在他的脚下穿梭。初春,当太阳渡上游的冰凌解封时,整个河道汹涌激荡,满河都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透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很壮观。这印象太深刻了,让他一辈子也忘不掉。后来他给自己起笔名时,第一个想到的是黄河解冰的情景,于是就叫了二月河这个名字。
如今,羊角山上的渡口旅馆已荡然无存,二月河小时候爱吃的崖畔酸枣也不见了踪影,他口中描述的千帆竞过的太阳渡,早已被一片黄灿灿的湿地所替代,湿地上长着齐整整的向日葵。有一群游客在看完黄河后,钻进向日葵地里自拍。我们看了一会儿嬉闹的游客,最后把目光聚焦在西边的落日上。
因为接近黄昏,一轮黄里透红的太阳,满身的光芒已不再,静静地挂在中条山的顶端;随着太阳光亮的减弱,两岸山坡逐渐变成了褐色,影影绰绰的;曲曲弯弯的黄河由上而下,一弯一弯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像一条红绸飘在那儿,煞是好看。我想起两句古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二月河好像不太感兴趣,看了一眼落日,接着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朋友在春秋路上的车马坑博物馆找到了小铁人,于是我们就驱车往那儿赶去。
之后,我对那次看到的落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恍惚总能联想到什么,却一直没能找到感觉。直到三年后的一个秋日,我再次来到羊角山时,看着远方的落日,猛然想到一件事,令我感到释怀。
我站立的地方,是一处塌方的陕州古城墙。太阳渡的对面,是与黄河平行的中条山;再顺着黄河往西看,夕阳下是隐隐约约的函谷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为了补充兵源,正在陕西省读书的八百青年学生踊跃报名,来到中条山上阻击日寇南侵,由于敌强我弱,这些被称为陕西“冷娃”的青年学生伤亡惨重,为了不当鬼子的俘虏,最后全部跳进滚滚黄河,谱写了中华青年为国捐躯的壮举。
惨烈的中条山战役,是国人永远的伤痛。如今,倭寇已除,国泰民安,那些曾经跳入滚滚黄河的“冷娃”们,得以含笑在九泉之下。眼下的河畔上,那一株株的金黄色葵花,不正是“冷娃”们的张张笑脸吗!
顺着黄河继续向上望去,函谷关,这座矗立两千多年的雄关,正隐藏在夕阳下的雾霭中,显得无比神秘。
很多人知道,函谷关是老子著《道德经》的地方,那里充满了神秘色彩。“紫气东来”本来是关令尹喜盼望老子心切,观天象时发现的一种吉祥预兆,可谁能想到两千多年后,自东而来的不是紫气,而是日寇进犯的阴气。
那是抗日战争后期,冈村宁次指挥数万日寇,翻越中条山,渡过黄河,向西进犯。我抗日军民拼死堵截,将日寇阻挡在函谷关以东。疯狂的日寇动用飞机大炮轰炸关楼,企图冲破关口,但英勇的抗日军民拼死抗击,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使侵略者始终不能突破半步,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扔下八百具尸体,退了回去。
函谷关,是侵略者的噩梦之地,从此日寇日落西山,为之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太阳在函谷关的方向慢慢往山后沉去,留下了一幅黛色的山影。我忽然从中悟了一些道理,莫不是那八百“冷娃”变成了天兵天将,让侵略者梦碎于此,让那面膏药旗从这里落下……我常常站在这高高的古城墙上,遥望函谷关的落日,仿佛看见那些“冷娃”们在灰褐色的山坡上放声大笑。
一对情侣嬉笑着从远处走来,他们的脚步停留在了我的身后。
女孩儿说:“看,落日多漂亮,我们站在这儿拍个落日背景照吧。”
男孩儿紧跨两步,打量了一下远处的落日,说:“我们下次上午过来拍朝阳,不拍落日,不吉利。”
女孩儿似乎明白了,点了点头。男孩儿伸出左手,握着空心拳头,似乎要把远处的太阳用手握住。
女孩儿说:“好,好,太好了,你就像夸父一样,把太阳捉住了。”
说着,举起手机,拍了一张图片。
小情侣嘻嘻哈哈地走了,我却对他们刚才说的话充满了敬意。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在这儿看落日,有年长的,也有青年人。我不知道他们从落日中看出了什么名堂,但相信多数人能悟出那一层深意。有时候,隐约可以听到他们指着落日在争吵,真希望他们争吵的内容与八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有关。
责任编辑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