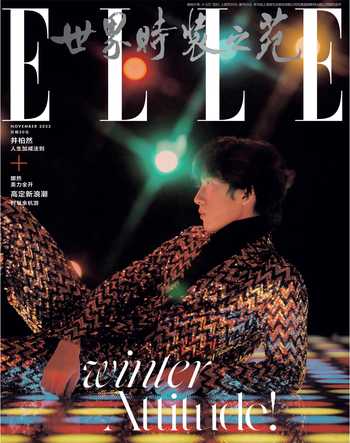从“厌女”到“厌男”,两性观念升级了吗?
2023-11-06于是
于是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露西· 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在《我的爱,向你》(J'aime à toi)中指出,法语和很多语言中存在固有的主客体混淆问题,比如“他”(il)和“他们”(ils)总是凌驾于“她”(elle)和“她们”(elles)之上,不管涉及的人群中有多少男女,都必须用“他们”加以统称。
语言是思想的中介,在tag模式泛滥的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偏爱简短发言,迅速站队,而这恰恰是不利于思想进步的言语方式。伊利格瑞提出了关键问题:当两性意识进入新阶段,女性主义者要颠覆男权社会时,有没有一整套可以正确使用的语汇?如果没有,怎么说、怎么争论都可能导致误解。
比如“厌”系表态——
厌女的完整表述应该是“男权体制下的厌女症状”。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厌男,完整表述应该是厌“厌女之男权体制”,厌恶之余,还有遗憾、绝望,乃至放弃。男性主义者所说的厌男,完整表述应该是“男性遭受(由厌女文化导致的)歧视现象”。因此,用“厌男”来调侃没问题,但用来和“厌女”对等可就大错特错了!
从波伏娃的开山之作《第二性》开始,研究两性关系的学者们都会从生物学和历史文化两个层面分析两性处境的本质,半个多世纪后,随着厌男情绪的高涨,男性学者也用同样的逻辑反思男性气概的由来,比如《生而为男?》( Are Men Arimals? )从睾酮素出发,考察了美国、墨西哥和中国男性(但记录上海相亲角的那段略显肤浅,和主旨关系不大),得出结论:男人不仅要成为抑制本性的公民,还要作为人类尤其是女性的头领、乃至神化的形象存在,这无疑也是对男性人性的一种扭曲。换言之,男权社会是对两性的共同扭曲。虽然在女性高喊厌男的当下,尚无男性公知主动现身讲述男性也可能厌男,但这是早晚的事。正如文学评论家哈罗德· 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言:尽管“厌男”这个词在文学作品中几乎是闻所未闻,但不难发现隐含着的、乃至昭然若揭的厌男倾向,比如莎士比亚最爱写女性下嫁,而男性总是那么自恋,不值得信任。厌男从未体制化,更像是弥漫在两性世界里的一种消极情绪。回顾女性主义发展史,你会发现半个世纪前的厌男言论更极端。
1967年,激进女权主义者瓦莱丽· 索拉纳斯(Valerie Jean Solanas)在美国出版了《人渣宣言》( SCUM Manifesto),也可意译为“消灭男性协会宣言”,主张男性败坏了世界,包括制造战争,应该由女性来加以修正。这本黑色反讽之作起初并未受到关注,直到索拉纳斯朝安迪· 沃霍尔(Andy Warhol)开了三枪,世界才注意到她这番乌托邦言论——她构想了一个没有男人、没有金钱、没有疾病和死亡的女性乌托邦。索拉纳斯彻底贬抑了男性的生物本质和文化倾向,后来得到了不少批判。这样敌视男性的言论既不能改变女性的现实处境,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贝尔· 胡克斯(Bell Hooks)就明确指出,这种妖魔化会导致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必要的裂缝。
当今女性主义者们不会再走这样的极端,哪怕依然保持愤怒。我们都在持续学习中,因为女性主义始終在进行时态,现在正是关键阶段,因为这一代人的观念势必影响到未来的两性处境,乃至文明的走向。女性主义者们还要面对和男性共处的问题:人口减少,未来不妙。伊利格瑞指出,两性必须承认性别差异,才能共建未来。从语法上,她建议把“我爱你”(Je t'aime)改写成“我的爱,向你”(J'aime à toi)。增加一个介词,意味着“我不会通过以你为中心的方式,把你作为对象加以获取。我更应当以我自己为中心,从而借助返回‘我来保持‘向你”。并借此强调两性关系不该成为权力关系,避免爱情和婚姻的权力资本化,更不用说暴力化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23年春夏出版的《我,厌男》和《她厌男,她是我女友》,两本书都是本国的现象级畅销书,译介到中国时都强调了“厌男”标签。有趣的是,这两本写的都是身在两性关系中的女性主义者的坚定厌男态度。她们都在反讽,都想以此唤起女性主义觉醒。也都指向了一种“厌而不弃”的理性。
“愤怒可以成为改变的跳板”
——闵智炯
1986年出生,韩国畅销作家,电影、电视编剧。2015年,以《 朝鲜公务员:吴希吉传》 在“韩国故事大赛”获奖。2019年,为电视剧《 Leverage:诈骗操作团》 撰写剧本。2016年,受到“江南站杀人事件”冲击,开始研究女性主义,并担任韩国电影性别平等中心的性暴力预防讲师。
ELLE: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研究女性主义的?
闵智炯:2016年,韩国发生了“江南站杀人事件”:在首尔江南站附近的公共卫生间内,一名男性在等待一位女性进入卫生间后袭击并杀害了她。犯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无视女性,认为女性会干扰自己。案发时也有男性进入卫生间,但是犯人没有对其进行攻击。然而当时的警察没有将此案件定性为“憎恶女性犯罪”。由于这起事件,韩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性犯罪问题引起了女性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用“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和“因为是女性所以死了”等词句来表达哀悼。还有一部分男性坚称“不存在对女性的憎恶和性别歧视”。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存在认知差异,韩国女权主义意识开始强化,也引发了“性别冲突”。
ELLE:这本书为什么要选用男性视角写作?为此,你有没有采访过男性朋友,或索性以自己的男友为原型?
闵智炯:2016年起,韩国涌现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等多部优秀的女性主义小说,其中不少是作者用亲身经历来替女性发声的,也充满了对男权社会强加的异性恋恋爱和婚姻(特别是不平等的婚姻生活)的抗议之声。我在确认自己的女性主义者这一身份后,还是选择了异性恋。虽然至今我还为此有负罪感,但同时也考虑过:难道“放弃”就是正解吗?
我想写一本不太被关注的“女性主义者与异性恋爱”的小说。我脑海中浮现出早年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以男性观察者视角描述了一位令人费解但又具有吸引力的女性,这种叙述方式可以巧妙地表现出男性在面对突然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前女友时所感受到的困惑。让我看到当代男女眼中的世界是有多么的不同!相比女性直接发声,无知的男性内心的郁闷还会产生黑色幽默的效果。
我的前男友们为此书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写这本书时,我也与多位男性朋友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其中有些人对女性主义有一定了解和共鸣,也有一些人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ELLE:你觉得“厌男”的反面是“厌女”吗?有些人认为这类标签会导致两性对立,你对此有何看法?
闵智炯:我更加感兴趣的是“厌女”,所以对“厌男”这一术语的来源并没有深刻的想法和调研。在韩国,随着“厌女”这个词变成了大众用语,一些主张“反向歧视”的男性以及抗议性差别的女性开始主张用“厌男”这个表述。在江南站杀人事件后,当“Feminism Reboot(重启女权主义)”开始在年轻女性中产生重大影响时,名为“镜子效应”的“策略”在韩国网络上流传—— 女性将她们过去经历的极端“厌女”情境直接用到男性身上,以强调性别不平等问题。首次听到这些话语的男性似乎非常愤怒,措手不及,开始主张自己受到了“厌男”的对待。
众所周知,“厌女”不是简单的对女性个体的喜爱或厌恶的问题。特别是在韩国这种曾是男权至上文化盛行的社会,女性仍然面临着性差别、性暴力、性别对象化等问题。目前,韩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如果不努力生存可能会被社会淘汰。但是,男性的困境不是由女性造成的。韩国女性也面临生存问题,但还要面对性差别、性暴力,处境更加恶劣,比男性付出的也更多。至少在韩国,特别是20到30岁之间男女对立问题的加剧,更多的责任应该落在那些创造和容忍了这种社会架构的政治家、特权阶层和老一辈人的身上,但他们反而把青年男性的愤怒转嫁到女性身上,想做出“因为女性剥夺了男性的机会才使他们生活困难”的假象。
ELLE:写这本书的过程里,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闵智炯: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这本书是否能被读者正确地理解,以及,我会不会受到攻击。韩版的书名直译为《我的疯狂女权主义女友》,乍一眼看去似乎是批判女性主义的。书出版后,我的样貌和名字被公开,不少网络水军对我进行过人身攻击。两年后被改编成漫画后,在人气颇高的男性交流社区里,还有上千条恶性留言,以至于我不得不报警处理。所有针对外貌的侮辱及性骚扰、无差别的语言暴力和诽谤,都只是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这是非常荒谬又遗憾的事。
ELLE:你如何处理两性间的差异和爱情的矛盾之处?厌女和厌男的人类有可能得到完美的爱情、性爱和婚姻吗?
闵智炯:虽然存在个人差异,但我认为,对父权社会中性别差异已有觉悟的女性与持有“厌女”价值观的男性恋爱、发生关系是十分困难的。爱情、性爱和结婚的意义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今社会,暂且不提性别观念,我觉得人们在想建立人际关系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相互尊重。在那種持有“厌女”价值观的人眼中,女性是得不到尊重的人类。所以,爱情和婚姻也必定成了难题。实际上,有不少女性主义者都与男性结婚或者保持着伴侣关系。当今社会中确有一小部分男性可以真正地理解和认同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和各种困难,认同应该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改变。这就是对他人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ELLE:女主很有愤怒的力量,请问你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性格?你认为愤怒可以改变现实状况吗?
闵智炯: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很愤怒的人,因为令人愤怒的事经常发生。实际上,韩国女性们通过“愤怒”聚集力量,然后发声,对改变社会起到了作用。我认为在遭受不平等对待、目睹非正义事情发生时,感到适当的愤怒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在很多应该愤怒的时候却愤怒不起来!有些情况下,我们不会先愤怒,而是先想到“理所当然”“无可奈何”。让人在感受到愤怒前先感受到无力,这就是特权阶层长久以来使用的策略。我们应该从愤怒中找到问题点。再通过与其他国民分享愤怒,发声,采取其他可以改变社会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愤怒可以成为改变的跳板。
ELLE:借女主之口,你的小说提示了很多关键词,指导读者去关注职场、婚姻、装扮等语境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闵智炯:女主经历的职场性骚扰是韩国女性一生中都会经历的事。另一个重点是,要让读者感受到这两人恋爱的真实性:尽管他们的想法不同,也一直在争吵,但能维持他们一直走下去的是互相喜欢的心,既讽刺又让人痛心。相信这也是许多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状态。起初,我想设定两人通过朋友介绍而相识。但在这个设定中,“女性主义者”和“韩男”会让他们彼此警惕,感情也不会轻易加深。再次考虑后,我决定将他们设定成四年前交往过但现已分手的情侣。
ELLE:像《熔炉》这类韩国电影(和原著)充分利用了流行文化的优势,甚至可以有敦促修正法律的推动力,你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在哪些层面扩大影响力?
闵智炯:韩国社会确实存在不少的变数。我们正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政府一直为生育夫妇提供财政支持,为结婚的人提供福利分房。然而,想要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真正关键点在于:要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当下多数年轻女性拒绝恋爱、结婚、生育,是因为她们明白了这在本质上只是在强迫女性牺牲自己。如果社会和文化层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无论提供多少财政支持,都无法轻易改变目前的趋势。通过这部小说我试图揭示——看起来非常私人的恋爱和结婚,其实是从属于社会的存在。同时,我也希望像男主那样的人能通过这个契机来审视一下自己。
ELLE:在韩国,关注、理解女性主义的人群构成是怎样的?你认为男性可能真正地理解女性主义吗?
闵智炯:在韩国,对女性主义感兴趣并有一定认知的大部分是女性,但参加性别教育及相关活动的男性也为数不少。当然,对女权主义仍持厌恶态度的男性也还是存在的,这导致了严重的“性别冲突”。多数韩国女性已经厌倦了试图去说服这些男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和更能理解自己的人相处,有些遗憾。我认为,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走向所有人都能共鸣的性别平等价值观的方向才是正确的出路。有一天男性会真正理解女性主义,我对此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
ELLE:在韩国的时尚女性杂志上有厌女、厌男的内容吗?
闵智炯:在考虑写这部“女性主义者的异性恋爱故事”时,我读到一位女性编辑在某时尚杂志上写的一篇有关作为女权主义者与男性约会的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她真实经历过的事,十分有趣。
ELLE:韩国时尚、美妆、女团风靡全球,你觉得时尚界应该在女性主义领域做些什么?
闵智炯:我认为韩国是外貌至上主义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女性就要苗条”等说法,无疑让女性背负着相当大的压力。我认为媒体和时尚业的责任在于影响人们追求的“理想女性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不同女性形象和多样化时尚已成新趋势。虽然这仍然具有挑战性和理想性,但我希望女性能摆脱“女性应该是这样”的所谓规定。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会因为穿什么而受到指责。

“女權主义就是我所认同的斗争”
——波利娜· 阿尔芒热
1994年生的法国女性主义者、作家。在一家救助女性强奸/性侵犯受害者的机构担任志愿者。她的作品包括《 我,厌男》《 身处支离破碎之所》及《 流产:关于自愿堕胎的私密故事》等。
ELLE:法国的女性主义浪潮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大量街头活动,作为1994年出生的新生代女作家,能否分享一下你的女性主义学习史?
波利娜:2013年,围绕LGBT婚姻有过公开辩论,还有过暴力恐同游行,整个法国都为之震动。我那时在Twitter上非常活跃,也开始认识到:作为女权运动的一部分,法国女权主义者是如何讨论LGBT权利的。我看了很多博客,读了很多书,在我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女权主义就是我所认同的斗争,不仅对我,而且对全世界所有女性和所有少数族裔来说都是。维吉妮· 德斯彭特斯(Virginie Despentes)的《金刚理论》( King Kong Theory)让我大开眼界,贝尔· 胡克斯(Bell Hooks)的好几部作品也让我很感兴趣,比如《女权主义适合所有人》(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和《改变的意志》( The Will to Change)。我也喜欢格洛丽亚· 斯泰纳姆(GloriaSteinem)的自传《在路上》( My Life on theRoad)。后来,我在 L'?chappée 做了 5 年志愿者:这个组织致力于帮助 16 岁以上(儿童需要特殊安排)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受害者。事实上,该组织陪伴的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其中大多数在童年时期曾是性暴力的受害者。个人参与的话,我每年都会在 3 月 8 日国际妇女权利日游行。
ELLE:你的新书中文版书名用的是misandrist的直译,很术语;美国版书名则用了一个短句:I HATE MEN。你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misandrist”一词的由来吗?许多人认为厌男和厌女的标签会导致性别对立,你对此有何看法?
波利娜:这很有趣,因为原版的法语书名(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并没有怨气或怒气,倒更像是厚颜无耻的坦白。我在书中明确定义了厌男,大家可以去看书!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哎呀,厌女很糟糕,但厌男也一样糟糕,只是性别歧视的倒转罢了”,但这绝对是错误的。所以,我在书的一开始就解释了事实:厌女是性别歧视制度所纵容的,而且,对女性来说是暴力的、伤害性的,有时甚至会致命。厌男不可能完全是厌女的反面,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母系社会里。不喜欢男人的女人不会去伤害男人,只会远离他们而已。我认为性别对立已是既成事实。现在有人谴责女权主义者挑动两性战争,但几千年来,男性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掌握了权力,他们早就对女性发动了暴力战争。
ELLE:写这本书的过程里,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波利娜:对我来说,很显然,这本书必须超出我个人的经历。我知道很多人就想从字里行间去胡乱揣测我的私人往事,他们会说“你看,她讨厌男人,因为她被虐待过/她从未被人爱过/她有恋父之类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事实。不过,我也不希望这本书成为纯粹的理论书,因为我不是学者,我是作家。所以,困难在于平衡个人观点和有据可查的事实论据。
ELLE:你如何处理两性间的差异和爱情、性爱的矛盾之处?厌女和厌男的人类有可能得到完美的爱情、性爱和婚姻吗?
波利娜:我要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绝对、永远不会把厌男者和厌女者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厌男者很有可能与其他人建立有意义的、持久的关系——我们是一群要求很高的人,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建立的情感关系更牢固、更值得尊重。如果某些男人看不惯我们的政治观点,那么他们就根本不适合我们。
ELLE:网络媒体让女性主义话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但tag式的短小发言容易让人站队,也不容易再出现像波伏娃《第二性》这类的严密的理论阐述。你15岁就是知名博主了,和互联网一起成长的你觉得网络在女性主义传播事业上有怎样的利弊?
波利娜:我现在29岁了!不可否认,社交媒体上的发言简短,加上那种算法,往往会导致讨论两极分化。但互联网确实是一个了解你本来压根儿不知道的东西的好地方!伊朗的妇女革命、阿根廷的妇女抗议、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在塔利班掌权后的遭遇…… 还有理论,因为当代女权主义思想家们有博客,也会在Instagram上分享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或是一小段真知灼见,让我们都很受益。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让你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很好的起点,也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好地方,还能让你跟上世界各地新闻的快节奏滚动。
ELLE:在法国,关注、理解女性主义的人群构成是怎样的?男性依然避而不谈吗?法国女性是如何应对的?对于欧美有些男性自称“女性主义者”、但事实上还在保持男权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你是如何看待的?换句话说,你认为男性可能真正地理解女性主义吗?
波利娜:妇女权利变得越来越重要,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这是一种伟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去做功课了(我的意思是,他们会闷头儿自己去钻研性别问题了)。还有些人确实试图装作女权主义的盟友去获取良好形象,他们很狡猾,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但我们总能闻出他们的真实气味。对男人来说,理解女权主义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闭嘴、倾听,教育他们的兄弟、朋友、父亲和儿子。
ELLE: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风格?身在时尚、美妆之都,你觉得时尚界应该在女性主义领域做些什么?
波利娜:时尚杂志仍然充斥着身材管理、看起来更瘦、取悦男人的建议……我完全不是时尚挂的,我总想穿得舒适一点(尤其是我生了娃之后),确保在照镜子的时候能认出自己。我对时尚杂志上的话题真的不太了解,裤袋不够大、没法双手插袋的时候,我会很抓狂的。
ELLE:女性主义是一项持续进行的事业,在《我,厌男》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之后,你还想有哪些方面的进步?
波利娜:我现在的目标是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写一些有助于稍稍改变想象的小说。我不打算用小说去改变世界,但这是我最擅长的,可以有所建树的。我写过自己堕胎的事了,也许接下去会写当妈妈的事,但我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