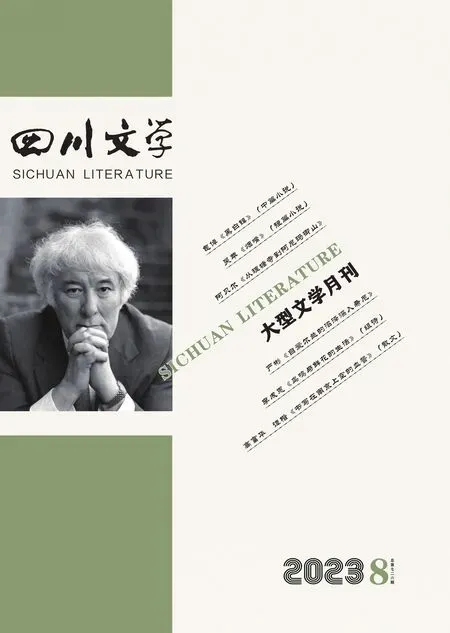烟嘴
2023-10-16吴苹
□文/吴苹
刚四点钟,屋内就已经暗了下来。棕黄色的旧家具变成了面目不清的暗红色,布式衣柜的拉链没有拉上,露出了散落在柜底的几条旧袜子,像条没来得及缝合的伤口。绍辉将打理好的行李箱放到沙发旁,站起来时感觉后背有些凉,原来阳台的窗户没有关。走向阳台的时候,他的头被什么东西拂了一下,是江菲的肉色连裤袜,蛇皮一般在钢丝绳上荡来荡去。绍辉摸了一下,上面似乎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气味:香水味、体味,还有其他。江菲说香水的气味是往上走的,每次出门前她都会往大腿上多喷一些;江菲还说香水是女人的衣服,这话应该不是她的原创,可能出自玛丽莲·梦露之口。
绍辉苦笑了一下,转回了身,现在这个房间倒称得上是空荡荡了,空荡荡得像一只被开膛破肚的羊,内脏已经被掏空了。人一个个走了,有些东西却没有被打包带走,没带走的东西已渗进房间的纹理深处了。
绍辉走出门又回身环视了一下屋内,这才关上了房门,砰——屋内的气息被关在了身后。
绍辉点了一支烟。打火机的光照亮了他拿烟的左手,还有手上的赘生物。那个东西长在左手小指的外侧,有肉有骨还有指甲,从一出娘胎就跟上他了。懵懂无知时绍辉还炫耀过,以为自己多根手指是天赋异禀,二郎神就比常人多只眼睛嘛。后来不再炫耀了,却也没有为此自卑过,这源于老天给他的一副好皮囊。见过他的人都说这孩子生了个好相貌,谁又会在乎多出的那根手指呢?大学期间常有女孩子喜欢他,只是到最后都没了结果。他曾指着那根六指问跟他分手的一个女孩:“莫不是因为它?”女孩哈哈大笑。直到那次江菲开玩笑似的说:“多根手指头有啥用啊?这要是多个肾该多好啊,摘下来还可以换几平方米的房子呢。”一句话将他的心打进了冰窖里,看着那根六指他第一次有了厌恶感。也不是没下过做手术的决心,第一次预约了医生他没有去医院;第二次办了住院手续做了一系列检查,等到该进手术室时,他突然嚷起来:“不做了!不做了!”唯恐医生问原因,他逃也似的跑了出去。
这次下决心做手术是因为公司。那次下班后,他和同事一起走出公司,他们先进了电梯,他刚踏进去一只脚电梯却提示超载,他只得退出来。这个时候,总经理从公司里走了出来,他忙和总经理打招呼,总经理嗯了一声,目光在他左手上盘旋了一下,他的心立时提了起来。总经理说:“小许啊,你现在是销售经理,你的形象可是代表着公司的。有句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比如,你和客户握手、吃饭,这些小细节就有可能影响你的业绩,你长得比较帅气,如果再注意一下细节,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了。”他自然听出了话里的弦外之音,连声说:“王总您放心,您放心,我这就去做手术。”唯恐说得不到位,紧跟着又补充了一句,“早就想做手术了,就怕请假耽误工作。”王总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说:“许经理,我果然没看错人。”
还没走下楼梯,绍辉就听到了刺啦刺啦声,小狗皮皮又在挠颈上的项圈。皮皮被拴住不到半年的时间,项圈和牵引绳已经被他咬断了三个,现在这个是金属材质的,好歹没有被咬断。
绍辉想着住院期间先将皮皮寄养在老六家。毕竟老六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也是皮皮的主人之一。大学时同宿舍的八个人全是从农村出来的,相同的出身,自然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毕业后几番聚散,有五个人留在济南,留下来的五人就有了难兄难弟感。绍辉和江菲认识之前,逢节假日,弟兄几个总要聚一聚,喝个酒撸个串,酒足饭饱后再相互搀扶着去打车。认识江菲之后,他们几个明里暗里都对绍辉说过‘交友要慎重’之类的话,那时绍辉颇不以为然,认为那几个光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为了向江菲表决心,绍辉转身就将那些话原封不动地卖给了她,惹得江菲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搭理那几个人。后来的这半年,他和江菲之间硝烟频频,生了气后的绍辉没地方去,每次都是找他们几个去倾吐,只是一次也没有找过老六。
如今,和江菲彻底分手了,绍辉觉得他和老六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拴了三个月才放出门的皮皮兴奋得近乎癫狂,又蹦又跳,围着绍辉的身体来回转圈子。看见树上的麻雀便汪汪叫两声,看见蝴蝶也跑去追。绍辉紧紧地握住手中的链子,唯恐皮皮从手中挣脱。
路过金利来宾馆,明知道江菲不在,他还是走了进去。前台站着的是江菲的同事,他问那女孩儿:“这期间江菲回来过吗?”女孩儿摇了摇头。他又问,“那辆……旧奔驰这期间来过吗?”女孩儿说:“没有,自菲姐走了后,那辆奔驰就再没来过。”
绍辉牵着皮皮往外走,心里在想着江菲和那辆奔驰的事。有几次,江菲出去上班后,他心里不踏实,往宾馆打过去电话,那边果然说江菲又没来上班……下台阶的时候皮皮跑在前头,他手里一松,皮皮就窜了出去。他在后面边追边喊,皮皮跑过人行道,跳过绿化带,窜向了马路对面。他刚要过马路时,对面亮起了红灯。等他过了马路,皮皮已跑向了护城河边。皮皮撒开四蹄沿着河边没命地跑,他在后面紧追不舍。倏地,奔跑着的皮皮停住了,他捂着胸口追过去,谢天谢地,是灌木丛将拖在地上的链子挂住了。
绍辉牵着皮皮走到老六家,老六提着锅铲给他开的门,老大也在。绍辉将皮皮安顿好后,他们两个已将饭菜端上了桌。
老大将啤酒倒进绍辉面前的酒杯里,说:“兄弟,其实这手术真没必要做,今年咱们公司的业绩很不景气,我和老六都准备跳槽了。”他说:“再待一阵子看看吧,能不跳就不跳。”老大叹了一口气说:“只怕到时候由不得咱们。”绍辉说:“还不至于到那一步吧?”老大摇了摇头:“你看,每个月都压了一部分提成没发,这一拖就是半年,老板说到春节时一起发,只怕到了春节又要变成肥皂泡喽。”他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三个人一时无语,房内的气氛有些凝重,老大率先举起杯,转移了话题:“为你重获自由身干杯。”他苦笑:“唉,真差不多等于刑满释放了。”之前半夜醒来,绍辉望着身旁那个人,她身上的肉随着打鼾在微微起伏,绍辉就感觉疲惫像大雾一样弥漫过来,将他重重包围。
那个周日,绍辉原是去公司加班的,到了公司才想起将资料忘在了家里。走到离小区不远的地方,听到一楼的铁门咣当一声,老六急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面带愠色,像在跟谁生气。他走到近前,叫了老六一声,老六站住,看了看他,咂巴了一下嘴。他问:“老六,你怎么啦?”老六没有说话。他晃了晃老六的胳膊:“怎么啦,这是?”老六嗫嚅着说:“嫂子……”一听这话,他的脑袋轰的一声响,刚想进一楼大门,被老六从后面拉住了:“四哥,天地良心……我看都没敢看……”
老六搬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八个人当中,原本属老六和他的关系最好。刚毕业时,老大他们几个租的是自建房,厕所是公用的,他嫌那种房子不方便,和老六一起在百花园小区合租了这套两居室。尽管有两个卧室,两人却喜欢挤到一个床上睡,直到江菲和他同居后,老六才搬去了另一个房间。在学校宿舍时,他和老六睡上下铺,入学时他分到的是上铺,因为他恐高,老六主动跟他换的下铺。交往这些年,老六的人品,他再清楚不过了,不然他也不会和江菲同居后仍让老六住在这里。江菲怎么样,他也清楚。当初两人是在网上认识的,同居之后他才知道江菲和别人领过证,江菲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举行仪式,他心里虽怀疑却没敢多问。江菲愿意跟他过,他认了,没想到江菲竟……
绍辉常想那次幸亏是老六,换了别人不定做出多么丢人的事来。他转念又想自己在那种场合也会那样做,毕竟是朋友妻,这点原则是个男人都会遵守。有时候他明知道老六没有做任何错事,却又莫名地怨恨老六,直到这次和江菲分手,他才感觉到释然。
老大说:“有些人是掐住咱哥们儿的七寸了,知道你能原谅她,所以才挑战你的底线。兄弟,你应该很庆幸,你们不是在结婚之后分开。”绍辉将一杯酒灌进了喉咙:“她也不是一无是处,有时候也是很好的。”老大看了老六一眼,说:“那是,那是。”两人刚同居的时候,江菲下班后,会做好饭菜等着他。饭后,电视机开着,江菲一边给他捏肩,一边说着她们宾馆的事情。临睡前,他喜欢看几页书,江菲敷着面膜坐在旁边陪着。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日子尽管不多,足以够他用来回味品咂的。
绍辉说:“随她去吧,毕竟没几个女人愿意过苦日子。”这话像一枚炮弹,那两个男人立时哑口无言了。老六说:“争取在毕业的第四年买房。”老大拍拍老六的肩:“兄弟,今年都第三年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无酒蒙头睡,先得过且过吧。”老六说:“三个学美术的人,现在全都扔了画笔,悲催啊。”三个人聊了一阵房子的事情,老大说:“想起来了,小叶还没找对象呢。”老大又说,“该结束的已经结束,该开始的也应该开始了。”他说:“恐怕不能了吧?”老大说:“上次的事情我都跟她解释过了,她还特意问了你的情况。”小叶是老大的老乡,看起来很恬淡的一个女孩儿,在某家培训机构里当老师,上次他和江菲闹掰后老大给介绍的。他和小叶见过一面,后来又在手机里聊过几次。江菲和他和好后,不知情的小叶曾打过一次电话,他刚接通就被江菲夺了过去。事后,他专门发微信解释,小叶一个字也没有回。老六说:“四哥,你可以再给人家解释解释,别让人家一直误会你,顺便也探探她的态度。”他感觉老六说得有些道理,就打开手机,给小叶发了一个“你好”的图片,等了片刻,小叶没有回,他也就把手机放到一边了。老大问:“百花园小区的房子退了没?”他说:“这次走得有些急,回来再退吧,到时去公司宿舍住。”
饭后,绍辉给老六交代了皮皮的饮食,准备走的时候听到手机嘀了一声,打开来,是一条微信:你好。是小叶发来的。
那条鲨鱼一直跟在绍辉身后,银色的鲨鱼。海水冰冷,绍辉使出浑身力气拼命地游,却越发体力不支。鲨鱼追到了近前,巨大的尾鳍翻搅着海水,浪头打来,绍辉一阵眩晕。鲨鱼张着大嘴,锋利的牙齿闪着寒光,绍辉已无力躲闪。鲨鱼跳起来,一口咬在他的左手上……绍辉大叫一声醒来,睁眼后先看自己的左手,伤口连带着手掌都被纱布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点点指头。“我的手?!”护士笑着说:“手术很成功。”他说:“我的手……”护士说:“你好好休息,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他说:“我的……手指呢?”护士说:“这会子你找它干什么呀?还是先回病房休息吧。”他从手术车上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护士按住了他:“你干啥呀?输着液呢。”他挣扎着:“不行!我要去找。”护士生气了:“你冷静一下好不好?!”他的声音里有了哭腔:“我要去找回来……”医生从手术台的一侧向他走过来,手里端着手术盘。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手术盘,直到它被递到跟前。
从医院回来的那个黄昏,绍辉提着一个手提袋上了山。山上种着很多树,松树、柏树、枫树、槭树,还有杏树、梨树等。风在树林里穿行,枝叶沙沙作响。绍辉转了一圈儿,到了一棵梨树跟前,梨树在半山腰,旁边有个凉亭,亭边有一潭水,想来因水汽的滋润,梨树长得粗大壮硕,叶片肥厚有光泽。绍辉瞧四下无人,拿出包里的铲子,在梨树前向阳的那面开始挖。因刚做了手术,才挖了一尺多深,他的喘气粗了,前胸后背也有了汗。他停下来,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铁盒,那个铁盒原是盛扑克牌的,盒面上印着如来佛祖化五指为山压住孙悟空的故事。整个画面上最醒目的是那五根手指,粗大壮硕,犹如五根肉柱。铁盒散发着浓浓的白酒味,当初他专门从医院的超市里买了一小瓶白酒,将酒倒进盒内一部分,高度白酒能防腐嘛。他盯着盒子看了一阵才将它放下,接着又往下挖了一尺多深,估计这个深度即便是下暴雨也不会将坑底的东西冲出来,他便停止了挖掘。他再次拿起那个铁盒摩挲了片刻,而后看了一下四周,确定无人后才把它放进了坑底。将土全部回填,用脚踩实后,天彻底黑了下来。他坐了片刻,才起身往山下走。
伤口拆线之后,留下一条小小的疤,伤疤不是很明显,离远了很难发现。绍辉的目光常有意无意地落在那条伤疤上,它还在隐隐作痛,它在提醒绍辉,那里失去了点东西。它在的时候应该拍张照片的,以前老是忽略它甚至厌烦它,可是一旦被切除,绍辉总觉得心里有点发空。
百花园小区的房子到底没有退,尽管公司有宿舍,老大也多次让绍辉搬过去一起住,绍辉还是决定住在老地方。一个人住着套两居室,月租一千七,想想是有些奢侈,但是绍辉总感觉住处很像人的鞋子,有旧鞋子穿着就不愿去换新的,毕竟承受磨合的疼痛需要时间和勇气。
自埋下铁盒后,逢晚上或周日,绍辉经常不由自主地就转到了山上。那棵梨树显得越发茂盛,尤其是叶片,肥厚得有些妖冶、有些异常。今年雨水旺盛,想必强劲粗大的树根已经扎进铁盒内,里面的东西早被树根吸收,随着经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每片叶子里了。绍辉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家里的鸡生了瘟疫,为了防止瘟疫传染,母亲便将死鸡埋在一棵杏树下,那年的杏子也是长得异常硕大、肥美,以至于很长时间绍辉都觉得每颗杏子里都住着鸡的灵魂。
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老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公司苟延残喘了大半年后再也无法坚持,人事经理找了很多人谈话,委婉地表示希望他们自行离职,否则技术和业务人员将大批量调岗到车间。为此事,老大特意找绍辉他俩商量:“事已至此,越早抽身越好。”“辞了再找谁知道要漂多久啊?”绍辉叹了口气说,“找工作,还有找老婆,原本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老大说:“现在哪还有那么长远的事?还不都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老六说:“四哥比较恋旧。”老六这么一说,老大就不说话了,毕竟很多事情他俩都亲眼见过。就像绍辉的那部旧手机,一用就是八年,那手机曾经损坏过几次,光维修的钱加起来就够买一部新机了。后来实在不能用了,绍辉也没舍得扔掉,而是将它放在了抽屉里。临走时,老大说:“你留在车间其实就是委曲求全,关键是委曲后能求来那个全吗?”
事实验证了老大的正确选择,他和老六离开公司没多久,绍辉去了生产线,也就干了一个多月,等来的是公司的彻底倒闭。
这是个周六的下午,绍辉没有出去,在家里洗了一堆衣服。将湿衣服拿到阳台上晾晒时,一抬手碰到了铁丝上的丝袜。江菲是初春时走的,现在已入秋了。熬过了最初那一阵子,后面的时间还是容易打发的。他扯下丝袜想把它扔掉,在手里攥了一阵子,又放回了铁丝上。丝袜晃荡着在他左手上拂了一下,停住了。左手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伤口已经不疼了,只是在碰触时有一点发麻。
一楼院子里的皮皮又在咯吱咯吱地咬项圈,咬项圈成了它每日的功课。那段梨树枝就放在小狗的旁边,晾晒这些天,差不多已经干透了。那个傍晚,绍辉又转到了山上,这次他特意在手提袋里放了一把菜刀。他到了那棵梨树下,看着当初埋东西的地方,数月时间过去,那里土壤已经变硬实了,丝毫看不出有挖掘的痕迹。铁盒内的东西现在到了梨树体内,正以另一种形式活着。正上方的那根树枝很粗壮,上面却没有挂果。等夕阳撤走最后一抹余晖,绍辉站起身走到那根树枝下,他左手抓着树枝的一端,右手挥刀,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那根树枝就被砍了下来。
将衣服晾完后,老大他们打来电话,问他新入职的这家公司的情况,他说:“就那么回事吧,一家做果汁的公司,产品走商超,我负责济南这边的业务,目前来说够吃饭的。”他挂了电话后,下楼买了点饭菜,才走上楼梯,兜里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小叶打来的。那次联系上小叶后,两人倒见过两次面,只是没有往深里聊。得知小叶加班刚回来还没顾得吃晚饭,绍辉忙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换了一身衣服,出了门。
绍辉找了一家不错的饭店,点了四个菜,再准备点的时候,小叶拉住了他。绍辉感觉小叶似乎和上次有些不同,就盯着她多看了两眼,小叶笑着眨了眨眼睛,绍辉才发现小叶摘掉了眼镜。少了一层障碍,小叶的眼睛看起来大了不少。绍辉用开水将餐具烫了一下,给小叶递杯子的时候,闻到小叶身上有一股很清爽的气味,是淡淡的香皂味。小叶应该是不用香水的。江菲爱香水,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让她只能网购,因此,香水的质量大多不敢恭维。出于礼节,绍辉用公筷给小叶夹了点菜,小叶也回夹了一次,离得近了,绍辉发现小叶的脸形还是很耐看的,至少比江菲的脸要耐看,眉毛是那种平眉,但眼睛很大很亮,鼻子也很挺秀,只是个头约莫比江菲矮一两厘米。
小叶问:“你女朋友……”绍辉说:“这次是真的分了,彻底分了。”小叶没有说话,垂下眼帘,看着放在桌上的自己的手。小叶的那双手很白、很干净,指甲剪得很短,每个都呈健康的粉色,根部有一牙小小的月白。江菲喜欢涂深色的指甲油,有次心血来潮她还给指甲做了雕花,为此花去了她近半个月的工资。“素手做汤羹”,也许拥有这样一双手的女人才是最适合我的。绍辉看着小叶的手,心里有了一点轻松和释然,他试探着说:“唉,只是目前我还没有房子,不过,结婚后肯定会买的。”小叶笑了一下:“目前我也没有房子。”绍辉一听这话,心里长出了一口气,又给小叶夹了一次菜。如果当初遇到小叶就好了,一切都没有跑偏,一切都在正轨上。今天吃过饭可以和她一起在月光下散散步,在护城河边的垂柳下坐坐。
这时,从外面进来三四个人,看到他们,绍辉心里咯噔一下,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同事。”绍辉跟小叶说完,站起来和那几个同事打招呼。几个同事来到他们近前,笑着打量小叶,还向他直挤眼:“绍辉,还不介绍一下?”他说:“我朋友。”其中一人说:“女朋友吧?”他说:“哪里,只是朋友。”那几个人笑着,坐到了离他俩不远的桌子边,边吃边往这边看。
接下来的这顿饭,绍辉吃得没滋没味,嘴里咀嚼着,心里却在不停地懊悔,自己不该选路边的这家餐馆,怎么说也得找个偏僻一点的,那样,起码不会遇到熟人。小叶似乎看出了点什么,也没有再说话。
两人出了餐馆,夹在饭后散步的人群中一前一后地走着。再往前就是护城河公园了,河里流水潺潺,岸上绿竹婆娑,多是情侣卿卿我我之处。他停住了脚步,走在前面的小叶见他没有跟上来,也停下了脚步。他说:“今天天晚了,回去吧。”小叶转身往公交站牌的方向走。公交车还没有到,两人站在那里,惹得旁边的一个女人不时地瞟他们。他说:“要不打车送你回去吧?”小叶说:“不用,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等就行了。”他说:“那我先回去了,有些工作得加个班。”
绍辉转身往回走,边走边踢一颗小石子。走了一段路见旁边有一条长椅,他坐了下来。旁边有几样简易的健身器材,一个男人正在做引体向上。少顷,那男人从双杠上下来,又做起了仰卧起坐。他不明白一天下来,怎么还有人剩余那么多力气。草丛里有只蟋蟀在嘀嘀地叫,他朝那里踢了两脚,叫声停止了。手机响了一下,是小叶发来的信息,他懒得去看,怕小叶打来电话,索性摁了关机,闭上了眼睛。
绍辉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个健身的男人已经走了,只余下一地孤寂的灯影。衣服和头发被夜露打得有些潮湿,他打了个冷战,忙起身往回走。
二楼的门口站着一个人,看到那个身影的刹那,绍辉的大脑出现短暂的空白,脚下的步子却加快了。走到近前,绍辉站住,盯着那个人。那人看着他,没有说话,身体却摇摇欲坠,在她将要倒下时,绍辉上前一把扶住了她。
绍辉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爬满了窗帘。江菲的两只胳膊缠在他腰上,搞得他做了一夜的噩梦。他将那两只胳膊轻轻拿了下去,睡得迷迷糊糊的江菲又搭了上来。“你别离开我。”江菲闭着眼睛说。他说:“我不离开你。”“你别离开我,我知道你对我好……”江菲的胳膊死死地箍着他的腰,他都有点呼吸不畅了。他将江菲脸上的乱发理到耳后,才半年没见,江菲的脸比以前憔悴了许多,眼角竟有了鱼尾纹。刚打开手机,老大的电话打了过来:“兄弟,今天周日,我和老六打算去你那边聚聚,怎么样?”他嗫嚅着说:“今天,今天加班……在公司里加班。”“靠!真的假的?你不会是在金屋藏娇吧?”老大的嗓门很大,他担心江菲听到,将手机转到另一只耳边。“还藏娇呢?加班累得要死。”他故意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改天吧,改天我去找你俩。”
将电话挂了后,他找到小叶的号码,把她拉到了黑名单。
这次江菲回来后,明显比走之前对绍辉好了。有时候,绍辉将脏衣服放到洗衣盆里,原本打算下班后洗的,下班后却发现它们已经被洗好晾在阳台上了,其中包括他的内裤和袜子。他对江菲说:“我的内衣和袜子我自己洗就行了。”江菲说:“反正这一阵子我在家里也没事,就顺手洗了吧。”晚饭后,江菲又开始给他捏肩了,逢他加班的时候,她会主动为他泡一杯茶。日子看似又回到了两人刚同居的时候,却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时不时地跳出来打扰他们。之前,江菲喜欢半躺在沙发上,一边吃水果一边追剧,她偏爱霸道总裁与灰姑娘之类的肥皂剧。某次,看到关键处,她一脸羡慕地盯着屏幕上的女主说:“瞧瞧人家,咋就这么命好呢?”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瓣沙糖橘,手指翘成兰花状,到了嘴边,手停了下来,还不忘回头瞥绍辉一眼,那眼睛里的内容毫不掩饰、一览无余。绍辉的心立时堵起来,嘴里却说不出来一句话。过了片刻,她见绍辉没反应,像不解恨似的又加了一句:“噢,忘了告诉你了,我前几天回老家,有人为我介绍对象,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有车有房,开的是奔驰,住在鲁能康桥,那可是高档小区。”绍辉说:“不就是一个包工头子吗,你回来后说几遍了?你看他好跟他过啊!”而现在,当电视里播放当下的某个婚恋剧时,江菲会无意似的拿起遥控器,将电视调到别的频道。这天晚饭后,绍辉起身要收拾桌子,却被江菲拒绝了:“你上一天班了,休息一下吧。”绍辉说:“要不,我来刷碗?”江菲说:“不用。”江菲刷好锅碗后,照例走过来为他捏肩,此时,电视里播放着一部民国剧:年轻的女主人公被电影公司的老板包养在一座公寓里,女人再不用为生计操心,幻想着自己从此过上了贵妇的生活。后来的一切和观众的预想没有太大偏差,女人失宠,老板再未踏进公寓一步。房租到期,房东又过来催房租,女人走投无路,只得拎着行李箱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看到此处,绍辉已经感觉到了,为他捏肩的那双手停了下来,过了片刻,一只手离开他的肩头,另一只手依然搭在上面,停在肩上的那只手渐渐变得沉重、僵硬。他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回头,他不想让江菲知道他已经觉察,他只是在静待她下一步的动作。少顷,另一只手也抽离他的肩膀,他以为她会拿起遥控器调台,没想到她走进了卫生间。
江菲洗漱完毕,脸上蒙着一张面膜从卫生间走出来,她穿过客厅,径直走向卧室。绍辉问她:“你不看电视了?”她头也没有回:“不看了,困了。”
这天,公司提前结束了每周例会,绍辉走到家门口时听到江菲在打电话,防盗门是老式镂空的,屋内传出来的声音虽小,却能听清楚:“……我在济南……嗯,妈,您就别管了,事到如今,只能是这样了,毕竟找个穷人,也有他的好处……”怕江菲怀疑他偷听,等江菲挂了电话后,绍辉又在门外待了片刻,才开始敲门。
即便没有这些蛛丝马迹,江菲离开他这大半年都发生了什么事,绍辉也能猜出十之八九,和她交往近两年的时间,绍辉可以说对她了解到骨髓里,哪个女人在高调离开之后能再转身吃回头草?也只有江菲了。这件事和老六那件事都是伤疤,长在江菲的身上,却疼在绍辉的心里。绍辉每每想起这些就感觉胸口发堵,真想狠狠心像其他男人一样对江菲来个快刀斩乱麻,哪怕酣畅淋漓地将她的疤揭开一次也好,这股气郁结在他的胸口久久盘旋着,到最后还是被他自己一点点地消化掉了。毕竟他还打算和江菲过下去。两人最初的那些美好不遗余力地从他的肉里往深处钻,如今已经钻到骨头里,他一直靠着那团记忆饲养着自己,他上了瘾且无法戒除。
老大说得没错,江菲是掐住他的七寸了。
绍辉将那根晒干的梨树段剥去皮,捡最光滑顺直的地方截下八公分左右。每天一吃过晚饭,他就开始加工那段梨木。他父亲是个木匠,从小耳濡目染,他对木工算是知晓一二,加上曾学过雕刻,对自己要做的活计还是有点把握的。尽管如此也不敢松懈,他先画了图纸,再用铅笔在梨木上画尺寸,尺寸是精确到毫米的。接下来是实际操作了,先按照尺寸将多余的木质凿去,凿成一个细长的圆柱体,然后将咬嘴的那一头削细削扁,将嘴身挖空。一个烟嘴的雏形出现了;接着雕花,给嘴身的另一头加上铜箍;最后,握在手心里打磨,等烟嘴泛起梨木特有的油彩一样的光泽时,才算大功告成。
江菲喜欢边敷面膜边看手机,手机网页里有一道心理测试题:某人去朋友家常常走一条路,那条路上有很多石子总会硌痛那个人的脚;另外还有第二条路,但是那个人从未走过第二条路,也许有鲜花也许有荆棘,无论鲜花还是荆棘都是未知的。“如果是你,你走哪一条路?”江菲问绍辉。绍辉想了想,说:“还是走第一条路。”江菲就嘁了一声。
梨木烟嘴全部完工后,绍辉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失去的东西到底又回来了,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因此,绍辉进门出门时都带着它,除了睡觉,基本上是形影不离。绍辉觉得自用了梨木烟嘴之后,香烟的口感变得香醇了很多。当烟雾经梨木烟嘴吸进嘴巴,再由肺输送到五脏六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放松了、踏实了、熨帖了。绍辉原来的烟瘾并不大,有时候一包烟能抽上半个月。有了梨木烟嘴后,烟瘾却一天重似一天。下班后,绍辉喜欢含着烟嘴陪江菲到附近逛逛,如果江菲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绍辉会拒绝,他不想走太远,他怕老大他们看到笑他。有一次陪江菲逛街时,老大和老六打电话找他喝酒,又被他以别的理由搪塞过去了。
风一日紧似一日地吹,吹落了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早晨,刺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擎着一层霜,越发显得形销骨立。这日,江菲一起床就干呕个不停,绍辉以为江菲吃坏了肚子,忙给江菲找健胃的药。江菲说:“别找了,可能是……有了。”绍辉算了一下,江菲回来快两个多月了,时间上是对的。绍辉请了半天假,带着江菲去医院检查。
江菲从B超室出来后,绍辉扶她到椅子上坐了一阵子。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就过去取了孕检报告单。“早孕,单活胎,孕约5周”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绍辉看了多遍,他特意往江菲那边看了看,见她正将脸扭向别处,忙小声问医生:“这个时间准吗?”医生说:“准的,如果有误差也就几天的时间。”他长出了一口气,听到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落了下去,吧嗒一声着了陆。
孕妇不能养狗,看来只能将皮皮再送到老六那里了,绍辉牵着皮皮顺着河边走。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冬阳将树影斜斜地映照在地面上,河水平缓如镜,边沿结了一层薄冰。天气这么好,不妨让它撒个欢。绍辉松开了手中的链子。皮皮跑了两步,听到铁链拖地的声音,回过头诧异地看着。他将皮皮的项圈解了下来。哪知道皮皮走了两步,停了下来。他轻轻踢了它一下:“跑吧跑吧,这下自由了。”皮皮又试探着走了两步,索性坐在了地上。他气得踹了它一脚:“我靠,没有它你反而不会走路了。”他将项圈重新给皮皮戴上,皮皮低头打量了一下项圈,又颠颠地跑了起来。他又好气又好笑:“哈哈,狗东西,你可真是个狗东西。”
自江菲怀孕后,绍辉一犯烟瘾便拿着烟嘴跑到房间外面。晚上他不愿往室外跑,干脆将香烟放进梨木烟嘴里,也不打火就那么叼着,有几次竟叼着烟嘴睡着了。惹得江菲揶揄他:“听说过度依赖香烟的男人还处在‘口欲期’,就和婴儿依赖奶嘴是一个道理。”绍辉说:“你还挺能的,你了解男人多少?”说这话的时候,他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段文字:成年人咬香烟、咬手指等行为是缺乏安全感的外在体现,蓦地,他的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话,应该是弗洛伊德说的,如果不能亲吻,抽烟就变得不可或缺。他发了半天呆,叹了口气作为终结。
又一个夜晚到来,和江菲做完该做的功课之后,绍辉看了江菲一眼,如同壮士断腕一般将烟嘴拍在了桌子上。江菲撇了撇嘴,扭转身睡去了,他却睡不着,借着手机的光看着桌上的烟嘴,权当望梅止渴吧。没想到望梅非但不能止渴还越望越渴,整个人六神无主心神不宁,胃里一阵接一阵地抽搐。实在坚持不住了,他爬起来拿起烟嘴径直奔向卫生间。
周日在家时,绍辉就给江菲肚里的孩子读书。读着读着,江菲会抓过他的手放在那个大肚皮上:“你摸摸,她在动呢。”绍辉感觉到手掌下像有脉搏在微微跳动,顿时心里麻酥酥的。趁着高兴,他说起了结婚的事:“今年已经将车钱攒够了,年底就提新车,再把证领了,把仪式举行了,明年就可以经常带着你和宝宝去兜风了。”江菲说:“嘁,还好意思说这话。”他说:“一年会比一年好的。”江菲停了一会儿,说:“你猜他/她是男孩还是女孩儿?”他说:“说实话,我还是想要女孩,男孩成年后压力太大,累啊。”江菲说:“女人就不累吗?要是找个窝囊老公,就得陪着累一辈子,像她妈似的。”他唰的一下抽回手:“你怎么说话呢?”江菲站起来说:“我说的不对吗?!”他有点哆嗦:“嫌我不好找别人去!”江菲说:“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混吗?我他妈的早就后悔了!”他浑身都在战栗,桌子上似乎有一样东西,他挥拳就砸了过去。
听到哗哗的水声,他才知道圆形鱼缸被砸烂了。两条金鱼掉了下来,在地上扑腾来扑腾去,扑腾了一阵子便不动了
“砸它算什么?要砸你就砸我!”江菲扑到床上大哭。
他抬手往墙上挥过去一拳,又挥过去一拳。
手上的血流到衣服上才住了手。他转身准备去卫生间包扎伤口,脚底下踩到一样东西,差点跌倒,他一脚将那个东西踢到了墙角。到了卫生间门口他猛地醒悟过来,折回身走到墙角处。梨木烟嘴破损了一个角,他还是将它捡了起来。
他拿着破损的梨木烟嘴走向次卧,这个房间原来是老六住的,老六搬走后便将它做了杂物间。屋里靠墙放着一套旧橱柜,是从旧货市场买的。他拉开最里面的抽屉,准备将梨木烟嘴放进去,发现里面已经满满当当:笔尖磨秃的旧钢笔、断裂的旧腰带、断腿的旧眼镜、外壳严重磨损的旧翻盖手机……他打开上面的橱柜门,橱柜内挂着一些旧衣服,最外面的是一件旧西装。那是他考上大学那年暑假买的,穿到他大学毕业时,西装小了,衣袖短了,他父母让送给他弟弟穿。他为弟弟买了一套新西装,也没舍得将这件旧衣送给他。
他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西装口袋,摸到几张纸,打开来,却是做六指手术时的检查单。他看了片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笔袋,将检查单和烟嘴一起放进了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