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识诗歌的三种关系
2023-10-12张倚胜
张倚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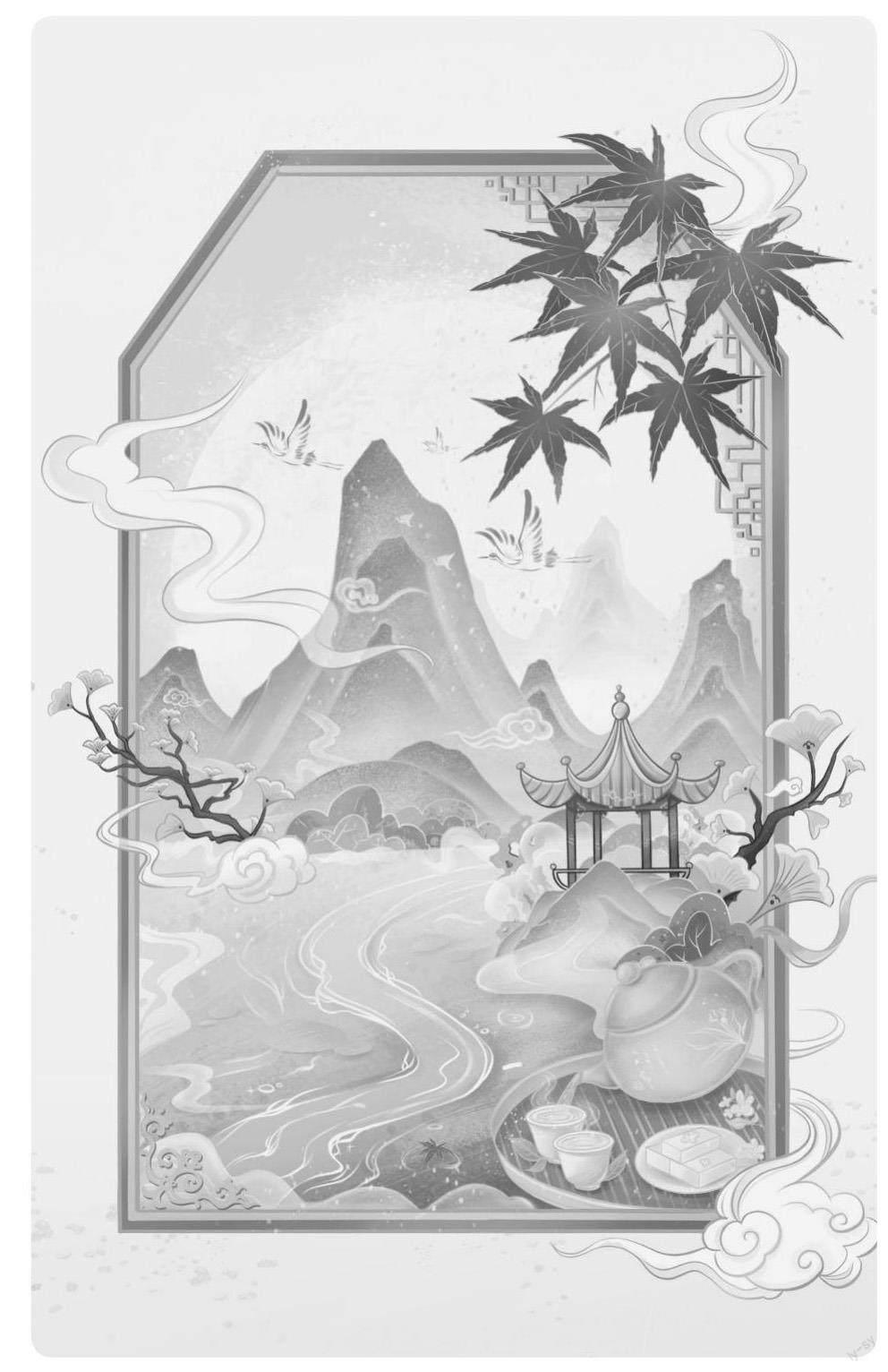
“多解”的背后代表上层艺术性。诗歌的发展必须走“精英文学”的路,也必须要求诗人具备一定的诗学基础理论知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似懂非懂时就立刻大胆地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多解”的表现就要使读者至少读出或理解一种对诗的感受,而后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平民大众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个性的就是普遍的。
当前,人们对诗歌的认识,特别是对汉语新诗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了解不透,误解不少,下意识地喜欢用过去的、通俗的文学标准对当下诗歌写作进行评判。由此,笔者有针对性地确定了关于认识诗歌的三种关系,将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解析诗歌的现实发展与内部平衡。
一、古典诗歌与汉语新诗的关系
20世纪伊始,最先彰显“文学革命”实绩的就是白话新诗,而新诗运动又是从诗歌形式的解放入手。我们究其原因,古典诗歌与汉语新诗的关系,最终的区别还是在语言上。因汉语新诗更加灵活,细节描述能力更强,巧妙地留白就能让读者产生想象力,而古典诗歌做不到千人千面。同比古典诗歌一般单纯靠押韵、平仄等建立效果,汉语新诗则依靠一些细微的安排、节奏、停顿、反复等来实现。
另外,汉语新诗题材的丰富和探索的广度不是古典诗歌可比,当语言指向极其细微的对象的时候,绝对的规范就会显出掣肘。当前,汉语新诗处在高速发展期、成熟期,呈爆炸式发展,需要形式、技艺甚至思想上的准则对当下的无序和自我突破加以矫正。胡适曾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新诗应“不用典”“不讲对仗”,要“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要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论新诗》)。一些现代诗人们,几乎把胡适可以“不怎么样”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把美文筛掉标点符号、散句分行排列的也叫作诗。我们知道,除排律每首超过八句之外,近体诗有其固定格式和字句:律诗每首八句,五律四十字,七律五十六字;绝句每首四句,五绝二十字,七绝二十八字。诚然,新诗自由,但是这自由是否具有一个“度”呢?拿格式为例,汉语新诗可以不用拘于字数、长短,那么多少句才能算得上诗?多少字才能算得上诗?一句话算诗吗?一个字算诗吗?答案是肯定的,如今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诗已随处可见在当今的诗坛之中。
由此,人们感叹:还有什么不是诗呢!
与其我们在观念上提前作出设定,不如在作品创作上用力。比方说,抒情—亲情、爱恋、思念或者孤独,我们写的永远都是这些基本的感情,但感情永远没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诗艺上的问题,于是引申到古典诗歌和汉语新诗针对诗歌创作本身的处理所具有的关系。
汉语新诗发展壮大具有必然性,此时古典诗歌也进入低潮期。现代社会所伴生的各式各样的事物已经无法被古典诗歌现存的模块接受。古典诗歌的语言环境已经退化,其所强调的诗境也就无法接纳现代事物。从清朝统治结束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生活习惯、文化、建筑风格等都进入中国,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建筑逐渐被现代的高楼大厦取代,生活用品的科技化也让人们再也写不出“寒光照铁衣”或者“玉枕纱厨”这样的生活场景。又如,随着新时代女性地位的提升,旧式的闺怨题材已经不再适用于女性,如果刻意为了写诗再写一些闺怨诗,也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用现代生活场景入诗,也就没有古典诗歌特有的美感了。于是,有的古典诗歌写作者或找各种替代词掩盖,或寻求新的语言格式,最后终于开始了古典诗歌的“变法”,试图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中的代表诗人胡适从外国诗入手学习,不久就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其中有名的一首为:“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蝴蝶》)
从诗体方面来看,新诗无疑是对近体诗所进行的一场革命,并且是“暴力”的革命。胡适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留学日记》)要想让诗歌变成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种文化产物,就要实现诗由雅到俗的蜕变,让诗歌所用的语言和平时说话一样,人人能读得懂,人人能写得出来。于是,新诗以摧枯拉朽之势把近体诗打翻在地并宣告自己的地位,摒弃近体诗对字句、平仄、押韵和对仗的要求,从而使得新诗获得空前的自由,这种“自由”则让千百万人迅速地成了“诗人”。
古典诗歌的高度精练与汉语新诗的绝美艺术。季羡林先生曾指出:“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些古老的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神州文化集成》丛书)这就揭示了汉语词在语法形式和功能方面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汉语属于孤立语,没有形态变化;二是汉语里的词既具有表意的灵活性,又具有普遍聯系性和整体性特征。汉语词的表意的灵活性特征是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的。这两点在古典诗歌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在语言表达上不追求句子的完整性,它也可以没有主语、谓语、宾语,甚至就几个词语排列。然而,我们可通过语序这一汉语的重要语法手段和汉语所具有的重具象、重整体、重联系的意合特征来理解诗句的含义。例如,黄庭坚《寄黄几复》中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两句诗中,它们仅仅是几个意象的排列而已,两句诗各用三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组成,且没有主语、谓语、宾语之分。就像林间小路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看不到前面的路,却能走上正确的终点,同时让读者自己去解读,发现新的“近道”。由此可见,古典诗歌的语言凝练峭拔而又蕴意无穷,寥寥数语就可展现出一个无穷深邃和广阔的意象空间,使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一点,古典诗歌应用得可谓得心应手。
而汉语新诗因为它的表现多元化,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独属于它的绝美艺术,具有了新的美学效果:一是随社会发展不断给意象灌注现代意识,它使现代意象发展到一对多的关系,使其含义也不止一个,充满多义;二是让客观意象拥有倾向性,它让事实和具象物拥有情感、立场、认知,既能继承古典诗歌的凝聚美,也能承载现代社会不断产生的事物;三是在诗歌写作上突破了语法的禁锢,它完美地展示了词的兼类和借用,让同一句中的同一词可通用为不同的语意;四是发展语感上的陌生化,它重视陌生化的使用效果,用停顿、换行、空行、空格及标点来造就艺术美,发掘熟悉事物的陌生感,“规避”常识,排除一切熟悉的说法,对熟悉的事物保持警惕。例如: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
—海子《九月》
这首诗太过出名,也能看到很多解析,但我们观察的不是诗人将异质文化的意象和本土风景毫无斧凿痕迹地融合在一起,也不是意象之间的彼此呼应,造就空间感和曲折的韵律美,而是现代诗歌所有别于古典诗歌本质的运用,是其中运用词语表达的停顿变化来体现诗绪的节奏、情感的起伏,是现代诗歌的“多解”性,是发展技巧、修辞的思维理念,要远远胜过明晰诗歌本身的类别和概念。像海德格尔所说,我们生存在语言之中,诗歌恰巧是语言开出的最光彩夺目的那朵花。古体诗虽然璀璨,但此时已经不再适用,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注定必将衰退,而敢于放下诗词格律的限制大胆开始创作新诗,也代表着我们敢于冲破封建传统的枷锁,寻找新生活。
二、现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诗歌相比之前更边缘于学术了,这与诗歌跟现代社会之间紧密相连有关。严格说,这其实源于当下最流行、最容易进入大众视野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唯美、文雅但整体诗意有限的诗歌,长此以往,诗歌的文学性就被大大降低了,其中颇有知名度的当数汪国真先生的小诗。另外,现在各大网络平台也大多如此,具有相对的群体性,诗歌的下层被多方面展开,同以前相比,倒是广为人知了。例如: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汪国真《热爱生命》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诗人大肆使用“陌生化”手法,这样就会导致对诗的误解,认为诗就是不应该完全看得懂的,看不懂,也就有了神秘感。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凡是好的诗歌,都是可以被理解的。无论古典诗歌还是汉语新诗,广为流传的都有一个清晰的调子,经得起反复推敲,“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否能全部理解,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凡是不能理解的诗歌,都是可疑的。例如:
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只把我当成/一只趴伏在餐具上的甲虫/抒情的话语,同银器,咖啡杯,以及/刀叉,让白炽灯照出了/惨淡的阴影,一部分是性别/另一些,感觉是中世纪的古老巫术
—陈亭夫《波伏娃的来信》(节选)
在诗歌写作中,伪神秘导致自娱自乐的东西其实占比不少。坚信诗歌就是神秘的,倾力表达那种无从道明的体验的诗人,最容易坠入其中。他们炮制出一种看似合理,其实却不具备有效的神秘的逻辑,自以为靠无法解释来探求神秘的路径,有点儿像探索“宇宙”,预先设定了无穷无尽,最后干脆蒙住眼睛。这种自我欺骗,称为“无意识写作”,或者称为“汉语重构”,但这也是其最高级的托词了。
我们正视弊端,了解到诗人们的基数增加,各种流派应运而生,难免互相丑化、吹捧。在媒体主导文化的时代,商业化、娱乐化的信息甚嚣尘上,为其诗歌的所有方面寻找合理性。下面笔者收拢思想作几点总结:一是大众化、平民化诗歌的兴起已成燎原之势,二是诗歌商业化、娱乐化凸显发展趋势,三是上层诗歌的诗艺探索进程缓慢。这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所有的结果,因此大多诗人踏着步子按照前人留下的轨迹行走。
诗歌自古是承载社会功能的,是以文载道,有谈论社会和责任的义务,当诗歌降低维度到日常生活中时,就是将事实向经验和认识转化,但诗歌的立身之道不在被理解,而在被激发,通过对内心的发现来认识到自己隱藏的方面,让我们猛然一惊,更加清晰地看待自己和世界。
三、诗人与诗歌的关系
从诗歌的源头诞生的民歌和童谣看,诗歌具有反映现实与对现实的纵深拓展的义务。同时,诗人以凸显现实之间主客体的互渗关系为雏形,在更高和更深层上进行思维建构,用非现实反映现实,融入现实,成就物态化的作品。需要客观基础上的主观,而不是平生的主观,是诗人对诗歌更高位的激活和表现。
从前,诗人对古典诗歌一句一语的经营就像攀爬雪山,一个词就是一次冰镐的楔入,一旦哪个词用得不好,都可能坠落,一毁全诗。现如今,那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的写作惯性占比失调,这是现代诗既承载着诗人描写生活的特定瞬间,更包含了诗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文章》)的感受奥妙的原因。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越到顶峰的诗歌越可能是“多解”的,或者越可能是情真意切、感染众人的,如诗仙李白所作的《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一句,简洁明了,家喻户晓。
诗人的道路,其实也是其心中诗灵的成长历程。当诗人写出第一批成熟的诗后,其马上面临如何发展的局面,于是,具有总结性特点的人生节点又赋予诗人突破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说,诗人对诗歌的思考,使诗歌最终能够攀上思想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