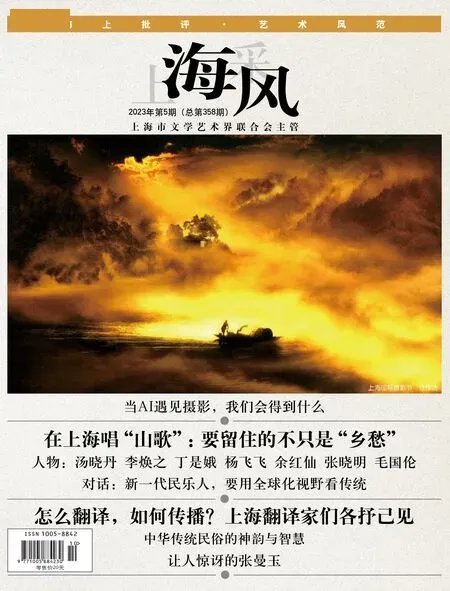在上海唱“山歌”:要留住的不只是“乡愁”
2023-10-11
■ 本刊记者 秦 岭

在芦苇深处劳动久了,人们唱一句甜美的山歌,不仅可以相互关照,更能怡情悦性
在上海本地人的口语中,“唱山歌”可以涵盖一切与歌唱有关的行为。但如果问,什么样的“山歌”是“上海的山歌”?不同的人可能就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也许是“一根紫竹直苗苗”的江南小调,也许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摇曳之音,抑或上海港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口耳相传的儿歌童谣,田间地头劳作时的田山歌,乃至哭丧哭嫁、乞讨叫卖的各种吟唱调……这些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民间歌调,根植于沪上生活的不同侧面,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对上海“山歌”(民歌)的完整记忆,其中,上海港码头号子、青浦田山歌、崇明山歌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青浦农村的妇女们到农田去割草,满载而归(摄于20世纪60年代)
何为上海民歌?其意义和价值何在?保护传承状况怎样?如何向年轻人传播、推广?这是本期“热点”试图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海民歌,作为中国民间民族音乐,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讨论文化传承发展问题时的一只“麻雀”,一个具体而微的标本和切口。
壹
上海民歌,顾名思义,指的是产生并流传于上海地区的民间歌曲。根据语言的地域特点,上海民歌可分为江口语音色彩区(崇明、横沙、长兴地区等)、东厢语音色彩区(川沙、南汇及奉贤东部地区等)、西厢语音色彩区(嘉定、青浦、金山、松江、宝山及奉贤西部地区等);根据体裁类型,又可分为劳动号子(以杨浦为代表,如上海港码头号子等)、田山歌(以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地为代表,如青浦、松江的吆卖山歌、落秧歌,金山的耘稻山歌、奉贤的大山歌等)、小山歌、小调、儿歌和吟唱调(如哭丧歌、哭嫁歌、乞讨歌、叫卖歌)等。作为江南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的人文地域、风土人情赋予了上海民歌清丽柔婉、细腻平朴的特性,而上海五方杂处、兼包并蓄的城市文化也为上海民歌的传承发展涂抹上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
著名民歌理论研究专家江明惇于20世纪80年代参与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上海卷》中,收录了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上海民歌800余首。江明惇曾历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也曾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对上海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倾注过大量心血。20世纪50、60年代,正是“音乐民族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1958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大二学生的江明惇,转入当时学院新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半工半读”,他和同学李民雄、滕永然等一起,扛着录音机,到田野里去,到人民中去,搜集、整理、记录下民间音乐丰富而珍贵的素材。他磨穿无数双鞋底换来的民间音乐录音档案至今还庋藏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档案馆里。
“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民间文艺是与这源泉距离最近,关系最亲密的艺术。”江明惇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价值和意义。现任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的郭树荟教授在刊载于《人民音乐》的《唤起大地之歌的回声——江明惇先生学术研究侧记》一文中记述,江明惇先生说他们当年“一个录音机一个话筒”去采录上海港码头工人号子,“老工人到仓库抬米,一袋100公斤,两个人抬,那种相合交替的声音力量,那种现场感,非常高昂,非常激动。虽然词少重复多,音乐也很简单就几个音,但是那种豪情万丈的自信是难忘的”,不曾身处民间音乐发生的场景,没有面对面地和劳动者接触,没有被深深打动过,是无法真正体会这些唱词背后的豪情的。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民歌就是人民之歌。社会生活和劳动实践是民歌产生的土壤,也是民歌纵情抒写的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歌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心灵的写照,也为文艺记录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代提供了重要抓手和生动素材。
就以先前提到的上海港码头号子为例。1870年以后,伴随着旧上海“远东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工业城市的发展,上海码头的货物吞吐量急速扩张。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这些码头工人以“五方杂处”的融合之势,创造出了与内地建筑、农渔类的号子迥然不同的上海港码头号子。这些号子生动记录了上海开埠到20世纪60年代一百多年间码头工人的生存状态,是码头搬运这一产生在特定情况下的职业在同一场景不同年代的缩影。作曲家聂耳曾在上海港码头与搬运工人一起劳动,以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码头工人歌》,淮剧《海港的早晨》和据此改编而成的京剧《海港》中,音乐和唱段也都是以上海港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的。透过码头号子铿锵质朴的节奏,淳朴高亢的呼喊,可以切近地感触到码头工人的心声和近代上海工人阶级的昂扬斗志和奋发的精神面貌,而这也正是上海这座“靠海吃海”的城市不断进步发展的根基。

2005年,青浦区文化馆工作人员对青浦练塘泖甸田山歌歌班进行了再次普查摸底。从左至右分别为:张永联、王叶忠、吴阿多、吴惠其、周岳均

2007年7月,青浦练塘东团田歌手在稻田中劳作并演唱大山歌
田山歌亦是如此。所谓田山歌,是指那些产生和流传于稻作水田生产劳动之中,主要以表现稻作生产和水乡生活风情为内容的山歌形式。根据《上海田山歌》一书介绍,上海田山歌的历史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七八千年前,当太湖流域开始有了原始的栽培水稻农业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吴越地区就已经产生了田山歌的原始形态。到了20世纪初叶,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当时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一些郊县中,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田山歌演唱班子,可以从“东方日出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稻花香里的田山歌显然不可能成为上海近现代崛起的城市文化的代表,它属于上海文化中的乡土一脉,展现的恰恰是五光十色的都市文明之外,沪郊农民的寻常生活——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部分往往为斑斓霓虹所掩盖,却又是这座城市历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就像《上海田山歌》一书的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伟明指出的,根植于上海农村的上海田山歌虽然很少融入现代城市居民生活,却是对古老传统和悠久历史的回忆,“聆听田山歌嘹亮悠远的曲调,我们似乎看到了被六千年崧泽之火照耀的勤劳朴实的上海先民,在稻田、河岸边创造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代代相传、口口相承,以田歌手旺盛的创造力和表达力将一曲曲清新、柔美的歌谣传唱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怀疑:上海民歌中所展现出的文化弧光,是这座城市文化自信的重要“来路”——知道“来路”,就知道了“你是谁”,知道“你是谁”,就能更明晰地看到未来的方向。
而“知道”是需要大力迈出的第一步。
贰
正在热播的《乐队的夏天III》,让很多观众“知道”了蒙古族的安达组合、壮族的瓦伊纳乐队,“知道”了蒙古族音乐和壮族音乐的某些“味道”。让我们暂且放下这些音乐性的问题:这两支乐队对于蒙古音乐、壮族音乐展示了多少,展示得好不好,艺术价值究竟如何评价,仅就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谈一谈民间音乐元素的“大众传播”,那么这些年来,少数民族音乐人在对本民族音乐的宣传和弘扬上,其努力确实收获了不错的效果,在相当范围内,为其民族音乐的大众认知度与大众认可度打开了当下的通路。
那么上海民歌呢?有没有这个方向上的例子?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2020上海夏季音乐节“山水田园——龚琳娜与乐队”专场音乐会上,著名歌唱家龚琳娜就曾为上海听众演唱过一首改编自崇明山歌的歌曲《潮水娘娘》,将自己从原生态歌手那里学来的韵味,化作自己的表达再传递出来,有观众表示听来“止不住流泪”。2022年9月,她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行走的声音”国风音乐会,又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她还在抖音号上教网友们学唱《潮水娘娘》,“榔头开仔花勒归”一句衬词,她反复教唱了好多遍。随着这首歌逐渐走红网络,不少年轻人也由此知道了崇明山歌的存在。
“五更鸡鸣鹁鸪啼,丫头嫁了太湖西,青山竹园望不见,浪白涛涛哪得归……”《潮水娘娘》的原名是《五更鸡鸣鹁鸪啼》。“看到《五更鸡鸣鹁鸪啼》这个名字,你会不会想要去听它?”据《解放日报》的报道,为这首山歌重新“描眉画眼”的,是沪上知名音乐人彭程。2015年,彭程受上海天地世界音乐节的邀请,挖掘、改编上海的本土民歌。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了这首《五更鸡鸣鹁鸪啼》。因为听歌的时候脑中冒出了“潮水娘娘”的形象,他便挥笔写下了这个名字。随后,他邀请崇明山歌非遗传承人张顺法、张小末兄妹在录音棚录下了这首原生态民歌,重新剪辑、编曲,打造成了带有民歌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民歌口口相传,很多连谱子都没有,只有大致的节奏和音调,这不符合当下的音乐欣赏习惯。我需要先把它们归纳成相对固定的旋律,再进行编曲、配器,希望能变成好听的音乐。改编的目的是好听,吸引大家听下去。”
龚琳娜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很喜欢,就去打听原唱者何许人也。“我原来以为上海是没有民歌的,就特别想找张小末去学这首歌。我找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萧梅老师,她告诉我说,你只能找她哥哥张顺法了,张小末已经去世了。我好伤心啊!”于是她又专门跑去崇明,登门拜访张顺法,向他请教正宗的唱法。
有意思的是,《潮水娘娘》小小地“出圈”之后,澎湃新闻的记者采访了张顺法,问他如何评价龚琳娜的演唱。张顺法说龚琳娜的嗓子非常好,就是“词唱到后来不大对,缺了崇明的味道,音有时不在调上”。张顺法还告诉记者,自家几代人都擅长唱歌,从小父母哄他们睡觉就是哼歌,“我们会讲话的时候已经会唱歌了,都是耳濡目染”。然而现在,长辈凋零,最会唱歌的妹妹张小末早逝之后,能唱好崇明山歌的人愈发稀少。“小孩音不准,大人味道不对”,张顺法的孙女还能哼两首,孙子不喜欢,“不愿意学”。
《潮水娘娘》是上海民歌传承传播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但同时也折射出了上海民歌在当下所面临的很多课题。酒香也怕巷子深,首先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上海民歌的丰富和精彩。“惊讶地发现”在新闻的表达上固然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文化的传承来说,却多少透露出遗憾。而艺术家深感兴趣,老百姓却“不愿意学”,冰火两重的背后则是传统“民歌”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体验到的尴尬和冲击。
“民间文化一定是跟民俗生活的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服务于民间的习俗、体现着民间的审美,当我们在谈论民间音乐的保存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它的民俗属性。”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遗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的郭树荟说。在《来自中国的声音》一书中,她就曾对民间音乐的不同特质与其所依附的生态土壤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入而详实地考察和分析。“比如说江南丝竹,在市中心的茶馆里演奏的丝竹乐和在乡间婚庆中演奏的丝竹乐会是一样的东西吗?它们都叫江南丝竹,但它们的语言语汇、风格特点、音色音响却有很大的区别。”音乐产生的土壤变化了,音乐活动发生的场域变化了,音乐本身势必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文明的渗透催化影响,动摇到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活根基的时候,传统的民间文化必然面临消退、萎缩的命运。成为‘非遗’本身,就已然充分说明了问题。现在每个区都有相应的传承人,但传承人趋向老龄化的趋势也确实不可忽视。”

2018年,由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组织、策划、主办的“江南传统音乐及世界传统音乐非遗经典传承联合展演”现场。上图为崇明山歌,下图为青浦田山歌
这些年来,上海市文联、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群众艺术馆及各区县文化部门围绕上海传统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工作。2021年,青浦区人民政府、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遗保护与研究中心首次举办了上海市民文化节江南民歌大赛,2022年则在此基础上举办了“民歌·上海”江南民歌大赛采风活动,在未来也将继续采用一年做民歌大赛、一年做采风研讨的形式推广传播江南民歌。当下,新一届的江南民歌大赛的预赛正在各区紧锣密鼓的开展。郭树荟是江南民歌大赛的评委之一。“我们将民歌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类别:传统民歌、新编民歌以及民歌风格的创新创作。这也是当下民歌传承传播的三个不同的层级与路径。”民歌的田野采集、整理、研究工作,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一直都在坚持,“但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做的更多是学理上、学术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民间音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有很强的即兴成分,演唱者本身就是编创者。如果缺少了有生命力的编创,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那民间音乐就势必逐渐走向衰亡。创作力是很重要的,”郭树荟强调,“现在很多人也在尝试,加一点电声,利用多媒体,或是在舞台表演中加上一点原生态的道具等,我觉得这些尝试都可以探讨。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从民歌的内核上,从艺术本质的层面入手。”
叁
“码头工人来四方耶,号子自有南北腔,哪里号子最好听哟,比比来唱唱哟,比比来唱一唱哟。嗨咗、嗨咗、嗨咗……”2021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江南民歌大赛上,来自杨浦区的男声小组唱《码头工人来四方》力压群英,获得了“最江南”演绎奖第一名。这首歌是2009年杨浦区文化馆为迎接世博会创作的情景剧《码头号子》中的一段,描写来自四面八方的码头工人聚在一起唱号子比赛的场景,曲作者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聘专家、作曲家侯小声。侯小声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上海民歌的挖掘和创作。2012年,侯小声曾携四幕田歌音乐剧《角里人家》登上了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博得观众和专家们的一片掌声。由他创作的上海民歌《上海谣》也被爱好者广为传唱。

朱家角歌班集体合影
“我们不但要看到历史、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未来,我们该怎么做,做些什么。”侯小声说,“上海民歌从原生态走向创新的这个过程,需要我们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丰富它、改造它、拓展它。好听的部分继承下来,普通的、不好听的部分扬弃掉,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从传统走向时尚。”就比如“码头号子”,它虽然大多是“吭呦啰”“嗨唷嗨”之类的虚词,但音乐风格犹为鲜明,充满了上海港口音乐的特色元素,是上海开埠以来最经典的民间音乐之一,然而,在目前反映上海文化的影视、歌曲和舞台作品中,却很难听到这种音乐。“如果‘码头号子’能经常被运用到反映上海文化的各种文艺作品中去,它被人们认识和了解的机会与价值,肯定会比仅被作为‘非遗’保存起来要多得多、好得多。”
“知道”来路,所为终究还是“创造”未来。
彭程也有差不多的看法。“民歌在当下也要发展。时代到了一定的阶段,人的听觉会不满足,这个时候就需要改变和推进,这是音乐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认为,对非遗音乐的改编需要谨慎,带着敬畏之心,同时,也必须有敢于尝试之心,“就像一些饮料里会加入茶的味道,不爱喝茶的年轻人也许喝着喝着会突然想要尝一尝传统的茶。大众审美兴趣需要引导,让濒临消失的非遗民歌通过改编的方式重新流传,吸引大家去关注、保护和珍惜,这也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责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民歌。这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吃透生活的本质,活用艺术的语言,这本身就是民歌过去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如此蓬勃繁盛的原因,它也应该是,且必然会是传统民歌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方法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