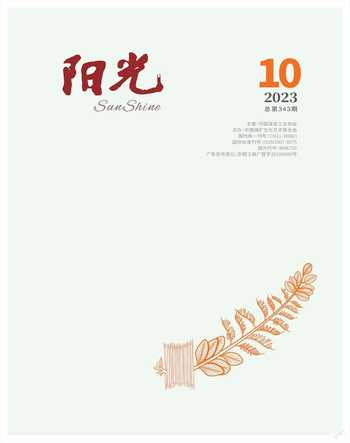梦回大院
2023-10-08章丽
章丽
“闲坐小窗读红楼,不知春去几多时。”时光匆匆如流水,很多东西被遗忘在了岁月里,但也有一些东西却永远地拓印在了我的心中。譬如家乡的食物、家乡泥土的芬芳,譬如家乡小镇的大院。它们都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无数次让我热泪盈眶。
我家乡的小镇,原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一条敝旧的土公路,仿佛一条蜿蜒的河道,自西向东贯穿整个街道。街道两旁种着梧桐树,叶片上常年覆着一层厚厚的灰,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灰白的眉毛。脱了皮的树干上有顽皮的孩子用小刀刻下的深深浅浅的伤痕,痂落了,疤还触目惊心地留在那些老树上。
小镇沿街分布着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院子,有粮站、卫生院、油坊、供销社、食品站、建筑队、信用社、乡政府和学校等。这些院子都曾是乡里各个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它们都曾拥有过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都曾掷地有声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那些由石头和泥沙混合砌成的围墙大院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现在那些大院残破不堪,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繁华与风采。每次当我推开那一扇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时,热气腾腾的往事便从那些断瓦残垣的缝隙中喷薄而出,顷刻间涌进我的脑海,我又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卫生院
在我十九岁之前,我和哥哥一直随母亲生活在乡卫生院的大院里。这个大院承载了我太多太多的童年回忆,以至于我现在每每梦回大院,它还是当年的模样。
时间倒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排砖墙青瓦的房子坐落于卫生院大院的正中央。前排房屋是医院职工宿舍,住有十来户人家。后排房屋从左到右依次为杂物室、药房、问诊室、治疗室、病房和妇产科。
我很少到后排的医疗区去玩,因为那里常年充斥着难闻的来苏尔的味道。医生手中操作的那个玻璃针管落到白瓷托盘上的声音,“咣当”一下,让人心生畏惧,仿佛接下来屁股上要挨针的人就是我。
如果说,后排医疗区的天空是抑郁灰暗的话,那么,前排家属区的天空则是温暖明朗的。每天清晨,母亲和其他屋的女主人们一样,早早地将自家的蜂窝煤炉搬到了廊前的空地上,劈柴,生火,烧水,煮粥。大院的每一天都是从生炉子燃起的缕缕青烟开始的。
晨霭消散后的上午,跛脚的院长双手紧握大剪刀,正在聚精会神地修剪着屋前那一排排齐腰高的万年青。随着那“咔嚓、咔嚓”声响起,万年青树上新长出的绿叶纷纷掉落下来,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新鲜草汁的味道。
那些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万年青,挨挨挤挤地站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母亲把清洗干净的衣服鞋袜摊晒在万年青树上,有风吹过,衣角翩跹。
阳光透过密匝的万年青树,漏下了无数个白亮的光斑。几只老母鸡卧在万年青树下的阴影里,不时地在那灰坑里翻个身,打个滚,拍一下翅膀,然后眯缝着眼睛,仿佛睡着了。当我经过那些正打着盹的老母鸡旁边时,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蹑手蹑脚地走近它们,然后猛地扑上前去跺一下脚。吓得那些迷迷糊糊的老母鸡魂飞魄散,使劲扑腾着翅膀,飞也似地跑到了不远处的围墙边,扭过头来盯着我,“咯咯哒、咯咯哒”地叫个不停。
卫生院大院的围墙边种有很多芙蓉花,我的家乡人称之为“大碗花”。古有诗云:“城头尽种木芙蓉,秋日盛开似锦绣。”一到秋天,那盛开的大碗花让那破旧暗沉的围墙一下子鲜亮起来了,连老母鸡都喜欢去那开满大碗花的围墙边散步。
母亲在大碗花旁边的荒地上开垦了几垄菜地,种了各种蔬菜瓜果豆类,保障了我们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蔬菜种类的丰富性。即使是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母亲也能从那盖着厚厚雪被的菜地里铲回来几棵鲜嫩的黄心菜,洗净后和豆腐一起放到煤球炉上的锅中焖煮。然后,一家人围坐炉边,就着那“咕嘟咕嘟”冒着香气的热锅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是我家一个极其寻常的生活场景,也是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最寻常的生活场景。海子曾说过:“粮食和蔬菜,这才是生活。”而我们的生活,也正是由这些看上去极其庸常的琐细,累积出了诸多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虽然我们大院的邻里之间也常会为你家的鸡偷吃了我家的菜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得面红耳赤,但当他们在听到后排医疗区突然传来“有人喝农药了”的大喊之声后会赶紧奔赴抢救现场,自觉地担负起救死扶伤的职责。
时光荏苒,我离开卫生院的家已有数年了,直到现在,每每忆起那十八年的大院生活,心底总会涌起浓浓的温情和暖意:它们都已在我的心中幻化成了触手可及而又刻骨铭心的诗情和画意。
粮 站
我的家乡是稻米之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均以种植水稻为生,卖粮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农民种的粮食除去一家老小的口粮外,余下的都会拉到粮站去卖,然后用这卖粮得来的钱去买油买盐、给孩子交学费、给老人看病、给家人添置一两件衣裳,还要购置化肥农药等。所以,每到收粮季节,各个乡镇粮站门口都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前来卖粮的农民,有的用肩挑,有的用板车拉,路程远的用拖拉机运。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粮站都可称得上是农民心中名副其实的“希望驿站”。他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躬身耕种于脚下的这片黄土地,只为换取作为一个农民该有的尊严和体面。
我们乡粮站与卫生院仅一墙之隔,站在我家门前的走廊上,可以看到粮站大院里那些神似蒙古包的圆顶粮仓,甚至可以听到那些偷吃粮食的麻雀们欢快的叫声。
粮站大院的北边是食堂,食堂外有一口井。我去粮站大院玩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人在井边打水扯摇轱辘发出的“吱呀吱呀”的声音,仿佛一个老人背着沉重的包袱,明明走不动了,还皱着眉咬着牙喘著粗气努力地往前走。随着井轱辘摩擦声音的渐渐停息,一个装满水的木桶摇摇晃晃地从那黑黝黝的井底升到了井沿边。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月里,那甘甜清透的井水曾是我们生活的重要源泉。它们从土地的底层经过人们的挖掘,再通过人们的肩膀,来到了千家万户的水缸里,和粮食蔬菜一起慰藉着每一个清汤寡水的肠胃。
我家所在的卫生院大院里没有井,所以我母亲每隔几天就要担起水桶去粮站大院挑水。那条连接两个大院的土公路上,留下了母亲挑水时不慎洒下的井水和汗水。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粮站大院玩,因为那里有跟我一般大的小伙伴,有可供我们尽情疯跑的大片的水泥场地,还有那些覆盖在粮堆上的灰绿色的雨布。无数次,我们爬到那高高的粮堆上面,然后再从那粗糙厚实的雨布上滑下来,就像城里的孩子玩滑滑梯一样。没几天的工夫,我的裤子后面就被雨布磨破了。晚上,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一边嗔怪着我,一边用同色系的布块将磨破的地方仔仔细细地缝补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粮站渐渐丧失了它意义非凡的职能,并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关于粮站大院的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的种种记忆终被隐没在了时光的大幕里。唯有那清洌洌甜丝丝的井水,和着那吱呀作响的轱辘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刻度。
供销社
作家毕飞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每天早上,玉秀都要到菜市场买菜。买完了,并不着急回去,而是要利用这一段空闲逛一逛,主要是逛一逛供销社。”
供销社对于童年的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观光场所,同时,它还像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香增色。
我们乡的供销社位于卫生院的斜对面,它也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临街的一排房子是各个门市部,有的专卖农机具,有的专卖农药化肥,有的专卖日用百货。
我最喜欢去的是日用百货门市部。每次放学路过那,我都要和同学们一起溜进去,隔着那半人高的玻璃柜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流连忘返。当然,有时我也会理直气壮地去买一支铅笔,或一个本子,或一瓶蓝墨水,或者就像毕飞宇笔下的玉秀一样,什么都不买,只是进去逛一逛,看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闻闻那些糖果好闻的味道。
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帮家里打酱油。尽管母亲每次给我的钱都计算得非常精确,但每次总会多个三五分的,那多出来的三五分便由我自由支配。于是,每次我都是兴冲冲地捧着酱油瓶直奔供销社。售货员接过我的瓶子,走到柜台里面角落的一个大缸前,拿起量匙,舀了一匙又黑又香的酱油,对着那插着漏斗的瓶口灌下去,一匙刚好装满一瓶。
我把钱放在柜台上,那售货员把钱丢在一个抽屉里,并不急着找我钱,而是径直走向柜台上那个大玻璃瓶前,从中抓出几个花花绿绿的水果糖,连同酱油瓶一起递到了我的手中。我把水果糖塞进衣服兜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剥开一粒糖果,放进嘴里,尽情地吮吸着那丝丝甜蜜。每吃完一颗糖,我都会把剥下的糖纸铺在桌上用手抹平,然后小心翼翼地夹在书里。收集糖纸和火柴盒皮,是童年的我们乐此不疲的一项课余爱好,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
平日里的供销社并无多少顾客,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观光者”。但一到腊月,供销社里则显得格外热闹,大堂里挤满了前来购物的人们,我和母亲也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母亲对售货员说:“麻烦给我称十斤红糖。”只见那售货员熟练地从玻璃柜台底下拿出两张报纸,铺在柜台上,然后把称好的一斤红糖倒在报纸上,熟练地将其包成一个三角锥形,再从柜台旁抽出一根稻草绳将其捆扎好,最后在三角锥的顶部夹上一小块红纸。如此动作重复十次,母亲买的十斤红糖就这样包好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人们只需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的商品。供销社和粮站一样,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物质生活越來越丰富的今天,供销社俨然已成明日黄花。但那琳琅满目、五彩斑斓的玻璃柜台,依然在我的记忆中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和光芒。
章 丽:合肥市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2019年创建个人微信公众号“章小皖”,发表原创散文近百篇,其中有多篇刊登于各类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