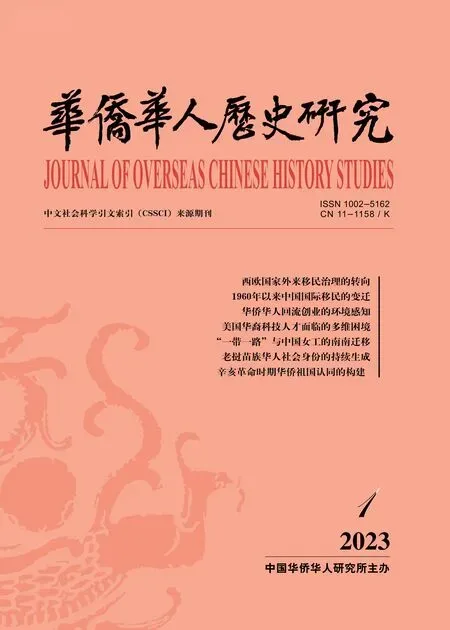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与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
2023-10-08潮龙起李朋飞
潮龙起 李朋飞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冲击下,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华侨的经济实力及其价值,从而改变了以往敌视华侨的态度,不再视华侨为“天朝弃民”,而是看作大清国的“臣民”,并在政策和行动方面采取以下举措来保护和利用华侨:遣使设领,保护华工,劝捐官爵,引导华侨回国投资,发展华文教育,筹建中华总商会,制订血统主义国籍法,引导华侨关注并参与家乡、宗族之外的中国事务。[1]清政府驻外领事官员也在侨社中积极倡导和推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导向的“孔教复兴运动”,推动华侨对中国传统文化效忠的国家意识。[2]严格来说,这些侨务措施和活动并不是为了塑造华侨对近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但为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以来,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在抵御外来侵略与创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和知识精英动员社会大众的有效思想武器。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也受到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作为反叛者和流亡者,因缘际会,几乎同时出现在华侨社会中。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为取得华侨的支持,改良派与革命派都通过创办报刊、游埠演说、兴建侨校等方式,向华侨揭露清政府的颟顸无能及其所导致的西方列强对祖国领土与主权的不断侵犯,不断塑造华侨的祖国认同意识和情感倾向,将离散到世界各地的华侨整合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离不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话语动员,正如王赓武先生所言,就海外华侨来说,“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他们能揭示和证实华人一切苦难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一种从外部训出的民族主义。”[3]颜清湟也指出,“19世纪末叶,如果没有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子莅临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运动可能不会发生。”[4]
鉴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及其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海内外侨史学界一直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不少研究成果既有对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性质、表现形式及其局限性的宏观论述,[5]也有对不同时空背景下华侨民族主义的具体探讨。[6]我们大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把握这些成果。第一,在华侨方面,相关研究探讨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行动较多,如捐款捐物、回国参加起义等,而探讨华侨民族主义情感和思想的相对较少;第二,在中国侨务方面,这些论著多关注晚清政府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以及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侨社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但对华侨动员所使用话语的探讨相对较少。实际上,一些学者尝试分析华侨祖国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侨务政策、文化背景及媒介传播等问题。[7]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跨国民族主义视角探讨了清政府、改良派和革命派等政治势力构建华侨祖国认同所采取的话语和文化策略。[8]但总的来说,从话语和思想的层面分析和阐释改良派和革命派华侨动员的研究,还较薄弱,成果并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从认同建构和华侨动员的视角,通过梳理辛亥革命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等史料,探讨这一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如何运用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来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并将他们吸纳到祖国政治变革的实践中。
民族主义具有对内凝聚、对外区隔的功能。关于民族主义的类型,凯拉斯(James G. Kellas)从民族凝聚力的构建要素将其分为三种,即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和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凯拉斯指出,不同于族群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强调共享的文化在构建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9]郑师渠认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10]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纵观人类历史,民族的振兴无不以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为保障,而民族的衰败也往往以民族文化的沉沦为预兆。辛亥革命时期,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认识到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中国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中华文化对于构建华侨对祖国认同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试图从这几方面对华侨开展动员。
一、推崇与弘扬儒家文化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孔子从学者身份逐渐上升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享受着历代王朝的尊崇和祭祀。文庙作为祭祀孔子的神圣场所,发挥了宣扬引导正统文化和履行国家教育职能的双重作用,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
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通过号召华侨在侨居地创办华文学校、纪念孔子诞辰、倡建文庙(孔庙)等活动,积极构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认同。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劝勉华侨兴办华文学校时,于《清议报》上发文强调:“若其中土孔子之教,敬天而爱人,尚公而亲亲,忠孝信义,爱国亲上,及四千年之礼俗史事,尤吾国人所宜不忘而熟讲者也”。[11]1908年,《南洋总汇新报》先后刊登了改良派伍宪子和徐勤在香港圣诞纪念会的演说辞,论及建立孔庙的必要性:“然其大纲领,则必在于先建孔庙。不佞曰:建筑孔庙,为孔教普及法之最善,又为速孔教进行法之最良”[12],并指出孔子圣诞纪念活动对海内外华人的重要性:“故一年中所谓大日子者,除正月元旦,守孔子行夏时之制;三月清明,守孔子慎终追远之意;五月端阳,守孔子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之义……今远识之士,特倡孔诞纪念会。其事诚为我中国薄海内外,所最重大之义举也”[13]。次年十月,围绕孔子诞辰纪念和孔庙兴建等活动,该报又先后发文数篇,劝告华侨休业庆祝孔子生日,号召华侨仿照祖国建立孔庙,颂扬“二十世纪的孔子”是国民信仰的孔子。[14]可见,改良派借助兴办华文学校、纪念孔子的相关活动,向华侨阐述中华民族尊孔崇儒的传统文化,焕发其对儒家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向慕,从而使其对中华文化产生真切的归属感。
与改良派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积极肯定不同,革命派在动员华侨时往往持批判态度。如1906年,《民报》刊载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他坚决反对孔教,认为孔教使人滋养富贵利禄的思想,不利于革命行动:“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15]反清革命人士秦力山在缅甸宣传革命时,认为儒术顽固维护封建君主统治,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不得不运用革命暴力手段打破这一状况:“欲中国人为独立之国民,则非弃绝儒术不可;欲中国人之废弃儒术,则非血染亚东不可”。[16]可见,在对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时,改良派强调华侨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属于精英分子,与革命派相比,他们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较多;革命派则大多出身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受儒家精英文化的影响较小,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的革命中,极力批判这种维护封建制度的儒家文化。
但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革命派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1909年,《中兴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孔子理当纪念,因他是中国民族主义之伟人,支持民族革命:“诸君敬孔子乎,诸君当知孔子者实我国羲、农、黄帝以来之民族主义所产生之一伟人”。[17]革命家卢信在《自由新报》发文,用孔孟学说的“夷夏之辨”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支持排满革命的:
孔孟所尊之君,为同种之君乎?为夷狄之君乎?孔子作《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诸侯有用夷礼者则夷之,以示不与同中国也。夫用夷礼小事耳,而孔子犹深恶痛绝之如此,况以我神明之裔胄,而为辫发夷虏之顺民!律以《春秋》之义,则满洲贱虏,非孔子所必排者乎?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以数千年相传之古国,变为满虏之私有物,岂非孟子闻所未闻者乎?夫夷夏之界不可不严,则满洲政府不能不排,如以排汉为违悖孔孟之遗训,是并孔孟之遗训而非难之矣。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尊崇孔孟者,乌可以臣事夷狄之君乎?[18]
可见革命派的华侨动员,多借用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夷夏之别,以文化界定“我者”与“他者”,塑造儒家代表人物孔孟为民族革命的伟人形象,试图利用孔子等圣人的声望以获得华侨对其排满革命主张的支持,正如颜清湟先生所言:“文化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孔教复兴运动,在不同时期被各种不同的团体用来促进他们的政治目的”。[1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派的这一文化观有利于动员当时华侨对反清革命事业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讴歌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爱国进取的民族精神
充满情感魅力的民族历史,最易打动民族成员的心弦,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都通过大众熟悉的文学艺术作品、历史著述来表达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华侨对祖国历史的自信与认同。
(一)讴歌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特别推崇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如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以“汉唐”文明为象征的“黄金年代”等,皆被民族主义者视为民族历史的辉煌往昔。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就指出:“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也,其开化远在希腊、罗马之先。二千年来,制度文物,灿然熠燿于大地,微特东洋诸国之浴我文化而已。欧洲近世物质进化,所谓罗盘针、火药、印刷之三大发明,亦莫非传自支那。丐东来之余沥,中国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认矣。”[20]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则感叹:“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与当今中国被迫割地赔款的惨境形成鲜明对比,勉励海内外华人勇担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21]
革命派在华侨动员时,也不时指出中华民族往昔的辉煌历史。革命家陶成章撰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于1904年在日本东京发表。该书在其叙例八则之一“读中国史,当知中国人文”中指出:“我中国为世界文明之一大祖国,其文化之发达,绍基于皇古,葱隆于唐、虞,盛于周季,而光耀于汉、唐。……漪欤软美哉,我中国也。”认为中国曾创造出远超世界各国的璀璨文化和先进发明:“我中国有二帝三皇之古训,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四千年绵延不绝之历史,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周季诸子百家之学说,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印度输入之佛教,发挥而光大之,以造成一新奇之哲理,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流传五千年单字单音特别之文字,世界莫能及。以言乎文化,若是其隆盛且久也。可爱哉,我中国!我中国有医学、历学、数学、音乐之发明,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火药、火器、诸机械之发明,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地震机、浑天仪之创造,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指南针、罗盘针之创造,世界莫能及。以言乎艺术,若是其早且久也。”[22]《中兴日报》也指出:“我华侨对于外人非自信曰唐人,其在内国非自信曰汉人……试问我华侨所谓汉人唐人者其始基立国于何方乎?我知我华侨必曰:汉人唐人,立国中华,堂堂中国,中外咸知,无容置辨也。”[23]
可见,“三大发明”“汉唐盛世”等蕴含的中华历史文化也是民族主义者用来增强华侨民族自信、塑造华侨民族认同的重要话语资源。
(二)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应有之意。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犯中国的严峻形势下,民族主义者大力宣扬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族侵略斗争的历史中为捍卫民族利益而不懈奋斗甚至牺牲的民族英雄,激励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国人要以他们为榜样,为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贡献力量,以抵御外来侵略。
改良派致力于发掘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以激起海内外华人内心的民族情感,鼓励其勇担救国复兴的重任。1910年,《南洋总汇新报》发表社论,指出当前中国形势岌岌可危,号召大家仿效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人物:“西晋之亡也,有刘琨、祖逖,击楫中流,闻鸡起舞,晋尚可偏安于东;北宋之亡也,有宗泽、岳飞,渡河三呼,背涅四字,宋尚可残喘于南。”争做救国英雄,以拯救亡国危机。[24]
革命派则注重宣传中国历史上汉族英雄人物征服或反抗异族的大无畏进取精神,激发华侨的民族意识,鼓舞其反清革命士气。1906年,章太炎发表演说,强调海内外华人要有汉人的历史自信,敦促大家学习民族英雄所拥有的“俊伟刚严的气魄”,并指出最可崇拜的抗击外族入侵的两个代表:“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认为二者“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25]
革命派在动员华侨时,还经常引用闽粤侨乡两个反清英雄代表——郑成功和洪秀全的事迹,追忆华侨被迫出洋的原因,借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章太炎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革命歌》就以郑成功光复明朝为例,奉劝华侨学习他的反清斗争精神,牢记自己的汉族身份以及种族仇恨,舍身投入排满革命:“再告海外众华侨,天涯万里总同胞……人人都敬郑成功,成功扶汉故称雄……一念祖宗二念死,胸中雪亮如观掌。”[26]1908年,《中兴日报》刊文描述汪精卫在新加坡的演说现场:“精卫先生演说,将我闽粤人所以流寓海外之原因,发挥尽致。知我祖宗皆缘受满虏残杀,不得已而避地于此,并举我汉族拒满虏之两英雄,一为闽人郑成功,一为粤人洪秀全故事。警声言之,慷慨激昂,闻者泣下。当是时,鼓掌顿足之声,如雷贯耳。盖我同胞于此已各怀一愿作郑成功、洪秀全之想,恨不勠力同心,即灭此满虏而朝食矣。”[27]
可见,上述民族英雄虽历经年代更迭,但其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他们的英勇事迹被各派政治势力不断追溯。在华侨动员时,这些民族主义者往往借助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将这些民族英雄的事迹重新诠释为充满情感魅力的民族历史记忆,激励华侨秉承其发奋拼搏、勇于牺牲的爱国信念,支持祖国的政治变革。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派的不少言论充斥着极端的民族复仇情绪,认为满汉民族利益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三)宣扬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
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侵略狂潮背景下,受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将华侨在海外拓殖的成功,归因于其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试图藉此构建华侨对祖国的精神归属。
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论及国人前途时,以华侨为例,认为华侨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富于自治之力”;“有冒险独立之性质”;“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善经商而工价廉”,最终会使中国人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28]同年,他又称赞华侨:“其人皆有冒险独立之性,久于阅历,颇通外事,商工之力,固足与欧美颉颃”[29]。1903年,康有为在劝导爪哇华侨兴办中华教育公会时,号召华侨发扬先民的殖民精神:“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发无边宏愿,结伟大团体,为欲令全岛四十万华侨,拂拭真智,湔涤旧染,兴化厉俗,宏我圣道。因以脱地主之羁轭,发扬我先民二百年前殖民之伟烈,被于中土,乃黾勉而集斯会。”[30]1905年,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上八大“殖民”伟人事迹,歌颂明清时期南洋华侨的开拓进取精神,将华侨出洋的历史解读为“华人殖民史”,鼓励国人发挥民族精神,“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31]
革命党人在动员华侨支持革命时,也大力宣扬华侨的“殖民”历史与开拓精神。1907年,《中国日报》发表告海外同胞书,认为华侨历史上的殖民成功得益于华侨勤俭进取的特质:“幸我汉人,富于殖民之能力,所至以其勤俭之特质,辟治草莱,耗血汗以营产业,故常能不依赖国力;以其个人,胼手胝足,而开拓殖民地。”[32]同盟会会员易本羲在《南洋华侨史略》一文中,指出明太祖和明成祖在南洋地区建立的“殖民”伟业:“明太祖成祖二帝,拓殖民地于南洋,为汉人立万世之功,何让于汉武唐宗?郑和、王景宏等,以一苇木筏,辟航路于数万里外,七衔使命,三禽蛮王,直泛重洋大海,如履户庭,何让于张骞,更何让于意大利之哥伦布,葡萄牙之麦志伦焉?”[33]在他看来,明朝代表了中国“殖民”南洋的高潮,明太祖和明成祖在印度洋上进行的伟大探险,恢复了汉人在南洋的权威,在南洋重建了“殖民地”,是世界史上的伟大人物,不仅能与汉唐两朝的创始人相比,还可与西方大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等相媲美。作者在抨击清政府对华侨敌视与迫害的同时,也称赞华侨的开拓进取精神:“以亡国遗民奔逃海外,内而受赐于满清政府之深仁厚泽者,海贼之徽号而已,锋利之刀锯而已,毒烈之弹丸而已,外而与之敌者,又复强暴无伦,而犹能征服蛮荒,开辟土地,……以至于今,且相率捐资兴学,以倡教育其思想之文明,志趣之远大,尤不可及也。”[34]
可见,这些文章通过对中国人在海外拼搏奋斗经历的叙述,提炼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殖民精神”,并将之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华侨海外拓殖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杜赞奇所述,革命者为华侨打造的“华人性”形象,与高雅的文化传统无关,而与新发现的冒险、创业、扩张的启蒙价值有关。[35]
三、强调中国语言和文化习俗的重要性
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是确认民族成员身份的重要标识,也是构建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在动员华侨时,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方面赞赏华侨仍保持着中华文化的特性,但另一方面也发现当地出生的很多华侨,在语言和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已融入当地民族,已失去华人特性,谈不上有什么中华民族的观念,如暹罗的“洛真”、海峡殖民地的“峇峇”、荷属东印度的“伯拉奈干”、菲律宾的“密斯蒂佐”等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后形成的混血儿,融化当地程度更高,更没有什么“华人性”。[36]
康有为在荷属东印度发表演说时就指出这种情况:“各位父老兄弟,多是久居此土,更有自远祖以来,即以此地为乐国,所有语言习惯,起居饮食亦与土人无异;其所以仍能知道自己为中国人者,不外仍然奉行本朝之制度,男子蓄发编辫,与及慎宗追远,祭祀祖先而已。除此之外所有饮食、装束、居处都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了。”[37]1909年,康有为在为南华公学所写的序文中,指出南洋华人不谙中国语言文字的情况:“南洋华人多不识中国文字者,其为语言皆操闽粤土音,而与中原音不通,于是名为中国人,实与异国人无异。同为中国人,相见而语言文字无一能相通,与陕、甘之人见南非、南美各种之人无异。”[38]1910年,《南洋总汇新报》刊载南洋华侨请愿国会代表陆乃翔的上政府书。该文在讲述中国与侨民关系时,提及南洋地区华侨因本土化而与祖国之间关系日渐淡薄的状况:
合南洋英荷两属爪哇苏门答腊暹越而计之逾六百万人,其旅居日久者,不读中国书,不操中国语,宫室衣服饮食一切与中国殊式,叩其籍则曰新嘉坡,问其国则曰雪兰莪,稍有知识者或曰唐山唐人,若习英荷文者则曰支那支那而已。斯时侨民固不知有堂堂二万万方里土地,四万万人民之大祖国也。而中国亦不知万里外犹有同怀之父叔兄弟也,祖宗斩其支裔,国家减其人民,任其长子孙谋室家营农工商事业,自生自灭于重洋群岛之中。[39]
革命派代表人物胡汉民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中也谈到这种现象:“福建人到南洋最早,福建的华侨还有许多不能讲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住在马来的代数很多,所以只能讲马来话,假使我们问他们的姓名,他们反而会觉得奇怪的。”并提及当时革命派没有立马劝说华侨剪辫子的缘由:“华侨有许多是拖着辫子的,但是如上述这种情形,我们不敢劝他们剪辫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拖着辫子的人,我们就可以很明显认出他是中国人,如果马上把辫子剪掉,从形式上认识中国人的记号不是没有了吗?华侨的思想、华侨的语言都已甚少中国的成分,仅仅是拖辫子这件事,是向内地中国人学来的。所以我不愿意他们立刻剪辫子,一定要他们的思想、语言、习惯都中国化了,那么这条拖着的辫子就该剪下来了!”[40]
《中兴日报》针对当时爪哇华侨社会出现“以入荷校学习荷兰语言文字为荣、以入华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为辱”的现象进行批判:“试问各国之侨民,有不先求本国语言文字而专求外国语言文字者乎?在爪哇经商有不用马来语言文字,而通用荷兰语言文字者乎?各国侨民既必先求本国语言文字,而华侨竟不求之,是自忘其本而甘为化外愚顽。爪哇经商既不通用荷兰语言文字,而华侨偏趋之,是自弃其学而乐同化于异族也。”斥责这些人腼颜事仇,敦促其重视中国语言文字。[41]
针对上述情况,这些民族主义者试图从华文教育、华文宣传等方面着手,先要华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恢复中华文化习俗,扭转其本土化趋向,这是塑造华侨祖国认同、取得华侨支持祖国改良或革命的第一步。康有为在荷属东印度发表演说时就认为,这些当地化的华侨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子民。[42]
康有为在《爱国歌》中对中国语言文字赞誉备至,认为它创造的中华文明远超海外诸国: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历史绵远莫我先。埃及金字陵,中绝文不传。印度九十六道,微妙隐不宣。惟我圣作,文字远而存,尧舜让帝创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汉唐开辟益光大,东亚各国皆我文化权。希腊兴周末,文章盛贺梅,罗马更是强汉世,皆只当我云来孙。何况欧洲诸国之后生,岛陆群蛮种属更何言!……中华地大比全欧,全国同文宰亚洲,日本高丽安南皆我语言文字之遗留。虽有闽粤音稍转,十六省语能通邮。印度文二十,语言分四流。欧洲十余国,国国语文殊异难搜求。奥国十四文,德国内亦分。英之威路士与爱尔兰,语言殊异难讲闻。彼遍设铁路尚如此,我无铁路乃能同语文,大地同化之力无如我神。[43]
1906年,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东京发表演讲,提倡国粹,其中就包括语言文字,认为它是爱国保种的力量:“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象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44]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尽管寻求社会变革的方式不同,但都认识到中国语言和文化习俗对构建华侨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宣扬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试图对渐渐失去中华文化特性的华侨再华化。
四、结语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和近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关键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始运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通过民族主义的思想宣传,动员广大民众从传统的“王朝国家”认同转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此动员过程中,改良派和革命派将华侨视为一支重要力量,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引导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保持中华传统风俗习惯,赞扬或倡导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华侨对中国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塑造华侨对中华民族的祖国认同。其中,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注重增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两派持有的文化观也有相异之处:改良派大多来自满清封建王朝的传统士绅和知识精英阶层,强调华侨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革命派则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强调华侨要弘扬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外族侵略斗争精神的文化。但总的来说,在建构华侨祖国认同的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始终贯穿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构建华侨祖国认同的过程中,改良派与革命派除了强调文化的要素外,也运用领土、主权、国民等民族国家构成的政治要素以及血缘种族等纽带,以塑造华侨对祖国的认同。面对来自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华侨结合其跨国的生存环境,思考自身的身份属性和认同倾向。其中不少华侨表现出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并从行动上大力支持中国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政治运动,如参与组建或踊跃加入带有改良或革命性质的团体;资助成立各种民族主义的报刊;为国内反清起义输财出力,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而回国投身起义等。总的来说,辛亥革命时期广大华侨掀起的第一次爱国高潮,不仅与当时祖国深陷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有关,也与侨居地政府对华侨的虐待压迫以及晚清政府的侨务举措相关。当然,改良派与革命派“从外部训出的民族主义”,从情感和思想上都增强了华侨的祖国认同,激发他们舍身投入到祖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之中。
[注释]
[1]参见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6~323页。
[2]参见颜清湟著,李菲译:《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1877—1911)》,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第211~244页。
[3]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136~137页。
[4]颜清湟:《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年,第293页。
[5]参见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颜清湟:《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颜清湟:《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年;庄国土:《论清末华侨认同的变化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等等。
[6]参见Lea E. Williams,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 The Gen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Glencoe, Illinois:Free Press, 1960;论文集编委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南京:《辛亥革命与荷属东印度华侨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陈三井、张希哲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北国史馆,1997年;黄贤强:《革命运动、跨域人物、社会图像:东南亚华人研究与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年;等等。
[7]参见L. Eve Armentrout Ma,Revolutionaries,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罗福惠:《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季云飞:《孙中山反清统战思想与实践》,《长白学刊》1997年第2期;[日]深町英夫:《革命宣传在南洋——以新加坡〈中兴日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金绮寅:《简析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对南洋华侨的“反满”民族主义宣传——以〈中兴日报〉观点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吴前进:《孙中山与华侨民族主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章扬定、陈庆胜:《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等等。
[8][35]参见Prasenjit Duara,“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1900-1911”,in Aihwa Ong,Donald Nonini (eds.),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6,pp.39-60, 54.
[9]James G. 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p.51-52.
[10]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1]《域多利兴学记》,《清议报》1899年第16期。“域多利”即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
[12]《香港圣诞纪念会演说辞》,《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10月19日。
[13]《孔子圣诞纪念会演说词》,《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10月21日。
[14]参见《华侨宜于孔子生日休业一天以志庆祝论》,《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0月2日;《二十世纪之孔子》,《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10月6日;《论华侨对于孔子诞之踊跃并望倡建孔子庙》,《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0月15日。
[15][25][44]《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期。
[16]秦力山:《革命箴言》,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7]《敬孔子者当知》,《中兴日报》1909年10月18日。
[18]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9]颜清湟著,李菲译:《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1877-1911)》,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第219页。
[20]《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1902年第27期。
[21]《少年中国说》,《清议报》1899年第35期。
[22]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3页。
[23]《警告华侨》,《中兴日报》1907年11月19日。
[24]《救亡危言》,《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1月7日。
[26]邹容:《革命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41页。
[27]《记本坡新舞台开第二次演说大会事》,《中兴日报》1908年3月16日。
[28]《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1899年第19期。
[29]《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清议报》1899年第26期。
[30]康有为:《爪哇中华教育公会发起词》,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31]《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新民丛报》1905年第63期。
[32]《钦州革命军布告海外同胞》,《中国日报》1907年9月13日。
[33][34]《南洋华侨史略》,《民报》1910年第26期,第24,25~26页。
[36]参见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226页。
[37]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2~193页。
[38]康有为:《南华公学序》,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39]《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总商会国会请愿代表兼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上政府书》,《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7月12日。
[40]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蒋永敬:《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283页。
[41]《论华侨不知自悟》,《中兴日报》1909年10月14日。
[42]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92~193页。
[43]康有为:《爱国歌》,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