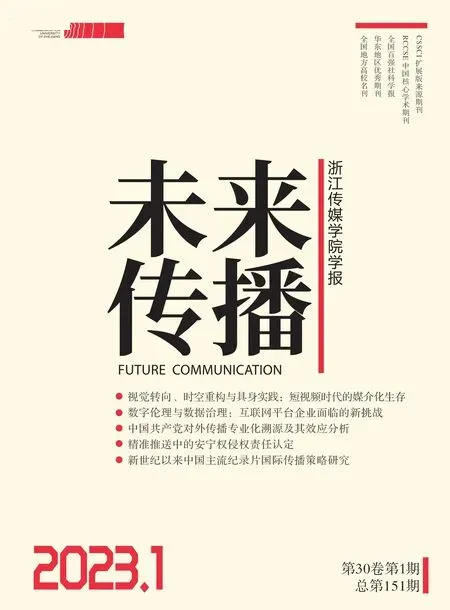视觉转向、时空重构与具身实践:短视频时代的媒介化生存
2023-10-07李文冰赵舒悠
李文冰,赵舒悠
(1.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18;2.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一、引 言
人类实现媒介化生存了吗?早在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数字化生存”的预言之际,人们似乎就已经相信媒介技术天然具有赋权的潜力,而这一特质将会引发积极的社会变迁。在大众媒体时代,狭义的媒介化生存是指以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媒介成为生产生活中工具性的存在。当今新媒体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媒介不再仅仅是受制于社会结构的专业信息系统,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全方位、全时空的渗透,成为人类基础性的生存框架。[1]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网络的提速,短视频自“出道”以来便以视觉信息的全景、立体、陪伴和体验颠覆了传统媒介观中的现实再现,经由算法武装的短视频平台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介依赖,转而作为一种技术配置体系,深刻地影响、诉说甚至决定着人这一主体在虚拟与现实世界中的媒介实践和生存体验。[2]短视频的传播实践与大众传媒相比,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在时间维度上,人的媒介接触已不再是大众媒体时代的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等相对集中清晰的片段,短视频应用以其碎片化、强社交、移动性的特征持续地嵌入日常生活;在空间维度上,人的身体被标记的符号意义能够逃离生物躯体所固在的某一特定场景或地点,媒介化生存伴随着人在多重时空中的移动同步展开。[3]
如果仅仅将短视频平台定义为社交媒体有利于引流和变现的新样态,将短视频看成是时间长度相对较短的影像形式,便远远低估了短视频应用打开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媒介“想象力”。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人们以短视频为形式、以平台为载体的媒介化生存呢?首先,本文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出发,阐释在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和网络社会的“时空重构”的背景下,人们的媒介化生存依托于短视频平台的合理性证据和合法性内涵;其次,通过对平台生态的追踪和观察,以视觉奇观、互动仪式和时空(再)生产三大现象为例,分析人们媒介化生存具体的动机、手段和过程;最后,以技术具身为切入点,探讨短视频平台对媒介化生存底层逻辑的改写,以及传播主体的根本性转变。
二、短视频平台的技术哲学
(一)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
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报以怀旧之慨叹的“说故事”类口传文化;第二阶段是以文学和新闻为代表的印刷文化;第三阶段是巴拉兹(Béla Balázs)以机械复制的电影艺术的诞生为标志提出的视觉文化。[4]当代社会呈现高度图像化或视觉化趋势,从印刷、影视作品到服饰、美容、商品包装,从城市建筑、广场、街道等公共场所到室内装饰、家居环境等私人空间,视觉形象显而易见且无处不在,几乎已经成为强迫性的生存体验。对此,弗莱博格(Anne Friedberg)称,新的视觉文化重塑着人们的记忆和经验,“不管是‘视觉的狂热’还是‘景象的堆积’,日常生活已经被‘社会的影像增殖’改变了”。[5]一个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预言的“世界图像时代”正在发生,其典型症候是 “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并逐步趋向于德波(Guy Debord)所描绘的“景观社会”。[6][7]图像化并非现代专属的状况,每个时代都存在视觉艺术的繁荣时期。[8]但是,随着短视频成为当下最为流行的视觉传播手段,文化的“视觉转向”在技术和内涵两个层面经历了新一轮更迭:首先,短视频平台通过多种媒介技术的融合,革新了视觉生产的实践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和重构着人的思维指向和逻辑形式;其次,图像化的感知和存在形式不仅改变了意义交流本身,更在根本意义上确立了人对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并形塑着人的生存经验。
根据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自主论”,技术可以以隐匿的方式决定其中的文化形式。[9]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看,短视频作为视觉艺术的新形态,成功促成包括录音、摄影等多媒体音像技术的融合和简化,丰富了媒介文本的生产、呈现和作用方式。当下的短视频平台已经搭建形成完整的技术框架,其主要贡献在于,将以专业性著称的影像生产,通过特色滤镜、创意混剪、肢体识别、舞蹈跟拍、3D渲染等功能,化解为方法上简单但效果上专业的用户操作,显著降低了个人的技术门槛和技术成本。[10]就意义的生产和接受而言,语言是抽象和线性的,文字产生意义的基础本质上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所指是形成于人的心理再现中与能指相对应的概念。而影像生产基于其机械复制的特性,具备复现物质现实的功能,且复现的方式和结果具有唯一指代性。以现实影像作为素材,无论是直接捕捉现实生活,还是对现实的再加工,都体现出更强的物质性。[11]因此,视觉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撼动了语言所建构的抽象逻辑认知,短视频成为新的劝服性生产实践,而人的观看行为则是一个在影像中联系和锚定现实对象的过程。视觉符号(短视频)对于语言符号(以文字为基础的博客、推文等)的优势,并不意味着文字将从日常实践中消失,而是影像成为文化的“主因”,其深层涵义在于人们越来越倚重于视觉形象来理解世界和自己。
所谓“观看先于语言”,媒体正日益从对世界、社会、事实的“言说”转为更加直接的“再现”甚至“体验”,短视频成为一种新的“符号术”,对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相对关系作出新的哲学解释。[12]按照伯格(John Berger)的“观看之道”,一切认识从观看出发,一切知识和经验在观看中模仿习得,有选择的观看行为确立了人在周围世界中的地位。[13]海德格尔则认为,现代的本质在于“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进程的相互交叉。[6](89)在世界图像中,存在者整体(指除人以外的其他存在)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14]这意味着,人只有将世界表象化,世界对人而言才是可感可知的,而通过将世界转化为能够被人把握的表象,人就为真实性寻找到了确定性的根基。[8]于是,现代化被描述为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人自行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力求成为一切尺度和准绳,并以此来摆置其他存在者。与此同时,图像成为现代基本的形而上学,人们不再观看图像,而是通过图像来体验,图像系统从根本上塑造并规制着人们的生存、感知,以及全部的社会经验,自我、他人甚至整个社会被整合为一个自动的图像“装置”。[15]简言之,在这个图像的时代,短视频成为人们把控周遭(umwelt)的新媒介技术,又反过来使人本身以某种“图像”或“景观”被表征,从而形成对人的规训力量和存在的确证。
(二)网络社会的“时空重构”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受万事万物的先验的“感性形式”,也是构成人类理性主义思维的两大基本维度。在时间和空间的博弈中,时间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被视为丰裕的、辩证性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概念,而空间则在时间强大的话语逻辑下遭到隐匿和贬斥,被认定为固定的、静止的、非辩证的,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都仅将空间看成纯粹的物质载体或容器。[16]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空间转向”思潮倡导了一种重视空间的本体论,福柯(Michel Foucault)着眼于权力的空间化,认为空间既是权力相争的场域,也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空间三元”辩证法,指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不仅指的是事物处于某一地点或场景之中的经验性设置,也是通过人类主体有意识的活动而产生的一种习惯实践;而索亚(Edward Soja)则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探索“他者化”的“第三空间”,强调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相互勾连、亦此亦彼的混杂特质和无限开放性。[17][18][19]
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既基于又进一步改写了基础性的时空要素。首先,新媒介技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空组织形式。在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关于声音技术的讨论中,声音这种被黑格尔称为“在形成过程中消失的存在”,由于留声机的出现,首次跨越时间的界限,逝去的人和事得以“以真实声音的方式存在”。[20]留声机还可以化无形为有形,将人无法直接看到的自然界中的部分物质,以实际可见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不再借助象征符号。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技术与此类似,电影制作在原则上不过是剪辑与拼接,即“在镜头前对连续运动或线性时间的切割”,而胶片为操纵这一“虚幻国度”的可能性提供了物质基础。[20](136)于是,视听媒介实现了时间的逆转,而逆转的必然结果是,“各类媒体在时间上相互交错,已不再遵循线性的历史次序了”。[20](133)对于新型时间轴的诞生,孙玮解释为,“当单一线性时间被切割,就形成了与真实时间并置的多个时间链条,它们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多重时间性”。[1]
针对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关联性,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的假设是,“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21]移动网络技术对于媒介时空的革命性突破,其一为“无时间的时间”,即最大可能地取消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其二为“流动的空间”,即时效的提高克服了远距离空间互动的域限和障碍。[21]相较而言,传统媒介铸造的想象空间缺乏多重感官的并置和即时性的互动,因此只能算作一种隐喻意义上的空间,而短视频平台不但创造了远程虚拟的在场方式,而且实现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转换与交融。[1]以视听体验来说,短视频的媒介技术和平台的信息网络解放了视觉叙述对物理媒介的依赖,信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可以以视觉图像的感知形式存在。[22]就社交方式而言,线上交流得以从时空的束缚中解脱,然而交流者同样需要置身于一种被感知的空间状态之中,这种感知状态离不开视觉图像的建构。[22]从具身实践的角度出发,短视频的空间(再)生产既涉及网红地点在虚拟空间里被合目的地“重新发现”,又要求人们的身体和感官在真实时空中相会。
三、媒介化生存的平台观察
(一)视觉奇观:个人生活的可见性赋能
对于视觉行为所涉及的权力关系,福柯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视觉乃“权力的眼睛”。[17]从边沁的“圆形监狱”、福柯的“全景监狱”再到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观看机制已经从监督者对身处封闭暗室的囚禁者的偷偷观察,变成了权力运作在全景式的透明建筑中受到全社会全天候的监视。穆尔维(Laura Mulvey)则从视觉快感的角度分析看与被看的角色相对位置,认为摄像机后的掌控者和荧幕前的观看者是主动的、欲望性的权力主体,而画面中的被观看者则是被动的、被“凝视”的弱势客体。[23]然而,短视频平台的视觉展演形式使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消解。绘画、雕塑、电影等传统视觉艺术的符号建构者通常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短视频作品一经发布便不再有明显的主客体之分,人人观看他人的节目,也都成为被他人观看的“节目”。[22]正如周宪所言,“图像就是力量”,视觉经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把握为图像”的东西才充斥着文化影响力,看见意味着优势和权力,看不见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排斥。[4](8)可见性(visibility)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可见不再是手段(means),而变成了目的本身(end)。[24]抖音的广告语是“记录美好生活”,快手的广告语是“看见每一种生活”,这两大头部短视频平台虽然商业定位不同、视频风格和平台文化差异明显、吸引的人群也少有重叠(前者更具都市时尚色彩,后者更乡土化、“接地气”),但它们的共通之处是,让广阔世界中人微言轻的个体通过视觉内容的奇观化(spectacle)和视频形式的蒙太奇(montage)为生活的可见性赋能。
从电影理论的角度来说,奇观电影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画面的组接来传递具有视觉吸引力和快感的影像,蒙太奇则是把不同的视觉素材组合成为有意义的整体的方法。鉴于短视频平台对用户群体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除了受制于15秒至60秒的主流视频时长,用户享有对音乐、场景、内容等的自由选择权和裁量权。基于“短平快”的宗旨,短视频的视觉内容不再严格以理性原则组织线性的叙事结构,而是追求奇观效果和快感最大化,也不再坚持以话语为中心打造故事情节和主题深度,而是转向强化画面的造型性和视听的冲击力。传统视觉叙事文本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为直接引发快乐情绪而采用的简单夸张的肢体表演搭配“洗脑”神曲、“魔性”音效的组合。
在创作实践中,人们的媒介化生存主要体现为不断寻找、发现和创造视觉素材的过程。取材于真实生活,素材的易得性成为人们拿起手机拍摄的基本动力,而素材的独特性又能够大大增强视频的可见性,这就驱使人们随时审视周围环境、规划自身行为。[11]短视频中的每个画面都是对现实场景的记录,通过镜头、场面、段落的分切与组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再现,最终形成独特的个人叙事。因此,“美好生活”就是独居女孩悉心筹备每日餐食、宝妈奶爸带娃的趣味崩溃日常,平凡的生活中也有值得记录和分享的不平凡之处;“每一种生活” 既有卖工地盒饭的阿姨在奋力翻炒、卡车司机在日夜奔赴,也有纽约白领参加街头快闪,人们互相邀请,既看见他人,也收获他人的关注与承认。[25]
(二)互动仪式:社交情境的新玩法
作为人类社会中特有的文化现象,仪式是“被一个群体内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按照某种既定程序进行的身体的活动与行动”,经常固定地、重复地在某个时间或某一特定情况下举行,并且承载着某种象征意义。[26]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识到宗教仪式是一种在社会水平上促进团结的强大力量,而戈夫曼(Erving Goffman)则将这一思想延伸至日常生活层面,认为面对面的互动形成大量情境,人们在不同情境中根据自己不同的角色和目标与他人进行互动。[27]在此基础上,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从微观情境着手探究仪式中的互动作用机制,提出“互动仪式”这一核心概念,指出互动仪式链的生成需要四个条件:人们共同在场、对局外人设定界限、有共同的关注焦点、分享情感体验。[27](61)短视频平台中的一切互动都是在短视频生产的情境里展开的,根据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新媒介—新情境—新行为”的关系模型,短视频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形式,导致传统社交情境的重构和新情境的诞生,而新情境又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互动行为。[28]短视频平台生态催生了社交情境的新玩法,人们的媒介化生存在社交方面的互动实践表现为以“模仿创作”为标志的共同行动和以“视频直播”为代表的共同在场以及其中被激活的情感联结。
“模仿创作”的共同行动可以概括为,基数庞大的普通用户通过欣赏热门作品获得情感刺激并试图加入流行话题,在技术引导和反馈强化的激励下产生循环往复的创作热情和创作行为。[29]在抖音历届潮流榜单中,有简单易学的舞蹈,如“海草舞”“C哩C哩舞”,有对明星语录的复刻,如海清的“你是我的神”(表示夸奖)、斯琴高娃的“这是可以说的吗”(表示欲言又止),还有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剧本表演,从“今天你真好看”“我妈不让我跟你玩”到对《甄嬛传》《小时代》经典桥段的“素人”翻拍。抖音为大众模仿秀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既结合用户浏览偏好设计了对热门话题和优质内容的推送机制,又在最大程度上优化二次创作的流程,用户可以使用“拍同款”(套用动作模版)或“一键生成”(系统智能选择相册内容并自动生成视频)直接加入热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29]转发、点赞、评论等互动方式相当于观看舞台表演时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通过赢得关注度和互动热度(即柯林斯所说的“反馈强化”),内容创作者所产生的愉悦的情感能量代替实质性的经济回报,激励下一轮的短视频生产。[29]这样的社交情境中所激活的群体符号,如“夺笋”(多损)、“针不戳”(真不错)等谐音梗,承担了在参与者和局外人之间设定身份区隔的功能,甚至演变为参与者共享的特色文化资本,从而使属于该圈层的用户迅速产生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由于无法实现身体在物理意义上的聚集,柯林斯对远程仪式的效果不无担忧。然而,短视频平台为用户创设了一个流动的接入界面,人们不仅可以对眼前的时空场景进行数字编码和传播,还可以将其他空间的活动围绕自身形成与他人的共同在场,实现“没有地域邻近性的社会共时性”,身体的虚拟共在和情感的远程联结已经成为当今互动交往的基本特征。[21]以视频直播为例,彭兰视其为由主播创造的个人媒介事件,其中所展现的不是生活的碎片,而是一个个完整、持续的真实生活情境。[11]尽管直播在很多情况下是无主题、无事件的,观看者依然乐此不疲,这是因为直播的场景往往也是主播生活的空间,而手机摄像头与主播的超近距离容易转化为“进入”和“在场”感,来自他人的注视使主播的私人生活公开化。[11]人们还可以随时进出不同的直播间,仿佛“在不同的聚会上同时现身”,这种随机性和随意性带来陌生人之间的相遇和想象中的亲密关系,却不会造成心理上的负担。[11]在直播间内,观众群体分享了共同的情感体验,比如考公考研的学习直播和刘畊宏的健身直播起到督促的作用,被比喻为“电子榨菜”的下饭吃播和ASMR助眠直播具有陪伴的效果,人们正在将参与视频直播融入个人的生活仪式。
(三)空间(再)生产:具身化的媒介实践
谈及媒介与空间或地方之间的关系,亚当斯(Paul Adams)的观点是,“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列斐伏尔则将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话语进行考察,认为空间是有目的地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生产背景,而是生产对象”。[30][18]在抖音热门城市视频的搜索发现中,西安的大雁塔、厦门的鼓浪屿、重庆的洪崖洞等网红景点都榜上有名,甚至司空见惯的民宿、咖啡店、清吧、广场等城市空间和土炕、瓦房、田野等乡村景致也纷纷成为短视频创作的舞台和展示的焦点,这种现象就是短视频的空间(再)生产。短视频生产所依托的空间经过创作者的挑选与设计,“在哪里”拍视频被赋予了意义,现实空间于是融入虚拟空间的象征结构中。这种生产实践并非对时空场景的“无中生有”,而是采用“增强”或“修辞”的策略对现实空间进行解构、拼贴和再现,从而使当地景色所具备的社会意义或商业价值在原有基础上发生“复合”和“叠加”。[10]人们的媒介化生存发生在虚拟与真实的交错中,“种草”虚拟空间中呈现和流转的影像成为具身体验的动力,而后通过“打卡”实现身体在物质场景中的相遇。
从古时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到图像时代的“人在家中坐,走遍全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常常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人的位置固定不变,关于世界的信息则摆脱其固有的地域性,通过影像的远距离传输使世界成为手机屏幕里跨越时空、往来穿梭的景观。[31]这便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描绘的“脱域”与“再嵌入”,即媒介以虚拟再现的方式,使位置从物理空间中脱出、挪移,实现与以肉身为存在形式的固定主体的接合。[32][31]然而,现代空间的异化正是源自虚拟移动性对身体物质性的剥夺,与物理空间的长期隔离遮蔽削弱了人介入现实的行动力,身体的重要性或从现实时空中退却。[33]
短视频建构性的视觉力量驱使人们的生存方式由媒介表征向具身实践转型,倡导以“体验”作为人的时空穿梭方式。第一步是“种草”,指的是把一个事物推荐给他人,使他人也喜欢这个事物的过程,人们透过手机屏幕被空间影像所吸引,产生亲临现场以确认其价值或意义的冲动。下一步是“打卡”,代表着自媒体标记某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中留存印迹,涉及人们接触网红事物、拍摄影像、上传至社交平台、引起其他用户的关注和互动的一系列行为。[31]在具身实践中,“打卡”意味着以身体感官体会物质场景中的种种活动,比如亲眼目睹某一个景色、建筑,亲口品尝某一种佳肴、小吃,亲手触摸某一样器物、动植物。[31]人们前往网红景点留影纪念,仅就表面现象来看往往被界定为跟风、蹭热度,但人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切身的联系。区别于一般旅游,“打卡”也不只属于个人的经历,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创造存在感,即“创造现身于新媒体平台与他人共在于某个环境中的感受”,通过在虚拟平台上基于同一地点的内容汇聚,以及在现实场景中共同“打卡”的相遇,虚实之间形成了多重循环。[31]
四、具身的传播主体与生存形式
移动网络时代的新型传播实践,在根本上改写了媒介化生存的底层逻辑,以短视频应用为核心的人类生存方式已经进入重造主体的阶段,传播的主体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cyborg)。[3]
主流传播学将大众传播定义为中介化的传播,信息必须借助符号才能从传播者到达接收者,传受双方的身体及其所依附的物质时空场景都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34]基于“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基本和身体无关”的共识,传播研究所论述的“人”多以价值认同、态度和意见的流动为尺度,交流者被确定为拥有理性意识的主体,从而形成对于一切身体感觉的拒斥。[35][36]这一去身体化(也作离身性)取向强化于第一次技术革命,也就是包括电力、铁路交通、冶金在内的工业技术的发展,此时“技术的界限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身体的界限,是同构的”。[37]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将“存在”解释为有且仅有的两种意义:“人作为物体存在,或作为意识存在”,正常的身体必定是身心统一的身体。[38]在基特勒看来,大众媒介的每一种形态都是对人体感官的肢解与剥离,所谓的“人”被割裂为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因此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身体。[20](17)这种二元分立的身体观源自西方哲学传统,在技术革命的加持下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也构成了主体的现代性危机。[34]
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也就是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的浪潮中,技术的具身性趋势显著加剧。关于人与技术的关系,伊德(Don Ihde)坚信,“我们始终通过我们的身体存在于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无法与技术相互分离的真实主体”。[39]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早就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但是孙玮认为,这一观点未能进一步预见媒介对于感知的介入并没有停留在对人体感官的复制和加强,而是“创造了一种交织媒介技术与人类有机体双重逻辑的新型感知”。[40][31]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具有连接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的桥梁性功能,主要表现在“用身体及其感觉来同化这个世界,就能把陌生的、 异质的、不可见的事物转化成可感觉的、可见的、 可理解的事物,从而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创造出一种关系和意义”,具身是人们参与这个世界的实践方式。[41]在人与世界的链接中,视觉媒体技术承担了必不可少的转化作用,也就是将人的身体所感受和所经验的,转化为关于图像的现象。伊德所谓的技术具身,意味着短视频不再被理解为外在于身体的工具,而是越来越透明化、越来越深地嵌入人的“知觉—身体”经验中。人们在面对和处理视觉图像时,知觉对象与认知器官之间的距离被抹除,甚至可以通过视觉幻象统领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其他感官体验,直接进入感知本身(比如观看“吃播”激起人对食物的味觉渴望)。[22]
因此,人们的媒介化生存主要依托于人本身成为自我延伸的新媒介,即赛博人,其所拥有的连接力实现的不仅是媒体间的相互融合或媒体机构与外界的融合,而是人类基本生存系统的解构与重组。[3]从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视角出发,“人类的存在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其主体性即在于作为活跃的生物以人类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这一理论的重点在于引入感性知觉以反驳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42]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指出,人这一主体拥有两个身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43]相较于电影、电视等传统影像,短视频在时长之短和技术之灵便的基础上,通过平台的技术介入将“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结合起来,解决身体在场的问题。首先,作为“接收器”的身体,其视听感官让人能够感知、解码、内化外界的讯息;其次,身体亦“发射端”,人通过(肢体)语言、穿着、表情等身体表现以及对时空场景的创造性(再)生产向外界传达信息。[29]通过人的不同媒介器官端口的输入和输出,身体不再是私人的、隐蔽的,而是同外界开放共享,成为真实时空和虚拟情境的共生躯体。赛博人作为可以将“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随时分离或融合的传播主体,其“化身”(avatar)能够随时现身于短视频传播的路途之中,在网络空间进行虚拟表演,也能够以肉身之躯抵达真实空间的任意角落。
五、结 语
回溯尼葛洛庞帝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初想象,媒介技术的实践已历经数次主流传播形态和主导方法论的更迭,引起了愈来愈清晰的媒介观念转向:从前,人们将媒介视为客观世界的再现,是附属于现实的次要事物以及通达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人们以大众传媒作为感觉器官来感受社会、感知新事物;现在,媒介不仅是“情景”的生成方式和“现实”的组织装置,媒介事件与日常生活的区隔、人与媒介的区分正在逐渐消失,长久以来外化于人的媒介融入主体、成为人的组成部分,人即是最终的媒介。[2][1]尽管人们以短视频为形式、以平台为载体的媒介化生存革新了个人生活的叙事方式和社交互动的在场形式,并且通过具身化的实践不断地确证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但短视频应用显然不会也不必是媒介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最终样态。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AR/VR/MR、区块链等技术集的成熟应用,以往纵深方向演进的技术谱系被组织整合,人类社会可以预见一个元宇宙的诞生,主体的存在形式、生存法则、交往方式正面临再一次的解构和重构,新的生存方式值得期待,人文伦理的动荡或将引起的疲惫、迷茫、堕落也值得保持冷静的担忧。[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