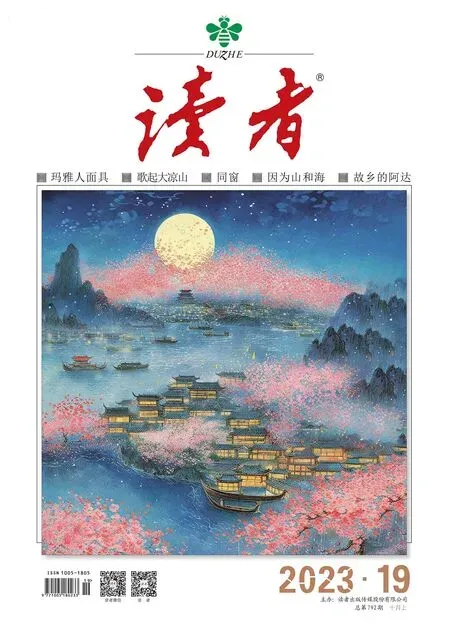何日君再来
2023-10-05陆庆屹口述罗晓兰整理
☉陆庆屹 口述 ◎罗晓兰 整理

妈没有见到爸的最后一面。
我哭得喘不过气来,妈说:“别哭了,你爸也86 岁了。”她躺在隔壁的床上,伸出蜷曲的右手,抓着我的手说:“人活着就是这样,总有要走的一天,以后我也是要走的。你别哭了。”因为脑梗,她只有右手能动。她叫我别哭,自己却边说边哭,还用右手指向纸巾,要擦泪。
我哥在北京,还没赶回来,第一晚,我独自守灵。灵堂设在一层正门的堂屋,以前放先人灵位的地方。小巷子被打掉了,中间一进门处成了一个很空的空间。爸的棺材在堂屋,妈睡在隔壁的床上,一样的摆放走向,位置对称。
守灵到半夜,我听到妈在唱歌,唱完之后,她说:“运坤,你听到了吗?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何日君再来》。”这是一首老歌,其中有一句歌词:“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拍《四个春天》时,一天黄昏过后,我看见天井对面,爸妈各处一室,隔着一堵墙。妈在缝纫,身体语言有节奏,我知道她心里有歌;爸在唱歌,挥手打着拍子。在黑暗里,他们像两个闪亮的画框中的人物,并列在一起,手势起落应和着,如此和谐。我静静地看着,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心中风起云涌,仿佛明白了“地老天荒”的确切含义。
他们两个人都痴迷于音乐,可以花一整天时间来听歌。爸年轻时自制笛子,用蛇皮做二胡,还买来各种晶体管做收音机。后来,我放披头士乐队的歌给他听,他慢慢地也爱上了。
当然,他们还是更喜欢听老歌。在天井里,爸拉琴,妈有时戴着老花镜看乐谱唱歌,有时手里舞动着红扇子和红帕子,边唱歌边跳舞。他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但因为都有挚爱的东西,在精神上的追求很相似,所以灵魂十分契合。
还有一天早上,爸在天井里给妈熬中药,妈从厨房出来,在后面站了好久,眼神温柔,抬起手抚摸爸的白发:“你的头发该理啦。”爸“嗯”了一声,她脸红扑扑的,笑了起来,用普通话说:“谢谢啦。”她在说一些难以启齿的话时,会换成普通话。爸说:“谢什么鬼啊!”她笑着说:“谢谢你的情啊,谢谢你的爱啊。”
从镇上搬回县城后,爸妈借钱盖房,很多年后才还清债务。房子在城边,离山不远,四面环楼,中间留个天井,井壁用的是100 多斤重的条石,都是爸一块一块搬起来垒上去的。
新房一年后意外着火,新电话、小数码摄像机、照片,好多都没了。爸在废墟里翻出了他的小提琴,背板快被烧成木炭,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见“沙沙”的琴声,那是爸爸在井台上拉琴。琴声很破,他的动作很轻柔,仿佛没发生过任何事。
第二天,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发抖。她也没问什么,跑到楼上去找老照片。爸妈说照片是记忆的物证,每年他们都会攒些钱,到照相馆拍照片。
温柔能带来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后来,当被问到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特质是什么时,我常常说,是温柔。
很多人看纪录片《四个春天》,以为我们是在农村生活,其实只是因为爸妈喜欢土地,就很自然地劳动。他们在楼顶种菜和花,有野生的蒲公英长出来,天气晴朗时,两个人爬上楼顶吹蒲公英玩,不舍得一口气吹掉,便约好下次再玩。
他们还喜欢爬山。爸对自然风景钟爱有加,一看到漂亮的风景照片,脸上就泛起特别温柔的笑容,轻轻地摇晃脑袋,啧啧赞叹。上山采蕨菜,他吹着口哨,鞋底掉了,他一跳一跳地抬起脚,笑着给我看。他用茅草搓成草绳捆住鞋底,听着松涛,又笑了,“好玩得很”。妈看了,笑得要岔气。
爸妈生命的热情虽然释放出来了,但依然被时间吞噬掉。
这几年,两个人渐渐衰老,身体都出过状况,住过院。爸很少再拨弄他的乐器。他脑部血管变细,开始堵塞,供氧不足,小脑萎缩,失去平衡感。他每天头晕、头疼,无论做什么、保持什么姿势都觉得不舒服,整天趴在桌子上,偶尔跟我说一句:“难受,想死。”
我最近几次梦见过爸,都是重复以前的回忆。有次梦见我离家出走,躲在同学家,爸找了过来。在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他没有责备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说:“哎呀,这风吹起来好舒服啊!罗甸老家门口的稻田没有这一片大,田埂比这边的硬。”在一片绿野里,爸很瘦,穿着白衬衫,因为左胳膊摔伤过,走起路来看着有些歪。
我很悔恨,偷偷流泪。爸回过头来,我假装没事,蹲下系鞋带。这里离家七八公里,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的行踪,不知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爸和我现在一样大,50 岁。
这些场景和他去世的状态,在梦里形成若隐若现的叠影。梦里我就在想,这些只是回忆,感觉空荡荡的。醒来后,我哭了。我想回到梦里,却又不想。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稀稀拉拉的灯光,我被拉回现实。人生如梦啊,梦里他们还在,一醒来,什么都没了。
妈有些糊涂了,对于爸去世,却很清楚。爸下葬后第二天,我和哥坐在她床边,她躺着唱了一段花灯戏。她那时候意识已经很混乱了,突然说:“我就记得陆运坤是我夫君。”
她再没说话,我们也都没说话,我出去在院子里抽了根烟。回去的时候,她还在看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