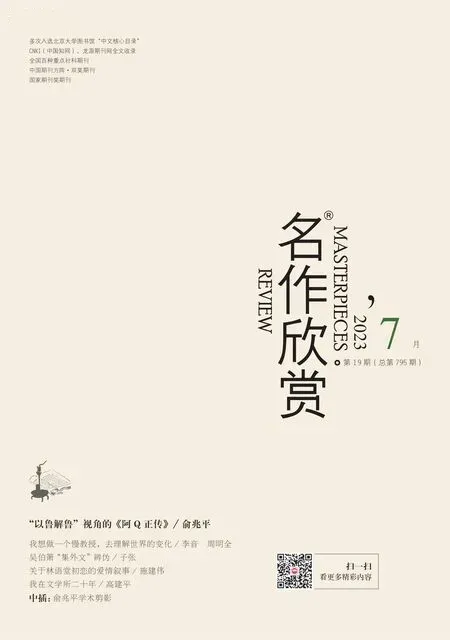我在文学所二十年
2023-09-28北京高建平
北京 高建平
我是1997 年7 月从瑞典留学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到2017 年3 月退休,在文学所工作了整整20 年。在这个集体中,经历了很多事,结识了很多朋友,面临过很多挑战,更有很多收获。一个机构,具有自身的文化,个人往往是与这种机构文化共同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所这个集体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人生的阶段上讲,从1977 年参加高考上大学,到1997 年学完回国,是我辗转求学的20 年,从1997 到2017 这20 年,则是我在学术上发力,工作上做成一些事的阶段。现在,我已经退休六年,回顾过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初进文学所
我于1996 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那时,中国人在国外读书的不多,去瑞典留学的就更少。在我完成答辩后的庆祝会上,参加答辩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说:这是瑞典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瑞典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乌普萨拉大学是一所古老的大学,1473 年建校,是整个北欧五国所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建校时还没有宗教改革,瑞典还处在中世纪,信天主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这所学校在欧洲是一所名校,出了不少科学史和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我回国的那些年,中国的教育界和科研学术界更看重美国的名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觉得欧洲的学位差了一截。尽管在国外,特别是人文学科,是美国深受欧洲的影响。
由于这种崇美轻欧的现象,又由于当时的文学所刚刚经历了一件事,因此我一来报到,就感到一种压力。文学所此前曾引进过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生。院里和所里都很重用他,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他的特殊待遇。可他来了一段时间却又突然离开,回美国去了。一时间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在那个年代,从国外引进一个人,要经过复杂的报批手续,克服很多困难。终于办成引进了,还任命他担任了重要职务,全所瞩目,全院关注,这时却突然离开,自然反响强烈。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引进了女婿,气跑了儿子。这是说,对引进来的人太关注了,使单位原有的人员受到打击。如果这个女婿再跑了,就会人心浮动,领导也要吸取教训。
我正是在这个时间到文学所的,人们自然而然会将对那位刚离开的留美博士生的感觉投射到我身上,这也使我时时感到一种观望的目光。在国外有八年之久,刚回国时我自己一开始也对国内的环境,办事方式不太适应。当时,文学所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人事处长郭一涛、科研处长严平和负责外事的科研干事郝敏,以及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很关心,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进入文学所,分配我在理论室工作。当时理论室的小环境特别好,杜书瀛和钱竞任正副主任,思想开明,在学术上持兼收并蓄的态度;钱中文任《文学评论》主编,许明任副主编,他们也经常参加理论室的活动。记得那时理论室人很多,老一辈的王春元、杨汉池、张国民、李传龙、李大鹏、栾勋、汤学智等许多人,有的还没有退休,有的刚退休不久,还常到理论室来。与我同辈的学者有孟繁华、靳大成、王绯、罗筠筠、党圣元、彭亚非、金惠敏,还有一位年轻的学美术出身的冷林,是一个热闹、欢快、其乐融融的集体。这样的氛围逐渐缓解了我刚入文学所时的不适感。
当时还有一些烦恼。有些烦恼是很具体的,要逐一奔走解决。例如,工作关系从天津转过来,先是天津的学校不同意,后来同意了,被莫名其妙地罚款几万元。孩子上学是就近入学却要交择校费,又是几万元。妻子的工作,安排好了,用人单位又突然变卦,一时还落实不了工作单位,如此等等,其中任何一件都让人焦虑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所也尽其所能地帮助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在刚回国的几年中,许多朋友见到我,都曾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对这个问题,一两句话很难回答,但文学所的科研环境、国内的学术需要、我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都能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文艺理论研究室
在文学所的20 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文学所理论室从事科研工作和科研组织的工作。从2002 年到2015 年,我总共当了14 年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文艺理论研究室是文学所的一个大室,鼎盛时期有20 多人,曾经是全国当之无愧的文艺理论研究国家队。当时,在蔡仪先生的带领下,编辑《文学概论》教材、《美学论丛》集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出版物,从20 世纪50 年代到80 年代,在全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到了90 年代,文艺理论研究室在所里仍受到高度重视。当时的引进人才指标,都优先给理论室。因此,后来的一些研究骨干,都是先进了理论室,后来又经过理论室而转到了其他研究室和其他单位。例如许明、叶舒宪、赵京华、孟繁华、党圣元等,原来都是理论室的成员。我刚进室时,听说室里正在做几个大项目。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王善忠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和杜书瀛任主编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
我接任理论室主任以后,一些人调往其他研究室,一些人退休,理论室的人有所减少。这一时期,进来了一些新人。现在理论室的一些研究人员,都是在本世纪陆续进来的。
这些年理论室的工作,除了日常的研究任务以外,还开了一些会议。为了传承和弘扬理论室的优良传统,我曾组织过几次蔡仪美学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的论文,由王善忠和张冰主编了一本论文集《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使这些研究成果集中起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那些年文学所的经费紧张,召开有关蔡仪先生的会,都要找当时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许明和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吴予敏赞助。他们两位是蔡仪先生的弟子,又有能力出资,当然这也是对我和理论室工作的支持。近年来我与这两位还常有接触,见面时常对当年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搞一些学术活动的往事感叹不已。
我担任理论室主任期间,尝试开启了与一些地方高校合作举办双边会议的模式。例如,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创新与对话——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参加者除了文学所理论室全体在岗人员,已经退休的三位老先生钱中文、杜书瀛和毛崇杰,还有两位国外学者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和泰勒斯·米勒,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外,理论室还曾一道去保定,与河北大学文学院合作举办会议。理论室的同事们还一道远赴拉萨,成功与西藏大学合作召开了双边合作会议,在雪域高原纵论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我担任理论室主任时,每逢春节,都将理论室的退休老人请来,在岗的人员也全员参加,理论室的研究生们也来,退休人员、在岗人员、研究生,三代人济济一堂,畅叙交流。每年的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喜气洋洋,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景。还记得何西来老师慷慨陈词,教导年轻的学子在思想上进步和学术上提高;钱中文老师说出了他的名言:学术要前沿,不要时尚。大家在一起回忆过去,讲述理论室的光荣历史,对当下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并寄托对青年的殷切希望。会后一道聚餐,刘保端老师曾唱起她参加北平地下党时学会的进步歌曲;钱中文用俄文唱他在留学苏联时学会的俄国歌曲;喜爱音乐的毛崇杰唱一些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歌。靳大成的民族唱法、彭亚非的美声唱法,也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理论室的工作还有一件大事值得说一说,这就是创新工程试点。院里开始进行创新工程工作时,要求各所先试点。这是一件此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要有人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文学所就决定由文艺理论研究室和当代文学研究室打先锋。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与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白烨围绕创新方案,先写出初稿,开会讨论,所里一次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再报上去,根据上级机关的意见再改。这种修改经历了很多次,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件辛苦的事。上级机关的意见常常不一样,有时稿子要改过去,再改过来。原因在于有时是院里的学部委员们审,强调学术性;有时是院部职能机关的领导审,强调导向性。这些要求不一样,此事以前也没有做过,没有固定的模板。于是,申请书反复修改,总是很难达到要求。我与白烨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喜欢早睡早起,白烨则喜欢熬夜。于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后半夜把改好的稿子发给我,我则五点起床,改到下午再发给白烨,两人通力合作。这个互助组前后陆续忙了大概有两个月,终于最后顺利过关。试点走出了新路,以后创新工程全面铺开时,创新工作方案就有了标准版,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在退休前为文学所理论学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申请“优势学科”。大约是在2015 年,当时,文学所研究文学理论的人员已经不再仅仅限于理论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室成立了,所里其他的部门也有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这时,院里有一个新的动作,要求各所申报优势学科,平均每所给一个名额,并给予一定的资助。于是,我将理论室、马文室、《文学评论》中的理论编辑,以及包括《中国文学年鉴》和网络工作室等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员整合在一起,主持写成申请书,再到院里的评委会上陈述。有了此前做创新工程方案的经验,这次做就顺利得多。经过一番努力,最终申请成功。从此,文学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有了固定的经费资助。这对此后直至今天理论室工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与文学所的工作
2010 年,我被任命为文学所副所长。在此前也曾参与过一些文学所层面的学术服务工作:
首先是参与组织了一些比较大的学术会议。记得第一次参与组织的,是1999年在社科院附近的“京都苑”召开的“全国文艺名家论坛”。当时的文学所领导决定,让我和黎湘萍、吕微三人做会议学术方面的工作。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文学所几乎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国内各高校文学学科的研究骨干参会。这些会议均由我们三个人在科研处长严平的领导下承担学术方面的服务工作。这其中包括起草会议的通知、会议新闻通稿、领导讲话的报批稿、会议综述,以及会后的各种汇报等会议文稿,还包括编辑会议手册和会议论文集,等等。另外,会议期间临时出现的各种学术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负责处理。会议的地点,大多在香山饭店或友谊宾馆。一年又一年,很多次这种有关文学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会议,都如期顺利举办。我们三个人在科研处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使每一次会议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类会议的举办,一方面加强了文学所与国内和国际文学学术界的联系,展示了文学所的科研实力,吸收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文学学科内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以及文学所内部不同研究室之间的学术联系。
在这20 年中,在文学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还策划和组织了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第一次是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际美学协会联合主办,由文学所承办的会议,题目是“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这次会议在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参加了会议,院长李铁映接见了与会的国外代表。来自国际美学界的20多位学者,其中包括当时的国际美学协会主席佐佐木健一、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秘书长柯蒂斯·卡特,以及著名的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沃尔夫冈·韦尔施、理查德·舒斯特曼,意大利的美学家格尔琪奥·玛琪亚努、芬兰美学家索尼娅等多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也有40 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反响强烈,非常成功。会后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论文集《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这些国外参会者中不少人当时是第一次到访中国,此后,他们来中国多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朋友。
2011 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中荷文化交流:文学、美学与历史”论坛。这是受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委托,与荷兰合作举办的双边会议,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莱顿大学、乌特勒支大学等著名大学以及文学研究所的研究骨干共20 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另外,文学所还分别与澳大利亚与俄罗斯举办过双边合作会议,还在徐州主办了一次邀请包括国际美学协会六位前任和现任主席在内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都很成功。
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所走出国门参加的会议,由文学所与国外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合作。其中有与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和科佩尔大学合作举办“文学的哲学阐释”双边国际合作会议,由文学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长杨义先生的带领下,赴斯洛文尼亚参会。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合作举办会议,文学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长陆建德先生的带领下,赴日本东京参会。这些会议都由我负责联络和牵头,做协调和组织工作。对于文学所来说,这也开了一种在国外召开双边合作会议的先例。许多参会者表示,组团出国开会,开拓了视野,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展现了文学所的学术实力。
从1997 年到2017 年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的过渡时期。全球化的浪潮,促进了学术上对外联系大门的打开,这种国际交流的发展,对于我们借它山之石,发展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在担任文学所副所长期间,除了承担一些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与同事们一道考察文学遗迹。我和文学所的许多年轻同事去了内蒙古、四川、重庆、江苏等很多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我们曾去万州在何其芳墓前行礼,去江苏无锡参观钱锺书故居,在重庆去了郭沫若、蔡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每年出去一次,回来都写出详尽的考察报告,积累了不少文稿。那些文稿应该还在所里吧,期待将来会有人整理出来发表。
兼职当编辑
在文学所,我的主业是做学术研究,自己写论文,同时也前后参编或主编过几份杂志,它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文学评论》《外国美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外文论》。
我参编的第一份连续出版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这是从2000 年至2010 年期间,在文学所领导下,由当时的各研究室主任参与编辑的一个集刊。记得当时为这个集刊付出比较多的,有蒋寅、吕微、黎湘萍、赵京华等人,所里指定由我在学术上负总责,严平处长和科研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对稿件的要求很高,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成熟一期就发一期。在那些年,后来流行的三大评价体系(南京大学的CSSCI、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院的AMI)还没有那么流行。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还能征得不少好的稿件,特别是一些篇幅较长且内容厚重的稿件。这个集刊发表过不少质量很高的文章。记得有一次参加社科院文学语言学科方向的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有四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的成果被各研究所经过评审而推荐上来,最终有三篇获奖。这个数字远远超越文学语言学科几个研究所主办的一些国内权威刊物。到了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由于不再能获得经费支持,只好停刊,现在想来很是可惜。如果能坚持下来,一定能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也能进入一些评价体系之中了。
我参编的第二个刊物是《文学评论》。我从2011 年起至2016 年任副主编,主要负责编辑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方面的稿件。《文学评论》原来就是国内的名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我们作为编者也不能只是乘凉,也要为这棵大树浇水培土,除虫剪枝。这是一个从办刊经费困难,需要多方筹款,到办刊经费能够维持,杂志走向正规化,向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转变的时期。在我参与杂志编辑工作期间,做了几件事:第一,杂志实现改版,从封面和版式的设计到一些专栏的固定化,做了一些阶段性工作。第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第三,电子投稿和审稿系统的尝试使用。随着社科院的杂志创新工程的实施,对刊物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于是,根据院里的要求,我与同事们一道为杂志制定了一些措施,并努力实施这些措施。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做到了与时俱进,保持了这个杂志在文学期刊中的权威地位。
第三个刊物是《外国美学》集刊。《外国美学》集刊是1985 年由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创刊并任主编的集刊,这是20 世纪80 年代美学热的产物,原本就在全国有很高的声誉。2000 年以后,由于原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人事方面的一些变动,刊物处在停滞状态,有五年没有出刊。受汝信先生的委托,我从2005 年开始接过此刊,并联系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从2005 年至今,已经有18 年了。从刚开始接手时每年编一辑,或者每两年编一辑,到了2013 年以后固定每年编两辑,这个集刊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集刊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院里经济上的资助,办起来很艰难。当然,也正是由于一开始就没有资助,才不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那样,断了资助就只好停刊。过去的18 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此前汝信先生编了18 辑,我接手后至今已经编了20 辑。目前,这个集刊的质量不断提高,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从2016 年起,这个集刊连续被评为CSSCI 集刊,2017 年起,被社科院科研局评为创新工程认可的集刊,2023 年又评为AMI 核心集刊,在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
我参编的第四个刊物是《中国文学批评》。这个刊物由社科院原副院长张江先生任主编,我参与负责学术方面的工作。刊物于2015 年创刊,创刊之初,稿源困难,在学界也不受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类的一份重要刊物,2017 年被评上全国百强期刊,此后,相继进入CSSCI 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AMI 新刊核心期刊。在中国文学类的刊物中,这个刊物栏目特色鲜明,问题意识强,有了很好的声誉。
我参加的第五个刊物是《中外文论》。这个集刊原本是《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年刊》,从属于中国中外文论学会,最初是学会年会的论文选。我接手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和会长以后,改名为《中外文论》,每年两期。这个集刊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目前正在努力,争取获得更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五个刊物外,我还曾参加了院里的一份英语人文学刊的编辑,参与者有黄平、朝戈金、陆建德和我。可惜这个集刊编了一期以后就没有能持续下去。
国际美学协会
我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习的是美学专业。1997年回国以后,积极加入美学界,参与中华美学学会的工作,同时也帮助中华美学学会建立国际联系。
我在国外学习时,就多次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通过这些活动,结识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在这些活动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参加世界美学大会和国际美学协会。
1995 年夏天,我赴芬兰的中部小城拉赫底参加了第13 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会议的参会者有四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学家。我在会上见到了包括阿瑟·丹托、今道友信、斯蒂凡·穆洛夫茨基、约瑟夫·马戈利斯等前辈学者,也见到了当时国际美学协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如阿诺德·贝林特、佐佐木健一、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柯蒂斯·卡特等人。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会上做了发言,发言稿后来发表在波兰的英文杂志上,这是最早向国际美学界介绍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 年代“美学热”的文章。
这次参会的经历使我感到,中国美学学者应该参与到国际美学组织和世界美学活动中去,这对中国美学学者了解世界、国际美学界了解中国美学都非常重要。过去的国际美学界受西方汉学家的影响,对中国古典美学有一些粗略的了解,但对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情况,则几乎是一无所知。这样一来,他们就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活化石。从孔子美学到清代画论,构成了他们对中国美学的全部印象。20 世纪的中国美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空白。中国美学研究者应该积极参与,向世界介绍现代中国美学,改变对中国美学的印象。同时,这种国际交流,对于在中国复兴当时还处在萧条状态的美学学科,建立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事。回国以后,我就积极争取,经过申请,来往多次通信,提交相关的资料,使中华美学学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
1998 年夏天,我赴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参加了第14 届世界美学大会。当时出国的经费还很困难,那次会议的旅费,部分是由国家人事部的留学回国人员办公室报销,部分由文学所报销。这一次,我是作为中华美学学会的代表参会的。我在会上介绍了中华美学学会的情况,也使国际美学界对与中国美学界建立联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世界美学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2001 年的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在日本千叶召开,这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召开,对于中国美学走向世界来说,这次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此前中国学者参加国际美学会议,还是零星的、偶然的,在会上也很边缘。这次在日本召开的会议,由于日本办会方的热情安排,组织了一组亚洲美学论坛,分别有日本、韩国、中国、南亚。在这些论坛中,有一个中国美学论坛,由我和叶朗、彭锋、罗筠筠、朴松山发言。除了这个中国美学圆桌的参与者以外,中国学者对这次会议的参与也是空前的,大概有20 多位来自中国大陆各个高校的学者参会。中国和亚洲学者的参与,受到了国际美学界的欢迎,也在新世纪之初给国际美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2006 年,在中国成都举办了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的中期会议。我在这次会上促成了2010 年在北京举办第18 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决定。
2007 年,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先生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赴土耳其安卡拉参加了第17 届世界美学大会。中国美学界对国际美学活动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也持续增长,大约有40 多名中国学者参会。从这次会议起,我开始担任国际美学协会的秘书长。
2010 年,由国际美学协会主办,中华美学学会和北京大学美学美育中心承办,在北京举办了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会议盛况空前,国外有400名学者参会,中国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共有近1000 人参会,中国美学家们与国际美学界的交流大门从此打开。
记得在北京的这次大会上,日本著名美学家、国际美学协会前会长佐佐木健一先生说:
日本原来乒乓球很好,后来就被中国超过了。看来美学也会是如此,中国要超过日本。
随着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复兴,中国美学也在走向世界。我从2007 年至2013 年担任了国际美学协会的秘书长,2013 至2016 年担任会长。2016年卸任会长以后,为了保持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的联系,我仍继续参与国际美学协会的工作,同时,推荐和鼓励中国美学界年轻、外语好的学者积极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争取被国际美学界认可。从1995年至2019年,我连续参加了9次世界美学大会。
其他学会的工作
过去的一些年,我主要参加了四个学会的工作,这四个学会分别是:国际美学协会、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
国际美学协会的工作,前面已经概述过。这个学会1913 年成立,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学会,是国际美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学术组织。我担任过三年副秘书长、六年秘书长、三年会长,现已卸任。目前还在参加一些协会的活动,并努力推荐年轻的中国学者参与这个协会的工作。
中国中外文论学会成立于1994 年,原来是由前辈学者钱中文担任会长。2008 年,我被选为学会秘书长。从2013 年起,我任学会会长至今。在过去的这15年间,该学会每年都举办年会和各种学术会议,对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会下属叙事学、符号学、巴赫金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等分会。
中华美学学会是1980 年成立的全国性美学组织。此前先后由朱光潜、王朝闻、汝信三位相继担任学会会长。我从2015 年起被选为学会第四任会长,担任此职务至今。学会每年举办年会,下属的十个学术委员会或专业委员会也各自举办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活跃了学术气氛,有力地促进了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于2014 年成立,由原社科院副院长张江担任会长,我担任学会的秘书长,参与了学会的创建工作。2019 年换届后,我担任学会副会长至今。这个学会致力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结合,以《中国文学批评》杂志为阵地,同时也每年召开年会,推动文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个人的学术著作、论文和翻译
我回国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前,在瑞典曾撰写和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中文著作《画境探幽——中国艺术的精神结构》,在中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另一本是英文著作《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出版。另外,还在国外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了20 多篇中英文文章。
回国后在文学所工作的20 年,即从1997 年至2017 年,先后写作出版了四本学术著作,分别是《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美学的当代转型》。在这期间,还翻译出版了四本学术著作,分别是《先锋派理论》《艺术即经验》《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弗洛伊德的美学》;主编了《西方文论经典》(6 卷本)、中英对照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发表的论文有一百多篇。
2017 年退休后,迎来了一个学术著作出版的高潮,先后出版了《文学与美学的深度与宽度》《回到未来的中国美学》《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观念史》《中华美学精神》,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1949—2019)》(2 卷本)、《20 世纪中国美学史》(4卷本),以及主编出版了三本文选,分别是《西方文论经典精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精读》《西方美学经典精读》,主编一本教材《美学核心素养》。除此以外,还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美学与艺术:比较视野下的传统与当代中国》,在加拿大的Royal Collins 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法文著作《中华美学精神》,另外还发表了近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现在,我正在做两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一是重大专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一是重大招标“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研究”,成果最终会结集出版。
展望下一步,各种学术行政、学会、编辑的工作,都会陆续卸下,但写书、编书、译书的工作还不会断。记得美学家朱光潜在80 岁后谈工作计划,结尾时说了一句话:春蚕到死丝方尽。朱先生是大学者,说的话也那么动人。我想说的是,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吧。工作是愉快的,坚持做工作是会使人长寿的。
当然,我会常回文学所看看,见老朋友叙叙旧,与年轻人聊聊天。我人生最好的年华是在文学所度过的,对文学所有一种永远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