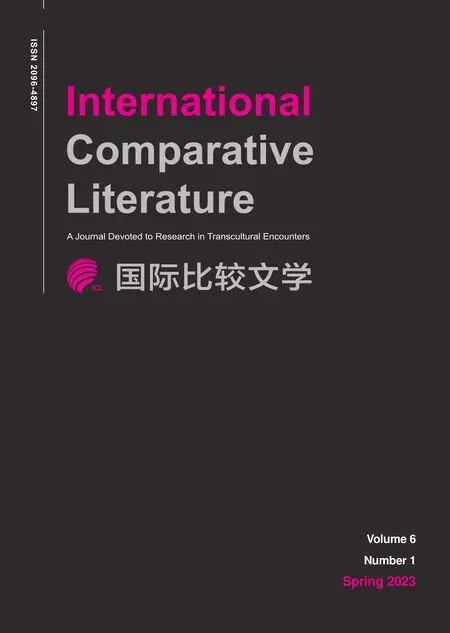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
2023-09-26顾钧北京外国语大学
顾钧 北京外国语大学
近代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心。辛亥革命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和中外学术交往的深入,在北京出现了多种英文学刊。但到底有多少种,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还无法精确统计,特别是有些刊物办刊时间短,印量有限,更增加了统计的难度。国内已有的成果主要是在中文期刊方面,无论是综合性的(如《解放后中文期刊目录》),还是专业性的(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都为今后从事外文期刊的整理编目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这批英文学刊均未有系统研究,本文作为首次尝试,在全面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将重点评述三份刊物:(1)中国政治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1916-1941)、(2)辅仁大学主办的《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oftheCatholicUniversityofPeking,1926-1934)、(3)燕京大学主办的《燕京社会学界》(TheYenchingJournalofSocialStudies,1938-1950)。这些刊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仅享誉国内,在国际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同一时期中文刊物的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学刊,主要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2 年创办)、《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创办)、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4年创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5年创办)。从起点看,《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创办于1916年,早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北大《社会科学季刊》创刊于1922 年,终刊于1943 年,共出版8 卷;清华《社会科学》创刊于1935年,终刊于1950年,共出版6卷;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办刊时间前后25年,共出版24卷。无论是办刊时长,还是出版数量,后者均处于领先地位。就近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来说,这些英文刊物的重要性都不容置疑。
一、《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以下简称《学报》)是中国政治学会的会刊。《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16 年4 月)的首篇文章《学会的缘起》(The Origin of the Association)有助于我们了解学会的基本情况。
学会建立的动议来自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1869-1923),他提议仿效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03 年建立)成立一个中国政治学会,旨在研究国际法和外交。芮恩施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后刊物的主编严鹤龄(1879—1937),严又向顾维钧咨询建立这个学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几位发起人决定召开筹备会议,讨论实施方案。由于顾维钧很快赴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学会的组织工作落在了严鹤龄一个人身上,严于是寻求伍朝枢(1887—1934,后担任学会秘书)的帮助和合作。伍朝枢全力支持建立学会的想法,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自1915 年9 月至11 月,不少中外学者被邀请参与筹备,为制定学会章程建言献策,其中特别活跃的是美国政治学者韦罗贝(W.F.Willoughby,1867-1960),当时任北洋政府顾问。
1915 年12 月5 日,中国社会政治学会(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大会召开,地点在时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官邸,65 名成员参加,会议一开始选举了学会的领导人。会长为陆徵祥,第一副会长为芮恩施,第二副会长为曹汝霖(时任外交次长),秘书为伍朝枢,财务为章宗元,理事为严鹤龄、张煜全、林行规、王景春、周诒春、吴乃琛、胡诒榖、麻克类(J.W.R.Macleay)、韦罗璧(W.W.Willoughby)等九人。从以上名单不难看出,学会领导以外交界人士为主。当然不少人同时也是学者,可谓学者型的官员。此后学会定期改选,继陆徵祥之后担任会长的有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胡适等人。
从学会建立之初,《学报》的创办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学会领导多次召开会议,就刊物的语言、目标、范围和性质等展开讨论。最后确定《学报》的语言为英文,主要目标是一方面引进国外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向外国读者介绍有关中国的信息和学术发展,而后者是重点。至于稿件的范围,则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主。我们发现,这些原则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办刊过程中基本得到了执行。
《学报》从第1卷第1期(1916年4月)开始,到第24卷第4期(1941年3月)结束,前后25年,共24卷、93期。《学报》为季刊,正常情况下一年四期,但也有特殊情况,如1920年第5卷为了集中刊载有关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文件和论文,将第1、2期(1920年3月、6月)合并出版;第6卷因故只出了1、2期,没有3、4期。另外,1921年停刊一年,没有出版。
起初《学报》只有英文名,1931 年第15 卷至1938 年第22 卷上有胡适题写的中文刊名《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学报》的发行不限于国内,从创刊之初就瞄准了海外市场,而且发行范围一直在拓展。如1937 年第20 卷上刊登的各地授权代理商分别为:北京法文书店、上海别发洋行(另有新加坡办事处)、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另有大阪、京都、札幌办事处)、纽约办事处。而到了1941 年第24 卷出版时,除了北京、上海、东京、纽约的代理商之外,又增加了伦敦、巴黎和莱比锡几处。《学报》的价格为国内订户年费4 元、单册1.2 元;国外订户年费2美元、单册0.6美元。
《学报》栏目分为论文、消息与札记(News and Notes,后来改为 Notes and Suggestions)、书评。值得一提的是,《学报》上不少文章都是在学会会议上的演讲稿。学会成立后,除了每年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外,还经常举行小型的联谊会(smoker),这些会议一般都会邀请1-2 位知名学者发表讲演。如1916年2月15日,芮恩施在美国驻华公使官邸召开了一次联谊会,约100 名会员参加,严复和韦罗璧应邀发表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古代政治组织概览》(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和《预算的性质与作用》(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a Budget),后来两篇演讲稿发表在《学报》第1卷第4期。
《学报》编辑部由主编、业务编辑、经营编辑组成。首任主编严鹤龄(第1卷第1期至第5 卷第3 期),此后担任主编的有张煜全(1879—1953)(第5 卷第4 期至第6 卷第2 期)、刁敏谦(1888—1970)(第7卷第1期至第14卷第4期)、蒋廷黻(1895—1965)(第15卷第1期至第18 卷第4 期)、萧公权(1897—1981)(第19 卷第1 期至第21 卷第4 期)、张煜全(第22 卷第1期至第24卷第4期)。
严鹤龄1908年考取浙江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就读,先后获法学硕士(1909)和博士学位(1911),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参加过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曾任驻美公使,并两次出任清华校长。张煜全1901年作为北洋大学官费生被派往美国留学,1904 年获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任清华校长。刁敏谦1916年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英文《北京导报》总编辑、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等职。蒋廷黻1912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萧公权1920 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攻读政治哲学,1926 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49 年底赴美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主编均有留学背景,所获学位和研究领域为法学、政治学、外交学,也正是《学报》的主要方向。
《学报》上的各类文章约630 篇,不计书评、札记、短文、编者按语,学术论文约360 篇。其中法学(包括国际法、外交学、国际关系)约120篇,政治学(含政府学、行政管理学)约50篇,经济学(含财政学)约60篇,社会学(含人类学)约30篇,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共13篇,人文学科(文史哲)约40篇,海外汉学47篇。
《学报》的作者队伍阵容强大,各类文章的中国作者约180 人,外国作者约150 人。就中国作者来说,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不少具有博士学位。法学如王宠惠1881—1958(耶鲁大学)、刁敏谦(伦敦大学)、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夏晋麟(爱丁堡大学)等;政治学如鲍明钤1894—1961(霍普金斯大学)、王造时(威斯康辛大学)、徐淑希(哥伦比亚大学)、崔书琴(哈佛大学)、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等;经济学如马寅初(哥伦比亚大学)、何廉(耶鲁大学)、方显廷(耶鲁大学)等;社会学如许仕廉(衣阿华大学);心理学如刘廷芳(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政府部门(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工作,另一类则为高校教师,其中执教清华者(很多也是原来清华毕业生)比例最高,以《学报》上政治类论文和书评的作者来看,清华师生占据了绝对优势:浦薛凤(1900—1997)、时昭瀛、王化成、张忠绂、沈乃正、崔书琴(1906—1957)、陈之迈、刘师舜(1900—1996)、杨光泩(1900—1942)、萧公权、王造时、邵循正(1909—197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的魁格雷(又名桂克礼,Harold S.Quigley,1889-1968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于1921 年9 月至1923 年6 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劳力(Selden G.Lowrie,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于1922 年9 月至1923 年6 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克尔文(又名恪而温,Edward S.Corwi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主任)于1928 年9 月至12 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
就外国作者来看,不少都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主要分布在驻华使领馆、中国政府部门、高校(特别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在华外国公司企业。就《学报》最为关注的法学方面来看,外国作者中有多位曾在中国政府担任法律(宪法、司法)顾问,如1912 至1919 年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有贺长雄、1914 至1916 年的法律顾问韦罗贝、1916 至1917 年的宪法顾问韦罗璧、1917 至1919 年的法律顾问德尼斯(William C.Dennis)、1919 至1929 年的司法和立法顾问宝道(Georges Padoux)、1921 至1930 年的法律顾问埃斯加拉(Jean Escarra)。
从《学报》上文章的数量来看,国际法学是讨论的重点。在国际法学领域,不平等条约的修订一直是热门话题。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留学生群体的民族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迫切地希望这个新兴的共和制国家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享有与他国一样的平等待遇。1920年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加入国际联盟,无疑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然而,就现有的条约关系来说中国仍处于不平等地位,这一现实与国人特别是留学生的期许有相当大的落差。
在民国初年的留学生当中,率先在《学报》上发文探讨修约重要性的是刁敏谦。刁氏于1916 年7 月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与各国条约上之义务》详细阐述了中外条约签订与执行中种种不合乎国际法准则之处,是最早从法理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专著之一。回国后刁敏谦沿着博士论文的思路,在1917年《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与和平会议:修约问题》(China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 Problems of Treaty Revision)一文,继续探讨相关问题。该文开门见山地指出,目前外国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之中,领事裁判权是比驻军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更为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在刁敏谦看来也未必对外国人真有便利可言,因为它不仅限制了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自由,也大大增加了外国领事的工作量。虽然英国早在1902年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中就承诺将考虑撤销这一特权,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2 册第103 页。[ WANG Tieya, Zhongwai jiu yuezhang huibian (Collection of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1949), vol.2,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2019, 103.]但十五年过去了,英国还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其他如美国、日本等也是如此。
刁敏谦写这篇文章时,一战还没有结束,巴黎和会也还没有召开,但他已考虑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中国应该向列强提出哪些修约要求,真可谓未雨绸缪。虽然惨烈的战争还在继续,但刁敏谦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从这次大战中将诞生新的世界,新的体制将被建立,在这样的前景中寄寓着我们的期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将根据理性的原则重新调整。”2M.T.Z.Tyau, “China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 Problems of Treaty Revisio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 no.2 (1917): 54.后来的事实表明,刁敏谦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要求确实成为巴黎和会时中方的一大诉求。
刁敏谦在英国的博士论文没有在《学报》上刊载,《学报》上发表的是夏晋麟1922 年在爱丁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英条约关系:国际法和外交研究》(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主体部分的7个章节,分7 次连载(1923 年第2—4 期;1924 年第1—4 期)。这7 个章节分别是:(1)领事裁判权;(2)专管租界与公共租界;(3)租借地及势力范围的历史概况;(4)租借地;(5)势力范围;(6)门户开放、领土完整与政治统一;(7)关税自主。夏晋麟同样主张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收回这一权力无法一蹴而就的,需要分步走。他在论文第一章的最后提出了六步走的建议:一、颁布新的全套的法律法规,建立新式的法院;二、如果案件涉及外国人,聘请外国法官与中国法官共同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审理;三、在通商口岸尽量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移送中国法庭审理;四、在内地逐步取消领事裁决民事案件的权力;五、在通商口岸逐步取消领事裁决民事案件的权力;六、逐步取消英国领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裁判刑事案件的权力。3Ching-lin Hsia,“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Chapter 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 no.2 (1923): 46-47.
虽然要收回旧条约中的权益不容易,但在签署新条约时完全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刁敏谦在发表于《学报》第9 卷第4 期(1925 年10 月)的《中国的新条约》(China’s New Treaties)一文中,回顾了“一战”结束后中国和智利、瑞士、玻利维亚、波斯等国签订的协议。举国上下反对领事裁判权在这些新条约中得到了体现,中国和波斯1920年6月1日签订的《友好条约》第五条中明确表示没有领事裁判权。和以前签过合约的国家再签约时,也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条。巴黎和会中国拒绝签字,后来和德国单独订立新的《中德协约》(1921年5 月20 日签署)时,德国放弃了领事裁判权。1921 年9 月26 日和墨西哥签订的《暂行修改中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条约之协定》中,墨西哥政府“自愿表示,将来正式修改该约,本国政府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一事,当居修改各款之一。”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册第183页。[ WANG Tieya, Zhongwai jiu yuezhang huibian (Collection of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1949), vol.3,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2019,183.]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苏联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 年5 月31 日签订),苏联政府宣布,“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同时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5同上,第399页。[ Ibid., 399.]刁敏谦对这些新的进展感到高兴,也对全面解决领事裁判权问题充满期待。
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在国家层面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动力,在个人层面也刺激了不少中国学子研习国际法,顾维钧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表示,自己在美留学期间“一直对外交关系有兴趣,并想改进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方法”。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 册第72 页。[ GU Weijun, Gu weijun huiyilu (Memoirs of Gu Weijun), vol.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72.]他1912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外人在华之地位》是最早全面讨论中外条约体系的著作,其中对于领事裁判权的由来、发展、作用有详细的描述。此后的英美留学生刁敏谦、鲍明钤、刘师舜等对此继续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顾维钧在论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修约的要求,而后来者不仅要求明确,而且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国际法知识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刁敏谦对“情势变迁”(Rebus sic Stantibus)原则的运用,这是国际法中一条古老的原则,它设定签订条约时缔约国是以某些根本情势的继续存在为前提的,但一旦这种根本情势发生变化,缔约国就可以根据该原则废除条约。刁敏谦在博士论文中使用了这一原则作为中国要求改订条约的法理依据。他后来在《学报》上发表的《中国与和平会议》一文再次运用了这一原则,他指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是清朝帝制时代订立的,现在民国已经建立,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旧的条约义务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因此其修约要求必须被正视。
二、《辅仁英文学志》
《辅仁英文学志》创刊于1926 年9 月,终刊于1934 年11 月,共出版9 期,1926—1929 年期间基本是每半年出版1 期,共计6 期,1930 年12 月、1931 年12 月分别出版了第7、8 期。之后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直到1934年11月才出版了第9期,也是最后一期。起初该刊只有英文名,第7期扉页上出现了《辅仁英文学报》的名称,第8、9期则更名为《辅仁英文学志》(以下简称《学志》)。
《学志》没有订阅费,免费向校友会成员发放。1—6期上有Printed in the U.S.A.字样,表明该刊当时在美国印刷;7—9期则在北京印刷,扉页上有“北平定府大街辅仁大学印行”字样。
《学志》上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另一类是反映大学创办情况的介绍性文字,通过后者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辅仁大学的早期历史。《学志》第1 期刊登了英敛之与马相伯致罗马教皇碧岳十世的信件《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Letter to Pope Pius X)、《辅仁社》(The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英敛之讣告》(Obituary of Sir Vincent Ying)、《辅仁大学的中文名称》(The Chinese Nam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四篇文章,全面展示了辅仁创办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英敛之起了关键作用。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爱国天主教徒。1902年于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牗民智作为宗旨。1913 年秋他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传授中国文化知识,成为后来辅仁大学的发祥地。“辅仁”出自《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句话,既典雅,又能反映中国文化特色。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不幸因病去世,临终前将校务托付给陈垣。此后陈垣与相关人士一起做了大量筹备工作,1927年底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辅仁大学正式成立。
《学志》没有标明主编和编委会,估计应该是在陈垣的领导下中外教师共同负责。就学术论文来说,《学志》以中西交通为主要内容,自第1 期起便把目光投向中国天主教早期历史,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如奥图尔(G.B.O’Toole)的《中国早期基督教漫谈》(Random Notes on Early Christianity in China,第3 期)、高福德(Francis Clougherly)的《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方济各会会士》(The Franciscan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第5 期)等。其他宗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的英译文,该文原载《国学季刊》,一经发表就受到高度评价。陈垣在说明该文缘起时写道:“今摩尼教久亡,经典焚毁殆尽,言摩尼教者只可求诸基督教史。然欲求中国摩尼教史料,则又非基督教史所有,只可仍求之汉文典籍,及诸佛教史中。然无论为基督教史,为佛教史,其对于摩尼,均具贬词。考古者只可取其言外之意而已。”7陈垣:《陈垣全集》第2 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42 页。[ CHEN Yuan, Chen Yuan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2,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2.]该文由英千里将其中第2 章《摩尼教始通中国》和第15章《元明时代摩尼教》译为英文,以Manichaeism in China为题发表于《学志》第4期。
英千里早年留学欧洲,精通英、法等多种外文,长期担任辅仁大学秘书长及西洋语言文学系主任,除了陈垣的论文外,他还翻译了多篇重要文献。发表在《学志》第5期的《景教碑文新译》(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storian Tablet)是中国学者最早的尝试。为了说明景教的衰落,英千里还翻译了唐武宗打击景教徒和佛教徒的直接资料——《武宗还俗敕令》(The Secularization Decree of Emperor Wu-Tsung),并发表于《学志》第6 期。此外,他还在《明朝末代皇帝与天主教》(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atholicity)中将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带给罗马教宗的中文信件翻译为英文。
景教是传入中国最早的基督宗教教派,在《学志》上备受关注。根据历史记载,聂斯托利派传教士于唐贞观九年(635)抵达长安,在明天启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立,现存西安碑林,正文汉文34行,1780字)出土以后,这一宗教即被称为景教。景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到会昌五年(845)被禁断,在唐代流传达210年,但是后世典籍中一直只有零星的资料,直到景教碑的发现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景教虽然很早传入中国,但因为中途断绝,加上文献稀少,对于它的性质一直存在认识误区,在中国历史上,有人将景教与祆教、摩尼教混为一谈,也有人将其与回教混同。直到20世纪,国人对于景教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聂斯托利派乃第五世纪之一异端,创于聂斯托利,聂斯托利生于西利亚(Syria),为安底奥血(即吾国古书之安都城Antioche)隐修院院长,律己严,善辞令,四百卅八年升为君士坦丁堡大宗主教(Patriarcha de Constantinophe),其所讲之异端道理,是反对圣母称为天主之母;……总之,依聂氏所言,从圣母所生者,是有形可见之人,成为司祭,受苦受难而死。天主物尔朋常与此人缔结,有不能分离之情;然天主物尔朋非降生为人焉,所以在基多有着行之二位:一、天主之子,二、圣母之子。”8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 年,第85 页。[ XU Zongze, Zhongguo tianzhujiao chuanjiaoshi gailu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The Roman Catholic Mission Press, 1938, 85.]中国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今天早已成为不刊之论。关于景教,《学志》上发表了3篇译文:英千里翻译的景教碑文、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翻译的《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部分)。
被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劫掠到法国的敦煌写本(代号:P.3847)《尊经》中罗列了三十部景教经典,但迄今为海内外学界所公布的仅八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宣元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9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第212 页。[ WENG Shaojun, Hanyu jingjiao wendian quanshi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Nestorian Classic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212.]其中景教碑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叙述此教流行过程的唯一文献。英千里将其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学志》第5期(1928年10月)。因为此前已有多份译文,所以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新”(new)译。奥图尔专门为译文写了序言,指出英千里的译文超过前人,可谓后出转精。遗憾的是,这份质量上乘的作品一直不为学界所知,朱谦之在权威的《中国景教》(初稿完成于1968 年)一书中详细罗列了各个时期的译本,却偏偏没有英千里的译作。10“景教碑自公元1625 年罗雅各(佐伯好郎认为是金尼阁)发表拉丁文译本以后,至1939 年福斯德(John Foste)教授之出版英译本,过去300余年间,在欧美各国作为著书发行之景教碑文研究,约有80余种。……至19世纪时,又有许多重译,英文中有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白里枢曼(Bridgman)译本,有1854年(咸丰四年)卫礼(Alexander Wylie)译本,见《中国研究》(Chinese Researches, pp.25-34)及何尔漠(Fritz V.Holm)《景教碑》(The Nestorian Monument, pp.11-20)书中。……日本则有明治44 年佐伯好郎(P.Y.Saeki)之《景教碑之研究》与1916 年(民国五年)之英译本,见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pp.162-181),尤为研究者所广泛使用(例如C.E.Couling: The Luminous Religion, pp.49-63附录佐伯译文,又Holm: ‘My Nestorian Adventure in China’, pp.159-183亦全录佐伯译文与 Wylie译文对比)。……截至近日,尚有如毛尔只英译两种,一见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p.45-52),一见 ‘The Christian Monument at Sian Fu’(1935),又福斯德(John Foster)之英文新译本见 ‘The Church of the Tang Dynasty’附录一pp.134-151(1939),真可算是洋洋大观了。”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85~88 页。[ ZHU Qianzhi,Zhongguo Jingjiao (Chinese Nestorianis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85-88.]英千里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他的译文也已经出版将近一个世纪,“新”译早已成为旧作,他的贡献应该尽快得到学界重视。
另需特别关注的是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两篇景教译文。在敦煌文献发现前,景教碑几乎是唯一的研究资料。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多的景教文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两种先为晚清收藏家李盛铎所有,后流失到日本,今存日本。
1931年陈垣利用拜访李盛铎的机会抄写了《宣元本经》卷首10行,约190个字:“时,景通法王,在大秦国那萨罗城和明宫宝法云座,将与二见,了决真源,应乐咸通,七方云集,有诸明净士,一切神天等妙法王,无量觉众,及三百六十五种异见中民,如是族类,无边无极,自嗟空昧,久失真源,罄集明宫,普心至仰,时景通法王,端严进念,上观空皇,亲承印旨,告诸众曰:善来法众,至至无来,今柯通常,启生灭死,各圆其分,静谛我宗,如了无元,碍当随散。即宣玄化匠帝真常旨,无元无言,无道无缘,妙有非有,湛寂常然。吾……”11P.Y.Saeki, “The Sutra on the Mysterious Rest and Joy,”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9 (1934): 119.他将这份珍贵的文献送给了佐伯好郎,佐伯将之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学志》第9期上。
值得注意的是,佐伯在个别重要概念和名称的理解和翻译上有商榷的余地。如他将“景通法王”翻译为King-ching(Mar Sergis,860-872 A.D.?),从King-ching 来看,是指景净(景教碑文作者),但从Mar Sergis 来看,又是指景通(景教碑文侧面人名中之“景通”,英文名字拼写为Ching-t’ung)。但在当代一些学者看来,将“景通法王”理解为耶稣更为合理:“在《景教流行中国碑》底侧面刻了许多僧人名号,中间也有‘僧景通’之名,但那景通只是‘副德’,不得称为‘法王’。景教碑的侧面,‘僧景通’三字上面还有叙利亚文注明是Mar Sergis,……由此看来,Mar 之为‘景’无疑,Sergis 之为‘通’也自在理中。若把这名字看做‘以马内利’也可通,也有‘通天教主’之义。那么‘景通法王’也可说是耶稣了。否则在保罗之前,能于拿撒勒城大显法力,七方云集,都来听他说教的,还有谁呢?”12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第160 页。[ WENG Shaojun, Hanyu jingjiao wendian quanshi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Nestorian Classic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160.]笔者认同这一理解,“景通法王”指的是耶稣,不是景净,也不是景通。
《志玄安乐经》(以下简称《志经》)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最早从李盛铎处看到原件的是日本东方学家羽田亨,羽田抄录并公开《志经》录文后,佐伯好郎参考羽田本录文率先将《志经》英译,于1934 年将译稿和汉字录文发表在《学志》第9 期上。佐伯在没有看到原件的情况下,首先将羽田本中有疑问的地方(用“?”在录字旁表示)根据自己的判断写定,其次是更为大胆的做法,将原写本首端残缺部分(第1-10 行,约残90 字)加以填补。佐伯后又将其录文收入1935年和1943年出版的日文著作以及193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的景教文献及遗物》(TheNestorianDocumentsandRelicsinChina)。由于佐伯的这三部书一直被视为中国景教研究的权威之作,在海内外学界影响极大,因此,在原件没有公布之前,学者所用《志经》文本,都是根据佐伯本录文。
由于种种原因,《志经》的原件直到2011年才公布。景教学者的最新研究发现,羽田亨当年抄录时有不少错漏,其中最大的错误出现在“船舶既全,前岸可到”这一句,“全”,底本作“全”,清晰可辨。羽田本作空格“□”,佐伯本补作“破”。“全”“破”意义截然相反。“前岸可到”,羽田本作“前岸不可到”,衍录“不”,佐伯本照抄为“前岸不可到”,并据此文义补羽田本“□”为“破”。英文翻译是“Though the boat may be able to sail over the windy sea,yet he may not arrive on the opposite shore,if the boat itself is already (wrecked).”13P.Y.Saeki, “The Sutra on the Mysterious Rest and Joy”, 119.这就完全与原文相反了。
尽管佐伯当年因为无法看到原件,跟在羽田后面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来看,他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一位景教文献的最新研究者指出:“佐伯好郎在完全没有见过《志经》原件和照片的基础上,仅凭羽田亨的录文进行研究,就大胆地把羽田亨踌躇未定的字确定下来,这种做法,在《志经》照片没有公布之前来看,无疑是冒有很大的风险,不符合历史文献整理的一般原则。但是今天看来,佐伯好郎确定的羽田本带‘?’标识的字词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其当年的冒失之举绝不是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臆测杜撰’,而应该是建立在对《志经》文本内容深入研究前提下进行的。……此外,佐伯好郎对第2-10下半部底本残缺文字进行的补录,以前也评价不高。但是,今天看来,在没有新的《志经》版本发现之前,要想推进《志经》的研究,只能从《志经》文本入手,结合其他宗教文献。佐伯好郎的补录文字虽然未必全对,但是最终大胆尝试的做法无疑值得肯定。总而言之,佐伯好郎实在无愧于中国景教研究第一人的称谓。”14聂志军:《唐代景教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40~141页。[ NIE Zhijun, Tangdai jingjiao wenxian yanjiu (A Study of Nestorian Documents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6, 140-4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佐伯《志经》录文和英译最初发表于《学志》1934年11月第9期,后来又收入其1937 年版英文著作《中国的景教文献及遗物》。以往学界普遍认为 1937 年版和1934年版完全相同,但据笔者查看,实际上却有一些出入,值得引起相关学者的高度注意。
三、《燕京社会学界》
英文《燕京社会学界》(以下简称《学界》)为燕京大学所办,半年刊,创刊于1938 年6月,1941 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关闭,当年8 月出版第3 卷第2 期后休刊,1948年8 月复刊,至1950 年出版至第5 卷第1 期后停刊。该刊第1、2 卷由位于天津的直隶印字馆印刷,第3卷由北洋印字馆在天津、北京两地分别印刷,第4卷则由辅仁大学印书局在北京印刷。价格是每卷国外2美元,国内3元。
各卷期的出版具体情况如下:第1卷第1期(1938年6月);第1卷第2期(1939年1月);第2 卷第1 期(1939 年7 月);第2 卷第2 期(1940 年2 月);第3 卷第1 期(1940 年10 月);第3卷第2期(1941年8月);第4卷第1期(1948年8月);第4卷第2期(1949年2月);第5卷第1期(1950年,月份不详)。
1938年6月《学界》创刊之际,北京已经在日军的统治之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立大学”南迁,“燕大”因为是教会大学得以在北京继续办学。但毕竟是战争年代,刊物无法做到半年一期,但一年两期还是基本得到了保证。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1948复刊,代理校长威廉·阿道夫(William H.Adolph)的复刊词是这样写的:“经过七年停顿,本刊第四卷的出版可以说是战后复员的又一举措。抗战胜利后,大学开始恢复数学、化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课程的本科教学,在此基础上,重建学术刊物是很适宜的。在从灾难中复原的时候,物质生存的根本问题占据了我们太多的精力,但生命更高层级的东西也必须找机会来表达,在苦难的时候诗歌往往很繁荣。因此,虽然内战的枪声还在远山回响,重新出版在社科领域的有创见的论文和研究材料,并非不合时宜。《燕京社会学界》的出版得到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The Princeton-Yenching Foundation)的资金支持,这个基金会由一群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发起,对于创建“燕大”法学院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的兴趣持续不减,不仅在于培养学生,也在于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政治研究项目。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持续的鼓励与支持。”15William H.Adolph, “Foreword,”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4, no.1, (1948): i.但因为政治局势的大变化,《学界》复刊后只坚持了一年多,就彻底停刊了。
《学界》的创刊主编为李安宅(1900—1985),从第2 卷第1 期开始,吴其玉接替李安宅担任主编,直到第3 卷第2 期结束。1948 年8 月复刊后的第4、5 卷由陈芳芝任主编。李安宅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赴美国加州大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留学,1937年回国后任燕大社会学系副教授。他只担任《学界》第1卷主编是因为此后离开了燕大,以教育部边疆视察员的身份深入甘南藏族地区从事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调查。李安宅后来受聘于华西协和大学,成为著名的藏学家。吴其玉于1927和1929年获得燕大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1933 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任燕大政治学系教授。陈芳芝1935 年燕大政治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39年获拜因麦尔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任教于燕大政治系。
《学界》发刊词是这样写的:“本刊旨在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发表平台。尽管也欢迎运用比较的、实用的、理论的方法研究国外问题的稿件,但本刊将主要致力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题研究,如家庭问题、当代城市建设问题等。本刊欢迎5 个方面的稿件:(1)用社会科学方法对当代及历史问题做出的原创性研究;(2)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3)田野调查报告;(4)书目文献;(5)书评。”16An-che Li,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 no.1 (1938): ii.该刊主要有3 个栏目:论文(Articles)、札记与释疑(Notes and Queries)、书评(Book Reviews)。论文以社会学方向为最多,其次是经济学、政治学,其他如文学、新闻学、教育学方向也偶有刊载。这也完全符合燕大的学术传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是该校三大支柱系科,其中社会学力量最强,影响也最大。书评栏目对国内外近期出版的中外文图书进行评论,以与中国相关者为主,如第1 卷第2 期郑林庄《评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陈其田《评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第2卷第2期陈其田《评费孝通〈江村经济〉》、第4卷第1期何国樑《评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这四本著作均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学术思想研究的名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撰稿人敏锐的洞察力。“札记与释疑”栏目主要服务于自由讨论和分享信息,文章相对比较短,也不像论文那么正式。李安宅这样表达对这一栏目的期待:“我们希望给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澄清立场和交换意见的空间,更希望从这里能够产生一种团队精神,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合作。这个栏目欢迎提出问题,发表新见,分享研究数据。”17An-che Li, “Notes and Queries,”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 no.1 (1938): 122.作为开篇,李安宅刊发了自己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必要性》(Notes on the Necessity of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一文,此外杨堃和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为老师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辩护、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孔子与〈春秋〉》(Confucius and the Ch’un-Ch’iu)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章。除了上述三个固定栏目外,该刊还不定期刊发“书目文献”(Bibliography),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其中第1卷第2期罗文达(Rudolf Löwenthal,1904-1996)的《犹太人在中国研究目录》(The Jews in China)尤为重要。
1948 年复刊后,刊物的主要栏目没有什么变化,专题研究的方向则有所转变,更侧重于中国的边疆、社会管理和国际关系。这反映了在新的形势下主编和编委会的意图。
《学界》的特点在于无论是论文、书评还是其他文章,质量均属上乘。这主要得益于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而这一队伍基本以燕大师生为主。在《学界》上发过文章的老师,按照院系排列如下:社会学系:李安宅、赵承信、杨堃、关瑞梧、黄迪、林耀华、蒋旨昂;经济学系: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戴乐仁(T.B.Taylor)、郑林庄、陈其田、文国鼐(Augusta Wagner);政治学系:吴其玉、陈芳芝、戴德华(G.E.Taylor)、顾敦鍒、何国樑、张锡彤(兼职);心理学系:陆志韦、夏仁德(R.C.Sailer);新闻学系:罗文达;哲学系:博晨光(L.C.Porter)、张东荪;历史系:王克私(Ph.de Vargas)、齐思和、王聿修;西方语言系:谢迪克(Harold E.Shadick)、刘乐意;教育系:高厚德(Howard S.Galt)、廖泰初;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赵丰田。这批燕大教师的特点是学历高,中国学者大都具有留学背景,而不少外国教师则是汉学家,如博晨光、王克私、谢迪克等。其他不是燕大教师的作者,不少和燕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夏白龙是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助理教授,1937—1938 年在燕大做访问研究;裴德士(W.B.Pettus)是北京华文学校校长,该校曾和燕大有过密切的合作。
在《学界》上,社会学家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特色。赵承信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计论文3 篇,书评11 篇。赵承信在美国留学时即专攻人口学,归国后继续从事人口研究,在《学界》上发表的3 篇论文中2 篇都是关于人口问题的。在《最近中国的人口变化》(Recent Population Changes in China)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具有相当难度。中国从汉朝开始就有人口统计,虽然很不完备,但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早的,而最近一次比较可靠的人口统计是1909—1911 年清政府为了预备立宪而进行的。进入论文正题后,他用一系列数据说明,1909 年之后中国人口的变化不大,从3.7亿增加至4.3亿(1935年)。现代学者对于人口压力的担心主要是基于马尔萨斯的理论,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焦虑。赵承信认为当下的关键问题是一方面控制出生率,另一方面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他在论文中重点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指出其理论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死亡率与生育率之相关性,只以死亡率来调适生育率。在《家族制度对中国人口的平衡作用》(Familism as a Factor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Balance)一文中,赵承信继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尔萨斯等纯粹生物学和技术论的人口研究路径,强调应该将人口问题纳入社区之中进行探讨,分析人口与土地、社区文化等的互动关系。文中他通过分析家族制度在中国人口平衡上的重要作用有力地说明了生育既是生物过程,又是文化活动。关于人口问题赵承信还发表了多篇书评,不仅涉及中国,还广泛地讨论了日本、欧洲、苏联的人口问题。他反复强调,研究人口现象不仅要从数量、组成及分布等角度切入,还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影响,旧的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尚未形成,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总之,他以动态相关性的观点来分析人口现象,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
李安宅是《学界》第一任主编,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第1 卷第1 期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必要性》一文具有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是依靠文献资料,是书斋里的学问或“图书馆里的研究”(library research),新一代学者需要从这当中解放出来。田野调查对于社会科学就像实验室对于自然科学一样重要。李安宅接着详细分析了田野调查的两个积极作用:(1)田野工作中的发现将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奠定基础,使研究者们获得一种崭新的视野,同时在教学中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材料,而不再需要仰仗外国的教科书;(2)将给予中国学者关于社会文化事实的真切体验,有利于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建设未来,而不必照搬别国的经验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李安宅反复强调,社会科学家不能只在书斋里做学问,必须面对中国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他在文章最后指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中国是一大块处女地,提供了广大的学术空间,同时考虑到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学科、不同国籍的学者可以合作,这样既能够扩大学术范围,又可以使自己的学科做得深入。李安宅在这里指出了近代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走出书斋和图书馆,走向田野,走向民间。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田野调查,本人也身体力行,20 世纪30 年代他前往甘肃藏区调研,后来又深入西藏,其名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就是这一工作的结晶。
林耀华早年求学于燕大,后于194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和李安宅一样在藏学方面成就卓著,他发表于《学界》第4 卷第2 期的《嘉戎的家族》(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Giarung)完全基于田野调查。嘉戎是藏族的一支,其社会既非父系,也非母系,每个家庭没有姓氏,仅有根据其房屋而起的名号。这个名号含义广泛,代表了家屋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包括住屋财产、屋外田地、粮税差役,以及族内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等。一般来说,这种名号得自于房屋创建之初,此后的继承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女儿或女婿,且每代只传一人,不能兄弟或姊妹并传。因此嘉戎社会没有形成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父系或母系世系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林耀华的初步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嘉戎位于贫瘠的川康边界山区,经济和人口增长均很缓慢,是物质环境和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这篇文章的缘起,林耀华后来回忆说:“1945年暑期,我又和我在成都燕大的研究生兼助教陈永龄一起去当时位于西康和四川交界处的嘉戎地区考察。这次考察的经费是由美国罗氏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沿途经过了汶川、理县、茂县、马尔康和理县羌族、藏族地区,重点考察限于理县北部的四土和五屯的嘉戎地区。嘉戎在今天已被识别为藏族的一个支系。但在当时,我们对于嘉戎的族属尚无定论。”18林耀华:《在大学与田野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97 页。[ LIN Yaohua, Zai daxue yu tianye jian(Between University and Fiel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97.]林耀华的这篇英文文章是国内外最早考察嘉戎家族制度的专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次考察大有收获,但也并非没有遗憾:“由于当时抗战胜利,燕大成都分校忙于返京复校。我的时间仓促,没有能够深入揭示嘉戎的这种世系制度究竟是怎样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和社会环境。……我当时实际上已接触到了今天人们热衷于讨论的‘实践’(practice)与‘制度’(system)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结构—功能学派理论的束缚,我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是一个仅仅由规范和制度组成的世界,没有能够看到规范和制度仅仅是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的框架,实具有主观意志的活动空间。能够权衡利弊的人们的实践固然受这种框架支配,但远非完全由其决定。”19同上,第99页。[ Ibid., 99.]
另外一篇基于社会调查的佳作是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和四川的私塾研究》(Rural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Old-fashioned Chinese Schools(szu shu) in Shangtung and Szechuan),发表于《学界》第4 卷第2 期。1905 年科举废除以后,新式学堂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并逐渐推进到乡村。新式学堂基本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但它们的大量出现并没有能够取代旧式教育。廖文选取山东汶上县和四川成都县的私塾作为研究对象,用大量数据和事实说明,在与新式学堂的竞争中,私塾由于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生命力依然顽强。据廖泰初归纳,私塾大致分为四种:(1)塾师设馆招生的私塾;(2)专收贫寒子弟的义塾;(3)设立在义庄或宗祠内的书塾;(4)一家或几家开设的家馆。如果按照教学层次,私塾又可分为蒙学、普通私塾、爨局、私塾大学。这些私塾基本可以满足乡村不同家庭背景儿童的需要,所以虽然政府力推新式学堂,甚至采取打压和取缔私塾的政策,但效果却适得其反。该文深刻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显示了“教育救国”过程中的重重困境。
四、英文学刊的价值
进入20世纪,随着学术的国际化,中外学人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增多。《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辅仁英文学志》《燕京社会学界》三份英文刊物的创办和发展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的世界意义和北京作为中国学术中心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文献。
这些刊物的作者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外国学者,其中不少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文章构成了海外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方法、视角以及结论对中国学界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1930 年代在北京访学的哈佛燕京学人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1906-2001)发表了《同文馆考》(The Tong Wen Guan,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8卷),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晚清机构开创性的重要论文。
另外一类,也是人数更多的一类是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此前国内外已经出版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他们英文著作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他们的中文著作固然重要,但英文文章更能直接体现他们在近代知识迁移和本土转型方面的关键性贡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20梁启超:《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206 页。[ LIANG Qichao,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Liang Qichao juan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lassics, Volume of Liang Qichao),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206.]民国以后,这一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随着以清华留美生为代表的近代留学生回国,西学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看这三份刊物就不难发现,当时的留学生在思想学术上是多么活跃。
近代北京的英文学刊见证了中国传统学术,如文学、历史、哲学的国际化,也见证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些刊物曾拥有一批学术精良、英语熟练的优秀作者,但很多长期被学界淡忘,如刁敏谦、英千里、赵承信等。进入21 世纪,不少学科回顾自身的百年历史,一些人物开始浮出历史地表,但范围多局限于他们的中文著作以及译作,对于他们英文著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有的完全不著录,有的著录有误。比如赵承信,还基本无人问津。即使是关注多一些的,如李安宅,问题也不少。近年出版的王川著《〈李安宅自传〉的整理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版)附录三《李安宅论著目录》就漏掉了他在《燕京社会学界》中的三篇英文文章。稍早一些,赵定东编著的《民国时期部分社会学家记事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中的李安宅部分倒是注意到了他在《燕京社会学界》上的文章,但只叙录了后两篇,遗漏第一篇,而且编者把刊物名称写成“《燕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也是不对的。21赵定东:《民国时期部分社会学家记事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326 页。[ ZHAO Dingdong,Minguo shiqi bufen shehui xuejia jishi ji (Chronicles of Some Sociologists of Republican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326.]再如杨俊光著《齐思和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附录一《齐思和学术年表》对于齐在《燕京社会学界》上的英文文章语焉不详。实际上,齐思和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和两篇书评,是他一生中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
这些英文学刊所包含的大量资料是一个宝藏,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即使是已经被学界研究得比较充分的人物,如蔡元培、严复、梁启超,他们在这些学刊上的英文文章也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就是他们的《全集》中均未收入这些文章。至于其他名气小一点的人物,受到的关注就更有限了。
以胡适为例。1919 年初,胡适在《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增刊《1918 年的中国》(China in 1918)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一场文学革命》(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的文章,这是最早介绍“文学革命”的英语文献。1922 年初,在白话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胡适再次用英文撰写了题为《中国的文学革命》(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6卷第2期上,又一次向英语读者介绍白话文运动。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先简要回顾了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近代欧洲语言兴起并取代拉丁语的历史,说明文言文和拉丁语一样,是一种脱离口语的死语言,应该被取代。接着他从中国自汉唐直到近代的历史中举了若干例子,说明白话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语言,是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结合中外的历史,胡适令人信服地指出,白话取代文言是大势所趋,文学革命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至于他个人的作用,则在于明确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率先喊出了革命的口号。和第一篇相比,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更多地谈到了近代欧洲语言的演变情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大利语、法语等现代西方语言的发展史是胡适思考中国语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考,他在文中写道:“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来摧毁文言的地位,这就是用一种自觉和坦率的态度来承认文言是一种死语言,因此不适合再作为现代中国的国语。但丁不仅用意大利语进行创作,还写了《论俗语》来为之辩护。薄伽丘也是一样。在法国,七星诗社大力宣扬法语作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杜贝莱专门写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的宣言书。白话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有意识的提倡。”22HU Shih,“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 no.2 (1922): 97.可以说,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绝不只是体现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 年1月《新青年》)等中文论著中,他的英文文章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全面关注各类文献才能真正把握胡适思想的全貌。此外,胡适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4卷第4期(1919年12月)发表的《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一文同样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些中国学人虽然不擅长英文,但他们的作品经由翻译出现在这些刊物上,如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绝对不能忽略的大事。另外如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对法国汉学家葛兰言《中国文明》一书的犀利批评(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5 卷)也提示我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至于人文社科之间的互通就更为常见。近代中国涌现了一批学贯东西的优秀学人,他们的成就需要全面检讨和评价。
食洋不化,不能洋为中用,是留学生容易犯的毛病。陈之迈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政治学者之一,并实现了良好的转型。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搜集和阅读各种中文文献,从法令、规章、文书档案到各种政府机关的报告,以期全面了解中国政府的运作情况。这也能从他的一篇书评中看出。193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英文著作,陈之迈很快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发表书评,指出该书最大的问题在于中文文献运用太少,作者只依赖有限的英文文献,而不愿意去查找和使用大量存在的中文资料,如《国民党指导下政治成绩统计》《立法院公报》《军政月刊》等。另外作者只注意到已经公布和正在实施的规章制度,却没有注意到那些没有公布或者虽然公布但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的法律文件,如《法院编制法》《预算法》《公务员任用法》等等,仅凭法律条文来研究政治现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注意法律实际执行情况“只会用美妙的字面迷惑读者,甚至造成错误的印象”。23C.M.Che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by Chih-Fang Wu”,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 no.2 (1935): 289.同样,对于各种数字不能只看字面,也要按诸实际。为此陈之迈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关于政府组织的法律告诉我们,国民政府委员为24—36人,立法委员为49—99人,监察委员为29—49人,……他们到底是多少人?对于像立法院这样的机构来说,人数的多少将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最少人数和最多人数之间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下面公布我所了解的数字,对于读者应该有所助益:立法院第一次会议是49 人,第二次63 人,第三次90 人,第四次86 人;监察院成立时是21 人,后来增加至42人。”24Ibid., 291.虽然《中国政府与政治》洋洋洒洒四百多页,前面还有孙科的序言,但资料贫乏,所以在陈之迈看来,“该书没有增加我们对于中国政府的认识,它只是把中国立法者期望的中国政治做了一个概括,而没有告诉我们实际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25Ibid., 292.
在近代中国政治学人中,转型最成功的非萧公权莫属。他1926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是对西方最新政治学说的探讨,回国后他开始全力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很快成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萧公权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发表了五篇书评,均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相关,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这一领域的见解和思考。在经济学人中,方显廷是最好的代表。他1928年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全面考察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以及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过程,该文在西方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回国后方显廷主动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近代工业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棉纺工业和贸易》(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in China)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典范之作。棉纺业是中国最主要的传统手工业,也是中国现代产业中最重要的工厂工业。方显廷在文中首先指出,1890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机器织布局是中国棉纺业的开端,从那时起这一产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890—1904、1905—1913、1914—1925、1925 之后。在第一期中国自设机器纺织厂开始出现,并发展至17家。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亚的经济形势有了起色,中国也从义和团运动的乱局中得到恢复,第二期内增加棉纺厂13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棉纺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因为这时外货来源断绝,本国企业获得兴隆获利的机会,这一时期全国纱厂增加到87 家。1925 年以后中国棉纺业进入衰退时期,因为“五卅”事件的发生引起上海等地纱厂罢工风潮(1924 年只发生2 次,1925年达38 次,1926 年高达78 次),所以新厂创设为数甚少。在对历史做了清晰的勾勒之后,方显廷从棉花的生产与贸易、棉纺织品的制造与销售、中国纺织业之劳工、中国纺织业之组织、中国手工棉织业、中国棉纺品之进出口贸易等六个方面对这一产业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论文不仅资料翔实、分析透彻,更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文中大大小小数十个表格构成了近代中国棉纺业最完整的调查报告,用方显廷自己的话来说,“通过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26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79 页。[ FANG Xianting, Fang Xianting huiyilu (Memoirs of Fang Xiant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79.]
从出版史,特别是北京出版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英文刊物的价值同样不容低估。中国近代最早的英文学刊是《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由首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于1832 年5 月在广州创办,停办于1851 年12 月。此后随着五口通商和国门不断被打开,在华出版的英文社科刊物日渐增多,主要有《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新中国评论》(NewChinaReview)、《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ofScienceandArts)等。但以上刊物均在上海、香港等沿海口岸创办,北京虽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中心,却一直没有一份高水平的英文社科刊物,直到《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状况。
这些英文刊物虽然在北京出版,但具有世界影响,考虑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做到这一点就更显得可贵。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飞速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已远非百年前所可比拟,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和硬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相对滞后。学术是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如何使中国学术尽快走向世界是当今中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些近代英文学刊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1)如何直接用英文的学术话语来表述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2)如何将优秀的中文学术成果翻译成英文,扩大其学术影响力;(3)如何创办中国特色的英文刊物,使之真正具有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