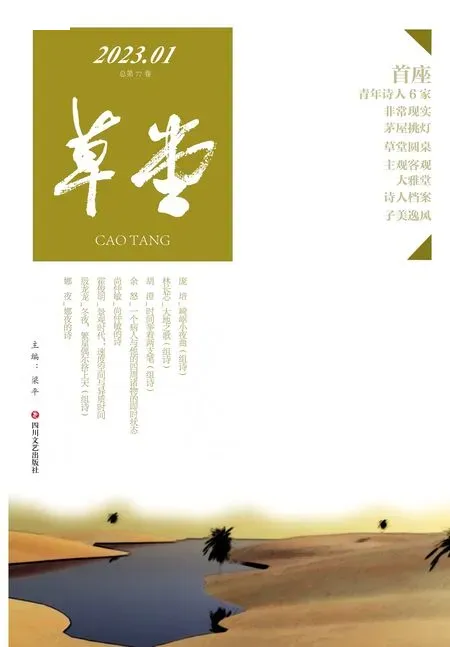南疆辞(组诗)
2023-09-25◎南子
◎南 子
[秋风辞]
诗人,请把诗篇从草原中取回来
山中的云朵是它的肺腑
把我的年华全带走!
诗人,请把诗篇从烈酒中取回来
丰收的粮仓是大地的金殿
三万亩汉代的麦田滚下了秋风
诗人,请把诗篇从八月里取回来
在江布拉克以西一只鹰跌落翅膀
它的血溅落在深夜的粮仓
诗人,请把诗篇从星空里取回来
麦垛在汹涌的风中翻身
半块破损的墙砖上字迹全无
诗人,请把诗篇从天山上取回来
一些露珠被去年的雪水养育
含着黄金正辗转于途
诗人,请把诗篇从史书中取回来
一声马嘶被大风拨亮
在苍凉的古歌中彻夜诵读
诗人,请把诗篇从树下的坟茔里取回来
我跑过一生的路最终在这里获得安宁
更远处,是青色的群山麦苗茁壮
[新的一天]
我常常错把一天当作一年——
当这一天在锋利的落日下止息
没有一丝阴影
我看不清
这一天背后的种种可能
譬如——人性的踌躇
和日复一日古老的凶险
我甚至看不清
天地间悠远的古意中
一粒金色的沙
但是新的一天也是万物的黎明
露水,草霜,山谷的皱褶
偶尔也会泄露马腹中的一声惊雷
新的一天
我在时间的密纹里悄悄哈气
感知着肉体的谦恭、活的气息
以及万物移动的温暖
[大自然的催眠术]
大自然的美
真的是一场伟大的催眠术吗?
无边的麦田
一直在这里,或者从来不在
天空清澈得像刚哭过
草垛,车辙,动物的蹄迹
在生命的次第相续中
获得了黎明的启示和力量
有时我也发出疑惑——
天呐!一道彩虹怎能让人陷入辽阔的昏迷?
风静下来的时候
我在想,草尖上的云有没有衣裳?
蚂蚁背上的土重吗?
麦仁成熟时的甜腥气息
是否让一条道路突然有了斜坡?
我甚至怀疑,此刻露珠一样短促的自己
身体中的毒素总是大于水分
每一个新的词语和形容
都是一次睡眠和停顿
在江布拉克
如此简单的真理
我却反复想了很多次
[山中一日]
我知道果实来自大地之血的灌溉
风来自山峦
麦苗出自《诗经》
我知道一棵不靠光源就留下影子的大树
体内必有一种刻骨的爱恨情仇
我知道金黄的草垛
有着马背波动的弧线
就像突然奔跑起来的山峦
微风使它猛烈地晃动
我知道一个人
消受不了那么多的虫鸣
这些无名的昆虫
叫得多么卖命
像是要唤回越来越少的农人
和越来越少的物种
我知道大自然的神性
它不可以独自聆听
不可以静止
甚至不可以独自沉默
独自隐喻时间,披上时空的风霜
——我知道,面对美
我应该更冷,更静,更缺席
[岩石有自己的悲伤]
此刻,秋天的自画像
是由草堆、车辙的色彩和线条构成
曾经消失了的农人镶嵌着风景
连老槐树也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再添上两三笔,麦田就成了
在左,在右,在绿之洲
可是,这孤独的美仍然缺少称颂——
就像星宿有它的缄默
岩石有自己的悲伤
流水的腰无力对抗庸常的法则
这些我都知道——
然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看不到
风拖长了影子在田间滑过
沉甸甸的麦穗正弯下头
种子引爆果实
就像爱在向爱本身致意
——其实它才是这座村庄丰富的人性
[南疆辞]
冬天的白杨树以悲剧的姿势
引领我走向你
离开多年
只有一个晚上,我梦到了你
——以移动的脊背
以爱欲,以围困的时间
以胸中挤压出的苦痛
梦见我中的你——
我爱过又恨过的出生地啊
尚需三年,我才能用出生
衔接你的死
我离你更近了,如同
更低了
[山水教育]
我写与古人相仿的诗句
去治愈客厅的白墙上贫瘠的山水
我养大杏树、李树和桃树
一张绿色的脸,却有着枯黄的灵魂
我迷恋杂草、乱云
常常遁迹于牧人的梦境和乡愁
我梦见群山被大雪冻结
它来自鹰飞翔时抖落的一阵灰
——此时,冬天的禁忌已接近尾声
铁丝网拉直了牧场的边框
草海的堤岸比发丝细
羊只隐忍着愤怒,被黑夜草率遮盖
一个永恒的疑问,有如车辙
完成了最清晰的穿越——
还要多少个寒暑,雪崩
还有马背上的历险
才能将一座草原送抵生的反面
并在人世的喧嚣处
发掘出大自然隐约的敌意
以及全部的,不安的美?
·创作谈·
救赎的栏杆
诗歌像是与生俱来地隐藏在人类的基因中,当然也隐藏在我的身体中,如同生活的秘密和救赎的栏杆,让我不动声色地打量这个世界、这颗心。这种对修辞的热爱与练习一旦开始,便意味着不停止,意味着一种隐喻般的习俗,一次永远循环着的成人礼。
当下可能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但我像其他诗人一样,依旧读诗写诗,我认为,诗歌虽是“无用”的技艺,但一个人若缺少了诗歌审美,那几乎不像是完美的人生。因为,诗歌对我们灵魂的滋养作用是难以言表的,那种穿透人生的力量,与人的直觉、经验、洞察以及激情,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所以,诗歌对我而言,依旧是“摇晃的世界”中所抽出的“新生的手臂”。它让我相信,自省的内心对于诗歌而言尤其重要。要知道,对自己的灵魂问长道短,不是为了回答风格和技巧的问题,而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的内心是在跟什么交锋——尽管它也矛盾重重。
它让我想起基尔凯戈尔曾经问过的:“做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个人生活,他的诗歌只是关于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从而使他的个人存在多少是诗歌和他个人的一种讽刺——生活所示,大抵如此。”
可是,当诗歌在我的内心世界扩展的时候,我依然没能说出词与物、纸与笔之间的有限和无限;没能说出与边疆异域生活与之相对应的开阔和丰富,比如充满隐喻色彩的玫瑰、正午、鸟、睡眠,还有沙漠深处的人群——那企图抓住永恒的徒然之举的噫叹,让我和你、物与事,在诗意的沉默之处,在颓丧生活的外衣里,构筑出人世的荒谬与欢笑的种种可能,即便是姿态,也会有足够的力量。
面对自己,我一直在问。
我喜欢带有个人经验的诗歌。因为它透露出个人生活的奥秘,有着被诗歌洗涤过的纹理。这种“个人经验”是诗歌中最隐秘的,也是最可靠的部分,它指涉记忆、情感,以及人身上所具有的复杂的人性,并赋予它真正的秘密,表达出对卑微者的赞美与悲悯,对人性的怀疑与反讽,以及对这个时代暗疾的诘问与猜测、宽容与体谅。
只是,在当下才气、趣味泛滥的诗歌写作风气中,如何让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有“根性”,而不流于意义上和技术上的高蹈?
我希望自己一直藏匿于生活深处,就像“潜水艇”,它是个体的、内向的、沉潜的、幽闭的,同时,我期待它也是机敏的、精确的、迅猛的和硬实的。我更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击破生活的表层,找到一块块长满棱角的石头,一个接一个地为它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