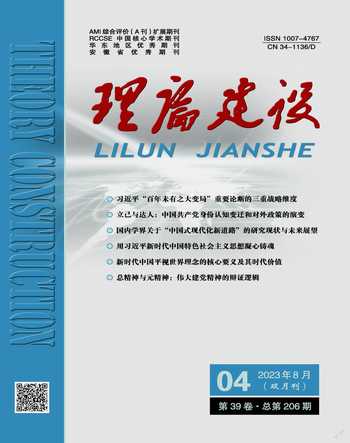习近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断的三重战略维度
2023-09-24牛一凡吴家丞
牛一凡 吴家丞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纪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非凡勇气准确识变,原创性提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战略论断。立足时代之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科学应变,敏锐把握战略机遇;以高超的斗争本领应对风险挑战,领导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确保党在大变局中永葆政治底色。面对全球发展难题与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强烈使命担当主动求变,用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弥合全球治理鸿沟,用中国式现代化形塑“东升西降”的国际战略新格局,展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感召力,为引领世界性大变局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23)04-0001-12
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影响了国际格局与发展态势。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科学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娴熟化解国内外重大风险,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应对变局的重大理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扭转变局的根本道路,牢牢掌握住中华民族发展的主动权,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所独具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与强烈使命担当。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识变”“应变”“求变”中彰显的战略家品格及历史主动精神,对于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领会新时代伟大变革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从而在党的二十大开辟的新征程上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战略自信、增强战略主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识变:把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缘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能变之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世界性战争和战后两强争霸带来的世界变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眼光精准把握变局态势,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功实现了战略突破,雄辩地证明了变局之能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战略定力充分把握内外发展机遇,稳中求进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以和平发展加快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世界大势悄然改变,形成“渐变之局”。进入新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终成“突变之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历史耐心和高超的战略智慧准确识变,加快布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手棋,牢牢掌握应变、求变的战略主动,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大胜利。
(一)能变之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1]392“能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属性,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成功的历史条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李鸿章等人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晚清变局,各种进步政治力量也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积极探索,先是引进西方先进器物,再是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如青年毛泽东就观察到“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2]。但这种转变只是中国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后产生的浮躁盲动、应急的变化,并未彻底扭转变局。这些探索缺乏对变局由何而来、由谁主导、往何处去的体认。
资本主义是造成近代世界性大危机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主义天然地向外寻求扩张,靠战争起家,以掠夺致富,使大多数国家成为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纪,“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4]288,最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阶级矛盾激化。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世界形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华民族“求变”的历程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恰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5]。
面对世界变局,毛泽东同志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深邃洞见,他于1935年11月刚抵达延安时就对世界时局作出了“突变性”与“急转性”的战略分析[6],提出了“持久戰”与“游击战争”的战略构想。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清醒地预见到,“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7]411,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敏锐的战略预判。至于变局向何处去,194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讲话中明确给出了答案:“我们的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三次,现在要改变第四次。”[4]56所谓“第四次”,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换两回朝”,先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冷战阴影下的两极格局,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了外交新局面,实现了战略新突破[8]。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世纪。面对全球竞争的新态势,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研判国际局势,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战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变局关头积累了丰富应变经验,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变局可变、变局能变,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解变局、开新局,只有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突变之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逻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把握好战略节奏,既要有条不紊、渐进发展,又要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完成跃迁式突变。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渐变之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战略定力,充分把握内外机遇,稳中求进,锐意进取,赢得了历史性战略主动。恰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1]108。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质变的飞跃,要通过量变来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一下子、兩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9]115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以坚定的战略决心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热情洋溢地展望道:“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10]156所谓“大变”,就是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1964年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战略目标及“两步走”战略规划,基本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底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具体来说,是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之家”[11],提出“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战略,强调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12]402。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是我们党在变局时刻扭转战略态势、取得战略突破的宝贵经验。所谓变局,意味着内部要素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矛盾冲突进而分化重组。1990年前后,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邓小平同志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判断可供我们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机遇[13]354。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告诫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13]383,进一步解放思想,释放市场活力,为扩大改革开放创造有利条件。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格局,同时也意味着直面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要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对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14]413,力争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
进入新时代,在瞬息万变的世情、国情下渐变之局已成突变之局,原先的顺势而上变成了“顶风”而上。中国能有多久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15]。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16]29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风险挑战加剧,地区冲突不断,“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12]60。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由外生性机遇为主逐步转向内生性机遇为主,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逐渐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17]12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保持强大战略定力,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作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的战略论断[18]821,尤其强调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战略眼光抓住机遇、利用机遇、扩大机遇、转化机遇,化被动为主动,稳稳地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时”与“势”,牢牢地守住应对变局的战略基点,掌握了突破变局的战略主动。
二、应变:明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准备
变与应变,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出现“自西向东”的位移,世界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带来大挑战的同时,也蕴藏大机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科学应变,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恢宏命题,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捕捉世界变局中的发展机遇,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应对国际乱局中的风险挑战,以伟大的自我革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充足的战略准备。
(一)以非凡的战略眼光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命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反映了世界力量分合的变化[19]165。新世纪初,江泽民同志判断“世界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国际局势总体趋于和平、缓和与稳定,局部仍伴随战乱、紧张与动荡[14]520。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急剧动荡,某些西方国家妄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2月所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五年来,对世界经济以及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大变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9]165-166。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背后,是国力之争、制度之争与理念之争。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从近代数百年世界大历史视野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20]241,“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大变局”[21]。大变局中,既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衰落,也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国家的整体性崛起;既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等逆向变量,也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正向变量;既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削弱,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中坦言:“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2]537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3]。这场变局实质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洞察大势和历史规律基础上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论断,迅速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接受与认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更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17]164。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4]397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下国际态势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战略预判,使我们充分把握了世界格局发展的“时”与“势”,我们才有定力、底气与决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牢掌握中华民族发展的主动权。
(二)以清醒的战略思维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机转化
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镇定自若,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越战越勇,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应有的战略品格。“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17]30,“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24]143,因此,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伟大气魄,清醒地作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25]42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26]60。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富有战略前瞻性和强大号召力的科学论断,势必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巍巍灯塔。
是否善于把握“危机”辩证关系,做到临危不乱、危中寻机、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政治素养与战略定力。危险与机遇往往相互转化,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能转化为和平,和平也能转化成战争[10]374。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12]419。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战略机遇期易失难得,抓住机遇就能赢得战略主动,反之将会陷入战略被动。早在200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就极具先见之明地指出,“能否把战略机遇期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宏观的战略决策”,强调“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用得好,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27]。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战略紧迫感与高度责任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时代之变,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判断当下“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17]122。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5]219-220习近平总书记总是谆谆告诫要“舍得花钱,舍得下功夫,宁肯十防九空,有些领域要做好应对百年一遇灾害的准备”[18]497,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2]423。习近平总书记这种对潜在风险作出科学预判的危机意识与战略思维,为我们打赢抗击疫情人民战争的总体战、阻击战赢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使我国成为全球抗疫成功的典范,成为化危为机的绝佳案例。
(三)以超前的战略自觉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是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与斗争历练的战略家,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品格是积淀了生动斗争本领与卓越政治智慧的战略家品格。1916年,毛泽东同志在日记中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8]透过文字的背后,我们充分感受到一种战略家独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毛泽东同志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提出了诸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战略构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高度的战略清醒。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16]287。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17]83。新时代这十年,习近平总书记以顽强的斗争意志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胜“打虎”“拍蝇”“猎狐”的反腐败斗争持久战,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及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等一系列战役,“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決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25]7。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新的历史“赶考路”开始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两个务必”拓展成“三个务必”,尤其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凸显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高度的战略主动精神。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深刻反映了两代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彰显了党不断锤炼斗争本领以应对世界性大变局的战略自觉。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12]258,“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25]542。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20]118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尤其是颜色革命的危险,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24]141。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勇于亮剑,才能有生路出路,才能跃过层层关山,踏过重重叠嶂,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深刻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着力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十年磨一剑,新时代这十年,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找出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自我革命旨在提高党不断发现并及时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一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自我革命是主体在主动意义上和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扬弃[29],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立足党的二十大开辟的新征程,我们“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持之以恒地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意志,以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胆气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领导我们把握变局、应对变局、扭转变局。
三、求变:增强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主动
战略问题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使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两种全球格局中的最新“矢量”,突出投射在当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发展窘境与治理赤字上。如何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协调各国参与全球问题治理、取得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突破,极其考验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思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主动求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全球治理空间,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牢牢掌握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主动。
(一)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在百年变局当口,从战略上准确判断当前所处发展阶段,进而创新发展思路、赢得战略主动,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雄韬伟略的充分体现。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7]155,此后我国经济受外部危机冲击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对此,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前瞻性地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所谓新常态,“新”就新在经济发展从以往量的增长转向质的飞跃,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22]245-246,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发展大局从大时空角度对百年大变局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作出的超前战略谋划和定位。
越是壮阔的征程,越需要正确理念与政策来领航,从而下好先手棋,掌握“两个大局”的战略主动。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22]197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强调要以此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洞察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22]253。对此,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之力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了经济重大结构性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最主要的系统理论体系[17]170。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地提出了区别于西方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从而全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是适应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更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统筹“两个大局”、破解发展难题的理论自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后,面对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深度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所独具的“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的非凡能力。2020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期间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17]174,立刻根据环境之变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在世界大变局中占据主动地位,“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练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17]175。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國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17]156,是顺应国内发展态势、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举措,可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正是有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战略性思想的科学领航,我们才得以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维度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回答世界之问,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协和万邦的战略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壮大,“红旗漫卷西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如火如荼。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毛泽东同志精准把握时势,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科学研判国际局势,确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认识,推动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成为危机中的希望,却触动了西方某些国家敏感神经,拿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来说事,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30]264。对此,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庄严宣告:“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3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华盛顿演讲时所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32]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保持高度战略清醒、作出正确战略判断的必然体现。
推动世界和平稳定,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是大国担当的充分彰显,更是战略家天下情怀的自然流露。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创作《念奴娇·昆仑》,其中提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前所未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就强调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0]272。世界不是被海洋分割成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22]478。党的十八大以來,从构建睦邻友好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打造网络空间、卫生健康等命运共同体,到共同建设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全球视野,用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响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传承了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理念,超越了西方一国一域的狭隘国际关系桎梏,为人类审视自身命运与未来前途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自觉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责任,彰显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人类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时代觉悟。
摒弃意识形态纷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要之举,更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宽阔胸襟的体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各国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17]483-484面对世纪疫情,有人作出战略误判,幻想“躲进小楼成一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无奈地发问:“我们能够携手并肩对付一个共同且危险的敌人吗?还是我们任由恐惧、怀疑和非理性左右,四分五裂?”[3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给出了答案:“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17]417,只有“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18]712,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世界才能拨云见日,走出迷雾。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过度放大文明异质性,强调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将文明冲突视为世界对立与割裂的根源,并在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下认定历史将“终结”于西方发展模式中。某些西方国家更沉迷于推广其所谓“普世价值”,肆意激化族群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对于此种行径,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2]522,这与唯我独尊、强行摊派的“普世价值”有本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24]229,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5]441,既是对西方所谓“文明威胁论”最好回击,又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天下情怀的生动演绎。
(三)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摆脱“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冲破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牢笼”。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从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到二十世纪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世界先后经历大殖民时代、大解放时代、大变革时代,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一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毋宁说是一部广大亚非拉国家被侵略被奴役的血泪史,其血腥度与野蛮性令人发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破坏与征服的原罪之上,“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17]124。这种以资本无限无序扩张为驱动的现代化,先天地带有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9]117孕育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周期性的危机与动荡,势必会引发两极分化、社会对立和精神焦虑等治理危机。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更催化了政治极化、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问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严重弊端,人类社会亟待找到一条破解西方现代化问题症结的发展正道。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7]407,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但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34]。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要想实现发展目标,就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模式。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2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2]367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必须从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中发掘原生材料,提出本土问题,开辟中国道路。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6]2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超越了西方国家人为制造冲突以图浑水摸鱼的现代化歪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牢牢掌握中国发展命运主动权的应变之路,是我们党扎根中国大地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创新之路,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之路。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深刻把握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为人类文明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超越资本主义旧秩序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变局向纵深发展,国际上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对于一些国家而言,现代化是被迫西化的过程,似乎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然而,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化路径早已行不通,反而使一些国家陷入党争分歧与社会动荡中。西方一些国家更不失时机地兜售“华盛顿共识”,开出“新自由主义”药方,而恰恰是其鼓噪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使国际垄断资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收割全球众多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和动荡,缩短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放大了全球经济运行风险,酿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乃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22]477。与之相反,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采用西方主流理论倡导的“休克疗法”,更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底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更雄辩地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的蓬勃生机,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3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开创性地对现代化作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深刻重塑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开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境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强烈的使命担当。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3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24.
[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9.
[6]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6.
[7]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萧冬连.关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际环境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22(4):87.
[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909.
[1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
[19] 曲青山.从五个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0]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3] 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29(01).
[2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7]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6.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4.
[29] 曲青山.曲青山党史论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031.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7.
[3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89.
[33] 守护文明精神的特殊战斗[N].人民日报,2020-02-20(03).
[3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
[3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3-64.
The Tripl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Judgment of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NIU Yifana, WU Jiachengb
(a. School of History; b.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eeply grasped the new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andemic of the century. With the extraordinary courage of a Marxist strategist, he has accurately identified changes and creatively proposed strategic propositions such as "unprecedented changes" and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the remarkable political wisdom of a Marxist strategist, has scientifically responded to the changes, keenly grasp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responded to risks and challenges with his superior struggle skills, and ensured that the Party would always maintain her vibrant strategic undertones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 changes with the spirit of self-revolut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deficit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his strong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a Marxist strategist,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ek change, promo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bridged the gap in global governance with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osture of "rising east and falling west"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demonstrates the powerful appeal of Marxism,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Chinese solutions, and Chinese strength to lead global changes.
Key words: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Marxist strategis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責任编辑:王 磊,孔令仙]
收稿日期:2023-03-01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创新项目:“中共革命中‘反动派概念的生成与流布研究”(KYCX2200_57)
作者简介:牛一凡(1997—),男,安徽阜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吴家丞(1996—),男,江苏常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