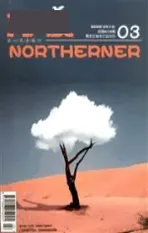生命是独立的美丽
2023-09-22毕啸南
毕啸南
人生经验浅薄。
以往,我总以为天下父母大都是一个样子,舐犊情深,人之常情。年岁渐长,才知不过是我幸运,这世间父母愁,儿女怨,数不胜数。
朋友秋说:“我应算是这其中的大不幸。”
秋生得漂亮,像她的家乡,山绕着水,水绕着山,袅袅婀娜。
“我十六岁离开我们村子,妈送我到村头,我爸连来都没来。我坐着村里一位乡亲的拖拉机到了县里,又从县里坐大巴到了市里,在一家餐馆找了份洗碗的工作,从此离家,一别就是六年。”秋穿着一身利落的时尚工装,靠在软白的皮质沙发里,言语脆硬,感受不到任何情绪。
我却听得有些讶异:“一别六年?什么意思,六年没回家吗?”
“没有。每个月都会往家寄钱,偶尔也会打个电话,但没回去过。后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跟着他去了北京,就更不方便回了。”秋摆弄着自己的手指,抬眼望了望我,带着些许自嘲的笑意,“当然,这也都是借口。我不回去,他们也不想我。寄钱就行。”
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起这位女企业家。
我们相识数年,她比我年长近一轮,既有女性企业家的果敢和霸气,也常有感性文艺的一面,算是很聊得来的朋友。但父母,却是第一次听她提起。
短短几句话,两次提到了钱。我意识到,秋看似淡然自若的状态下,藏匿着一个复杂而刺痛的故事。
“所以你认为,你爸妈只是爱你的钱,不爱你,是吗?”和秋,我想不必弯弯绕绕,便直接问。
她身子侧对着我,在摆弄她桌上的绿植。我见她怔住了,半晌不动。“也许吧。”她许久才诺诺地应了一句,不知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她自己说。
秋,家中排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
父亲重男轻女,一直想要个儿子,但母亲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母亲问起个什么名字好,父亲闷着头蹲在院子里说,随便吧。
母亲没念过书,想是秋天生的,就叫秋吧。
秋说,与大姐不同,她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大姐是头胎,父母觉得还有盼头。怀秋的时候,母亲特爱吃酸,农村人讲酸儿辣女,父亲听得高兴,天天换着法儿地给母亲弄酸的东西吃,结果一生下来还是个丫头。
秋的记忆里,父亲从没有抱过她,连好脸色都很少。直到弟弟出生,她才知道原来父亲也是会疼人、会讲故事,甚至是会哼歌的。
“你知道冰冷可以有多冷吗?”秋问我,还没等我回答,她径自地说,“小时候,弟弟犯了错也会被哄着,大姐犯了错会被父亲打骂。我经常故意犯错,他却从不理会我,像没看见一样。我宁肯他们打我骂我,那样至少活得还有些人气。但连这些都没有。我在这个家中就像不存在一样。那种冰冷,是窒息的。”
秋学习成绩不錯,但到了弟弟上学的年纪,家里供不起,秋不得不辍学。大姐在家帮忙种地,秋不想继续待在这个对她冰冷的家里,她跟母亲说,要去城里打工赚钱。
从成都到北京,这个四川姑娘,咬着牙熬过了生活给她的所有黑暗与挑战。她靠无尽的努力和坚忍扭转了命运,如今已成为一名成功的女企业家。秋说,她赚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爸妈买了新房子,给他们买衣服,出钱给他们报旅行团。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当年他们最轻视的那个孩子,如今反而是最孝顺的。”秋低着头,声音却清亮,“我就是想证明,他们错了,全都错了。”
但生活从来没有剧本。
比来不及表达的爱更痛苦的是,你根本没有机会理清一切。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秋的父亲母亲在这场灾难中双双离世。
如鲠在喉,如刺在心。
秋已经记不清,十几年前的那天,她接到大姐的电话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悲痛吗?崩溃吗?恨吗?委屈吗?不甘吗?
那年盛夏,秋终于回家了。
那个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
大姐远嫁,弟弟在外打工,都躲过了一劫。三兄妹忙完父母的后事,坐在村头的山包上。那儿是他们儿时的游乐场,捉迷藏、丢手绢、荡秋千……
曾经的快乐,已支离破碎。
三人望着远方,弟弟说:“二姐,家里对不起你。”
秋的眼泪像瀑布,顺着山包滚下去,冲刷着这破败的村庄。
秋去大姐家住了几天。晚上,俩人像小时候一样窝在一床被子里,并排躺着,四只眼睛瞪着窗外皎洁的月亮。
大姐一晚晚地跟秋讲父母的故事。“妈是爱你的。”大姐说。
“可是她更爱弟弟。”秋回。
“那她也是爱你的,你得理解她。我们都一样。”大姐语气沉缓。
“那爸呢?”秋问。
大姐迟迟没有回答。
沉默像这个夜一样,深得看不到远方。
在后来绵长而煎熬的日子里,秋时常回想,母亲也许是真爱她的,她的棉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虽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要尽着弟弟,但每次母亲还是能像变魔术一样,不知在哪儿藏了一小碗偷偷拿给秋;秋坐在拖拉机上离开村子的那天,她似乎听到母亲跟她说过“当妈的对不起你”。
只是记忆太遥远了,也太恍惚。秋只模糊地记得那个身影,那个矮矮的、小小的、木讷的、懦弱的、沉默的女人。
而关于父亲,这个男人,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她到底还是一无所知。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去问一问,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一丁点儿都不爱她这个可怜的二女儿。
秋说,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自己和父母就如同沙漠中的仙人掌,截了一段下来,各自生长,彼此便毫无关联。
直到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前夫跟秋说:“你以前总抱怨你爸妈这样那样的不是,但你在感情中却总是在重复他们的错误。慢慢学会和他们的错说再见吧,你得允许自己过得更好。”
秋愣住了,一个人坐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呆怔了许久。
她突然想起前夫以前反复抱怨的那些事。过往,只要两个人一有矛盾,秋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既不吵架,也不沟通,冰冷着脸,能持续大半个月,直到前夫反复认错求饶。这不正是她童年所遭受的冷暴力吗?不正是父亲对待她的方式吗?
意识的阀门一旦被打开,迷局瞬间变得清晰。
秋发现自己在情感中的很多自我甚至自私都藏着父亲的影子,在感情中遭受痛苦时的躲避和懦弱与母亲如出一辙。
她竟然在无意识而又深刻地重复着父母的错,那些原生家庭的模式、曾经伤害过自己的言行,都在她身上自然又意外地流淌成河。
“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看心理医生,”秋看着我,“你是做人物访谈的,你猜我那时候在想什么?”
“你在痛苦,从头至尾,你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不幸?”我也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回答。
一颗流星从她眼中滑过,她低下头。
也许,所有子女都犯了一个错误——父母被我们神化了。
儿时,他们是我们心中的天,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就是一切。等我们长大了,才渐渐明白,他们也是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
又过了许多日子,我们也要开始学习为人父母,又发现,真的就像是小时候上学那样,有人考出了好成绩,有人确实会不及格。
有的父母,他们缺乏知识,不懂方法,做得很糟糕,但只要爱是真实的,时间总会让你感受、理解和体谅。
有的父母,他们面对不同的子女,即便都深爱,但人性使然,总会让他们潜意识里更偏向一个,而“冷落”了另一个,就像父母两个人在我们心中也会有些微妙的差别一样。
有的父母,他们真的就是不及格,甚至连分内的爱都没有,那就勇敢地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但不要因他们的错而绑架自己,也要学会与他们的错慢慢分离。
生命不是谁的延续,它就是独立的美丽。
秋说,她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要用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即便这个“他人”,是父母。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你们离开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