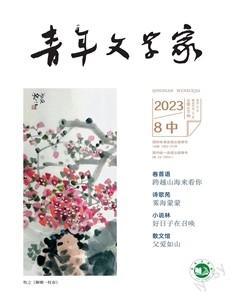陶渊明诗歌批评浅析
2023-09-21陈玉娟
陈玉娟
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潜列入了中品诗人的行列,并对陶潜作出了评价:“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首先,钟嵘提出陶潜诗的体貌风格出于应璩,又协有左思风力。《诗品》中,钟嵘将应璩列入中品诗人的行列,认为其诗风古朴,祖袭魏文,陈述事理委曲尽意,这与陶潜诗“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风格特质暗合。应璩曾为了规劝擅权违法的大将军曹爽,专门写《百一诗》讽谏,言辞恳切,“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着(著),易用受侵诬”,以表其规劝之心、渴望政治顺达的情怀,堪称经典之作。而陶潜也在诗文中表达过类似的劝讽,如在《闲情赋》序中提到“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可以见得陶、应二人诗作的一脉相承之处。此外,陶诗还善于化用古代典籍之语入诗,例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化用《论语·卫灵公》中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二)化用《论语·里仁》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等。沈德潜《古诗源》评陶诗:“先生(陶公)专用《论语》。”刘熙载《艺概》也示认同:“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而“善为古语”的应璩也常以典故嵌于诗中,质切古朴,如《百一诗》中的“三入承明庐”指应氏三次为官,借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中的“谒帝承明庐”;“是谓仁智居”则是化用《论语·雍也》中的“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指应璩堕官后避居于偏远的水乡间。应、陶皆善于用典,故“其源出于应璩”言之有理。其次,“又协左思风力”定位陶潜的诗歌与左思相类。《诗品》中对左思的诗作评价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即谓左思的诗多借史实典事抒发胸臆,表达怨情,颇得《诗经》讽喻之旨。左思的“怨”多来自内心渴望建功立业却始终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抑郁之情。《杂诗》记载,左思本是“高志局四海”,却囿于西晋门阀制度下寒门的等级现实,最终只能“块然守空堂”。而陶潜因其经历与左思相似,诗中时时流露出对政局的失望和晦暗社会的抨击,如“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其二十),“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二十首》其二)。除此之外,《诗品》谓左思之诗体貌风格出于刘祯,刘祯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协”即相同,陶、左二人诗歌都可以追溯到刘祯,风格高迈、意气凌霜之句时常流露于字里行间。例如,陶潜在《咏贫士》《咏三良》《咏荆轲》等诗作中所抒怀抱不乏孤高耿介之语,“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言”(《咏贫士七首》其五)表陶公虽身处穷困而泰然自若,就算箪瓢屡空也晏如无碍;“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咏三良》)为三良之忠直死节而感伤遗憾;“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咏荆轲》)追思报国志士荆轲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大义凛然等。借用钟嵘在《诗品》里评刘祯之诗,即陶诗也有“贞骨凌霜,高风跨俗”的一面,兼具关怀社会和对现实愤郁不平的思想感情,豪放中其风骨可见一斑。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首所言“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说的正是。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谓其文体,“笃意真古”谓其文意,“辞兴婉惬”谓其文辞。整句即谓陶诗风格简洁明净,绝无烦冗之词,文意古朴深厚,文辞婉曲恰当之意。许学夷于《诗源辨体》卷六曰:“靖节诗不为冗语,唯意尽便了,故其中长篇甚少。”陶潜喜用简短清明的文学体裁抒情表意,如四言诗《停云》《时运》《荣木》等;但五言诗使用最为频繁,陶潜诗今存一百二十五首,五言诗就占了一百一十六首,诗人以诗笔写诗心,常有佳句流淌于笔端。钟嵘在《诗品序》中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陶潜可谓是充分发挥了五言诗抒情言志的优点,言尽而意无穷,状物绘景,如在目前。“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此句言人品和诗品,谓其诗意真率古朴,诗多兴会,婉曲惬意。陶潜作咏怀咏史诗喜用史书经典中的古事典则,诗句精练且内涵深厚;写景抒怀的诗作又直抒其意,冲淡清丽,浏亮自然,非他人用力之所能学也。陶渊明一生求本求真,追求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状态,一种心灵的安适之所。由于其性情闲静,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天然忘机,对自然万物天生喜爱,于是诗句平淡而有思致,如“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停云》)以八字起兴之笔委婉叙亲友之思,充满悠远画意;“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简明地描绘了清晨薄雾渐消,和风使新苗张开翅膀恣意生长的画面,勃勃可爱;“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述耕种农忙时节过后闲适安乐的悠游娱乐生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神》)对生死之事直言不讳,传达出自己乐安天命、顺应自然的豁达的生死观,表露出陶潜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虽为简短之句,但恰好概括了陶潜的文风品格,赞扬了诗人返璞归真、自然率真的秉性。
“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陶渊明一生所作诗篇即为其人生的写照,可概括为“文如其人”。陶潜人品高洁无瑕,于阴晦的世俗也纤尘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世俗官场的蜗角虚名和蝇头微利嗤之以鼻。他的一生返璞归真,人品之孤高不同于流俗,发之为文,人品之耿介高洁如在目前。戴建业教授评价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为“洒落”,他认为“从诗人应世观物的情感态度、内在的心境到诗歌的语言、音调、节奏,无一不烙下他相同的体验方式的印记:恬静、冲和、节制”(《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相对于剧烈的心灵骚动,不管是穷达成败,陶潜都没有露出相应的大喜或大悲。朱光潜先生后期称“渊明则气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诗论》),这是一份独特的人格魅力,心境的清旷冲和使诗人能够以清明恬静的心态应付任何人生际遇。面对诸子不肖的事实以委任自然的态度处之;期友不至仍然神闲气静,颇自怡悦;出门乞食也未失去精神平衡;更不必说他“宽乐令终,好廉克己”的品德,“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颜延之《陶征士诔》)的为人。此外,苏轼也为陶潜坚守节操所叹服,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大加赞誉其为人之真率坦诚:“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字里行间尽是对陶潜的仰慕和欣赏,并在《与苏辙书》表白自己后悔半生东西游走追名逐利,陷入蝇营狗苟之泥潭而致亏损名节,于是细和陶诗一百零九篇,表明自己“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追和陶渊明诗引》)的志愿。此外,李白在《戏赠郑溧阳》中把陶潜当作可亲的长者—“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中表明了对陶潜青松竹柏之人格的向往—“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更是推举陶潜的气节—“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无数文人都不吝笔墨表明自己对陶潜的高风亮节的敬仰,陶潜也成了历代文人失意时得以暂时回归憩息的心灵港湾。
“世叹其质直”谓当世之人惋叹陶渊明诗过于质朴率直,略显不足。齐梁时代,诗歌创作的流行风气重视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骈体文,不重视质朴率直、自然淳美之文。正如刘勰所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赞其“文取指达”,未谈及诗作;阳休之在《陶集序录》中说“(陶诗)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连杜甫也在《遣興五首》其三叹其诗“颇亦恨枯槁”。囿于晋宋之际社会诗风偏好雕彩繁缛之辞、数典用事和讲求声病的局限,渊明诗受到许多偏颇的见解,沉没于当时而未掀起诗海波澜。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骈文逐渐衰落。自宋代开始,陶潜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轼眼光独到,指出“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颇为精当。陶潜以诗人笔法写田园光景,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和夸张手法,着重写平凡普通的生活,却能写得诗意盎然,如陈酒飘香,散发出久而弥醇的诗味。秋菊佳色之英华,南山豆苗之长势,东园青松之姿态,山涧河水之清凉;堂前桃李,远村墟烟,霭霭停云,蒙蒙微雨……朴素的笔触中又饱含警策绮丽的美感,似醇酒飘香,余味悠长。
“‘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欢言酌春酒”一句出自陶潜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诗人陶潜从乡间朴实的生活之景说起,初夏之际,草木茂盛,归鸟和诗人都乐得其所,由于身居僻巷,少有故人来往。摘蔬酌酒,风雨俱来,耕作事毕便沉醉于读书的乐趣中,与古人神交畅谈的“俯仰终宇宙”之乐溢满情怀,情调安雅清闲。这皆是诗人陶潜物我两忘、超乎尘世的思想境界的体现,在物我交融的乡居体验中,诗人以纯朴真诚的笔触讴歌了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体现了诗人高远旷达的生命境界和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
“日暮天无云”一句出自陶潜的《拟古九首》其七:“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月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美人于温婉月色之下,和煦春风之中,手持团扇,醉酒而歌,将人引入一幅极富美感的画面,如身临其境。然而,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美人“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多有人生无常,良景易逝之叹。朱颜辞镜,青春不再,时光如流水无情地奔涌而去,不由得感慨“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此诗文辞优美,诗意盎然,情感细腻丰富,将一种独特的悲情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意为风调华美,韵致清丽,哪里是一般的质朴无文的农夫能写得出的鄙俚之语呢?晋、宋时期,文风盲目追求华靡绮丽,陶潜诗作与当时的时代审美格格不入,所以诗坛寂寞,才秀人微,取湮当代。直到梁初,钟嵘独具慧眼,在《诗品》中将其列入中品,评价陶诗风格“文体省净”“笃意真古”,借用这两句极力表现了自然超群之美的诗句,在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将“田家语”的贬低之说驳倒,指出陶诗别有一番风味,蕴藉高远,华彩非凡。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这一句昭示了陶潜在历代文坛的地位。钟嵘给了陶潜极高的评价,对其诗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钟嵘在《诗品序》中极力推赞“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而陶诗风格恰好符合这一标准:“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陶诗自然旨趣鲜明,少有刻意安排、矫揉造作之辞,歌咏自然之物,直抒胸臆,神意灵动,写尽胸中之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两句自然而然地将诗人所见描述出来,不仅体现了“即目直寻”,也体现了诗人追求隐逸生活的纯朴的心境,此种心境岂止一个超凡脱俗了得。陶潜以其冲淡的品性为中国隐逸诗歌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官场庙堂之外开辟了田园诗歌的一片耕地,称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谓实至名归。
陶潜于今日的文坛地位可谓是高不可登,从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超逸的胸怀及冲淡的品性,无一不对我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陶潜已经得到了后世广泛的认可,观陶潜在现代文坛的地位,再看当年钟嵘列陶潜为中品这件事也无可厚非了。钟嵘将陶潜赞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对其已有所擢拔,将其列入中品诗人的行列,实属慧眼独具,魄力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