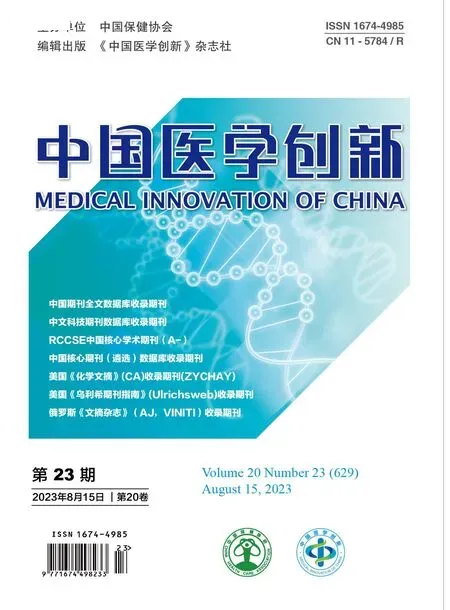细胞因子与肝衰竭的关系*
2023-09-08廖银英赵晓芳梁春妮方瑞超刘旭东林海
廖银英 赵晓芳 梁春妮 方瑞超 刘旭东 林海
肝衰竭(liver failure,LF)是指机体的合成、解毒、代谢与生物转化功能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出现失代偿,是由病毒感染、酒精、药物、肝毒性物质等多因素引起的肝脏损害,表现以凝血功能障碍、不同程度的黄疸和腹水,严重时可出现肝肾综合征及肝性脑病等为主的一组复杂的临床症状[1],治疗难度大,预后差,病死率高。
近年来,关于细胞因子在肝衰竭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成为临床研究热点,有研究报道指出肝衰竭的疾病进展与免疫损伤有着密切的联系,肝细胞直接损伤与免疫介导起到了有效的协同作用[2-3];另外,研究也显示细胞因子在肝细胞坏死和肝细胞再生方面发挥重要的生理病理作用[4]。本文为综述性文章,细胞因子种类众多,本文重点介绍其中几种肝衰竭相关细胞因子。
肝细胞直接受到病毒、药物等损伤后,会致使机体启动细胞免疫,激活一系列免疫细胞,分泌促炎因子与抑炎因子,促炎因子在肝脏中聚集,发生炎症级联反应,导致肝脏的二次损伤,引起肝脏炎症进行性加重,最终导致大量肝细胞失去功能,发生肝功能衰竭[5]。细胞因子在免疫反应与炎症反应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与肝衰竭进展过程中的肝细胞坏死和临床预后密切相关[6]。近年研究发现,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缺氧诱导因子-2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 2α,HIF-2α)与肝脏的生长密切相关;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α,SDF-1α)、基质细胞 衍 生 因 子-1β(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β,SDF-1β)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对于肝衰竭的损伤修复有积极影响;此外,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33 的免疫调节机制成为研究的重点。下面将简单总结一下这些细胞因子。
1 EGF和HIF-2α
EGF 是一种在人体内分泌细胞中极为重要的细胞生长因子,具有多种很强特异性的内分泌生理活性。Liu 等[7]的研究资料表明,其在调节细胞正常生长、增殖分化和细胞分化活动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Wu 等[8]发现EGF 对组织损伤具有充分证明的保护作用。EGF 能通过激活在多种哺乳动物组织中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刺激多种生物反应,且有研究调查显示EGFR 配体在肝脏损伤期间通过刺激肝细胞增殖,能促进肝细胞再生[9-10]。同时,Takemura 等[11]通过研究证明了EGF 的表达与肝脏中胶原蛋白基因的表达呈正相关,也表明了EGF 在肝衰竭中可能具有保护作用。Kong 团队研究证实,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NF4-UMSCs)与肝细胞的共培养主要通过HNF4-UMSCs分泌的旁分泌因子HB-EGF 对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发挥治疗作用,也为EGF 治疗ALF 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12]。
HIF 是一种低氧诱导DNA 结合蛋白二聚体,在多种辅酶因子存在的条件下,与低氧反应元件或DNA 序列结合介导靶基因的表达。目前科学家认为在人体结构中的HIF-α 亚基主要有下面3 种结构形式:HIF-1α、HIF-2α 和HIF-3α。Tian 等[13]在1997 年克隆出内皮PAS 结构域蛋白1(endothelial PAS domain protein 1,EPAS1),即HIF-2α。有研究表明HIF-2α 与骨髓造血、血管生长、能量代谢及肿瘤进展过程密切相关[14]。HIF 也与肝细胞再生密切相关,在通常情况下,HIF 是人体发育的关键因子,一项研究表明在哺乳动物中,若缺乏HIF-1的基因,将会导致胎儿死亡[15]。同时,研究表明肝脏中HIF-2α 的激活调节了肝脏稳态,并由此确定肝细胞脂肪变性、炎症渗出和变性纤维化均是由HIF-2α 激活后刺激肝脏系统引发的一种直接反应[16]。此外又有研究结果发现,HIF-2α 还有可能有效抑制慢性脂肪肝病变的再次发生、发展,可从中推测反映出机体自身在协调维持多种脂肪酸合成代谢功能平衡的过程中,HIF-2α 亦是能够起着极其重要的调控代谢作用功能的重要因子之一[17-18]。
综上可见,EGF 和HIF-2α 与肝脏生长密切相关,具体相关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但在肝衰竭大量肝细胞坏死期间,这类细胞因子可促进肝脏生长,改善肝功能。
2 SDF-1α、SDF-1β和G-CSF
肝衰竭进展过程中导致的肝细胞损伤可刺激一系列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的分泌,而这些因子同时参与了随后的损伤修复。其中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DF-1)是参与促进肝细胞再生和自我修复的很重要的一种细胞因子,其有两种表达形式:SDF-1α和SDF-1β。直至目前,调查显示SDF-1 可以在许多组织(包括脑、心、肺、肝、骨髓、脾脏)中表达。有研究发现,损伤坏死的局部组织能够通过SDF-1α 的表达扩张末梢血管来达到通过增加组织血流、促进组织血管壁重建和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逐渐归巢移植到局部损伤组织部位,以实现促进损伤坏死局部组织周围的正常肝细胞组织再生功能且可以进行肝细胞自我修复。目前关于促干细胞归巢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证实SDF-1α在移植干细胞向损伤的组织迁移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19]。Sun 等[20]在通过使用移植方法治疗肝衰竭的研究中发现肝组织中SDF-1 与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相关,证实了其对肝组织损伤有所改善。Yuan 等[21]研究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促进VEGF 分泌,肝组织的SDF-1 表达情况和人血浆VEGF 水平的异常表达及水平的变化呈正相关,可促进肝功能恢复。
G-CSF 是一种可以促进粒细胞增殖的细胞因子,主要作用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粒细胞减少症。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G-CSF 对肝衰竭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有观点认为,G-CSF 主要通过促进骨髓干细胞及肝干细胞在肝内的增殖以修复肝脏[22]。有相关文献报道称在肝衰竭患者中,G-CSF 可以直接动员骨髓干细胞进入人体外周血,并且为将来的肝移植提供足够的细胞数量,被证明是有效并且安全的[23]。Duan 等[24]的研究进一步提示了应用G-CSF可以有效改善肝衰竭的临床预后,其确切作用机制应是G-CSF 通过促进体内CD34+细胞的增殖来达到肝细胞的再生。国外一项研究显示,G-CSF 治疗可提高急慢性肝衰竭患者的生存率,并预防败血症、肝肾综合征和肝性脑病的发生[25]。可见,目前研究普遍认为其治疗肝衰竭的机制可能为G-CSF 调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细胞因子介导作用下募集于损伤的肝组织,并增殖、分化为相应肝细胞改善修复组织功能。
3 IL-6和IL-33
肝细胞在受到损伤后,会致使机体启动细胞免疫,激活一系列免疫细胞,分泌的促炎因子在肝脏中聚集,发生炎症级联反应,导致肝脏的二次损伤,引起肝脏炎症进行性加重,最终发生肝功能衰竭。Kasahara 等[26]研究了49 例关于急性肝衰竭尸解病例发现,在肝坏死区域中可见大量炎症细胞的浸润。有研究者在病理学观察中也发现往往是在那些急性肝病与各种亚急性肝衰竭晚期患者的肝组织器官中出现大量的炎症细胞浸润,例如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27]。
IL-6 是一种活性极高的免疫调节因子,可以直接由正常人外周血T 淋巴细胞、纤维母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及其复合体细胞等合成。IL-6 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不仅自身可参与感染性疾病的病理过程,同时还能直接作用刺激其他因子的释放,参与该病理的反应过程[28]。IL-6 作为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促炎因子,临床诊断上亦可用于早期评估细菌感染。近年来,有研究者对比了两组肝硬化腹水且合并腹腔感染的患者发现,好转组血清IL-6 水平明显低于恶化组[29]。周超等[30]也发现在肝衰竭患者中IL-6高水平组4、48 周的总平均病死率远高于所有应用IL-6 治疗的低风险水平组,且其4 周死亡的总平均风险系数约是所有低风险水平组总和的2.2 倍,48 周死亡的总平均风险水平则是全部低风险水平组约1.74 倍。有小鼠肝炎研究显示:肝脏中的促炎细胞因子IL-6 和趋化因子在肝炎发病期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同时出现肝脏炎性细胞浸润的增加[31]。此外,有研究表明在IL-6/STAT3 信号通路研究中可直接用于募集并活化中性粒细胞,经过这一系列趋化、黏附及渗出血管壁,最终可引起肝细胞的损伤[32]。
IL-33 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剂,在调节性免疫反应中具有多效性活性,并且在过敏、纤维化、感染性和慢性炎症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IL-33 已被确定为在炎症过程中,从上皮细胞和不同人体组织和器官释放的“警报剂”[33]。据研究者发现,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克罗恩病患者炎症组织中的IL-33 mRNA 主要来源于内皮细胞[34]。据调查显示,在小鼠和人纤维化肝脏中,与健康肝脏相比,IL-33 水 平 及IL-33 mRNA 表 达 均 更 高[35-36]。另外,IL-33/ST2 信号通路触发的炎症反应导致中性粒细胞扩增,而肝脏非实质细胞是IL-33 的主要传感器。在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小鼠模型研究中发现,对乙酰氨基酚过量会导致肝脏细胞大量坏死和细胞内免疫细胞积累,并伴有IL-33 和趋化因子释放。因此,炎症细胞因子与肝衰竭进展过程中肝细胞的坏死和疾病的临床预后密切相关,大多数学者认同肝衰竭的发病机制中的“三重打击”学说及“肝脏的二次损伤”学说,两者均表述了炎症细胞因子在肝衰竭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水平的变化与肝衰竭严重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37]。
4 总结
目前,肝衰竭的发病机制尚不确切,大量研究结果发现肝衰竭与多种细胞因子密切相关。已有的研究表明,一些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导致肝细胞大量死亡,加速肝衰竭,而有一些细胞因子参与肝脏损伤的免疫修复与再生,尽管有了这些新发现,在肝衰竭治疗却无广泛的应用。因此,在肝衰竭发生发展过程中,提高对评估病情的细胞因子的预警认识,以及如何应用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改善肝衰竭是研究者及临床医生应思考的关键问题,从细胞因子着手探索治疗肝衰竭的新方案也需要临床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