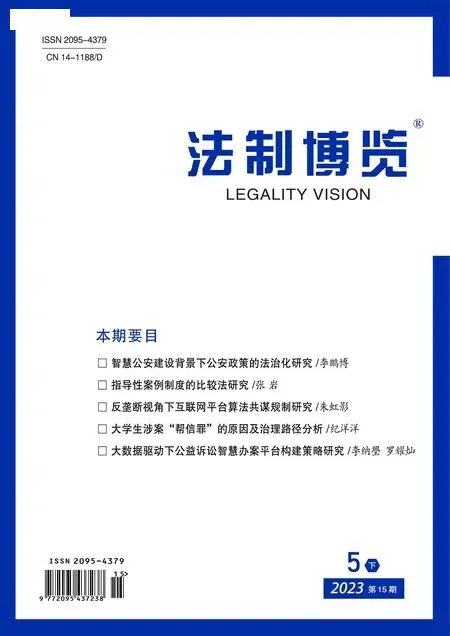民法视域下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定位
2023-09-03王千昱
王千昱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冷冻胚胎案的基本案情
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是沈某南和绍某妹,原告诉称其儿子沈某和儿媳刘某因为自然生育存在困难,遂于2012 年2 月前往G 医院生殖中心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来孕育后代,夫妻双方原本将在2013 年3 月25 日进行胚胎移植手术,但遗憾的是在手术的前一天,夫妻双方因车祸而不幸去世,遗留的冷冻胚胎将何去何从,怎样处理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冷冻胚胎在法律上是属于“物”还是“人”,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清晰的规定,这让原告和被告以及第三人对冷冻胚胎的归属和处理争论不休。原告认为,根据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认为,冷冻胚胎是他们儿子和儿媳的生命继续,应当由其来监管与保存,所以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G 医院将其儿子和儿媳在此冷冻的胚胎交由原告监管保存。然而第三人G 医院这样说,胚胎在法律上的属性并没有明确为“物”,不属于沈某和刘某的遗产,不能够由其双方继承,并且沈某和刘某夫妇在此前已经签订了将过期胚胎抛弃的协议。然而冷冻胚胎的作用只是辅助生殖技术用来帮助那些自然生育困难的人群,帮助他们解决自然生育难的问题,胚胎并不能用于买卖,这在我们国家是禁止的,如果胚胎被拿出去,那胚胎唯一能够存活的方式就只有代孕,然而代孕在我们国家也是被禁止的,代孕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国家是违法被禁止的,当事人双方没有权利去行使沈某和刘某的生育权。所以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冷冻胚胎案的裁判结果
Y 市人民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交由其监管保存,然而冷冻胚胎并不属于法律上的“物”,在法律上并没有清晰界定它的属性,它是不同于普通物的特殊物,在一定情况下它能够通过孕育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新生命,所以冷冻胚胎并不能像普通物一样由其父母来继承,不能够成为我们法律上的“物”,不能够成为转让和继承的标的。同时沈某和刘某夫妇冷冻胚胎的目的只为生育,不能出于其他目的,因为在我国代孕和买卖胚胎都是违法行为,所以他们只能够有生育的权利,不能够买卖胚胎,也不能够找人进行代孕等等,所以当他们两个人去世之后,他们的生育权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只能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在一审法院判决宣告之后,沈某南等人不服判决,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明确将胚胎禁止继承,对于原《继承法》上规定的其他合法拥有的财产,这一点胚胎应当是满足的,所以能够被继承;第二,沈某夫妻二人和G 医院签的那份协议涉及的是他们在该医院进行胚胎移植手术成功之后,对于剩余胚胎的处理权,然而现在夫妻双方已经去世,手术已经不能进行,所以无论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还是根据合同规定,医院都无权处置该冷冻胚胎,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将导致冷冻胚胎没有权利主体,无人能够行使权利。上诉人希望撤销原来的判决,改变判决为胚胎由上诉人保存。
二审法院主张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保护,Y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沈某南两人和刘某法两人一起对冷冻胚胎进行保存。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尽管沈某和刘某夫妇在去世之前和G 医院签了知情同意书,协议说明胚胎要保存1 年,如果超过1 年院方就将胚胎进行处理,但是现今沈某和刘某均因车祸去世,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知之事件,使得合同无法进行,所以,G 医院不能独自处理胚胎。第二,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没有对胚胎的定位进行说明,所以我们要考虑下面的几个因素:一是涉及伦理的问题,胚胎是沈某和刘某遗留下的,其胚胎当中所携带的DNA 当中蕴含的遗传信息来自两个家族,该胚胎拥有家族的遗传物质,属于特殊的物品,对于胚胎的处理应该考虑到伦理性问题,所以原告沈某南二人对于胚胎具有一种亲情上的关联性。二是人类感情问题,原告沈某南二人在暮年之时丧失了独子独女,对于老年丧子的痛苦并不是外人所能感同身受的,然而沈某两人所遗留下的胚胎,乃是双方家庭唯一的寄托,此胚胎能够缓解双方父母失独之痛,能够寄托哀思,所以将这个胚胎交给双方父母保管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人们的正常情感。三是出于特殊利益的维护,冷冻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之物,具有成为一个人的潜能,相对于普通的物,对于它的处理应该更加尊重道德伦理,而在沈某两人去世之后,其双方父母最关心其胚胎的处置,且对于胚胎的处置享有最大的直接利益,所以,根据上面的理由,法院判决双方一起对胚胎进行保存,这样有利于保护双方的权利。当然权利主体在对胚胎行使权利时不能够抵触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能够与社会的已有的正常风俗对抗,不能够对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第三,G 医院在诉讼当中所提出的卫生部的部门规章之规定,这个是卫生部对于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单位与人员的约束,而且部门规章是不能够对抗权利人在私法上所享有权利的。所以应当交由沈某夫妻双方的父母对于胚胎进行保存和监管。[1]
三、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
胚胎细胞是男性的精子与女性的卵子相结合而形成的,其具有孕育为生命之可能,在如今的社会发展当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女性的生育不再局限于需要两性的结合,只需将男性和女性的精子和卵子取出,在体外将其二者结合之后进行培育,培育一段时间之后形成胚胎细胞,再植入母体将其孕育成生命。然而科技在进步,[2]但是我们的法律却具有滞后性,对于胚胎细胞在法律上的定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通过了解各国的民法对胚胎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规定:第一,日本法律并没有规定胚胎是客体还是主体,只是明确胚胎是人类的初始阶段;第二,法国规定了胚胎只在其权益保护范围内承认他的主体地位,除此之外只有存活的婴儿才是民法上的主体。[3]对于胚胎细胞是属于法律上的主体还是客体得不到确定,这就使得在实践当中面对这样的案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于胚胎细胞是属于主体还是客体在国内外的学术界,现今主要有三种观点:主体说、客体说、折中说三种学术观点。[4]
(一)主体说
有学者认为胚胎不能够用民法上的“物”去衡量,而且胚胎也不能够被当成人体的器官,民法所说的“物”,是指存在于人体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并且能够由人力所支配的物质。然而人体器官是指由多种组织构成,能够行使某一种特定功能的结构单位。[5]民法上对于“物”的定义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我们都知道胚胎的唯一作用便是将其植入母体孕育为生命,但是当它失去母体之后便无法被孕育为生命,然而我们国家的法律还规定了胚胎是不能转让、赠送和买卖的,所以胚胎也不能带给我们经济价值和其他的实际效用,但是对于“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介绍上,法律并没有明确写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需求,除了物质需求之外,我们还有精神需求,[2]将该“需要”解释为精神需要也未尝不可,而胚胎细胞在某些时刻它是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的,代入上述案件当中,双方老人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和独女之后,胚胎细胞是两位年轻人所遗留的唯一带有他们遗传物质的东西,这对于双方老人来说,也可以说是很好的安慰,但是在该案件当中,法院判处胚胎归于双方老人看管之后并没有相关法律作出的规定要怎样看管,放于哪里看管。虽然有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对于胚胎的处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但是这并不起实质的作用,没有具体细化将怎样保管,放于何处保管,这也给了保管者极大的自主权,对于保管者是否会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善良风俗也起不到很好的约束作用。更有的学者说,胚胎作为一种进一步就能成为人的特殊的产物,对于胚胎的法律规制在考虑到利益的基础上,还应考虑人格权上的规定。而笔者认为将胚胎细胞解释为法律上的主体是很荒谬的,主体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包括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属于民法上的主体,而将胚胎解释为主体也就意味着将胚胎解释为自然人,然而在我国《民法典》中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第十六条当中规定了,胎儿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与胎儿利益相关的情况之下,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胎儿只有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利益保护的前提之下,才被视为民法上的主体,然而这也透漏出了胎儿并不被民法承认为是主体,然而胎儿是比胚胎更加接近于生命的物质实体,但是却连胎儿都不能够被解释为主体,更遑论胚胎的法律地位。
(二)客体说
客体说认为,将还不是生命的胚胎细胞当作自然人主体来看待,不管是在法律还是自然科学上都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在我国《民法典》上的胎儿利益保护条款中也得到了支持。以杨立新教授的观点来看,该观点将物分成了道德伦理上的一种物质、比较特殊的物质和与其他普通物质一样的物三种类型,将冷冻胚胎离开了人体组织之后的器官和组织作为是一种道德伦理上的物质,不将其当作是主体,此时也能将它的法律地位和属性清晰表现出来。然而对于客体说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称,既然胚胎被当作了物,那便属于了财产的范畴,在自然人死亡之后,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并且能够赠送与买卖,反对者们认为这是在法律上所不允许的,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三)折中说
顾名思义就是胚胎细胞既不是人也不是物,而是处于一种人与物的一种中间的状态,但是这样将会让人无所适从,我们的法律只规定了客体与主体,还没有出现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的情况,既然折中说认为胚胎是介于人与物的中间状态,那我们在适用法律时是将他看作客体还是主体?如果都不能,那它将游离于法律之外,无法规制,势必造成混乱。
在笔者看来将冷冻胚胎看作是一种客体,属于物的范畴能够得到很好的支持。第一,在我国《民法典》当中,对于胎儿的保护上所表达的意思为,我们只有在为了胎儿利益考虑需要保护的时候才能够将胎儿视为是具有民事权利的主体,然而法律在对于即将出生为自然人的胎儿,都只是将其在一定条件下视为主体,并没有将其直接规定为主体,显然将胚胎看作是主体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经不起推敲。第二,冷冻胚胎乃是脱离了人体而独立存在的有体物,在人体组织、人体细胞脱离了人体之后,便不再具有了人格属性,应当将其归类到物之范畴。第三,将冷冻胚胎定位为物的范畴并不是让其像普通物一样可以任意买卖,而是将其归类为物但区别于普通之物的伦理物,即属伦理物,对于它的处理便不能像普通物一样随意买卖。然而在部分其他学者的观点当中又将胚胎称之为人格物,之所以将其称为人格物,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可以发展孕育为人的生命信息,在未来将有可能成为法律当中的主体,此称谓与伦理物虽名字不同但是观点却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胚胎作为物的范畴,能够更好使它在法律当中找到合理的定位,能够很好地将胚胎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都清楚表现出来,能够使其在民法当中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没有必要将胚胎看作是主体,抑或是物与人中间的一种客观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