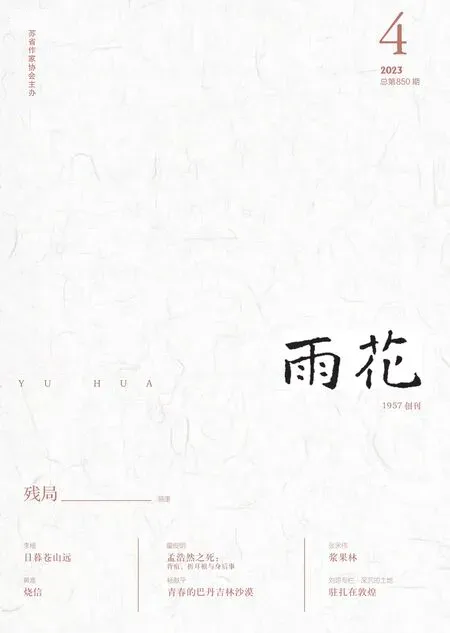青春的巴丹吉林沙漠
2023-09-02杨献平
杨献平
春天的安静遭遇
那是2002 年初春,准确说,巴丹吉林沙漠的初春,依旧是冬天。空气中不过多了几丝飘来飘去的暖意,人体内,也涌动起些许微妙的感觉。站在窗前探身,就可以看到,房前房后,远处近处的树木依旧颜色灰白,干瘦的枝条侧伸或者直立,完全没有被暖意唤醒的迹象;只有几处向阳墙根,谁家种的韭菜倒很快变绿,高蹈的风捕捉不到它们,总在头顶轻轻捋动。
在沙漠戈壁的我们,每年此时依然棉衣紧裹,害怕突然的冷暖,害怕它们制造的身体的小小厄难。早上,我和其他人在饭堂埋头吃饭,嘴巴发出的声音很响亮,其中还有些小声说话和大声咳嗽的人,表情各不相同,内心当然也迥异。我就在他们之间,某一张桌子上,不怎么说话,也不想弄出进食的声音。每每这时候,我总是吃得很快,想尽快离开。我一直对公共餐厅很排斥,甚至讨厌,究其原因,一个是不安静,一个是自身的自卑感,还有一个是讨厌人在吃饭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事实上,只要容身于某个单位,大多数时间肯定不够安静,安静只在喧闹的缝隙里。每次,我总是第一个走出饭堂的大门,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的自卑大抵源于对外在的不满、个人境遇和乡村成长时期的各种受辱,以及家境的贫寒、卑微等等因素。多少年了,在异乡,在这个单位,我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见过各种场面。人头攒动或者正襟危坐,那种气氛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对个人生命活力和精神空间的抑制。我也一直觉得,人吃东西的时候,最好不要发出声音,尤其是让人看起来有些贪婪的那一种。食物是天地给的,也是真正劳动的人给的,过分享受,似乎有罪。
我这样的想法,大致是不妥的,但却根深蒂固,偏激和偏见大都如此。回到住处,从把钥匙插进锁孔,我感觉身体一下子松弛下来,好像一团棉花的感觉。打开的房间如此安静,桌子、凳子、洗脸架、电视机、床以及床上的被褥,除了门外偶然窜进来的风,它们不吭一声,待在我喜欢的位置,也保持着我喜欢的姿势。
独立的房间才是真正的一个人的世界,甚至可以称之为宫殿,尽管简陋,但简陋在很多时候是一种美德。老子《道德经》说:“人生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其中的慈和俭,我觉得犹如我现在的生活,也像那些家具和物什,在我的房间,它们沉默的宁静的表情,似乎一直在等着我回来。我突然有些感动,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物件,我应当真诚地感谢它们,应当向它们深深鞠躬。
坐下来,我时常会想些什么。想想现实生活,想想自己,想想家庭、故乡以及命运究竟……不管怎样的内容,我觉得都需要一种安静的环境,哪怕一枚曾经硌疼脚板的石砾,无意识地呆坐,漫不经心地阅读,还有某些时刻的惭愧和悔悟,如此等等。安静才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成长的必由之路。
在一个人的空间,我觉得时间、生命和个人竟然如此宽阔和从容。可时间久了,猛然起身,眼睛发黑,也会伴随一阵眩晕袭来。觉得自己的身体虚虚的,一朵柳絮一样,一阵风,或者一口气就可以吹起来,宛如空中的灰尘。
事实上,在巴丹吉林沙漠,更多的时候,却没有如此长的安静时间。在某一个单位当中,一个人充其量只是一粒沙子,掺杂在众多的沙子里面,没有、也不需要固定的地点和方向。可作为一个人,也是一个生命,单位及其位置,也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其中每一种行为,都关乎心灵、精神乃至灵魂。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做的或者不需要做的,最终都必须去做。而且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在这里,个人的时间不叫时间,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或者碎渣,一旦有事情了,他们想怎么样剥夺都可以。我常常有此类遭遇,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身患重疾等待手术的人一样。
电话响了,这种时候,我的心总是很忐忑,不知道该接不该接。而它响着,顽强得近乎催人老的时光。它响着,决不妥协。谁打来的呢?我飞快地将那些可能的人和事情在脑子里想了一遍,并且快速判断。我想我必须接,如果不接,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敲门。一样地麻烦。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家里的亲人打来的,家在距离我所在单位一百多华里以外的地方,一片荒漠戈壁的边缘。儿子还没满周岁。只要醒着,总是手脚不闲,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玩得腻了,还哭叫着要到外面去。有很多时候,我正在和家人说话,小灵通却响了起来,一看,是领导的,不得不接。领导要我做事,尽管那些事情无足轻重,但还是要去做,不能推诿,还要做好,叫领导满意。
很多时候,一个中午或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在如此的嘈杂和纠结中过去了,我渴望的个人的安静时光,成了一种近在咫尺的奢求。对有些事情,我总是想尽快做完,恢复到安静的状态当中,这是我最为欢喜的事情。可越着急,往往越会出差错,这里的,那里的,甚至是一个字词。一个词语,有时候就像一把刀子,一枚制导导弹,触碰不得。
除了那些被掠夺和瓜分的时间,余下的就是自己的了。我乐意陶醉其中,安静是一种心境,是一个人和天地神灵促膝论道,是一个人和自己身边的物什的一次忘我旅行,是空间中的一粒微尘,甚至病菌,自由并且孤独,悠闲而又紧凑,多么快乐!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
可有一个正午,和往常一样,在饭堂吃完饭,回到宿舍,钥匙刚刚插进锁孔,裤兜里的小灵通就响了。我想,会是谁呢?应当是家人吧。我接了。她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我脑袋转了一圈儿,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使有,也无碍大局,根本掀不动我们渐趋稳固的生活和感情。
我说,你不要吓唬我了。她说,是真的,我们放在幼儿园的书全部丢了!我说,怎么会呢?她说,四百多本,确实全部丢了!这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无法扭转。那些书都是我自己写的,自费出版,送了一部分出去,剩下的,不知道送给谁,就堆在先前临时住过的幼儿园,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个人事情上,我总是很邋遢、懒惰,不把很多事情放在心上。那些书,出版社寄来之后,我就堆放在那里,几个月过去了,它们在我心中慢慢淡化,偶尔想起,也只是一阵哀叹。想赶紧把它们处理掉,哪怕送人,也算是了结了一件事,可是我没有,我觉得它们已经过去了,成为僵死的一群。
可是它们丢了,这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可惜,但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后来的消息有点不好,在安静的中午和晚上,一个一个传来。她又说,她到大餐厅吃饭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服务员拿着我的书在看,就问了,说是另外一个白姓的服务员带她去拿的。白姓服务员和我们较熟,我们搬到新居之后,就把老房子留给她住。我打电话问姓白的服务员,她说在她之前门就开着,另一个厨师告诉她这儿有书。厨师说,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捡垃圾的老头拿了不少书,大致是当废品卖掉了。
我觉得这样也好,反正,我之前的那些文字,大致和废品差不多。更重要的,我不想这件事影响我的心情。我想要的是安静,没有一丝风吹的那种安静,当然,最好的,还是那种可以把空气拧出水、把时间搓软、把自己真正融进大地的安静氛围。可我没想到,那位白姓服务员反而觉得委屈,对我态度极差,甚至说,她的老板是我的一位同事,神通相当广大,与单位里的头头脑脑都有交往,常以哥们或者老乡互称,经常一起把酒言欢。我有点气愤,旋即又觉得无聊,如此的人,如此的话,如此的事情让我气恼又感到好笑。
我没想到,四百本书的后面,竟然有如此不堪的一些隐藏。我懒得理睬,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情,在这个春天,安静占据了我的心灵。我需要它,远比丢书的事重要。安静的心灵、心情和心理何其重要!可是,她又说给了治安部门。治安部门说,一些书,又不是啥的,不重要的话,就算了。她很气愤。我倒是很理解,书籍在这个年代,犹如良知,包括文化,人们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致。
因为这件事,我对周围的人和事突然感觉异常陌生,本来一件稀松平常的遭遇,牵涉到的人和事,还有一些现象,让我觉得心灰意冷,也以为,人在很多时候的自觉表现,往往显示出了一个时代的某些本质和特征。四百多本书丢了,我本不在意,可那些原本并不陌生的人,却表现得令我不明所以,甚至感到悲哀而又可笑,还有些诡异。平时嘻嘻哈哈、笑容满脸、礼数周至的人,遇到事情之后,一下子全变了,面目可憎,言语凶恶,我觉得不可思议。
此时,春天的事物正在逐渐萌发,在杨柳树上,在地表,在人的身体和天空中。至于我,在这个春天,在这个集体,乃至更大的地方,我不想吭声。春天已经展开了,向着夏天,以及夏天以后的季节,显得平静而又隆重,自然而又略显蹊跷。我的那些书们,此刻肯定还待在某个地方,还没有化为纸浆。它们肯定也如我,在一种佯装甚至有些虚假的安静之中,沉默、孤独、迷茫,进而会逐步消失,不留任何痕迹。
沙尘暴中
杨树刚刚吐芽,青草还在枯叶之下,梦想着未来的世界。而风暴,这隐身于沙漠深处的孤绝之神,就开始狂妄了起来,把瀚海大漠,以及附近的戈壁、零星的村庄和绿洲,当作它疯狂的舞台。十多年的时间,我已记不清在巴丹吉林沙漠经历了多少次风暴,以往总是对风暴采取忍让、躲避甚至厌恶的态度,躲进房间,在它巨大的践踏声中瑟缩发抖,或者诅咒这凶猛的自然灾难,而没有用心去体察和感悟这一凶猛的自然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尤其是近年来对巴丹吉林沙漠当中一些旧朝遗迹的探访,如西夏遗址哈日浩特、两汉时期的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都尉侯官府邸等等,使得我对这一片旷古的沙漠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哪怕是一粒黄沙,一丛卑贱的骆驼草,也使我感到十分的神秘和博大。在它们身上,隐藏着人类难以参详究竟的内在品质和独特精神。
2000 年4 月18 日,又是一个庸常的傍晚,置身落日之下,总觉得自己也是大地上某一种轻飘的存在,空气中的些许暖意如同久违了的手指,让人发痒,且又充满了蓬勃与刚劲的动感。吃过晚饭,我到附近的商店买了一些日用品。按照常理,这时气温应当下降,即使穿两件毛衣都不觉得热,而我仅穿了一件薄薄的羊毛衫,就觉得浑身燥热,细密的汗珠从帽檐下涔涔而下。刚一进门,我就被告知,停电了!我想,这大概又是电厂出了故障。可就在我举步上楼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万马奔腾的巨大轰鸣声,由东向南,轰隆而过。我的脑海里迅速闪出一句话,哇,风暴来了!
上楼,打开房门,风暴已然在咆哮怒吼了。在关窗户的时候,我看见大片的杨树齐齐低下头来,整齐划一,没有一棵腰杆是直立着的。窗外,粗大的沙粒犹如冰雹砸地,又像呼啸着的利箭,前赴后继,在空气中飞速前行。我听见它们击打玻璃的声音,“嘣嘣”,连续不停,像是剧烈而又错乱的鼓点,敲得人心发慌,整个身体都在颤动。马路上的人齐声惊叫,携儿带女,抱头捂脸,飞快地向家里逃跑。连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也顾不得什么风度了,平日高昂的头颅和龙行虎步变作了抱头鼠窜。
巨大的黄尘像漫卷的浓雾,天空骤然暗了下来,淹没了附近的村庄和树木。我站在宽敞的窗前,看见那些刚刚出世却又被沙粒击打得千疮百孔的叶片,心在隐隐作痛。可我并不能阻止什么,也不能像爱护幼子一样,将它们一一收进怀抱。很多时候,真善美和丑陋、凶残注定要同时出现,也注定要刀兵相见。美的东西必然是脆弱的。这时候,几乎所有被人抛弃的东西,就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目光乃至生活当中。各色垃圾袋如同一面面飞扬的旗帜,又像是一对对充满恶意的翅膀,在空中飘飘扬扬,它们不可一世的样子,充满了对寻常事物的蔑视与摧毁的欲望。
其中有几辆没有来得及躲避的四轮车,如同笨拙的毛驴,在马路上左冲右突,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司机一手转动方向盘,一手遮脸,仓仓皇皇,从我的窗下经过。倒是几台卡车显得稳重一些,轰鸣着迎风而驰。在连绵的风暴当中,那些平时在窗外“叽叽喳喳”的小鸟们,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风暴的粗暴嗓音代替了它们的婉转歌唱。
好一阵子,似乎一个多小时了,风暴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我也不希望它这么快就销声匿迹。细碎而又蓬松的灰尘洋洋洒洒,贴在窗玻璃上。我嗅到了它们浓重的陈腐气息,并且进入了我的肺腔,呼吸顿感沉重。此时的窗外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风在叫嚣,像几百万头冲出牢笼的困兽,嘶吼着,奔跑着,携带着浓重的尘烟。它们在寻找一切可以捕杀的“猎物”,什么都不可以阻挡。它们巨大的足音,震颤着我的心脏,敲打着我的骨骼。
这经常的风暴,是对巴丹吉林沙漠乃至其周边人事物的覆盖和篡改,风暴就类似于末日来临式的恐怖之梦,类似于一宗永远都无法侦破的暴力案件、一场突如其来的生命约会。在窗前站得久了,我突发奇想,何不到风暴中站立一会儿,让这猛烈的大风,吹吹我早已弯了的背,吹吹我僵化了的脑袋。我翻身,找出一顶太阳帽和一件风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可就在下楼梯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发虚。门外的风格外强劲,一波一波,仿佛汹涌的海浪,携带着巨大的粗糙的声音,在人的身心之内,制造恐慌与绝望情绪。
刚刚抬脚出门,我就后悔了,但后退不是我的风格。我抬头看了看天空,一咬牙,就快步冲进风暴。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仿佛要将我的身躯像那些垃圾一样送上高空。但它还不足以将一具六十多公斤重的物体托举起来。由于还算高大的围墙,巨大的风暴形成了一股股回旋的暗流,像大河中的暗流,使我的身躯左右摇晃不定,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这多么像充满突然的现实生活呀!永远都无可逃避,自我选择的权利也在情愿不情愿地被他人和时间无情地剥夺着。
我到房后的那条笔直的马路上,去体验一下刚才那些人遭遇风暴时的心情。在这里,风向是笔直的,感觉就像有一根粗大的木棒,在一下一下,猛烈打击着我的身躯,仿佛要将一个人的肉体捣成肉酱或是碎片一样。我呼吸困难,沙尘毫不犹豫地扑进了我的口中,鼻子和耳朵早已被塞满了。我突然想到,人是多么简单呀,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只要轻轻一击,就会销声匿迹,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绝对不比一株杨树坚强,又比一粒沙子重要多少呢?
我狼狈地跑回房间,木然感觉身上沉重了许多。我知道,无可避免的沙粒已进入了我的衣衫,乃至肉体。它们就像一群毫无礼貌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类似于人生的某些章节,时时都有可能被篡改和拒绝。我没有立刻洗漱,仍然站在窗前,怔怔地看风暴是如何运行;看风暴之中的各色人物和动植物的行为表现。在同样的环境中,人和动植物的命运迥然不同。人有房屋可以栖身,躲避风暴的吹袭,而树木只能依靠自己错综复杂的根系来维持和保护生命。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就说过这样一番话:“虽然人类社会的根基深植于人类生活的开端,但比较而言,人类在解决其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复杂局面,每一代新人都会面临着这一新的复杂局面所产生的新的烦恼。”
人在不断为自己设置障碍,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也许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风暴、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等等就不足为怪了。在自然看来,人的本性是狂妄并且懒惰的,必须要时时给予提醒,不然,它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就会与其他一些动物一样地愚蠢。看着风暴,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敬畏自然应当是一种极其高贵的品质。傍晚七点二十一分开始,风暴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晚上十点三十四分,在我写作和思考的时候,风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场风暴就像一场梦,让我在经历了痛苦和焦灼之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而我的脸、脖颈、手臂等处依旧隐隐作痛。可风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留下的印记或者创伤远不止这些。一场风暴,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次洗礼,就是一场生命与突如其来的强大事物的遭遇战。
生命何其脆弱和渺小!对于自然甚至人文的那些环境,一个人根本无法选择,只有不断经历、融合、体察和感悟,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坚韧与宽阔一些。在巴丹吉林沙漠,对于我个人来说,一场风暴就是一份独特的人生经历,一种充满暗喻的警示和鞭策,也是一种自然和人的相互指认和觉悟。可在很多时候,难得有人能够在风暴中静下心来,仔细观察风暴自身的运作秘密,以及风暴之中人和事物的那些异于寻常的表现,并从中发觉一些天地与生命的秘密与厄难的因由。
春节的过程或者心情
春节到了,作为文化干事,单位那边需要布置,即用一些灯笼、彩旗、横幅和灯光之类,营造一下繁荣、吉祥和愉快的气氛。几个同事在此之前已经离开。如他们在,这些事务可以分开来做,各自负责就可以了,而他们都探亲休假去了,只剩下我,我必须做,个人的事情只能放在后面,在一个集体当中,无论是谁,都要屈从于虚无但又很实际的意志,它高高在上,姿态凛然而又纹理坚实。
我不能例外,是本职工作,我从中取得了一些生存资本,就没有理由推脱。虽然有些不自在。事实上,前几天,我们几个就开始忙活了,做出一副认真负责的样子,对每一只灯笼、横幅、彩旗都进行了精心安排:买来的旗子面积很小,只适宜插在办公楼顶上;横幅很宽,白色的大字需要醒目,为了让人们都能看见,就悬在街道上面,高度适中,其下还要行车;树木零落,枝丫干枯,彩灯可使它们在夜晚显露生机;除了回家的人之外,一些人必须留守,为营造欢乐、吉祥的气氛计,还得为他们举办游艺活动,猜字谜、玩游戏、甩扑克、打台球等等,活跃一下生活。布置好了这些,年三十就到了,上午收尾,又逐项检查了,自觉可使领导和战友们基本满意。
车子在风中奔行将近一个小时,到了大门口,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在耳畔炸响。春节真的到了,这样一想,瞬间一阵轻松但又很快消失。平心而论,倒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节日,是习惯在起作用。幼时也曾为此欢呼雀跃,总觉得这个日子神圣了得,盎盎然忘乎所以,但却转眼不见,剩下的只是红尘俗世的重重羁绊和凌乱缠裹。至今,倒有些厌倦了,总觉得节日的人为色彩太过浓厚,常常令人感觉猝然而又不由得随波逐流。
打开自家的门锁,就又见到了远道而来的母亲,虽然只有八个月但已经可以喊叫爸爸的儿子。只是,早就买回的对联还没有贴上,红灯笼还在一角沉默,厨房还没有溢出熟悉的诱人的香味。但春节的气氛在房间的空气中流传,像是从内心淌出来的一样,感觉窗外的太阳也有别于往常,黄黄的光芒穿过白色的玻璃,在窗台和地板上泊出一汪宁静。
贴了对联,点了灯笼,节日气氛就非常明显了,抱过儿子,心中的喜悦不自觉地又浓重了一层。与单位不同的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氛围,更是一种心情。个人由此彰显。两者比较,最重要的是多了自由,多了信任,因而心情澄明,那些猜疑、犹豫和收缩甚至遮掩消泯了踪迹。母亲抱了孙子,坐在沙发上,看着屏幕上的那些喜笑颜开的人们,我在厨房“叮叮当当”。夜色在我们的活动中伏地而起,渐渐覆盖了巴丹吉林沙漠和沙漠边缘的房屋。街灯笼亮了起来,一串一串的灯笼从南到北,一只一只,微风使它们微微摇晃,红红的光晕串联了我们的目光。孩子们追逐玩耍,不时点燃鞭炮,清脆的声音直击耳膜。
我坐下,拿起电话,向远方的亲人和朋友祝福新年,心情激动,我对在老家的父亲和弟弟说,我爱你们,话一出口,泪就流了出来。我对朋友们说,祝福你,祝福你们……如果祝福可以成为事实,我愿意一直说下去,只要还可以发出声音。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加缪说过这样一句话:谁可以确定永恒的福乐可以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事实上,经常的痛苦比永恒的福乐更为真实和坚决。
儿子身手不闲,嘴巴里“呀呀”说着什么,一会儿又“唔唔”叫了起来,像是在唱歌。我们谁也听不懂,也不需要听懂。我想他肯定不知道今夕何夕,他只是遵从生命,在时间里成长。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语,他也对我们的笑和表情表示诧异,又很快忘掉,专心他自己的事情。趁儿子自个儿坐在沙发上玩电话的空儿,我说,吃了饭还得去领导家走走。平心而论,这种事情我最不愿意做,但又没有办法,有些习惯是可怕的,甚至是对人的一种伤害。
把儿子交给母亲,我去商店。那里灯火明亮,顾客虽然不多,但购买货物的“价码”要比往日高上数十倍,粗略一看,这些人大都是像我甚至比我职位更低的人们。各自在高档商品架下挑选自己认为合适的那些货品。他们要送给何人?我不得而知,但目的却没有太大的区别,买了东西都是要送给别人的,这里所谓的“别人,”一定是那些比我们职位高、权力大的那些人。
先我而来的那些人又先我而去,手里提着各种精致的货品。他们去向谁家?其实这疑问很是愚蠢。他们同样不知道我去向谁家。我和妻子在货架下仰头低头,摸了拿了看了好多的货品,用心掂量,不是货品的轻重。我在想应当把它们提到谁的门庭,他们看到又是怎样的一副神情,以及我们放下、离开后他们会对此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其实也多余,我们没必要想得太多,我们买了,送到他们家里,说一些话儿,就算完成了,尽管那些昂贵的货品,连自己和老父母都不曾享用过。
路上的灯光很是明亮,照得人有些不自在。来来回回的人们大都拎着东西,都在小声说着话儿,各自走向要去的人家。我和妻子骑着车子,挨得很近,我说,先去那个谁家吧?声音还没有消散,目的地就到了,敲开门儿,自是一副笑脸,招呼着“坐吧坐吧”,看见了我们拎的礼品,笑容不自主地多了好多道儿。嘴里边说,来就来呗,带东西干啥?我们几乎同时说应该的应该的。坐定之后,喝着茶水,自然要说些什么,大都是无足轻重的套话,几分钟的时间,漫长得像是整整一夜。
出了一家,我们又到了商店,挑选了东西,要到另外一家。忐忑地叩开门儿,几乎是故景重现。如此几次,回到家里,脱掉大衣,长出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桩重大的事情,心情再度轻松起来。母亲说,这样做不好。我说,简直有点无耻。逢迎权力,不仅是对自己的良心和公义的恶毒践踏,还是一种无耻的推波助澜。可是,生存,这一强大的字眼,其尖锐和疼痛程度,常常让我们无法面对。这一种荒诞的欢乐,我听见有人在说:“静下来,让黑暗降临到你的身上,那将是黑暗。”
历来歌舞升平的晚会嘈杂着,整个房间都是这样的声音,那些虚假、口是心非的说笑和祝福,让我感觉到这世界一片空旷,所有个性独立的事物,我相信他们此刻都是孤独的,但除了这些声音。可我们是庸俗的,必须为自己找寻一些欢乐。黑暗的缝隙虽然距离阳光、清风和露珠的路程遥不可及,可我们必须寻找,哪怕虚妄冥想。
钟声还没有敲响,鞭炮声就铺天盖地了,一波一波,爆响在巴丹吉林沙漠的黑夜,那些脆响的鞭炮,经由不同手掌点燃,爆炸成灰,它们都是从单位带回的,鞭炮的响声是否会带来一些欢乐抑或快感?如果我是它们当中的一个,我想会的。
鞭炮声一直持续到天色放亮,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到这家那家拜年。我们没有去,谁的家里我也不想去,一家人一大早包了饺子,围坐在桌子旁,外面的声音,一会儿远了,一会儿近了。直到中午,礼堂那边传来铿锵的锣鼓声,母亲抱着儿子去看热闹去了。我打开电脑,发了几个邮件,我觉得这一天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时间的指针毫不停歇,依旧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嘀嗒”作响。
大年初一的晚上,单位举办了焰火晚会,礼花朵朵,在空中炸开,在下落过程中逐渐熄灭,看不见的灰烬洋洋洒洒,落在衣领、脸颊和满是尘土的地面。那么多人仰头望着,接连发出惊叹,尽管眼里堆满虚幻。
前妻的几家亲戚驱车来到,一阵欢笑之后,开始围坐在一起饮酒,说些高兴的话。一夜下来,白酒少了数瓶,若在往常,我必然会酩酊大醉,头昏脑涨,早不知此身何处了。次日一大早,打车到前岳父家,又是饮酒,好不畅快,如此到初七,若不是第二天要上班,我还不想这么早就回单位,在尘土、落叶、日光、沙砾、车辙、桌子、电脑和办公室之间,按部就班地做那些事情。
后来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只是其中一粒/流水的叶子,石头上的黑色苔藓/壁虎爬来爬去,你知道它们总是在重复/因此,黄昏的笑意是轻薄的/尽量不要让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