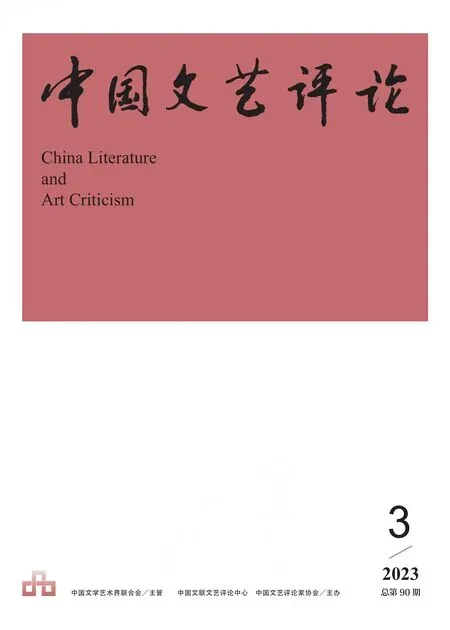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与“破圈”之道
2023-09-02王亚芹
■ 王亚芹
在媒介融合的数字时代,文艺作品从创作、流通、接受到再生产的全过程都呈现出大众化、互动性与即时性等特征。根据《2015美国新媒体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数字媒介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P”,即“个人化、移动化、参与性与弥漫性”(Personal,Portable, Participatory, Pervasive)。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1]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第5页。相应地,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融媒体的信息交互性使得自由批评、多元表达成为当下文艺批评的常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了“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批评生态之中。但是,这种“狂欢式”批评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文艺批评的“圈层化”痼疾。
实际上,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圈层化”的本质是批评话语生成逻辑的异化,它体现了当前文艺批评话语建构的混乱。由此,文艺批评要么成为超验性的“审美乌托邦”,要么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流量杠杆”,要么成为粉丝们“圈地自娱”的情绪宣泄。每个圈层都编辑了一套只有圈内人才能破译的“批评密码”,各圈层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并由此造成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有限性融通和公共批评的丧失。因此,如何加强理论、评论、文本之间的多元互动,平衡各圈层之间的关系,促进批评的有效融通便成为当下加强文艺评论建设的关键问题,也是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作用的题中之义。
基于此,本文从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茧房”效应出发,着力探讨批评生态“圈层化”的问题表征及其内在本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阐释性批评与现象学批评的反思,倡导一种直面文本与社会真实、尊重历史与当下感知、融合理论阐释与批评实践的“新感受力批评”,并以此作为解决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圈层化”困境的突破口。
一、“茧房”效应:当下文艺批评的生态表征
目前大量新媒体微平台和互联网群组的建立,拉开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序幕。海量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理论话语上的“去中心化”和对话语霸权的消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任何人都可以对“异己性”的话语批评进行质疑和解构。每个“圈”“群”的存在,都体现了自由、公平、友爱的嵌入型社会结构,并成为观测当下文化走向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人人都是批评家”,那么批评的边界又在哪里?况且“网络上(线上)的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线下)的公平”[1]Daniel Miller: Why We Post? Social Media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World, September 15, 2016, https://www.ucl.ac.uk/why-we-post/discoveries.。数字技术与消费文化的合流,使得“狂欢式”的批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圈层化”与“分流化”现实。
其实,在“前数字时代”也存在用于区隔不同群体的“圈层”,但是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程度的限制,当时的社会圈层关系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以区域为基础的“地缘圈”、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友圈”、以工作关系为基础的“事业圈”等。而随着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拓展,在互联网世界涌现出了更加多样化和大范围的圈层互动。因此,本文所谓的“圈层化”,主要是指“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编辑之友》2019年第11期,第5页。。以趣缘为纽带的同质化个体借助数字技术的东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群体”,并成为今天人们网络化生存的真实写照。以“95后”为主要对象的圈层文化营销平台“天猫青年实验室”就充分借助了商业资本和全球顶级数字娱乐IP的双重力量,打造了一系列以“二次元圈”“国风圈”“电竞圈”“模玩圈”“硬核科技圈”等为典型圈层的“天猫无限派对”。这些“Z世代”的亚文化圈层有着超强的活跃度和极强的影响力,也成为各种新物种和新关系孕育的成长地。“圈层化”批评成为很多人在网络空间中探寻人类联系的新机制。“网络空间是圈层文化兴起的‘趣缘空间’,这种趣缘空间具有了‘部族’或‘新部族’的特征,代表着当代社会关系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以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趣味为中心。相应地,网络文艺批评的方式也日趋圈层化、多元化。”[1]胡疆锋:《作为事件的网络文艺与新文艺评论的再出发》,《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第46页。因此,“隔圈如隔山”“说了你也不懂”“懂了你也不听”“听了你也不做”成为很多网络批评群体“圈层化”的形象表述。当我们将“不懂勿犯”视为网络时代“圈层化”交往的基本礼仪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网络评论经常出现“非黑即白”的对立与争吵了。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生态圈,也改变了当前文艺批评的生态场域。在数字“圈层化”背后的生成机制中,商品、资本、消费以及流量等因素其实发挥着比批评话语本身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圈层化”不仅是网络空间交往的一大趋势,也是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主要表征。
实际上,数字时代文艺作品的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趣味”判断,同时又夹杂着商业资本的运作,由此导致批评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如果说,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是人群之间“区隔”的重要标志,并影响了其阶层的“趣味”与个体“习性”的话,那么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种“区隔”更多是与技术媒介和网络文化的“趣缘空间”紧密相连的。数字技术应用的多元化,使得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由于个体多重身份的叠加,网络空间中的评论话题更加多样化、程度也日益深化,并呈现出越来越细碎化和“蜂群化”的发展趋势。每个“蜂群”通过划定特定的网络空间进行信息与观点的分享,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吸引更多人加入群体,并形成笼罩整个群体的价值观念。表面看不同群体在各行其道、百家争鸣,但其内部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大相径庭。这就是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即在看似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我们往往“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2][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8页。。不同的圈子文化通过信息流的方式被不断灌输给圈层内的每一个个体,在这种持续性的接受过程中,个体会在“茧房”效应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建构起一种信息的自我过滤和自我保护屏障,并在延绵不绝的同质化信息流的轰炸下,形成一种特定的圈层化的认知偏见。而当某个群体长期禁锢在自己所建构的某一种程式化生活中时,便同时意味着它失去了接触和认识其他差异事物的机会,沉浸在自己的“圈层文化”之中。数字媒介平台的交互性使得文艺批评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批评场域,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依然盛行。
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圈层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用“趣缘差异”不断进行“区隔”的过程。那些无法获得“圈层密码”的人被拦截在外,只有拥有共同体价值、思想统一的成员才能在“信息茧房”的推动下进一步巩固其群体的粘合性。在这一过程中,圈层内部的自我认同感不断加强,而圈外的话语则作为一种“他者”遭到了排斥,网络文化批评圈由此完成了对圈内和圈外的社会身份认同。毫无疑问,这种以自我圈囿为特征的“茧房”效应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圈层化”文艺批评的本质是什么?它在数字时代的主要表征与问题有哪些?
二、“圈层化”危机:话语建构主义的批评魔咒
随着传统文艺批评话语模式的日渐式微,数字时代的文艺评论出现了情绪化和碎裂化等批评新形态。这一点在学术产业化和消费主义的综合作用下显得更加杂芜。文艺批评首先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想话语”(intellectual discourse)[1][美]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其本质是为批评圈及其之外的世界缔结一种直接而强有力的关系。从库恩科学范式的角度来描述就是,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由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样貌的呈现。在此意义上,数字时代批评的“圈层化”现状,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建构主义的混乱。
(一)当下文艺批评的主要圈层及其话语特征
据此,我们将当下文艺批评的形态概括为:以“绞肉机式解读”为主要特征的学术圈批评、以“流量密码”为标准的自媒体圈批评和以“圈地造梗”为主要特征的饭圈批评。每个批评圈层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自说自话,各种专业化、符号化、行业“黑话”漫溢,真正有效的批评交往模式有待涌现。
1.“绞肉机式解读”的学术圈批评
一般来说,学术圈中的文艺批评主体主要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们,他们判断文艺作品的标准往往是以“审美”“超验”“价值引导”“精神引领”等为依据,具有明显的形而上色彩。一些学院派批评家不屑于日常生活经验与艺术的重复与琐碎,他们习惯性地将“审美超越”“审美理想”“审美救赎”“审美乌托邦”等视为自己判断一部文艺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正如伊格尔顿所坚信的那样,人类即使已经处于“上帝已死”的后人类语境中,我们依然不会、也不能放弃对于信仰与超越的理想性追求,这依然是当代学院派批评家们的普遍情结。因此面对无厘头的短视频或者娱乐段子,学院派批评家们更愿意将其精神主旨定位为一种“神学的置换性片段”[1][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宋政超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4页。,也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更多思想性的东西。实际上不少学院派批评家并未真正了解、更未参与网络文艺创作,他们常常用过硬的智识代替了体验和情感活动,面对数字媒介时代难免有很多“不及物”与“隔膜”。
由于学院派批评圈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批评极其注重学理性和学术性,话语逻辑和表述方式也呈现出专业化和艰深性的特点。对此,崔宰溶曾经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关研究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常用的词语主要包括:本质、深刻、辩证、复杂、深度、精神、创造……以及浅薄、轻松、单调、无深度、模仿等。[2]参见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1年,第40页。不难发现,这些批评话语看似客观、准确,实则包含了强烈的价值立场和优劣区分。同时,很多学院派的批评方式常常是以理论先入为主,或者是以方法论为主的。这被美国学者詹姆斯•J.索斯诺斯基称为“绞肉机式解读”,也就是用理论范式与方法论解读作为衡量一切作品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批评方式中“任何文本解读都被绞碎成了与之沾边的理论术语”[3]转引自[美]杰弗里•J.威廉斯:《文学制度》,李佳畅、穆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由此,文艺批评就成为维护批评理论话语的神话了。
诚然,随着媒介的日趋融合,有的学者身兼文艺评论家、“网络大V”与“饭圈”粉丝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有些文艺批评文章会被同步发布到线上,学院派文艺批评的“跨界”“破圈”尝试也在不断进行。但是由于其评论话语的专业性和方法论性质,仍然让网民们“不明觉厉”,故而它们在网络空间和数字平台上的影响是有限的,并未真正“出圈”。
2.“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批评
在数字时代的批评场域中,相比于学院派批评,自媒体批评具有平台门槛低、传播速度快、流传范围广、批评内容自由化、传播交互性强等特点,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商业杠杆(如流量、订阅、点赞、打赏等)的影响比较大。自媒体批评通常以策划文艺活动、制造文艺事件、实施营销策略等方式展开媒介批评。因此,这样的文艺批评从形式上来讲,往往短小精悍,语言生动活泼,易于激起阅读者的感性愉悦。网络上曾经有一篇点赞量很高的文案,把小成本文艺影片《隐入尘烟》推上热搜。该影片在短视频平台的持续发酵,引发了一波波新的关注,成为2022年关注度很高的文艺片。这充分体现了自媒体批评对于一部电影的宣传价值和传播影响。这种驳杂的“流量式”批评,一方面使得很多自媒体都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评价体系和话语模式,其阐释密码似乎只有“圈内人”才能解释得清楚,从而形成了一种不断变换的符号内循环;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平台设置内含了商业资本与流量经济的逻辑,点击率、转发量等数据化考量体系使得大众自由评论的独立性很有可能被资本收编,很多文本沦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无形中消解了文本的纯粹性与批评的思想性。
同时,某些自媒体特别擅长“造梗”策略。所谓“梗”,就是某个圈层内的网友所共同熟知的桥段。某些自媒体平台通过创造一系列的评论“新梗”并将其迅速传播到游戏圈、动漫圈和“饭圈”等多个亚文化群体中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自媒体批评往往通过“造梗”来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并由此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流量。此外,很多自媒体批评以感性语言的蒙太奇来制造和煽动网民的情绪,以断章取义的奇观化标题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以各种广告营销来增加阅读量和曝光率。这种文艺评论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普通网民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却由于流量等的需要而过分炒作,从而放弃了文本合理的逻辑分析,而呈现出语言上的跳脱性与碎片化。在此,自媒体批评已经超出了话语层面的意义,而成为网络社交中的一种货币建构形式。
3.“圈地自娱”的“饭圈”批评
如果说粉丝们将大量时间、金钱投入到追星活动中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饭圈”则是追星模式的团队化和体系化。因此可以将“饭圈”视为粉丝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饭圈”成员们往往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他们不仅是偶像的崇拜者,更通过一系列的群体行动(如应援、打榜、控评、反黑、轮博等)成为偶像的养成者。有的“饭圈”选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自娱自乐,并以此实现对主流话语的“抵抗”。
首先,“饭圈”批评从语言上来说,多采用“圈地自萌”和“造梗”的方式,创造独属于自己的行业“黑话”。“饭圈”批评常常由一种挪用的语言符号构成,一方面借用了很多二次元的语言符号,另一方面夹杂着英文缩写、拼音缩写等形式。其次,“饭圈”批评的圈内话语还带有明显的口语化、情绪化和排他性。“饭圈”批评常常是在固定的贴吧或者线上群体中产生的即时性互动,强调交流的具身化和情境化。与学院派的严谨逻辑相比,“饭圈”批评不仅缺乏必要的学理性,而且很多语言组织都违背了拼写的规则或者语法规范,圈外人很难“解码”。同时,“饭圈”批评中还存在一定的语言暴力和排他性。这与粉丝们对某些明星偶像投入过多的情感有关,所以他们的很多批评都具有一定的情绪化特征。再次,“饭圈”的圈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壁垒,交织着潜在的话语斗争与权力的博弈。粉丝们话语权的大小往往与他们的活跃度、发帖数、贡献值等密切相关。有的“饭圈”内部还出现某些圈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于是控评、互撕、屠版、人肉甚至直接删除某些异见者变成了他们的惯用策略。有学者把“饭圈”批评的这种特点称为“自反性”,并认为正是饭圈内部的这种“自反性”,“使得粉丝之间、粉丝与学院派批评家之间真正平等、有效的对话往往仅停留于想象层面”[1]李雷:《粉丝批评的崛起——粉丝文艺批评的形态、策略与抵抗悖论》,《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第93页。。某些不懂圈内规矩的“菜鸟”如果随意发言,还有可能被处以“禁言”的惩戒,甚至被视为“叛徒”而遭到清理,这种局限在特定封闭空间中的“话语仪规”业已成为当前圈层文化批评的重要表征。
(二)“圈层化”:一种话语建构机制的异化
我们知道,随着“法国理论”的发展,“话语”的建构主义大行其道。一般而言,“话语是指涉或者建构某种实践话题的特定的知识生产方式。即一系列的观念、形象和实践,它能够提供人们谈论特定的话题、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制度层面的某种方式和知识形式,并由此实现对人们的价值引导。……所以说,‘话语’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宽泛的术语,主要用来指涉意义、表征和文化所构成的任何路径”。[1]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Sage, 1997, p.6.由此,我们可以说,目前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主要圈层之间,由于主体场域、话语体系、趣味判断、价值诉求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文艺批评中的区隔与鸿沟,导致了公共批评的失语。这种“圈层化”的本质是当前文艺批评话语建构主义的一种异化。
相对于学院派文艺批评而言,自媒体批评和“饭圈”批评所营造的话语热潮虽然干预了文艺的创作,并通过资本和流量的介入影响了大众的接受选择,但是其批评效能一般仅仅止步于线上的评论,而未能在文艺评论的理论大厦中添砖加瓦,更由于其网络圈层语言的排他性而导致很多人尚未有机会认识到其评论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自媒体和“饭圈”本质上都可归入亚文化圈层,很大程度上其立场不是为了“对抗”主流,就是为了和主流分庭抗礼。与此相应,学院派批评却常常迷失在理论的王宫中。所以说,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和认识并非源于他们的观察或者体验,而是源于某种圈层话语的建构。对此,福柯在法兰西公学就职演讲中,详细分析了由“言语惯例”“话语圈”“信仰群体”等所形成的语法规则是如何规训人们的话语形态的,并由此揭橥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权力与知识共生的关系。
但是,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知识的建构关系已经从主体与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性关系,转换为话语对主体的建构性关系。也就是说,批评知识并非源于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而是源于话语和主体之间的建构性关系。说到底,文艺批评不过是话语的产物。这种思想彰显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转换特征——即由表征代替了“在场”。因为“在场”所面对的更多是客观事物的直接性经验,它本来就是表征产生的依据。但是,数字时代的很多批评话语生产机制,其实是用表征对在场的一种征用,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在场”。这些批评话语的建构只能通过各种符号表征出来,但是主体根本无法实现对眼前事物的一种直接的认识与评价,它用表征性的符号取代了对“在场”直接经验的分析与把握,由此隔断了知识、真理与主体的种种现实的物质实践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圈层化”,实际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些文艺批评形态在根本上割裂了观念与物质实践之间的关系。
面对变幻莫测的数字文艺现实,精英文化话语生产范式中的理论先置性判断遭到质疑,文艺批评似乎已经不能、也不再肩负再现真实和道德评判的任务。有的学院派文艺批评话语不仅隔断了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变成了批评的建构主义。而“饭圈”批评和自媒体批评则逐渐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话语场域,这种场域先天的排他性和理论厚度的缺乏使得学院批评与其融合的梦想目前更多呈现在浅表层面。这正是数字时代文艺批评话语建构主义的危机。其实,话语建构主义的主要倾向就是“用话语、差异、他性、去中心化、缺席和不确定性等概念来对抗普遍主义、本原、在场、根基论、神学和元叙事等”[2]Warren Breckman, “Times of Theory: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rench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71, no.3(July 2010), p.340.,拒不承认多元性的理论。因此,目前我们文艺批评“圈层化”的本质是批评话语生成逻辑的建构主义混乱或者说知识生产规则的异化:一方面是消费主义扩张与数字理性的冲击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人文学术研究本身和现实问题的隔膜有关。
换言之,当前文艺批评“圈层化”既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关,也是当前人文学科话语生产机制的体现。特别是有些学院派批评仍然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形势去审视当前的文艺批评现实,不能真正直面文艺发展的现实和批评的实际土壤;而“饭圈”批评和自媒体批评等则在用框定新的游戏规则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由于没有充足的理论支撑,其推广性和普及性也值得推敲。二者本质上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话语建构主义空间中的“圈地自娱”。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当下文艺批评理论“若继续我行我素,回避对公共阅读经验作出有效回应;文学学者们若不能对诗歌与小说有所触动,却只反叛与发表倍感兴奋的话,那么人文学科必将付出被社会不断边缘化的代价”[3]范昀:《批判的限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页。,是时候探索一种新的文艺批评话语生产了。
三、“破圈”之道:一种“新感受力批评”尝试
面对文艺批评话语建构的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固守原有立场、继续坚持“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还是放弃自己的理论阵地,在技术和消费的渗透下,将文艺批评沦为消费主义和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对此,“新感受力批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介入当下文艺评论的现实状况和文艺肌理。
(一)“新感受力批评”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在场性体验
我们知道,“新感受力”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的批评文集《反对阐释》(AgainstInterpretationandOtherEssays)中最早提出来的。当然,与话语生产逻辑不同,“感受力”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要以言语来框定一种感受力,尤其是一种活跃的、旺盛的感受力,人们必须审慎而灵活。”[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但是,难以言说并不代表不可言说。因此,要将“新感受力批评”言说清楚并付诸实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强调的是,桑塔格的“新感受力”思想仅仅是我们理论言说的起点和依据之一,本文所说的“新感受力批评”主要是基于当前数字时代文艺批评话语“圈层化”的现实而作出的一种批评尝试和话语探索。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数字文化是一种生产过剩的文化,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导致了我们感性体验中很多敏锐的感知正逐渐丧失。消费的丰饶与感知的拥挤纠合在一起,并钝化了我们自身的很多功能。正如桑塔格所言:
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现今所有艺术评论的目标,是应该使艺术作品——以及……我们自身的体验——对我们来说更真实,而不是更不真实。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2][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当下数字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痼疾。因此,桑塔格关于“新感受力”的论述至少说明了两点。
其一,“新感受力批评”的目的是淡化理论与概念对评论的作用,倡扬对自我感知的一种重视。“要确立批评家的任务,必须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自身的感知力(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感觉和感知力)的状况。”[3]同上,第16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阅读、更多地批评、更多地反思来直面文本,实现对更多感知的恢复。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观点,我们与其将艺术的激进理解为一种社会批判,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对感觉的更新和生活的丰富,因为“当代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4]同上,第348页。。即使是思想,也是对于感受力形式的思想。“新感受力批评”具有一种对抗“体系硬化症”的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新感受力”并不是对理性阐释的否定,也不是纯粹主观偏爱的领域,而是一种能够对于趣味的生成起到支配性的、具有连贯性的作用的“某种类似趣味逻辑的东西”[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这正是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容易滑向的一个极端,即将“新感受力批评”视为一种日常经验的主观性再现。这种建构主义的批评话语逻辑本质上基于主体对世界的想象,极易沦为主观私欲的产物。所以,我们倡导“新感受力批评”的主要目的,不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和对于文艺作品的个体经验全部恢复过来,而是反对数字时代文艺批评要么无视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的隔靴搔痒;要么无视理论,模糊地将一切都资本化的建构逻辑。重申文艺批评感受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把文艺作品从抽象的理论思考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归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中去,促使其追求一种思想意义上的感知。
其二,“新感受力批评”强调直面文本本身,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在场性”体验。按照桑塔格的阐释,任何类型的文本都具有感受力,但是不同圈层文本的感受力是有差异的。例如,高雅文化中的文本具有一种道德性的感受力;先锋派艺术文本具有一种极具张力性的感受力。坎普是坚持在审美层面上体验世界,而这正是桑塔格所倡扬的“新感受力”。“新感受力”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性,是直面文艺文本的批评。具体来说,“新感受力”说明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的特殊性,是对其形式的一种规定,即直觉的、直观的、当下即得的把握;二是它能够从直接性中获得收获,既包括理论上的新知,也包含体验上的新探索。也就是说,“新感受力”是对某种事物的经验或体验,其最终获得了某种“体验物”。进一步来讲,“新感受力批评”在强调感性经验的基础上,“意在揭示作品的‘感性表面’,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主观概念,而是一种注重感性在审美中回归的社会文化效果。它更新了我们关于作品的意识,赋予了批评更多的纹理”[2]钱烨夫、徐剑:《数字时代粉丝文艺批评的“新感受力”与价值反思——兼与李雷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第113页。。作为一种与文本阅读活动有关的情感体验,“新感受力”以其直接性和敏感度的文艺批评标准,表达了一种批评的普遍性。因此,“新感受力批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知和体验,而是体验与形而上的联系,即如何从感知来规定文艺的形而上学。在这里,“新感受力批评”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艺批评方式,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具有本体论的含义。“新感受力批评”重在重新唤起富有感知的理知。也即是说,开展“新感受力批评”的过程,就是文艺批评家进行理论思考与“在场性”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过程。
因此,“新感受力批评”的关键不在于建立某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指向的话语空间也并非传统的伦理思想空间,而是一种致力于反省经验、强调深入而敏锐的感知状态的批评方式。简言之,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恢复感知、倡扬新感知批评的新契机。反过来也可以说,“新感受力批评”是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发展的未来走向。
(二)“新感受力批评”是一种多元化、开放性的批评视界
桑塔格最初提倡“新感受力”,旨在在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即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它是对既定二元对立批评标准的搁置或“中立”,从最深处瓦解当时“作出区分、排斥异己、设置等级”[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译者卷首语,第7页。的批评圈层的基础。在桑塔格眼中,她之所以要重点强调“新感受力”,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对西方传统文化和经典理论的激进式的怀疑,而是一种基于创造性的积极守护与理性尝试。它试图在高雅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在情感体验与社会评判之间、在理论阐释与文本实践之间架起一座理性交往的桥梁。概言之,“新感受力批评”开启了一种新的、更开放的批评视界。
如前文所论,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存在多样化的批评形态,各种批评形态由于文化立场、身份差异等的区隔造成了批评话语体系的圈层化。而“新感受力批评”则强调批评的“悬置”和价值的“中立”,它的立场和价值评判标准是多元的。具体来说,首先,“新感受力批评”强调历史性与当下性的统一。“它既致力于一种令人苦恼的严肃性,又致力于乐趣、机智和怀旧。”[2]同上,第352页。也就是说,“新感受力批评”是一种开放性的、具有历史意识的批评方式。它并不是只关注于当下的读者反映,而是一种与历史相关的情感体验。[3]关于这一点,曾有学者认为:“桑塔格所强调的感知力是一种与阅读受众的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情感体验,它不是一种历史维度上的情感结构,而是读者当下的反应……”参见钱烨夫、徐剑:《数字时代粉丝文艺批评的“新感受力”与价值反思——兼与李雷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第113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桑塔格的观点。与其说桑塔格的新感受力是对历史的消解与否定,不如说它是一种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因此,“新感受力批评”本身“不是历史化的敌人,而是其有价值的补充物或同盟者”[4][美]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其次,“新感受力批评”强调审美体验与文本阅读的统一。“新感受力批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审美体验的正名,但是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理论概念或者建构思维的彻底否定。“新感受力批评”的宗旨并不是弄清楚文艺作品本身的本质性存在,而是呼吁我们尊重对文本本身的阅读感受和个体的阅读体验,重视文本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和我们自身的切身参与,同时敦促我们客观地正视自己真实的审美反应,将更多的焦点放在文本接受和言说的行为上,而不是文本所言说的内容与实质上。再次,“新感受力批评”体现了理论阐释与批评实践的统一。作为一种直面经验的社会践行,它既不同于某些学院派“重话语轻实践”的问题,也不同于自媒体和“饭圈”文化对抗主流圈层的话语策略,即不能只是靠语言上的圈地自造和话语的对抗,而更主要是付诸经验的实践。它“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这被理解为(新的)活力形式的再现。道德评价的作用在这里并未被否定,只是其范围被改变了;它变得不那么严厉,它在精确性和潜意识力量方面的所获弥补了它在话语明确性方面的损失”[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这充分表明了“新感受力批评”并不排斥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联性,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因而,“新感受力批评”不是在处心积虑地进行术语与概念的新的知识生产,也不是对社会文化现实展开无休止的虚假辩护,而是用理论直面文艺作品的本身。最后,“新感受力批评”倡导一种“共情体验”(emphatic experience),“它可以公平对待不同的审美际遇之间的差别的力量和强烈性,同时不会认同本质主义者对高雅和低俗艺术的二元区分”[2][美]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页。。“新感受力批评”并不是要用大众文化论者的论调去捍卫当下的自媒体批评或者“饭圈”批评,也不是要反对精英主义的阐释性批评,而是想论证尽管二者存在明显的“圈层”与“区隔”,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的情感和感受力认知是值得考量的。它以一种知行合一的姿态,将阐释和评论的权利更多地留给人们对于文本的感受。它充分实现了对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体验与认知等层面的兼收并蓄。据此,“新感受力批评”不但能够改变我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而且改变了文艺对于我们价值与精神世界的内在影响。
以“弹幕”批评闻名的“哔哩哔哩视频网站(B站)”的“破壁”之旅,充分说明了“融合”“跨界”已经成为当前数字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新感受力批评”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精妙,它日益成为后现代主义者们所谓的“微观政治”或“文化抵抗策略”的突破口。恰如罗兰•巴特对于文艺批评的“解神话”(demystification)描述的一样,它“并不等于文化中神话方面的消解,它最好的诠释也不只是拆解神话化程序,设法用清醒的思考来破除迷思”[3][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导读,第2页。。同样地,“新感受力批评”也不是一定要在纯真的审美乌托邦与无限收编的策略的两难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文艺批评圈层边界的打破,并不意味着圈层文化的个性和独立性的丧失,因为真正优秀的批评往往是有“圈”无“壁”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感受力批评”似乎具有现象学美学的影子。按照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理论宗旨,我们的文艺批评应该超越文本的内容和隐藏内涵,更多地直面文本本身,既不依赖已有的理论阐释体系,也不凭空猜测或过度阐释。这种多元开放的姿态,主张将批评的本质指向对文艺作品的感受本身,在此基础上指向孕育作品的社会生活本身。
简言之,“新感受力批评”是一种融合了历史学与现象学、尊重经验批评与阐释批评、倡扬多样化与体验性的新尝试。它既尊重理论的复杂性,也不会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它倡导一种对情感、习惯、体验、理念等多种影响批评效果的关注,倡导跨学科的多元主义,而不是试图把握情感的性质而急于对其进行解释与评判。在面对众多的数字文艺现象的境况下,“新感受力批评”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地避开理论的无休止的建造,而以更直观的姿态直面真实的社会和纯粹的文本。与桑塔格试图调和当时西方“两种文化”的美学初衷类似,数字时代的“新感受力批评”倡导的是个人同周围现实环境之间的沉浸式体验关系,人们常常由这种关系来感知和想象世界,并在意识形态中识别出自我与他者。因此,这种“新感受力批评”不再是个人化的呐喊,而是一种基于多元批评语境下的必然选择,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整体化生活方式。这正是“新感受力批评”在数字时代所践行的审美原则。
四、结语
“圈层化”不仅是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主要趋势。实际上,文艺批评“圈层化”的本质是批评话语生成逻辑的异化,是一种话语建构主义的迷思。目前“学术圈”“自媒体圈”和“饭圈”等圈层共同构建了数字文艺批评的生态地图,其中每个圈层都建构了一套只有圈内人才能破译的话语“批评密码”。文艺批评要么成为“神学的置换性片段”,要么成为以“流量杠杆”为标准的消费意识形态,要么成为粉丝们“圈地自娱”的情绪宣泄。在“人人都是批评家”的“狂欢式”批评背后隐藏着“圈层化”危机,造成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有限性融通和公共批评的丧失。由此可见,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无论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绞肉机式”的阐释话语,还是商业资本与消费合流制造的“轻文明”假象,无论是理论大于实践、口号大于行动,还是流量重于思想、表层漫过深度,它们都是数字时代学术产业化、话语建构性的结果。
这种融媒体的话语批评现状,不仅改变了当前的文艺批评场域,也催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让文艺批评真正介入文艺现实,如何真正有效地对公共批评和公共生活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依然是当下文艺批评亟待思考与践行的紧迫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加强积极的正面引导,“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13页。。基于此,只有在对“圈层化”问题进行充分反思的基础上,才能重建文艺批评的常识感与现实性,真正有效的公共文艺批评实践才能成为可能。在此,“新感受力批评”可以视为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一种自我革命。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数字时代恢复感知批评的新契机,也为未来文艺批评的发展方向探索了一条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