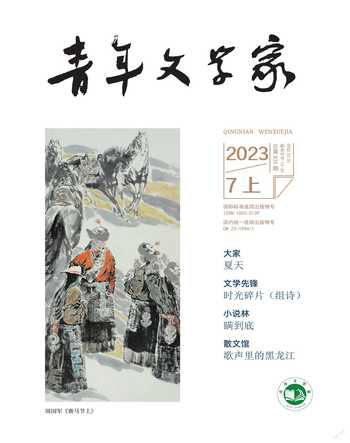自由而无用
2023-09-01陈霞
陈霞
现代社会所谓的进步并没有带来人类整体幸福感的提升,反而越来越使人陷入恶性竞争的死循环,对人生价值评判的单一性给现代人的心理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直至把人逼向崩溃边缘。如果不能建立主动隔离于标签化成功学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之外的专属个人的独立价值观,人就永远不可能摆脱被异化、被规定、被操纵的命运。人就只能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体系内的传送带,利益链条上的棋子。
工具理性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主要含义是人的行为动机主要是被对功利的追求所驱使,其极端化将使手段成为目的,造成对人的异化和物化。
有没有人曾经深刻反思过人类这种自相残杀的行为,有没有人曾经试图逃离过“内卷化”社会的残酷压迫,寻找到人类本应有的自由存在状态?有,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陶渊明。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然而,要做到陶渊明的选择,却不那么容易。此外,要说“真个不要”,佛教徒的“出家”是最干脆利索的途径,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有没有“即世间”,同时却也“出世间”的解决方案?不像儒家那么恳切地积极入世,也不像佛教那么决绝地出世,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有,而且其思想对今天处于“内卷化”愈演愈烈之水深火热境况中的人们是一剂难得的救世良方。这个人,就是庄子。这条路,就是庄子的“游心于世”的路。在当代社会如何重拾人的尊严,如何避免人被工具化,是今天研读庄子的重要意义之一。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那是一个诸侯混战、朝不保夕的时代。庄子处于这样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如何保全自身,进而保持精神自由,避免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就成为庄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指向。
庄子是怎么应对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呢?为了找到有力证据,需要从《逍遥游》开始,对内七篇进行详细考察。
一、《逍遥游》
此篇借许由之口指出“予无所用天下为”的避世态度,对外事、外物冷眼旁观,绝不允许自己沦落为统治阶级的利用工具。而且用“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进一步形象说明之。后来,司马迁说庄子是“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是从庄子拒绝被利用这个角度说的。结尾处又用大樗树的寓言从反面提出要避免像狸狌那样“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的悲惨下场,庄子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对那些“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富贵功名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了警告。反观儒家的价值观,《论语》中记载,孔子感叹“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渴望把自己卖出去,就是后人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生怕自己不被利用,认为只有被利用了,人生才有价值有意义。孔子周游列国,最终也没有找到肯任用自己的地方。儒道两家的境界,真是云泥之判。
二、《齐物论》
“内卷化”社会人们的典型状态是什么?“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小恐惴惴,大恐缦缦”“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这番“内卷化”社会中人们孜孜以求却最终“异化”成为自己追求目标的奴隶的描写,让几千年之后的人读来,也依然有脊背发凉的感觉。几千年来,社会的物化形态尽管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人类从战胜大自然到以邻为壑的“内卷化”斗争的残酷,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呈愈加激烈的趋势。庄子提出要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为深陷红尘纠葛中的人类提出了上升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月亮”和“六便士”的纠结所在。可是,为生计奔波的芸芸众生,有几人能有心境上的余裕,可以抬头看月亮,可以从小我中自我提升到天地的高度?庄子自己也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庄子·大宗师》),有限的资源,单是生存下去已经榨干了大多数人的全部心力和体力,“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更何况有多少人不是不愿意如动物般为衣食所驱使,而是世界根本就没有给他们脱离动物本能,往更高的“人性”和“灵性”爬升的机会。有幸生活在资源较优越环境中的人,会为了保住资源,并进一步占有更多资源而倾尽全力,也少有能够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转而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质量。人类就是这样可怜,或者局限于物质,或者局限于人性本来的贪婪。庄子也生活困窘,只当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常以卖草鞋为生,却能够在沟渠中抬头,仰望更高的实在,问世间能有几人哉!《齐物论》以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结尾,正是指明了逃离“内卷化”世界获得的最高奖赏—物我两忘,诗意栖居。
三、《养生主》
怎样才能做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是每一个生存于世间的人必须经历的考验,每一项都不那么容易做到,庄子提出的建议是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关于第三条“缘督以为经”,王夫之的解释是:“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者也。缘督者,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庄子解》)这个后来就被纳入到道家的养生修行中了,倾向于技术层面。难的是前两条。“为善无近名”,也好理解,民间的通俗解释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做慈善,也容易被人泼污水。做善事也必须低调行事,为了博取名声而做善事,初心就错,何况后面还有极其复杂的人情世态需要应对。有意思的是,庄子居然说“为恶无近刑”,而不是像后来刘备教导的那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遗诏敕后主》)。难道庄子是说可以作惡,只是要注意别触犯刑法?应该不是,这里应该是把“近刑”作为“近名”的对待之语,名声一旦成为目标,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跟刑罚也差不多了。此篇里有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但对处于“内卷化”社会中身心俱困的人而言,最后一个“秦失吊老聃”的故事可能更有启发意义。其点睛之笔“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对心理疾病频发,自嘲“不敢崩溃”的现代人也是一剂良药。“内卷化”的机器碾压过来,无法逃脱的人都被压成单面的工具性的纸片人,再也不能具有丰富的、全面的、立体的人格魅力。激烈对抗,也许只能面临以卵击石的灾难后果。庄子教导人类努力开拓内在心理空间,接受个人暂时无法改变的现实世界,让自己先平静下来,在顺应中寻找摆脱的机会。人一旦要是成为自己情绪的奴隶,就几乎无法客观且理性地看待自身和外部世界了,不等外部世界来碾压自己,内在的负面情绪就会让人体系统崩溃。这一点不但古人早已了解,也一再被现代心理医学所证实。对外要“安时而处顺”,对内要筑牢心理防范的围墙,内心留出一片清静之地。“哀乐不能入”,这片清静之地是一个人私密的心灵花园,可以绚烂,也可以空寂,其无穷的能量可以让一个人先稳住自己,再从容应对世界。
四、《人间世》
王夫之评此篇:“为涉乱世以自全之妙术,君子深有取焉。”(《庄子解》)确实如此,内七篇中,《人间世》对人世险恶的描述是最惊心动魄的,给出的乱世中求生存的建议也是最切中肯綮的。南怀瑾说:“庄子所说的人间世,就是如何以出世之道,转而逍遥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南怀瑾讲〈庄子〉》)
颜回想去匡救卫国,动机非常伟大,“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也是儒家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经世济民思想的体现。但孔子警告他:“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接下来,在师徒讨论中,孔子详细解说了君人之心、世人之心之险恶,最后归结到“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上。
此篇教育意义最大的是“栎社树”的寓言。栎社树就因为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才得以躲过斧斤之祸,成其大,成其寿。栎社树托梦给匠石,说其他各类果树,“以其能苦其生”,是“自掊击于世俗者也”。且直接宣称自己的全部生存经验就是“无所可用”,并讽刺匠石是“几死之散人”,哪有资格批判此树为“散木”!后来,匠石的弟子问师傅,如果此树有志于“无用”,为什么还要做社树,这岂不是也是某种“用”?这时匠石的回答就是《人间世》顶级的智慧了:“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也就是说,彻底无用也不是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彻底无用就不会有任何存在价值,还是难免被清除的命运,必须还有点用处,这个用处既可以免于其他有用的果树“实熟则剥,剥则辱”的悲惨命运,又能够因此一点利用价值被允许存活下来。这就是最高难度的生存智慧了!不能有用,也不能无用,而是在有用、无用之间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点,安顿身心。南怀瑾的告诫是“人生啊,你有用也倒霉,没有用更倒霉;要做到好像有用,又好像没用,才是没有用的大用”(南怀瑾《庄子諵譁》)。后面又有商丘之木和支离疏的故事作为补充,“栎社之树有托,处富贵之善者;商丘之木、支离,处贫贱之善者也”(钱穆《庄子纂笺》)。三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一个道理,就是在一个“仅免刑焉”的世道如何自保。
终篇之语,“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何其沉痛,境界之高,世间又有几人能懂?
五、《德充符》
此篇有一句道出了庄子的核心思想之天命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故意列举各类型残而才全之人,点出如何才能应对自身的缺陷和世界的不完美:“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王安石在《答陈柅书》中评价道:“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内卷化”社会的整体性内耗、毁灭性竞争、自杀式进取,不过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不过是功名利禄而已,庄子把死生存亡都算进去了,这些比起生死来又算得了什么?逃离“内卷化”社会,拒绝加入争夺大军,必须从价值观上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彻底摒弃这种社会通行的世俗评价体系,用所谓的成功来给个人做标签的价值评判标准。只有建立了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体系,才能把“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排除在外,不允许它们进入内在清静之地。先做到摒弃世俗评价体系,进而参透生死,那才能不被外界裹挟,达到内心真正的平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无限接近道的境界。对于普通人而言,对自己的要求不必像庄子那么高,能够参透“死生之外,都是小事”已经殊为不易了。
六、《大宗师》
此篇再次重申了庄子的安命论:“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同时,宣称要“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最后,提出用“坐忘”的方式达到“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境界。俗世间人,匆匆忙忙,不过图碎银几两,过富贵关已然难上加难,何况要求大家参透生死关?庄子这个境界,就是修道人也很难达到。《大宗师》篇,对于普通人,也就是看看罢了,不能强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经典论点也出现在此篇中,并且两次出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不管是不是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是错简原因,这份看待生死的达观态度,确实是只有道家,只有庄子才能达到的高度。要想真正逃离“内卷化”社会,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甚至摆脱生之困境,一切物质性“有待”条件的困境,必须走修行之路。就算在“内卷”中最后胜出,成为所谓的“卷王”,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互相争斗、抢夺算计的圈子只会越来越大,永无尽头。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如果一味外求,只会最终把自己的全部心力耗尽,直到油尽灯枯,被榨干最后一滴血。大多数人也会在人到中年时,逐步看透世相,逐步跟自己和解,跟世界和解,也由于个人体力和心力的逐年下降,而最终选择终止战争。很多人经过年轻时代的“卷”与“被卷”,也差不多争取到了社会公认的普遍的“成功”标签,可以“金盆洗手”了。新一代成长起来,杀进“屠宰场”中,故事又在新的人群中继续。道家不关心全体人类的拯救问题,所以这样轮回中生死浮沉的人类到底值不值得拯救,以及最后能不能得救等问题,道家没有丝毫论述。道家是思想派,不是宗教家。这也是道家跟道教的根本差异。
七、《应帝王》
郭象对此篇篇名的解释是:“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王夫之的解释是:“‘应者,物适至而我应之也。”王夫之的解释显然更符合文意。此篇最后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才是应付外在世界最高级的手段!“用心若镜”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卷”也罢,“不卷”也罢,应该把心修炼到镜子的境界—物来则应,物去不留,外界的一切在自己的内心留不下丝毫痕迹。真正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当哭则哭,当乐则乐,事过了无痕。身段极其柔软,韧性灵活性极其强大。有能力在外界与内心设置一道距离感,能够从自身分出另一个自我,用慈悲的眼神看着这一个暂时寄居于此世的我。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身忙而心闲。大多数人对“内卷化”社会感到身心疲惫,主要是心理空间被严重挤压,先从内部崩塌,心理疾病引发身体疾病,从而内外交困,整个人沦为工具理性社会的牺牲品。
以上是内七篇中庄子对现代人如何逃离并超越“内卷化”社会的超越时空的谆谆教导,有一些比较容易做到,有一些却令人望洋兴叹。
从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外在形态、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可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人类心灵所面临的问题亘古如新,人的“异化”问题随着社会的演变呈愈演愈烈之势。论物质生活条件,古人可能根本无法望今人之项背;论反抗“异化”,逃离“内卷”的勇气和力量,今人可能必须回到古人那里汲取精神上的养料。
庄子在他的时代,就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他面对权势时的傲岸风骨,面对死生时的乐天达观,对汲汲于富贵者的讥讽嘲弄,对超越俗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汪洋恣肆的笔法,瑰奇无双的想象力,都使他成为古往今来多少不甘沉沦者的精神导师。面对现代社会机器对人的尊严和精神的压榨,人类要想自我拯救,庄子的思想依然是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社會上多一个人读《庄子》,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一个人多读一遍《庄子》,精神就多上一层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