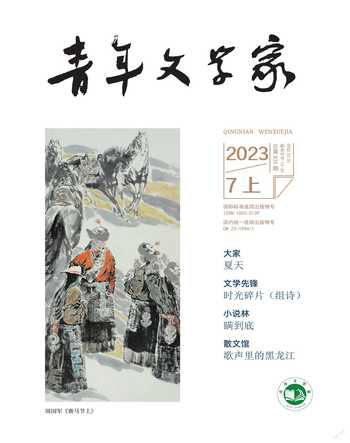论元代诗歌与民歌的关系
2023-09-01靖然
靖然
元代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这一时期诗文作品数量庞大,作家人数众多、地位显赫。虽然元诗一直不如元曲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但是从元代的文学生态来讲,元诗在元代文坛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李维在《诗史》中这样评价元代诗歌的艺术成就:“迨至末季,杨维桢倡霸于越,倪瓒为之羽翼,倡比兴风谕之旨于乐府古诗,一时诗名,无出其右,悠悠末运,独能以诗振一代之势……则元代大家,当以此老为冠。”乐府古诗最早是民歌的文字记录,李维认为杨维桢模仿乐府古诗进行创作,成就突出,可以被称为元代诗人之冠。后代评价元代诗歌成就时,也常常以杨维桢为中心展开讨论。杨维桢的诗歌在元代诗歌中极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也将从杨维桢的诗歌入手,分析元代诗歌与不同时期民歌的关系。
中国的诗歌最早来源于各地的民歌,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总集,搜集整理了我国先秦时代的民歌;汉代乐府搜集汉代各地民歌编成《乐府诗集》,“乐府诗”便由此演化而来。虽然后期诗歌与民歌开始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两者之间始终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元代前期和中期的诗歌受到时代更迭和“理学”的影响,前期南北各异,呈现出很大不同;中期社会趋于稳定,理学所倡导的“雅正”诗风逐渐成为诗坛主流。而元代后期因政权不稳,政治上的动乱动摇了“理学”的统治地位,所以各个诗派发扬个性,呈现出了纷繁多样的特点。杨维桢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风格多变、博采众长,深受乐府民歌和当世诗歌的影响,在体制、内容、创作主张等方面,都和民歌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时代背景
元代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做官入仕不再是人民过上优越生活的唯一途径,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元末,随着政治的分崩离析,诗歌创作也逐渐摆脱了“理学”的束缚,一改元代中期对“雅正”诗风的追求,转而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思想。尤其是杨维桢所在的吴地,繁荣的经济使市民表现出对饮食服饰和各种娱乐活动的热爱。这既是一种自然人性的抒发,某种程度上符合民歌的风格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诗人的诗歌创作。
整体而言,元代社会市民阶层的兴起使诗歌与市井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而民众的生活和所思所想又恰恰是民歌反映的主题之一。这一现象的出现:一部分是诗人受到经济因素的驱动,为迎合富贾权贵,投其所好;还有一部分则是出于自身创作的需要,由于生活比较安定、富足,没有强烈的情感和深沉的感触需要抒发,因此从身边取材,丰富创作,着力观察市井生活和自然风物。
杨维桢就是第二类诗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培养了他直率任性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使他有足够的闲暇发展个性,在创作中展现真实的自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创造的“铁崖乐府”。杨维桢受当时“宗唐”思想的影响,风格上模仿李白的浪漫雄奇和李贺的奇崛诡谲,以古乐府的形式表达自己独特的个性追求。笔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乐府民歌在元末新的发展。
二、杨维桢诗歌在手法和内容上与民歌的关系
杨维桢的诗歌中有两类诗与民歌关系较大:一类是竹枝词,这类诗一方面师承自刘禹锡的乐府诗歌,另一方面来源于元人对古代“采诗”制度的模仿,学习当时的民歌进行创作,表现出元代社会生活的活力;还有一类是铁崖乐府,这类作品主要模仿古代的乐府民歌,邹志方在《杨维桢诗集》的前言中评价“铁崖乐府风格多样,有的幽艳奇诡,隐含汉乐府的情调;有的柔媚旖旎,具有南朝民歌的风味……”表现出作者在模仿的基础上也产生了灵活多变的独特创作风格。
(一)竹枝词与民歌
竹枝词最早来源于巴蜀、川渝一带的民歌,唐代的刘禹锡将当地民歌与文人创作相结合,形成了既具有文人风格又具有民间色彩的竹枝词。此后,唐代的白居易、皇甫松,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进行过竹枝词的创作。到了元代,竹枝词创作主要集中在西湖地区,以杨维桢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将当时杭州地区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创作的两百多首竹枝词编辑整理成了《西湖竹枝词集》,自己也创作了著名的《西湖竹枝词九首》。
杨维桢的《竹枝词》在内容和写作手法上都与民歌有所关联,这一点在李欣怡的《民歌的文学化—论元代竹枝词》,以及万志全、万丽婷的《元代竹枝词的民俗文化与民歌色彩探究》中,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解读。
首先在内容上,竹枝词和民歌都以歌咏爱情和风物为主,同时也有少量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据统计,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九首》中有半数以上都是描写爱情的作品。例如,第九首中的“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浙江潮信有時失,臂上守宫无日消”,就描绘了一个思妇苦苦思念爱人,期盼爱人归来的场景。第四首中的“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则提到了西湖的风物景色。而其《海乡竹枝词四首》是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将视线聚焦于盐民的苦难生活。第一首,“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描绘了盐女在盐地上辛勤劳作的画面,表现出对盐民艰苦生活的同情和对官府剥削的强烈不满。
竹枝词虽然来源于民歌,但并不能完整表现出当时民歌的全貌。吴国富和晏选军在《元诗的宗唐与新变》一书中提到,竹枝词中多描写爱情和风物,是因为元代诗人在模仿古人“采诗”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民歌主题的局限,只选取了当时相同主题的民歌进行学习和模仿,这与唐朝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情况差不多。因此,竹枝词既是对当时部分民歌的模仿,也有对古代民歌主题的继承。
其次在手法上,一方面,竹枝词大多学习民歌的特点,运用白描、比兴等手法,反映百姓的生存智慧。如《西湖竹枝词九首》其五:“湖口楼船湖日阴,湖中断桥湖水深。楼船无柁是郎意,断桥有柱是侬心。”开头描写湖上景物,实际上是以此起兴,为后文用楼船比喻郎意,用断桥比喻侬心作铺垫。另一方面,创作中不避讳使用重复的词句,甚至还会在诗中使用方言或者俚语,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表现出明显的口语化特点。例如,“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使用江浙地区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侬”,以第一人称视角直抒胸臆,表现出对艰苦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词口语化,通俗亲切。
据研究,竹枝词产生于诗人对民歌的模仿,而在创作完成之后也会再交由民间进行传唱,做到了诗歌与民歌、文人与民间的相互融合。
(二)铁崖乐府与民歌
杨维桢的诗歌创作以其“铁崖乐府”最为著名。与模仿当时民歌进行创作、反映当时民间生活的竹枝词不同,铁崖乐府是杨维桢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模仿古代乐府民歌创作的作品。铁崖乐府的创作主要受到了“宗唐复古”思潮的影响,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诗人创作风格的熏陶,因此灵活多变,奇艳诡谲。体现出杨维桢独树一帜、与时人不同的创作特点。
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形式上,铁崖乐府模仿乐府古体诗创作的形式,比较自由,不拘格律,因此也能较好地表现出杨维桢独特的艺术审美;内容上,铁崖乐府继承了汉代乐府“缘事而发”“讽喻现实”的传统,试图在乐府中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百态,既表现出了对社会黑暗面的抨击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关怀,也表现出了对符合传统礼教观念人物的赞美。例如,《履霜操》一诗通过描绘小儿露宿田野,以荷叶为衣、以葶花为食的生存状况,表现出对底层人民食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的同情;《独禄篇》则通过描写矮小的孝子凭借过人的勇力成功战胜仇人,表现出对替父报仇的孝子的赞美。
但是,铁崖乐府对乐府民歌的模仿是一种不完全的模仿。汉代乐府民歌有明显的叙事特点,描摹人物形象,展现社会人生。而在后代对汉乐府的继承中,受社会思潮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其内容逐渐由表现社会现实转变为抒发个体价值,逐渐由叙事写人转向抒情和表现诗人自身。这一对乐府诗主题的转变早在“建安七子”时期就开始出现,只有如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少数作品还保留了叙事的传统。
铁崖乐府也没能摆脱前代的影响,对乐府的模仿依然忽视了其叙事传统,转而重视对个人、个性的抒发。同时,铁崖乐府注重对唐代“二李”风格的模仿,“二李”的风格主要体现在抒发个人独特的情感而不是叙事。因此,铁崖乐府的叙事也难以真正学习到乐府民歌展现社会人生的精髓。铁崖乐府中的《望洞庭》《五湖游》《石桥篇》等等都有对“二李”明显的模仿,表现出丰富奇幻的想象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叙写描绘。
再者,虽然杨维桢在诗歌作品中有注意到人物描写的方面,但他的描写是一种对古乐府机械的模仿。因此,描写对象主要是古人,如《春申君》《吴钩行》《平原君》等诗,有咏史诗借古抒怀的意味,却忽视了对现实社会众生的反映。少数描写现实人物的诗歌也主要是借人物抒发个人情怀或对政治人物的赞美,缺少古代民歌的鲜活和灵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其竹枝词的创作虽然个性风格上不如铁崖乐府明显,却更加真实、活泼,也更具有感染力。
三、杨维桢诗歌创作主张与民歌的关系
杨维桢的诗歌提倡“情性说”,这也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主张。他在《吴复诗录序》中提到“古者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其学之成也尚己。故其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也”,这里的“山出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就是指诗歌中要真实反映个人情感,表达自己的天性。在诗歌内容和格式的关系上,他提倡“先情性后体格”,体格要为情性服务,内容大于形式,不拘泥于格律的要求,不受“四声八病”等诗歌理论的束缚,与情感真挚、体式自由的民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情性”一词最早来源于《诗经》的《毛诗序》,“情性”理论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乐府民歌。元代的张宪曾在《玉笥集叙》中这样评价古乐府:“古乐府,雅之流,风之派也,情性近也。”杨维桢也认为古乐府与创作者的“情性”相贴近,不同于当时无病呻吟的“公卿大夫”诗歌,是一种正确的诗歌创作方式。因此,效仿古乐府的“铁崖乐府”,便是他“情性说”艺术理论的主要实践形式。
不过,随着朝代的更迭,“情性”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汉魏时期,“情性”原本是指“社会性情”,即讽喻社会现实,表达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开始转为对个人内心的关注;而后经过齐梁、唐宋的变化发展,“情性”的含义逐渐由关注社会性情转变为关注个人内心。杨维桢此处的“情”指的是个人产生的情感,其中,包括个人因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种种情感;“性”指的是人的天性。因此,他的性情说师承乐府民歌,既继承了汉乐府关注社会、教化美刺的功能,又受到后代对“情性”理解的影响,着意展现个人独特的天性和内心情感,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追求。
如《淇寡妇》一诗,写一个洁身自好的寡妇被强盗玷污之后,由周圍妇女的模范变成了被周围妇女所不齿的对象的故事,既如实反映出当时社会寡妇的弱势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表现出作者对寡妇的同情,抒发了个人的所思所想。
关注社会和关注内心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杨维桢在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中表达出自己内心对社会和黎民百姓的关切,以及独特的个人体验。因此,“情性说”也可以看作是杨维桢对古代乐府民歌关注现实、抒发个性传统的继承和新的发展。
杨维桢作为元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其诗歌与民歌之间的关系密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诗歌与民歌的关系。一方面,他的《竹枝词》反映社会现实,生动活泼,体现出当时诗歌有从民歌中借鉴和学习;另一方面,他也试图直接从乐府民歌中提取古代民歌的精华,并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虽然他对民歌的模仿在内容和手法等方面还比较狭隘,没有完全学习民歌的特点,但是这也反映出元代诗歌与民歌之间的普遍问题。而其对乐府民歌的模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代乐府诗歌的影响,体现出乐府民歌在多个朝代流变的结果:忽视了汉乐府的叙事传统,重视表现个人的思想情感,对人物的叙写集中在对古人和政治人物的歌颂,比较机械。
杨维桢在创作上主张“性情说”,“情性”在元代一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诗歌理论。杨维桢的“情性”理论也可以溯源至乐府民歌,在传统民歌的风格基础上既进行了综合性总结,又进行了个性化发展。
除了诗歌及其理论对前代和当代民歌有继承和发展,他模仿乐府民歌创作的“铁崖乐府”,不仅在元末诗坛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也影响到了明清的诗文和诗歌理论,具有先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