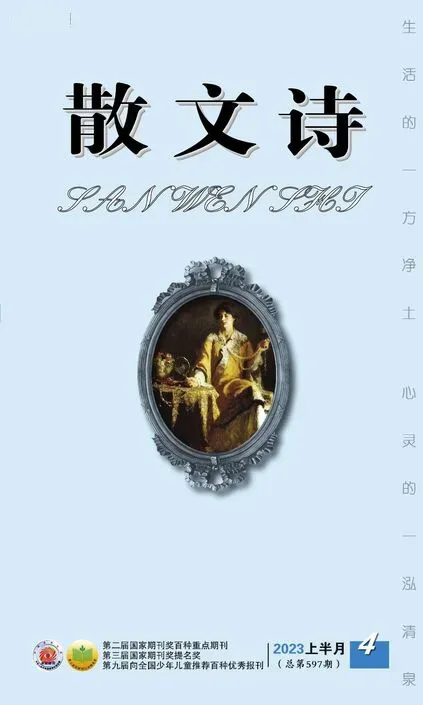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论崔国发《撒播的印记》
2023-09-01◎茱萸
◎茱 萸
初读崔国发的《撒播的印记》组章,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那章《撒播》。从表面上看, 它涉及的主题无非是农事, 囊括的元素或提及的物象无非是土地、时令与作物, 但作者于其中添加了一些颇具抽象色彩的词, 如创造力、意义、语境、隐喻,它们连缀起了这首表面上以典型农事诗(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诗歌的一大类型)面貌出现的诗中的具象元素, 使得整章散文诗不止具备“生活中的真实与朴素”, 还拥有很强的沉思与玄想的气质,甚至关联了作者对写作这种持续性精神劳作本身的理解。换句话说,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 它或许可被视为一种“言诗的诗”(该概念出自德语Poetologische Lyrik)的变体, 如桑德拉·波特(Sandra Pott)论及诺瓦利斯到里尔克的德国浪漫派以来的“言诗的诗”谱系时所言, 这类诗 “通过将文本理论道出并应用于自身”, 从而最终“指向了自身”。
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1941—)有首极短的诗《爱荷华,一月》, 大概作于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驻留时, 收录于诗集《时间与物质》(2007), 内容只有两行:“冬夜漫漫, 庄稼汉梦狭难熟。/左翻右覆, 又进入犁沟。”一位毕生从事文学创作和高等教育工作的诗人、教授, 如何以庄稼汉自况? 就如同崔国发, 或许早年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 但早已不在农耕一线, 他写撒播与收割、稻菽与小蔬、“棉花、玉米、高粱和谷物”及“绿油油的麦浪”,要么是偶然旁观或体验农事劳作, 要么是在象征层面使用它们的语义, “一辈子的耕作都殚精竭虑”难道会是实指对农事的躬亲吗? 就好比哈斯这两行诗, 不过是基于对这个经典比喻的一种诗意的扩充或转喻, 即, 将作家在稿纸的空白格上的劳作, 形容成农人于田垄犁沟间的耕耘与撒播:诗人在漫长冬夜里失眠, 翻来覆去无法睡熟, 干脆披衣起床至桌前, 如农人惦记着在田间的种植与收成一般, 奋笔疾书, 遣此寒夜——这个比喻质朴、诚恳而又稍显老派, 却是一名资深诗人对精神劳作个中甘苦的夫子自道, 是对犁耕松土、撒播种子等农业文明特征的体认和转化。
但要严格地说, 《撒播》又不是“言诗的诗”, 可能也不够称其为盛行于现代性写作风潮中的“元诗”(meta-poetry)。它更接近于陶渊明或谢默斯·希尼那一路的农事诗, 经验直陈与头脑思辨偕行, 天人感通和反躬自省并作, 既有极为朴素的风貌形绘, 又有精神世界的向内挖掘与自阐。前述哈斯的两行诗, 使人想到希尼《耕耘》的诗题和主旨, 又似在向它的开头两行与诗的主体内容间的互文关系致敬:“食指与拇指之间静静地/躺着短粗的钢笔;像握着一把雅致的枪。”崔国发的“一辈子的耕作都殚精竭虑”,则仿佛是陶渊明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 “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一联所呈现的作者心声的悠长回响。农事的种种特征, 犁耕与撒播, 呵护与收割, 关联了沧桑世事, 又寄寓着作者的浩茫心事, 至于这撒播与收割留下的点点印记, 对于以笔为犁的诗人来说, 则又不止于一季一岁的收成与 “丰衣足食”,还有一章章别有怀抱、别具深情的诗篇。
我在众多植物(不止是农作物)中看到了崔国发的怀抱与深情, 比如“拥有更真切的年轮”的树, “在暗中深藏已久”而“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的笋, 在雨中帘外“扇形的展开”的一叶芭蕉,“高洁与隐逸”的菊花,“在幻梦的尾翼上飘着”的黄叶……凡此种种, 无非循着“托物言志”的传统路径款款而行, 但又掺杂了哲思与议论, 叙议结合, 节奏协畅, 自有一番别致的风韵。
除植物而外, 他又注目于自然界固有的或经人力而生成的种种现象, 比如给予我们“温馨提示”的月光、荒野上“如风雷一样激荡的风暴”, 宛如“银白色的精灵”却又“锋芒毕露”的闪电, “在金色的闪烁里嵌入白昼的可能性”的一盏盏晚灯, 有“一具高尚的头颅”的“思想者”雕塑, 在锤子击打下深入“过于封闭的木头”的钉子, “沧桑而悠远”的晚钟, 化身为“今世的淙淙溪流”而“冰释一腔幽怨”的残雪……诗人在这些事物里窥见了造化的宏大秘密, 但它们的垂教, 常常以幽微玄妙的细节和喁喁喈喈的低语的方式呈现, 而不是明示。这种垂教, 是一种思想的柔术, “柔弱者生之徒”式的领悟, 犹如水给予人类的启迪一般。当然, 崔国发常常写到水, 如《水的极速版》《聚龙泉》《长白山天池》, 无一不与提供柔弱示教却蕴含无限奥秘的水有关。在这三章散文诗里, 作者写了很多具体的景象, 但写景与对自然界的文字素描并不是他的旨归, 在其中找到并揭示超拔于自然和世俗的妙谛, 才是这一类写作的意义所在。
但大道多歧, 妙谛何在? 倘若要在崔国发这组诗篇中找到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 那么, 《入门课》《编织术》《野牛阵》三章散文诗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气质, 以及它们的标题所能提供的隐喻和象征意味, 可能是合适的。笼统地说, “入门课”是问道的准备,“编织术”是技艺的锤炼, “野牛阵”则是“所向披靡”的践行和验证。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 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家的如水之柔,可能还需要添加一些儒、佛两家的“自强不息”与“勇猛精进”。就崔国发散文诗写作所呈现出的独特气息而言, 以我此前虽则有限、却多少得以“管中窥豹”的阅读, 结合这一组作品中呈现的气象与风致来看, 他是一位“柔术”与“猛劲”兼具的诗人。
回过头来, 想专门再说一说《笋》这章散文诗。笋和箨, 作为诗咏的对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商隐的七律《初食笋呈座中》和五律《自喜》。较之《初食笋呈座中》以笋喻意气风发, 却对前途不无担忧、渴盼前辈鼓励的青年俊才, 崔作里的笋意象, 形容的无疑是一种更加爽朗而乐观的类型, 有“温暖”与“活力”, 有“梦与远方”。《自喜》中说的“绿筠遗粉箨”指向笋终蜕变成竹的跌宕自喜;而在崔作里“分化与解构”的笋与箨, 则长成了生生不息、虚心有节的心安理得。三章散文诗如此一番对读、参证下来, 倒也颇有“从里向外地打开”的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