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的“边界”
2023-08-31农文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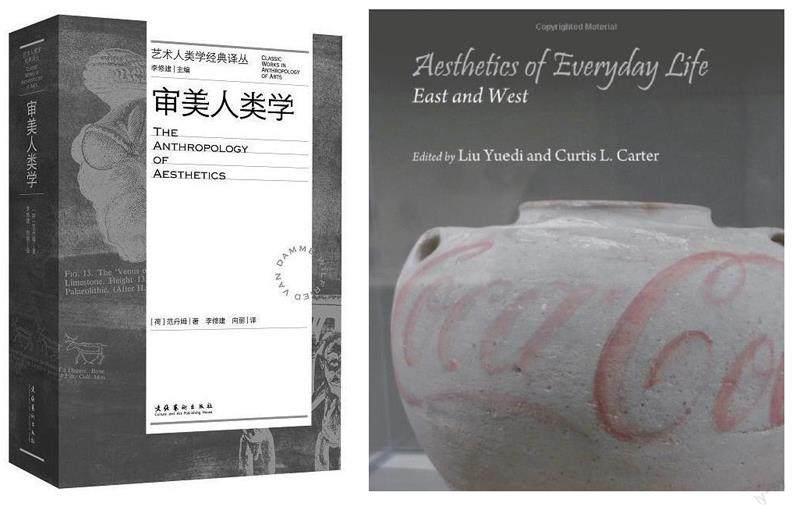
摘 要: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作为不同的美学话语形态,以打破美学与日常生活边界的相同方式拓展美学研究领域,共同昭示美学研究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固守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已然不可取,边界的全然破除却有可能使美学沦为日常生活的附庸而丧失学科品性。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一方面以日常生活作为美学研究的生长点,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维持灵活的界线。“内在超越”本质上关联着美学与日常生活边界的破除和重建,它意味着美学研究不再寻求外在于日常生活的乌托邦式超越,而坚守内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是对美学走向日常生活与保持自觉独立的双重回应。
关键词:审美人类学;日常生活美学;美学边界;内在超越
美学边界向日常生活的扩张是当代美学的显著特征,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在这一层面具有共性并显示出可对话性。作为美学研究“生活转向”背景中的不同美学话语形态,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的差异不容忽视。从外延上看,审美人类学是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指明了学科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領域,而日常生活美学的指涉性较难把握。后者或可指涉以列斐伏尔、斋藤百合子为代表的国外日常生活美学研究与国内“生活美学”的理论沉思,也可涵盖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及其隐含的美学走向。从“日常生活”的内涵来看,审美人类学的日常生活研究尽管并不忽视消费化、娱乐化的后工业日常经验,但更重视少数民族、偏远地域的地方性文化内涵,日常生活美学则倾向于大众化、世俗化、主流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但是,以美学边界的扩张而言,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共同面临着破除边界与持守边界的矛盾,即如何在走向日常生活研究的同时保持美学自身的学科品性?“边界”的问题与“审美超越性”在此杂糅一处而亟需廓清。
一、审美人类学破除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
日常生活在审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可谓举足轻重,大体表现为:审美人类学从日常生活的物质经验中寻求学理依据,并且将日常生活用以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从美学的角度看,审美人类学在“当代美学危机”[1]139所生发的反思经验与研究契机中获取学理依据。审美人类学的倡导者将美学危机归结为理论框架挪移产生的语境冲突,问题的反思与求解也就意味着将“中国美学的理论根基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1]141,这一经验层次指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乡约民俗。因而,审美人类学对日常生活的接纳是势所必然。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求实精神不啻为对西方传统美学抽象思辨精神的有力反拨,将形而上的学术研究方式转向形而下的具体层面也就成为审美人类学的学科品性。因而,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具有天然的亲缘性,对日常生活的接纳也就顺其自然。即是说,审美人类学的日常生活倾向并不造成异议,日常生活与美学研究之间似乎不再留存泾渭分明的边界。
对审美人类学而言,在日常生活与美学之间构建联系以致消除彼此的间隙,根本地涉及一个美学原则,即审美普遍性。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者同时从人类进化论的角度和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阐发审美普遍性的意义。一方面,从人类进化论的角度,审美感知不仅关涉人与动物的生物学差异,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亦扮演某种角色。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对此作了较为可靠的论述,她企图证明艺术及其相关的审美态度是“生物的或‘自然的”[2]7。迪萨纳亚克以行为学为方法,将艺术看作是生存的、进化的、遗传的行为,“艺术就像戏耍、像分享事物、像嗥叫那样是一种行为”[2]64。她的著作因此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者用作审美感觉普遍存在的佐证,并用以“说明审美人类学赖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和特征”[3]。覃德清亦试图借助人类起源论以说明审美感觉伴随着人类种族的诞生,“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拥有发达的外感知神经,人类能够自觉调节身心,借助歌咏、音乐还有虔诚的宗教崇拜,获得心境的安详和愉悦的审美体验”[4]。除了时间上的回溯,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者同样侧重民族地域空间中审美评价与审美经验的普遍性,或在服饰、器物等民族物质生活中发掘审美经验[5],或在部落习俗中总结色彩偏好的评价机制[6]89,由于地域空间的独异性,这类研究的实质是审美相对性与审美普遍性的融通。异质空间所呈现的是尚未被西方美学观念同质化的审美偏好,其中的文化相对性恰恰确证了审美的普遍性,范丹姆称之为“跨文化的审美普遍性”(transcultural aesthetic universals)[7]142。在审美普遍性与审美相对性的双向思维中,审美人类学将研究目光投向传统美学所拒斥的“地方性审美经验”[8],既而打破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
另一方面,从美学发展史的角度,自德国古典美学延续而下的审美自律性一直是审美人类学不断冲击的美学壁垒。康德区分感官愉悦和审美愉悦,黑格尔将美学限定为艺术哲学,西方美学史的标志性事件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被视作亟需开拓的狭窄路径。范丹姆认为,20世纪盛行的“哲学美学”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了康德与黑格尔所开启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它们的特征表现在:“艺术”的而非“美学”的;限于高雅艺术的;艺术经验而非与之相关的经验性调查;西方中心而非跨文化视野[7]。与之相反,审美人类学广泛涉及物质性的生活经验,以审美现象代替纯粹艺术对象,以跨文化视野而非西方话语分析异质性的审美感觉和审美评价。转换到中国本土语境,郑元者认为,八十年代“美学热”以来相关的美学研究难以脱离本质主义的局限,尤其是美本质或艺术本质的定义“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艺术中的解释力非常有限”[9]。他进而总结了美学学科面临的问题与契机主要在于:中国美学要直面民间艺术经验而形成“富有生机的美学思考”,摆脱精英式的美学观念;在提升理论与思想原创性的同时,让中国现代美学走出对西方美学思想体系的习惯性依赖[10]44。不论是美学精英立场的摆脱,还是原创性的提升,共同的吁请都需要改变日常生活经验匮乏的现状,固守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已不再可能。
从晚近的情况看,审美人类学学者将审美普遍性原则延续至审美人类学的“当代性”之中,以直面美学当代语境的共时性弥补以往历时维度的单一性。2016年,“文化经济”作为新名词进入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并被视为审美问题复杂演变的时代征象,而审美人类学在如何应对文化经济时代审美、文化、经济多重纠葛的问题上被寄予厚望[10]44。2020年,“消费化、网络化、全球化、娱乐化”被表达为审美人类学当代性的“四重挑战”,审美人类学需承担起理论批判性、实用性和引导性的职能。2021年,审美人类学研究首次尝试通过“艺术乡建”探讨“艺术介入”问题,寻求以实践姿态融入日常生活的当代现实[11]。
总而言之,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呈现出不断突破的情况。一方面,日常生活不限于传统人类学所面向的“过去式”的既成生活经验,也不囿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批判的“消费社会”的当代现实,日常生活在何种情形下进入审美人类学的视野是由其生发的审美经验决定的,日常生活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美学不再仅仅指涉艺术,审美自律性交由审美他律性来承接,凡是审美经验发生之处皆可作为审美对象。因此,日常生活與美学之间不再横亘着沟壑以严格区分彼此,二者的关系在审美人类学中表现为一种“破而后立”的平衡。审美人类学作为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已经不再持守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边界,亦不断拓宽日常生活的视野,与其将它看作美学研究的突破,毋宁说“是学术渊源与知识结构的重新组合,是冲破学科壁垒,由美学界和人类学界的研究者取长补短而携手共进的一种新的尝试”[4]32。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审美人类学如何区分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经验?如果美学与日常生活边界的破除是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必要前提,那么学科逻辑的严谨性同样要求对美学如何避免日常生活的同化做出回答。即是说,美学研究尽管走向日常生活,却仍需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唯此才能以反思的姿态介入日常生活而避免遭受日常生活庸常性的统摄。由此形成了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两重性质:既要“批判美与日常生活的疏离”[12],也要“继承批判美学的学术脉络,在对当代审美文化的批判上,保持美学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觉性”[13]。批判美与日常生活的疏离就是批判传统的审美超越性,保持美学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就是延续并转化美学的超越立场,它意味着审美超越性以某种匿名的方式作用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审美人类学以此寻求两方面的平衡,以确保美学研究的日常生活倾向与美学的反思、批判姿态得以兼容。
二、日常生活美学对“边界”的持守?
与审美人类学相比,日常生活美学在“边界”问题上较为复杂,原因在于日常生活美学既非美学下属学科的有意识组建,亦非美学问题的一致性探讨,而是不同价值立场、不同言说方式交织而成的美学话语形态。为了讨论的规范性,日常生活美学还需分作两个层面来看待,第一个层面是日常生活美学进入中国学界时所伴随的论争,“日常生活审美化”一时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第二个层面是日常生活美学的自觉建构,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而开展日常生活美学的理论实践。
“日常生活审美化”(或简称“审美化”)作为一个美学命题通常被溯源至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在国内,周宪与陶东风最早流露出对这一命题的敏锐意识,并表达了看待“审美化”的两种典型态度。在周宪看来,“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带来的问题很多”[14],“今天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许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美的审美境界”[15]。美学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美学的救赎功能、美学的批判精神主导着周宪的价值判断,“日常生活审美化”置成质疑的现象与命题。陶东风则以相对开放的态度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亟待接纳的文艺/审美活动巨变,他主张在文学研究中接纳“审美化”现象,但也“越来越多地带有深深的忧虑与批评”[16]。周宪与陶东风两种言说立场不妨简括为:(1)根本上质疑“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合法性,从而继续恪守传统美学的“超越性”原则;(2)认可并接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既成事实,但在价值层面予以质疑与批判,即事实层面的接纳与价值层面的反思。从2002年至2005年,不少学术期刊围绕“审美化”问题开辟专栏,不少学术讨论会亦以“审美化”作为中心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热烈讨论中成为时髦话题而言说者甚众①。其中,王德胜的文章较为独特,他的立场可简括为:(3)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持乐观态度,美学研究应当借助日常生活扩展研究范围并突破旧有的美学原则[17]。彭锋对“审美化”的言说也颇为典型,他的观点呈现为:(4)从“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转向“日常生活美学”展望。在2007年发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一文中,彭锋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以美的名义扼杀我们的审美敏感力”从而“必将走向自身的反面”[18],而2010年发表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变容》则展望一种“关注广大日常生活领域的生活美学”[19]。此外,亦有学人将“审美化”及其论争视作反思的对象,进而采取旁观的、审慎的态度而不轻易作价值判断,如陆扬、罗如春,可归为立场(5)。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复杂性当然无法通过上述五种立场得以全面描述,但大多数研究者对“审美化”的言说态度都可从中找到关联或对应。例如,童庆炳“食利者的美学”的尖锐批判与杨春时对“超越性美学”的坚守皆可视为立场“(1)”,钱中文、朱立元、朱志荣、鲁枢元、潘知常等学人莫不在此列;高建平在艺术回归生活的潮流中展望“美学的复兴”,同时并未舍弃美学的人文批判,可视作立场“(2)”。有的研究者(如李西建)看到了“审美化”的二重性,进而以深度审美性提升日常“审美化”的庸常性,介于“(1)”与“(2)”之间。
从以上言说立场的划分与归类可以看到,尽管我们试图搁置言说者各自的差异而获得同一性,以便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寻找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所在,即回答:“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究竟对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作何处理?其结果似乎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审美化”论争的价值就在于众声喧哗的事件本身,多元化的美学观在其中得以展现。对于立场“(1)”而言,日常生活与美学的固有边界不变;对于立场“(2)”而言,“边界”出现了松动,但仍可在日常生活与美学之间做出分隔;对于立场“(3)”而言,“边界”的问题形成了与审美人类学相似的情形;对于立场“(4)”而言,“边界”则面临着重建。若仅仅停留于论争事件,“边界”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
事实上,亦有学者在“审美化”的喧嚣中走向日常生活美学的理论沉思,以某种“出走”的姿态找寻日常生活與美学的边界所在。刘悦笛著有《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2005)、《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2007)、《生活中的美学》(2011)、《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2018),是汉语学界屡为“生活美学”著述的美学研究者。他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是“生活美学”而非“日常生活美学”,区别在于,前者在“日常性”上与日常生活具有连续性而在“非日常性”上与日常生活留存边界,后者则将日常生活视作统一体且不做分辨[20]。在审视国内外“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的过程中,刘悦笛发现,“日常生活”遭遇了潜在的同质化,导致其中的差异结构无法呈现并造成言说的含混。他进一步回顾了美学史上的“艺术否定生活论”与“艺术与生活同一论”。德国古典美学所确立的艺术自律性要求艺术与生活保持绝对距离进而实现观念的引领,其理论前提是艺术高于生活,艺术要否定并超越生活的非自由状态与非完满状态。20世纪以来的分析美学与实用主义美学反思“艺术否定生活论”中的超验预设与乌托邦情节造成的美学困境,从而走向艺术与生活同一。“但吊诡的是,无论是‘艺术否定生活论还是‘艺术与生活同一论,都具有共同的理论缺陷,也就是都未将现实生活解析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来加以分析。”[21]在此意义上,刘悦笛将日常生活区分为“日常性”与“非日常性”,从而恢复了日常生活与美学的张力,而不必在“美高于生活”和“美是生活”之间做二难抉择。美作为一种动态生成的活动,“正是位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特殊领域。”[22]日常生活的日常性是美的活动生生不息的源泉,但美又绝非与日常生活完全同质化,美的发生意味着日常生活日常性的阻断及其非日常性的显现。非日常性不仅意味着美学与日常生活间距的留存,同时意指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可以指涉生活真理的发生而达成美真合一。由此,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问题得以灵活对待,它既非“有”亦非“无”,而在有无之间;美学既回归日常生活又可保持自身的学科品性。
日常性与非日常性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现象学的直观理论。“感性直观”与“本质直观”成为日常生活差异结构的观念来源[23]194。胡塞尔谈论的“直观”伴随着方法论上的突破,即对直观中被给予的感性材料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从而获得纯粹现象,纯粹现象亦即事物的本质,现象与本质的分野借此获得了弥合。现象学的变革意义在于,使“本质”脱离抽象逻辑、概念思辨并交还给“现象”,因而直观既包含感性杂多,亦可通达本质。在刘悦笛看来,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直观性”。日常生活是可以被直观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因而是一种“感性直观”,而“美的活动则是一种奠基于‘感性直观并与之相融的‘本质直观。”[23]195刘悦笛由此借道现象学的变革路径来消释美学与日常生活的间隙,实现了美学研究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同时也避免美学向日常生活庸常状态的沉沦。
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到“生活美学”的自觉建构,或许已然昭示了日常生活美学—作为一种广义上的美学话语形态—范式演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审美化”论争的视角而言,多元主义的美学事件的确呈现了学术研究的良好生态,但美学研究的进路或需交由自觉的理论建构来铺就,它需要同时符合美学的日常生活走向与美学的超越性姿态。因而,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边界既要打破也要持守。美学的超越性姿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是回归日常生活的“内在超越”。
三、审美人类学
与日常生活美学的“内在超越”
相对而言,日常生活美学在对待美学与日常生活边界的问题上比审美人类学更具直观性。日常生活美学以自觉的理论沉思表明:美学研究尽管走向日常生活,美的活动确实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但审美经验若使自身成为可能则必须与日常生活的庸常状态保持间距,因而审美经验的生成是日常生活日常性的阻断及其非日常性的显现。如果日常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是有效的,那么它应当在其他从事日常生活研究的美学领域当中具有同样的效应,以本文语境而言即意味着,“内在超越”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审美人类学当中。
由此观之,审美人类学打破日常生活与美学的边界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边界的重建。审美人类学在审美普遍性的原则下可能将其研究范围覆盖日常生活的全域,并在观念上尊重地方性的审美意识,在此意义上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但当它发掘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之时却仍然与日常生活产生间距。例如,杰里米·库特以审美人类学为视域对苏丹南部的尼洛特牧牛人进行考察与分析。他看到尼洛特人对牛角的喜爱、对牛的毛色的偏好塑造着尼洛特人的审美观,以至于模仿牛身斑纹来装饰人身形成一套“普遍的习俗”。尼洛特雕塑与绘画对牛的偏爱也说明当地人的审美观“能够摆脱经验性的束缚,升华为一套抽象的美学观念”[6]93。可见,杰里米·库特的描述尽管深入地方性的日常生活,但同时也通过“习俗”“观念”来寻求脱离日常生活日常性的契机。“日常生活中的视觉奇迹”作为标题恰恰表明了他的用意所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尼洛特人,他们对牛身毛色的模仿、以流苏装饰牛身的行为,也是当地人与日复一日的牧牛生活拉开距离的独特方式。再如,国内审美人类学界一向重视对民歌的研究,少数民族民歌与西方经典艺术形式的差异性及其“与日常生活的水乳交融性”[23]296恰好彰显审美人类学扎根本土的学科品性,并且“民歌也与当代一些重要的美学问题紧密相关,如民歌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问题,民歌与大众文化问题,等等。”[24]293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审美人类学研究发现,民歌并非只是“乡间的歌、乡下人的歌”“实质上是一种贵族的艺术、高贵的艺术”[24]297。所谓“贵族的艺术”表现在黑衣壮民歌具有优美的形式、严密的结构、典雅的风格,它允许现代艺术家以现代音乐知识进行系统的、有机的、严整的乐理分析;所谓“高贵的艺术”指的是,黑衣壮以歌唱的方式装点着日常生活的不同场合,在水源匮乏、山石林立的生存条件当中“歌唱着生活、诗意地生存。”[24]299“黑衣壮人以山歌超越了苦难的人生,以山歌提升了平庸的人生,以山歌创造了诗意的人生。”[24]300正是在此意义上,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者反观“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并认为民歌研究给予了启示,即“日常生活中的艺术也可能像高级艺术、精英艺术一样精致和富于精神超越性。”[24]301尽管对“超越性”缺乏分辩,但审美人类学在走向日常生活研究的过程中显然并不认为日常生活同化了美学。
以上说明,审美/艺术与人类学的结合并不能够回避“超越性”的问题,将美学研究奠基于物质经验也并不妨礙在观念上对审美性/艺术性向日常生活的超越作出规定。无独有偶,2023年1月,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第九场)中,赵毅衡讨论了艺术之为艺术的“艺术性”问题,以“超脱说”重新定义了艺术泛化背景下艺术可能具有的一系列品格,不论是美感论、情感论、形式论还是崇高论,都可能以“超脱说”来界定②。超脱区别于超越,前者是在“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引发的艺术与生活密切关联的趋势下对艺术与生活边界的重新界说,并且它要克服传统“超越说”的局限性。
美学的超越大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美学所确立的审美超越性(外在超越),及美学回归生活世界之后的审美超越性(内在超越)。其中,形而上学美学又可划分出本体论美学与认识论美学两个阶段。本体论美学热衷于美本质问题的探讨,并将其归结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最终实体,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起源,数的和谐就是美;柏拉图认为美的原型是理式;奥古斯丁将绝对美等同于上帝,等等。因而本体论美学的超越性就指向现实世界之外的美的绝对本质,它实际上伴随着本体论哲学(起源哲学)对存在本质的追寻。认识论美学由鲍姆加登所开启,鲍姆加登不仅创立了“美学”,还将美视作一种认识能力。认识论美学最根本的特征是理性—感性的二元结构,由于认识论的内涵被归结为认知主体如何运用理性能力将现象世界的感性杂多综合为最终真理,美学因此参与了对形而上学真理的认识过程,认识论美学的超越性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真理的获致。黑格尔美学被视为认识论美学的典型体现,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真理的命名,而艺术(美学)成为了绝对精神的三种实现方式之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作为黑格尔的著名美学命题恰好展示了认识论美学的超越性。除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尽管不属于前述意义上的认识论美学观,却以特殊方式承接了对形而上学真理的追寻。自黑格尔以来,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思想界所憧憬的理性大厦坍塌,形而上学再难支撑起理性统一体,法兰克福学派(尤以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转而在美学/艺术当中寻求形而上学真理的实现,即“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是旧式审美超越性的透彻表达,美学与形而上学真理直接相关,以超越异化现实的方式许诺着自由、善、幸福等终极诉求。简言之,形而上学美学所确立的审美超越性将现实生活世界视为感性表象而置于真理的反面,形而上学真理(世界本源、理性统一体、终极自由)成为传统审美超越性的根本指向。
所谓“生活世界转向”可视为美学走向日常生活的哲学前提,它作为一个哲学事件通常追溯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书中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生活世界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对抗欧洲思想界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哲学危机,另一方面——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是为了“检査超验还原过程的严密性和清晰度”[24]185,即避免超验还原对作为发生现象学边缘视域的生活世界的忽视。在内涵的理解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并不直接等同于作为日常现实的生活领域,而是发生现象学的前概念、前思维、前对象化的构造阶段。但是,从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来看,胡塞尔的确开启了“生活世界转向”。此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列斐伏尔、K·科西克、阿格尼丝·赫勒以不同形式的命名昭示了这一哲学转向[25]。生活世界转向的根本特征是主客融合,尽管胡塞尔并未完全实现,但其后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都以不同方式弥合了主客裂隙。美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受此影响,因而同样立足于生活世界领域,形成美学研究的“生活转向”,衍生出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等不同美学形态。生活世界转向之后的审美超越性,意指审美超越不离于日常生活领域,不在生活世界之外许诺美学/艺术的乌托邦,因而是一种“内在超越”③。内在超越顺应了美学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同时在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保持灵活的边界,以满足美学批判反思的超越立场。
从外在超越过渡到内在超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哲学原理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胡塞尔区分了“超越的两重意义”[26],一种是非直观的、非自身被给予的超越,它尤其指涉客观认识在主客分裂的条件下从主体体验直接超越到物质世界客体的存在问题;另一种是直观的、内在的超越。胡塞尔的做法是悬置一切外在的超越认识,如经验世界客体的存在问题,以获得意向性的超越作为现象学的认识论依据。意向性的超越指的是意识活动中的感觉材料向意向对象的构成[27],因而是不折不扣的内在超越。海德格尔对超越的内涵进行了生存论的转化,将它理解为此在在实际生存中“超逾”出与其他存在者共在的状态,以寻获生存的“根据”并向着“根据”上升[28],因而超越的最终指向是存在的意义。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的内在超越广义上归属于“生活世界转向”的美学思潮,也可通过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超越的哲学规定来解释自身。
四、结语
综合来看,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在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边界问题上具有共性,同时它们处于回归日常生活的美学走向,又同时拒绝日常生活对美学的绝对同化,既打破边界又重新确立边界。边界的打破满足了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拓展美学研究范围的需要。边界的重新确立——以灵活而非僵化的方式——是对美学日常生活走向与审美超越性的双重回应。在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内部,正是回归日常生活与传续审美超越性的双重诉求促成了内在超越的形成,换言之,内在超越对审美超越性概念、内涵的转化更新由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的研究实践来确证。内在超越的起点是日常生活的日常性,终点是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日常性-非日常性的结构萌发于日常生活美学内部作为“生活美学”的自觉理论建构,对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也同样有效。审美人类学研究起始于日常性的物质经验,又往往上升到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美真合一)。以山歌研究为例,审美人类学研究发现当地居民“诗意歌唱”的生活姿态,或以此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或作为一种内在于日常生活程序的意向性超越,总之,是不脱离日常生活领域的内在超越。在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外部,内在超越汇入了从形而上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哲学、美学思潮,亦不妨视作审美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在新形势下共同遵循的美学原理。
注释:
①期刊专栏与学术讨论会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推动,可参考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1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56-661.
②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9日。
③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导论》中以“纵向超越”和“横向超越”分别命名主客分立、主客融合背景下的哲学超越,而本文的“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指涉美学研究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前后的两种审美超越性。
参考文献:
[1]王杰.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M].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户晓辉.审美人类学如何可能——以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5):52-55.
[4]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1.
[5]张利群.民族审美人类学[J].民族艺术研究,2002(4):14-21.
[6]库特.“日常生活中的视觉奇迹”:对尼洛特畜牧文化的审美人类学研究[J].海力波,译.民间文化论坛,2017(2):79-97.
[7]范丹姆.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M].李修建,向丽,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8]王杰.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2.
[9]郑元者.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史、理念、事实和方法[J].杭州師范学院学报,2007(6):87-91.
[10]王杰,肖琼.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J].思想战线,2016(3):39-44.
[11]向丽,赵威.艺术介入:艺术乡建中的“阈限”——兼论审美人类学的当代性[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1(4):120-128.
[12]范秀娟.审美人类学的历史视野与批判精神[J].思想战线,2022(6):135-142.
[13]王杰,方李莉,徐新建.边界与融合: 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的交叉对话[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1(5):1-14,121.
[14]周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J].哲学研究,2001(10):66-73.
[15]周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4-68.
[16]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J].河北学刊,2004(5):86-92.
[17]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J].文艺争鸣,2003(6):6-9.
[18]彭锋.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9-73.
[19]彭锋.日常生活的审美变容[J].文艺争鸣,2010(5):44-48.
[20]刘悦笛.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3.
[21]刘悦笛.日常生活美学的哲学反思——以现象学、解释学和语用学为视角[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0-35.
[22]刘悦笛.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89.
[23]王杰.审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5]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J].中国社会科学,1994(2):115-145.
[26]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5.
[27]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9.
[28]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8.
作者简介:农文聪,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