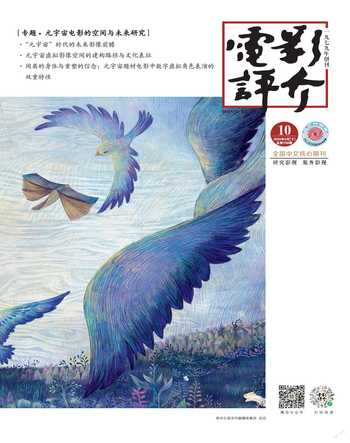声亦有形
2023-08-23许涵之周冬莹
许涵之 周冬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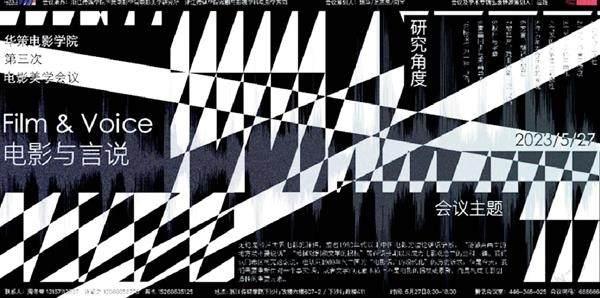

2023年5月27日,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电影美学研究所举办了以“电影与言说”为主题的第三次电影美学研讨会,会议在浙江传媒学院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兼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学部主任陈旭光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应雄教授,中央戏剧学院徐枫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厉震林教授,上海戏剧学院王旭锋教授,西安文理学院张晋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敦副教授等1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研讨。本次会议由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姚争教授、华策电影学院院长范志忠教授、华策电影学院副院长向宇教授担任策划,并由北海道大学教授应雄担任会议及学术专辑出版特别策划人。姚争副校长、范志忠院长为会议致开幕词,华策电影学院周冬莹副教授担任会议主持。本次会议得到了《文艺研究》杂志和《电影评介》杂志的学术支持。
回溯世界电影理论话语脉络,影像说话的“道”与“术”一直占据重要的篇幅。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理论家认为言说减损了影像表现力,然而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史中充满了对于“说”的电影性探索。“说话”并非是反电影性的,我们对于电影性的理解和表现,在于对言语与画面关系的持续性探索中。在电影中,与其抹灭语言,毋宁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这是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让-皮埃尔·梅尔維尔(Jean-Pierre Melville)、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与达尼埃尔·于伊耶(Danièle Huillet)等电影作者的探求,也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甚至在主张“丢掉戏剧和文学的拐杖”的时候就已经在悄然摸索的创作实践,甚至也是1940年代的费穆已然开始的电影探索。
文学与语言究竟是视觉陈述的累赘,还是影像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数字化浪潮狂飙突进的今天,这一经典议题依然充满丰富而广阔的讨论空间。为此,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举办的第三次电影美学会议,将议题聚焦在了“电影与言说”之上,探讨电影中的言说与电影性之间的多维关系。与会专家们从“说”与电影、方言与译制片、言说与思考和表达的关系、言说与创作和探索的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一、“说”与电影
在“‘说与电影”的小组研讨中,专家们从电影本体维度出发,将电影之“说”的具体呈现放置于不同历史语境中进行比较观照,认为它是建构时代性理论话语的重要思路。陈旭光以《电影言说的合-分-合:艺术综合?媒介融合?话语狂欢?》为题,提出电影言说的历史在经历了电影艺术的综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之后,走到当下媒介融合、话语狂欢的新时代,在这一历程中,电影言说经历了合—分—合的发展流变。电影言说可分为内部语言(蒙太奇、长镜头、构图)与外部语言(诗歌、戏剧)。电影曾通过外部语言的融合内化衍生成独特的视听样式,以实证综合艺术的身份。如今,在媒介突出的文化环境下,游戏语言、二次元语言、界面语言的强行介入电影,电影在形态上走向拼贴与交杂,形成强调差异、断裂的新“合”势。另外,“诗电影”构成了电影言说的另一种形态。比如《城南旧事》(1983)、《巴山夜雨》(1980)中诗意的慢镜头、自然景观的表现与人物游弋的动作表现,这些与《路边野餐》(2015)、《我的诗篇》(2015)中大段的诗歌朗诵和呓语形成了鲜明区别。
诗的诵读是对线性叙事的有意中断,它打碎了传统的电影言说时间链条,形成德勒兹意义上的“晶体”:即时间自行敞开,影像涉及过去、现在与未来,梦幻和现实难以识别。以上是一种“分”的体现。戏剧的形式则对电影中的言说形成另一种“合”。近几年中国高概念电影制作中的集中化场景、三一律结构的回归,以及“剧本杀”电影的流行,都再次彰显了电影中的戏剧性元素。陈旭光提出“网生代”观众正通过拼贴和重新组接的方式,摆脱循序渐进的时间流,重塑未来电影的言说接受方法,抵达新的想象力和吸引力消费。陈旭光指出,电影言说方式革新的研究,是一个充满价值的方向。
厉震林从数字时代电影言说的形式更迭出发,着重探讨了演员这一言说的现实载体的训练调整与修养提升问题。他提出,电影进入数字时代以后,对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和工种提出不同要求:一是超越性,创作者要比观众“快一拍”;二是新样式,观众审美心理的重大变化需要电影言说方法的重新排列、交互和塑形;三是代入感,重视代入与沉浸体验的审美需求。因此,数字时代演员的自我修养需重视三个问题:首先是身体管理,奇观电影的大景别尤为考验演员的身体表现力、创造力、可塑性以及轻盈感;其次,情感管理,保持生命体验的纯粹和敏感,才能更从容和极致地去理解人物,呈现充沛、准确的表演;第三,想象管理,随着XR、AR、MR等数字技术发展,表演进入虚拟视界之中,需要丰富的想象思维;最后,修养管理,这为演员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演员提升人文综合素质,加强人文学科自我修养,以适宜数字时代影像需求的表演呈现。
徐枫提出的“说与示”的标题源于佛学,说即言说,示即指示/示现。如果“说”对位于语言学,“示”则对位于符号学。通常认为语言学是更宽泛的符号学的一种,但也是符号学的一种典范,其他的符号的表意方式,总或多或少地参照着语言。索绪尔对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性”“不可论证性”关系的论述,作为理论源泉先后引导出结构主义对语言结构决定意义的共时性理论框架,和后结构主义对言语行为(书写/口头的)产生“延异”的个体化和历时性理论认知。而这都与电影历史中声画关系/电影声音/人声/对白的美学思考和实践有着互文本关系:爱森斯坦的声画对位理论;雷诺阿在同期声实践中寻找到的“现实”的二元对立或三元对立关系;安东尼奥尼的影像和声音(包括对白)中的症候发现;让-达尼埃尔·波莱的“冥想蒙太奇”声画文本。同时,东方佛学体系中,“名”(五蕴中的“受想行识”)和“色”(四大)的假合关系,能(主体)和所(对象)的双空状况,同样也使语言的言说一次性地成为真相被指示又被遮蔽的方式。因此“无有语言文字”符合非二元化的绝对真相(不二法门)的显现方式,“拈花微笑”的“示现”就是如此。同时在相对真相层面上,言语的意义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要求准确性。这在东西方电影中都有非常引人深思的佐证。武则天为《华严经》所作的序言中的话语,“虽则无说无示,理符不二之门;然而因言显言,方阐大千之义”堪称对这一问题较为完美的总结。
应雄提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去尊崇“能够用画面的地方就不要说话”这样一种过于朴素的电影“教义”,电影史上的众多事例,恰恰呈现的是不同的伦理。他以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作品为例,展示同一导演作品序列中“说”与“不说”的一体两面。在其作品里几乎占一半的法式黑色电影中,因主要人物常常是对自己从事的“活儿”熟练有加的职业人(职业枪手、专业警察、职业兑酒师……),导演竭力压低台词出现的频率,如阿兰·德隆(Alain Delon)同意出演《独行杀手》(1967),首先就是被导演读剧本时开篇7分钟几乎没有一句台词而吸引。但梅尔维尔的第一部剧情片《海之沉默》(1947)则是一部忠实小说原著、不停在“说”的充满文学性的作品,“说”的样式和“文学”元素的凸显,反而酝酿出电影充满韵味的“默片感”和“影像感”。被认为不够“电影感”的“说”在特定情境下却是最“电影”的构成元素,这一实践案例分析阐明了电影如何在“最不电影”的时刻才发明出自身的“电影感”,再次验证了“言说”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性。
二、方言与译制片
在“方言与译制片”议题的讨论,主要关注电影中语言的地域性和转化与文化特征展现和审美转译关系的话题。王垚从译制片入手,在对1950年代至今的新中国配音译制片生成机制、组织机构、技术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礎上着重考察了配音译制的媒介问题和文化效果。他指出,译制片既是对建国初期国产电影产能不足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新中国电影在尚未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时对苏联东欧国家电影的学习过程,是一种“全球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中国方案。从媒介问题来看,配音译制是一种“声音表演”,天然地适合广播节目的传播,并反过来对电影创作技法产生影响。从文化效果来看,“译制腔”的生成在发明了一种口音的同时,也承担了“世界想象”的职能。他以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将配音译制与当下的偶像剧配音联系起来,从配音演员职业转型的角度,分析“声音表演”中“声音与身体分离”的表演技巧与工艺流程如何演进成为今日的媒介形态。
张晓月关注近些年活跃在中国银幕上的“沪语”言说,从近三年来的电影方言现象出发,试图追溯其在当代电影创作中的历史脉络和表现特征。她分析了全沪语影片《爱情神话》(2021),以及局部出现沪语对白的《流浪地球2》(2023)和《中国乒乓》(2023)等热门影片,提出从默片时期至今,上海城市空间与上海人一直是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对象,但上海话在当代中国故事中的显性表达却较少被提及。在创作具有地域特色题材时,是否使用上海话是一项重要的创作选择;在人物形象塑造时,是否使用上海话同样关乎个体特点凸显和人物关系构建,重视沪语的创作表达对理解当代中国电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言说:思考与表达
在“言说:思考与探索”主题探讨中,王敦借用法国电影学者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所著《电影所发之声》(The Voice in Cinema)一书提出的“voice”概念,追寻与银幕相伴的电影声音发自何处。他从Voice与Surface的关系入手,提出电影声音是与银幕光影捉迷藏的游戏。①如果把电影的光影与声音分开来讨论,可以命名为基于银幕即surface的幻术,和基于发声即voice的幻术。voice应该被理解为动词性“发声”和名词性“所发之声”的前提与叠加。在中文的电影研究语境中,对于电影之voice的理解,就成为一个有待阐释的问题。voice的不在场性质,造成了电影声音的独特性。
袁海涛则从德瑞克·贾曼(Derek Jarman)的《蓝色》(1993)、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小姐与流氓》(1918)、《猜火车》(1996)等影片出发,探讨了独白的定义、类型与电影化(cinematic)问题。他指出,自白(soliloquy)与独白(monologue)具有差异性,独白允许一个角色大声思考,自我辩论角色的内心困境、冲突和选择,从而帮助情节发展,同时向观众呈现人物的反思,提供关于角色的认知。独白通常是私密的、值得信赖的言说,有利于角色和观众之间建立更紧密的情感关系。根据米歇尔·希翁对“共振”(synchresis)、“共同呈现”(co-presentation)原则和联觉反应(synesthetic responses)的阐释,独白不仅是一种声音,还可以伸展自我并分解为振动,既将其返回自身又将其置于外部。独白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无声的独白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呈现意义,有声独白则具备声音本身的特性,观众“听”到“独白”,不只是“感知意义”,还包括了声音本身的传播与共振。观影者的聆听除了感知意义外,还能通过声音听到自己、看到自己、触摸自己。
张晋辉以电影中的非叙境声音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在电影创作中的具体功能。非叙境声音意指影片中与故事的叙述世界没有逻辑关联的声音部分,是角色的主观想象,是创作者的情感抒发,也是刻意营造出的艺术境界。非叙境声音自由灵活,影响影片的意义,却不进入影片的故事结构中。它在《春潮》(2019)、《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中体现为情绪传递功能,在《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树上有个好地方》(2019)中实现对零散影像片段整合,在《柔情史》(2018)、《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兰心大剧院》(2019)中有暗示隐情的效果,而在《我不是药神》(2018)中非叙境的音乐形成场景连带。声音不仅提供听觉和画面的解释,还有自在的逻辑,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表意作用。结合影片具体场景,“非叙境”的声音不仅平行、同步画面,还能开创画面无法呈现或表现不充分的信息内涵。
四、言说:创作与探索
在“言说的创作与探索”的主题研讨中,潘志琪从自身纪录片创作经验着手,以纪录片创作中的语言为视角,结合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模式、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述行纪录片等创作类型及理念,论述了语言在纪录片创作机制中所产生的不同话语关系。他指出语言不仅是纪录片叙事的一种手段,在现实题材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中,语言往往可以转换为一种创作话语,改变拍摄者与被摄者的权利关系,重新构建作品的叙事与表达。二十世纪20年代,格里尔逊秉持“艺术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的创作理念,诠释了“画面加解说”模式的制作机制及宣传教化功能;60年代,“真实电影”的提出实现了语言的介入与互动,改变了纪录片创作的叙事话语;而90年代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为代表的表述行为型纪录片的出现,语言以夸张、结构、拼贴的形式强调了创作者个体经验和情感的表达,主观放大真实事件,并以诗歌和独白贯穿叙事中,彻底革新了纪录片的言说样式。
王旭峰结合电影导演大师们的声音观念及其作品实践,比较语言声音的反影像及放大影像效果两种对立观点,并对《大独裁者》(1940)、《神女》(1934)两部影片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电影言说在故事建构中的价值。他认为,在当代电影中语言声音展现出了无可替代的、强大的个性化的力量。电影中的语言声音,除了语义、语调、潜台词信息之外,包括大到文化的、民族的信息,细到具体的响度、节奏、音色等属性,都是建构故事的不同维度。凡是基于人物性格的、基于故事发展需要的语言声音,就能够做到跟影片有机结合,成为电影浑然天成的一部分。
黄也将电影与语言、画面与台词间颇具复杂且矛盾的关系前置为问题意识,以日本新生代导演代表人物滨口龙介(Ryusuke Hamaguchi)对于美国独立电影教父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作品的电影评论作为具体范例,试图将台词与画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地前景化。他试图论证台词与画面,并非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充性说明与附庸,而是相互辅助、互相依存,结构成一种台词如何成为画面,画面如何改变台词的动态关系,以及深入研究这种关系如何颠覆主客体分明的二元形态,呈现更意味多元的美学价值与意义。
余思从感官转化、时间延展与心理共振几个方面出发,探讨了电影声画对位的多重审美功能,指出“声画对位”的电影声画关系,是对“同期声”模式一种升华飞跃;“声画分离”使听觉“视觉化”,“视觉”听觉化,将听觉释放为独立的艺术表达方式,增强影视画面的内涵与厚度;“声画并行”超越时间线性顺序、空间任意转场的逻辑,延展了影片信息量;“声画对立”有意营造声音和画面的背离,造成审美预期落差,形成更高阶的审美快感。
结语
数智时代,媒介形式和功能的巨变、影像制作技术与工业流程的革新,使电影的视听表达、镜语系统、美学特征产生显著变化。“媒介是人的延伸”,新信息环境引起的大众心理和社会文化新图景正在成形,网生代、游生代观众对影视艺术审美样式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在人机交互、虚实结合的制作环境与想象力消费的市场驱动下,既有的艺术规则、形态、理论和评价方式需要改造,经典电影本体理论亟待革新。本次会议以电影本体美学研究为立足点,聚焦电影中“言”与“说”这一至关重要的创作元素,体现了时代性与融合性两大特征,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研究面向和深刻、敏锐的专业洞察。学者们的研究既从电影史话语流变与沿革出发,时序性梳理电影言说形式与功能的更迭与演进,又结合全媒体时代转向的观众审美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影像言说的“未来式”进行思考和推演。本次会议采取的研究路径、涉及的研究方法全面多样,既有美学层面的延展,又有东西方哲学的映照,既容纳微观的个案分析和导演创作方法谈,又涵盖了高屋建瓴的产业发展趋势探讨和宏觀的文化语境研究。从理论走向创作,从创作回归、反哺理论,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动态构成了全面、丰富的话语图景,为中国电影新时代的“银幕言说”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参考的同时,也拓展了学术视域的新空间、新面向和新路径。
【作者简介】 许涵之,女,浙江宁波人,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电影史论研究;周冬莹,女,浙江诸暨人,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电影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