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楚文化的人道和宽容
2023-08-23曾勋
曾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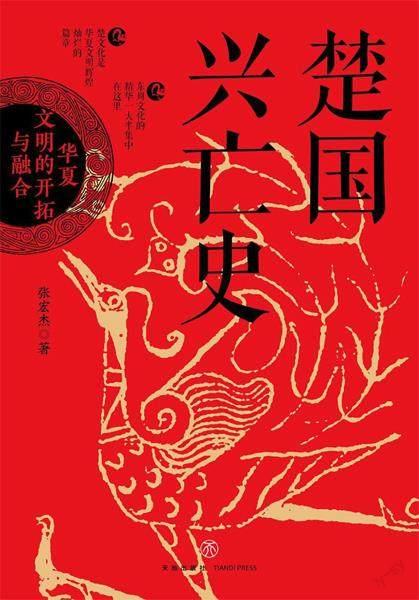
有一个被“遗忘”的文明,它最鼎盛时是一个方圆5000平方里的大国,春秋时期,它打败了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而称霸。在崇尚权诈的战国时代,它依旧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的文雅。它创造了斐然的文化,现当代出土的各种奇谲瑰丽的文物展现了这个文明曾经的辉煌灿烂。它就是楚国。
楚国800年盛衰荣枯的历程堪称波澜壮阔,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宏杰所著的《楚国兴亡史》出版,该书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典籍里的记载,完整、系统地讲述了楚国的兴亡,以揭示历史背后值得深思的规律。
创新的动力:最先创制郡县制的雏形
廉政瞭望·官察室:楚国国君去朝见周天子时,穷得拿不出朝贡的礼品,只配给周天子“看火”守燎,那穷酸样被各诸侯国国君笑话。一穷二白的小国,能发展成与晋国、秦国抗衡的大国,除了地理位置的优势和资源禀赋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张宏杰:当然是有的,比如楚国统治者实行了比较高明的民族政策。楚人从立国之初就身处各民族林立的环境当中,因此明智地采取“怀柔”政策,除了进行必要的战争之外,还争取与各民族友好相处。到了国君熊渠统治的时代,更明确地制定了民族包容政策,以图获得境内和周边民族的支持,因此“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史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楚人的蛮夷性,这里的蛮夷并非贬义词。楚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弑君传统”。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这一做法最有效地保证了权力传递的有序和政治局面的稳定,却也容易导致统治者一代比一代孱弱。楚国经常破坏这个规则。作为一个非华夏国家,楚国礼仪纲纪观念淡薄。如同草原民族一样,楚国最高权力的更替经常充满血腥。楚国历史上出现过五次政变,而且总是“利于少者”。不断地弑君,保证了在楚国王位上,坐着的都是年轻的、生命力极其强悍之人。
廉政瞭望·官察室:楚国在春秋中后期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种不囿于传统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为楚国的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宏杰:是的,最大的表现就是楚国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在各个诸侯国中,楚国一直是一个更为集权型的国家。楚国虽然也模仿中原国家,采取分封制,但是由于它非华夏国家,不受西周封建体制的约束,所以它的分封制度不如中原诸侯那样完善而稳定。
楚国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早地开创了郡县制的雏形。篡位者熊通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灭掉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它分封给臣下,而是以权国故地设立一个县。所谓县,最初就是“悬”字,悬挂的悬,就是这块地方“悬着先不处理”的意思。他任命斗缗(权国国君)为权尹。
廉政瞭望·官察室:县的出现相当于收紧了楚国的权力,制约了贵族的权力,对当时的格局还有没有其他更为深远的影响?
张宏杰:县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常重大。分封制相当于一种地方自治,国君想直接从各地贵族手里征发百姓,征收税款,会遇到贵族的阻挠和反对。而县尹是国王任命,随时可以免掉,并不世袭,这就保证了国王对新征服土地的绝对控制权。因此楚国先于其他的西周诸侯国建立起了官僚管理体系的雏形,在春秋战国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占了先机。后来各国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国家慢慢演变成郡县制。这是战国变法的基本逻辑,其实也是一千多年后中世纪后西方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逻辑。
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制度创新往往是在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或者说,边缘国家、边缘地区,往往是旧制度束缚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这就是“蛮夷”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发展的矛盾:“中原化”是把双刃剑
廉政瞭望·官察室:楚国原本被中原的诸侯称为蛮夷,楚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的“中原化”政策,包括礼制和文化等等,但您认为中原化是把双刃剑,如何理解中原化的正反两面?
张宏杰:春秋列国竞争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些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大国,都是边缘型国家。五个称霸之国,齐、晋、楚、秦、吴,都不是完全的中原诸侯国,而是华夏文化和边缘文化融合的国家。
秦国地处西北,在与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培养起了虎狼之性。齐国地处最东,在与东夷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晋国与北狄和山戎做了几百年的邻居,从他们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悍。
中原化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全面脱胎换骨和升级换代,给这个国家带来更丰富、更高层次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中原化的前期,中原的高度文明与边缘国家的野蛮气质相结合,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实力或者说国际竞争力的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社会剧烈分化。
廉政瞭望·官察室:也就是说,统治阶层失去了蛮夷的力量和改革能力,从狼性向羊性转变了。
张宏杰:是的,这種转变将给国家带来致命打击。社会上层会在温柔乡中失去早期的质朴、勇敢和力量,而下层人民也因为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与之离心离德,整个民族因此不再团结一心。一旦边缘民族的质朴、好战精神被吹散,那么,这个民族的噩运也就随之降临。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鲁塞在总结边疆民族汉化的规律时说,“过二、三代后,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仍然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 楚国正是这样,王室贵族毫无节制地吸取民脂民膏,很快就受到了报应。被楚灵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国,现在已经成为它身边另一个野蛮民族,吴民族眼中的猎物。虽然吴师入郢发生在楚灵王身后,但史学家普遍认为,与“明实亡于万历”一样,楚国之衰,实缘于灵王。
成功的秘诀:法家不相信感情
廉政瞭望·官察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后,春秋的礼乐时代结束了,迎来了更为残酷的战国时代。儒学式微,法家崛起,七国都争先恐后地变法,意图以变法强国。秦国的商鞅变法与楚国的吴起变法,一成一败,是什么原因?
张宏杰:两次变法一成一败,其表面原因是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则得到了秦国的更有力更长久的支持。背后的原因,却是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与法家文化的契合程度不同。
从表面上看,在天下各国中,秦国与楚国是最相似的。当楚国在中国南方“以启山林”时,秦人则在西北“逐水草而居”“杂戎翟之俗”。 两国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顽强进取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楚国一样,当时的边疆小国秦国也一直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认。两国的区别只是秦国比楚国还要落后,蛮夷化的程度还要深。秦国的地理环境远不如楚国。它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
但是,在改革大潮中,秦国却能顺应时代,迅速成功。商鞅变法,使秦国发生了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由此迅速崛起。和楚国竭尽全力中原化不同,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一直不那么热衷。楚国的强大,是因为它背靠蛮夷,却不断向中原汲取文化力量。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
廉政瞭望·官察室:是否可以说文化基础不同,导致了秦国和楚国变法的结果不同?
张宏杰:可以这么说。与楚国人一样,秦国历代君主都有着特别强的奋斗精神,他们通过与中原国家交战,敏锐地发现了中原文明的弱点:那是一种过于文弱的、精致的、不合适战场的文明。从秦穆公开始,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向戎狄发展,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秦霸西戎后,戎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有主导地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它与中原文化有很大距离,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草原文化。秦国和游牧民族一样,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秦国的简单、质朴、野蛮、残酷和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诞生于半草原半农业区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残酷、简单、直接的特点。法家学派的思考,完全是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丝毫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法家不相信感情,只相信利益。
值得我们回望的楚文化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在“楚国的灭亡”一章中写到,屈原的自杀,为楚文化的毁灭奏响了不祥的序曲,800年的楚文化就此永远消失。在您看来,楚文化有什么特质?
张宏杰: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和秦国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就并非只有“压服”和“杀戮”一策,而是更多采取怀柔政策。及至强盛之时,更是明确了“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夷”的混一夷夏政策,楚人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既有华夏文化的遗传,又有巴人、越人、荆人、徐人等少数民族土著的贡献。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来吸取周边文化之长,使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楚国文化因此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楚人热衷扩张,却并不致力于掠人为奴。他们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表现出强烈的人道精神。比如在大冶铜绿山的考古中,人们发现,在春秋战国多年的开采中,并没有发现矿难及虐待致死现象。
楚文化比秦文化更人道,更宽容。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領域上,开创了一个发达的东方楚文明。孔子周游列国, “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欣然前往楚地,但是他却西不入秦。显然,秦国在孔子眼中,是一个蛮夷之地,不可能实行王道。
楚文化的特点是浪漫主义的,楚人创造的老庄哲学,思想浩瀚恣肆,思维深广诡怪,特别是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主义想象。而楚辞、离骚等文学作品,更创造出一个个幻想漫游的世界。
廉政瞭望·官察室:是什么塑造了楚文化这样的特质?
张宏杰: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楚人就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
此外,楚国人也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楚人性格强悍,不甘人下,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他们不买周天子的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问鼎中原”,理直气壮地自称“我蛮夷也”,充分显出楚人桀骜不驯、“敢为天下先”的强烈个性。这样的楚文化仍然值得我们回望。
在春秋战国的强盛期,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成就都是相当可观的。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齐鲁的儒学及魏韩的法家成为中国文化中鼎立的三大流派。以屈原为首的“骚体”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楚国的灭亡,并不代表楚文化的结束。楚文化以种种形式流布在中国大地上,比如湖北、湖南人的性格火辣、敢斗、务实、正气凛然;楚国的一些民间工艺和民俗传统仍然在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