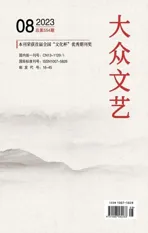灵魂之约 生命之舞*
——动画《平家物语•犬王之卷》叙事中的狂欢化色彩
2023-08-22熊明明叶佑天
熊明明 叶佑天
(湖北美术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一、引言
狂欢化诗学理论是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通过研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和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而提出的一种诗学理论。所谓狂欢化,即在狂欢节期间所形成的一系列特定的象征性仪式,从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群众戏剧到个人的狂欢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同它相近的(具有具体感性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1]158简而言之,将狂欢节上的具体仪式、内容等抽象转译为文学语言,便是巴赫金所指的狂欢化。其渊源是狂欢节这一活动庆典本身,具有狂欢节的全民性、仪式性、亲昵性、插科打诨等形式特点,且意蕴深刻,呈现出狂欢式世界感受这一内在特点。巴赫金将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归结为“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虽然狂欢化诗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小说体裁问题,但是其超文学意义是巨大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体裁及文学的范畴。而对于大众富有影响的狂欢仪式本身,以及这种仪式所引发的集体思考方式的转变,对电影叙事的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同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狂欢节仍在影响着21世纪今天的大众文化,从商业电影到肥皂偶像剧,从文学小说到流行音乐,再到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都渗透着这一文化的影子,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狂欢化诗学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在动画《平家物语•犬王之卷》(以下简称《犬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犬王》是汤浅政明导演的动画新作,改编自古川日出男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时期天生畸形的能乐师犬王和盲人琵琶师友渔,通过“能乐”艺术相互成就和救赎的故事。《犬王》极尽渲染的仪式化表演,人物命运的生与死、王权覆灭与交替之间的参差对照给了我们用狂欢化诗学理论来阐释《犬王》这部动画作品的可能。
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加冕与脱冕
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观礼和摘掉狂欢节国王这一节庆形象的王冠。加冕典礼和摘冠,这是一个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双重性仪式。即在加冕中已经包孕了未来脱冕的前景,而脱冕仪式的完成又会显现出新的加冕。由此可以得出加冕与脱冕的相对性与双重性特点,二者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相互转化。狂欢式里所有的象征物(包括形象)无不如此,总是在自身中包孕着否定的(死亡的)或者反面的前景,从而彰显了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交替与变更,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
进入《犬王》的创作背景,小说《平家物语》是绕不开的主题。这部成书于13世纪的日本古典名著是所有故事的起点。《平家物语》讲述了日本12世纪末的“源平合战”,即源氏和平氏两大贵族武士集团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长达6年的日本内战,这场内乱最终以平家的灭亡而宣告落幕。全书以一首小诗《祇园精舍》开篇:“祇园精舍之钟声,响诸行无常之道理;沙罗双树之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真谛。”作者在这里以古天竺圣地名寺祇园的钟声和娑罗双树一枯一荣的花色变化暗示了平家盛极而衰的命运,说明了“盛者必衰、新旧交替”的道理,至此,书中王权更替所呈现出的加冕与脱冕的象征性意义在动画《犬王》之中也得到了极尽的诠释,显现出交替与变更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犬王》的故事扎根于底层艺人对表达的追求,又被幕府将军的强权所扼制,整部动画的叙事策略呈现出了一个“加冕—脱冕”的故事结构。如果将视野聚焦于剧中人物的成长之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犬王和友渔从加冕到脱冕的过程,二人才秀人微与荣辱无常命运之间的对照,无不充斥着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剧中的犬王诞生于诅咒之中天生畸形,能够听到来自平家亡灵的声音,每当完成一次精湛的表演,传达出亡灵的心声,诅咒便会随之退散,身体就会发生一次蜕变。就这样犬王倾听着平家亡灵的心声,与亡灵定下“契约”,以歌舞表演向世人述说不为人知的平家故事。在电影开始,身体畸形的犬王和盲人琵琶师友渔在灯光昏暗的京都以歌舞相交,两个底层艺人的命运在此交汇。故事展开,二人的第一次六條河边的表演,桥上是手持琵琶的友渔,桥下是戴着面具、拖着巨手舞蹈的犬王,一人执琴、一人狂舞,吸引了大量的群众驻足围观。这是友渔加入“觉一座”之后的第一次独立表演,也是犬王第一次登上舞台。二人凭借着酣畅淋漓的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场面一度火爆,甚至盖过了同时在祇园(即“比叡座”的舞台)演出的头领(犬王父亲)的风头。以及演出结束后出自群众之口:“头领已经过时了,犬王比较创新。”“新的故事,舞台效果又好,歌舞都很有新鲜感。”等等对犬王演出的讨论可以看出二人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便已经收获了极佳的群众反响,可以说是二人的第一次加冕。二人的第一次加冕也随着犬王的胳膊恢复常态落下了帷幕。在第二幕犬王之作•《鲸》的表演伊始,“比叡座”的观众已寥寥无几,随着百姓出走祇园“要看比叡座就看犬王!”,大家纷纷前去清水舞台看犬王的表演:“我等不及要看了!”,即开场便表现出二人的加冕之势,最终犬王依旧展现出了惊艳的舞蹈,乘鲸而上,在背后鳞片的褪去中完成了再一次的加冕。
犬王及友渔的加冕之势就如同歌词一般:“就连近江比叡座的栋梁,也比不上的精彩表演,不断向上直冲天际。”二人凭借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全新故事和惊艳的舞台表演,迅速成为顶流。友渔随即创立了“友有座”势与犬王将二人的作品《犬王之卷》唱遍大街小巷。很快,二人开始出入贵族的宴请,获得了诸国的狂热支持,并且得到了时任幕府将军夫人的青睐,将军保利义满遂邀请二人在将军宴席上登台表演。“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觉一座竟然能到皇室表演。”琵琶法师能够得到为皇室表演的机会,可谓极尽荣耀,就连昔日为皇室表演的“观世座”也只能为“失宠”在台下暗自发恨。犬王与友渔二人从敝野的桥洞到步入宫廷皇室,这是一个典型的加冕过程。加冕即意味着脱冕,犬王表演时日食的出现,日月一体的设置在此时也颇具象征意义。随着皇室演出的谢幕,犬王成功破除诅咒,摘下面具蜕变为绝美的人形,在自我净化中完成了最终的加冕。然而,对抗主流并非没有代价,狂欢之后,随着平曲正本的修订,“当道座”升为官方正统,犬王的故事因有损将军威严被勒令禁止传唱,“友有座”也遭到灭门。当艺术的价值被否定,自我的实现被剥夺,犬王与友渔的人生才刚开始便已经结束。当然,狂欢式中没有绝对的否定,透过犬王和友渔的脱冕,我们看到了蕴含着创造意义的死亡形象和更新交替的精神,也预示着下一次的加冕,《犬王》也在结尾给出了答案:年少的藤若(“观世座”首领观阿弥的儿子)改名为世阿弥,并留下了多部著作与自作曲,为今日的能乐艺术奠定了基础。
在这“加冕—脱冕—加冕”的不断循环中,犬王与友渔二人荣辱无常的命运正是这一狂欢仪式更迭的象征性意义,从而彰显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一切都在循环交替的过程中演变。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加冕和脱冕,是合二而一的双重仪式,表现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也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1]160
三、人性之追求的场域:狂欢广场
狂欢广场,即狂欢节演出的广场,也指“文化意义得以延伸的符号场”。[2]在巴赫金的眼中,狂欢广场是一种全民性的、意义得以无限扩大和深化的场域。只要能为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提供相聚和社交的场所,就会被赋予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某种程度上是“底层民众、节日文化的荟萃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在这里等级制和“单一的权威话语”土崩瓦解,人成了自己的主宰,身体达到了自由自在的境界,生命欢快、自由吟唱。
《犬王》的故事发生在平安王朝覆灭,南北割据又统一的悲剧历史时期。王权衰落,朝代更迭的社会背景下,人民过着相对刻板常规、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在此背景之下,犬王与友渔二人凭借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故事、惊艳的舞台表演,俘获了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族的青睐,在诸国民众之间掀起了一场狂欢热潮。在第一幕表演<犬王卷>开场前,镜头对下层民众纺织、刨木架桥、制鼓等劳作场景的展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辛勤劳作、恪守常规的社会图景。表演开始,六條河桥上车水马龙、人群攒动,二人奇怪的装束,有悖世俗的“游女”妆容,吸引了无数群众驻足围观。现场随处可见的农民、工匠和商贩以及穿梭其中的武士和头戴纱笠的贵族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相聚在此还原了一个囊括各个阶级的狂欢广场。
犬王的演出结束,也引发了一场全民的激烈讨论:“新的故事,舞台效果又好,还要求观众跟他一起摆动手脚或拍手一起唱……”“犬王很有趣,我也跟着跳了,观众都在疯狂跳舞。”村口的孩童也都纷纷模仿犬王的舞蹈,甚至连上层贵族也开始在宴席上讨论起犬王的演出:“他还要求我们也一起跳舞!”,足以可见犬王与友渔二人的狂欢表演已经成了人民的日常娱乐活动。
在犬王之作•《鲸》的演出中,《犬王》对演出现场气氛可谓极尽渲染,在犬王表演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纷纷往台下“跳水”的观众(跳水/人群冲浪,即现代音乐节或者Live House上常见的活动,通常发生在乐迷密集的时候,一般跳水者站在舞台上或高处,仰面跃下,乐迷们用手支撑跳水者在头顶上方传递),聚光灯下,台下的观众共同托举传递着一名浑身布满女性唇印的赤身裸体的男子,透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由亲昵的全民狂欢广场。在这里没有等级、没有权威,也没有刻板与禁欲,人们相互间的距离消失,身体从世俗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呈现出一个普天同庆、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世界。夕阳伴着歌声落下,场景完成昼夜的转换,观众相约而至来看犬王的表演,表明了人民已经沉浸在这场不分昼夜的狂欢热潮之中。这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中断、官方生活的偏离,人们跳出一切世俗生活投入到犬王的表演之中,成为与日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第二种生活”(即巴赫金所指的“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在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室町幕府时代,当人们疲惫于世俗生活,一群穿着放荡不羁、曲风新奇洒脱,舞台效果绚丽夺目的怪人出现,便使人忘缺了所处的时代环境。《犬王》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为民众访寻了一种心理的慰藉和精神的宣泄,释放出一种生命的力量,从而消解了时代的严肃气氛。与此同时,这种“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也蕴含着反抗的力量。
演出《龙中将》,犬王和友渔从昔日的敝野来到严肃的将军幕府。“亡灵比以往还要兴奋。”犬王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改编平家故事,传递亡灵心声,帮助平家亡灵成佛升天。起初,犬王克制的表演,优雅曲风始终无法打动亡灵。为了完成“镇魂之约”,犬王与友渔不惜撕破伪装揭露真相,选择以抗争的姿态,一改表演伊始将军偏爱的优雅格调,以生命起舞。灯光闪起,帷幕拉开,伴随着快速的节奏,犬王尽情释放着属于自己的表演美学,镜头和灯光隐去了骄奢铺陈的将军府邸和贵族的在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热闹张扬的皇室表演上也许只有犬王与友渔两个在场者的生命之舞,使原本的皇室表演演变成一场为平家亡灵“镇魂”的狂欢仪式,是一种濒临末路的狂欢。二人所演唱的平曲,在幕府将军即将完成南北统一大业的特殊政治时期,不失为一种时代杂音,游离于官方主流价值之外,是巴赫金所指的广场语言:“在广场上充满了一种特殊的言语,无所拘束的言语,……与教会、宫廷、法庭、衙门的语言,与官方文学的语言,与统治阶级(特权阶层、贵族、高中级僧侣、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的语言大相径庭。”[3]广场语言与亡灵的在场增添了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使得庄严、肃穆的将军幕府变成了狂欢广场。演出结束后二人的命运快速陨灭,时间在狂欢,历史在狂舞,而命运却在狂笑。犬王宁愿吞下悲剧的恶果,也要以生命之舞完成镇魂之约,直至诅咒退散,自我净化蜕为人形,进而实现自我的救赎。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犬王对人性的追问和生命诉求过程中的原始样态,在含笑过去和送葬现在的同时更倾注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畸形的身体、僵化的一切活动起来,充溢着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创造精神。
结语
《犬王》中透露出浓重的狂欢化色彩,影片对犬王及友渔二人荣辱无常命运的解构,显现出“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更新”的一般规律,照应了狂欢仪式中的核心精神和感受;犬王虽诞生于诅咒,天生畸形,却仍怀着对人性的追问和生命诉求以生命起舞;对全民狂欢场景的极尽渲染,显示出对权威的消解、教条的颠覆,是自由生命的彰显,在遥远的历史长河里为民众访寻一种心理的慰藉和精神的宣泄,表现出对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一部寄寓着导演人文情怀和话语的诚意之作。如汤浅政明本人所语:“即使是强大而有才华的人,也可能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赏识,我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但一个人的成就终会被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注意到,那些成就将被传承和铭记,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狂欢外衣之下包裹着其对历史与当下生活的观照,寄托了作者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或许,这便是《犬王》这部动画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