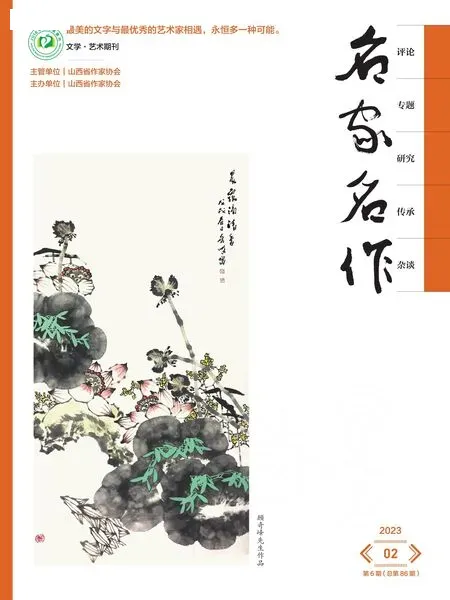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影对“伤痕文学”的赓续与突围
——以电影《牧马人》与小说《灵与肉》为例
2023-08-22陈胤竹
陈胤竹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学是电影的基础和源泉,电影则是文学的延续。麦克卢汉曾说:“一种媒介成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只有这样,它的效果才强大而持久。”[1]在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转换为以画面为载体的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影视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学作品的缺憾,并扩大其影响力。“伤痕文学”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旨在揭露这段时期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虽有着划时代的创新意义,但又容易落入过分夸大伤痛而忽略反思的陷阱。电影《牧马人》,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影片在保留原著的大体叙事框架与伦理基础上,对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总基调进行了微调。不同于原著大肆渲染的感伤基调,谢晋导演有意将人与人之间的许多日常温情巧妙地纳入影片叙事中,使主人公弃“肉”取“灵”的决定更加真实可感,亦突破了原著“伤痕文学”过于厚重的悲伤压抑,有效防止受众深陷悲伤情调而带来的反思欠缺。
一、不变的叙事伦理——个体生存叙事的赓续
所谓“叙事伦理”,是指“在叙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2]它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记忆,在个人的记忆图卷徐徐展开中所呈现的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借由叙事伦理,可以推测一个人对待生活与生命的态度。“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浪潮,它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引领了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弘扬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平凡俗人的生活悲歌取代了过去的英雄赞歌,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在十七年文学里,单个的、活生生的“人”被隐去,有的只是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群像,即使有零星几个大书特书的“人”也只能是伟人。个人的心灵世界以及小人物的生存处境被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伤痕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的出现。
(一)“ 小人物 ”命运书写
小说《灵与肉》与电影《牧马人》均把视线聚焦在了那位被下放农场劳作的许灵均身上,并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细腻深刻地展现了他的痛苦彷徨以及感受到的温暖。小说《牧马人》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了许灵均被下放到敕勒川劳作,受到了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的照顾,结识了美丽贤惠的妻子李秀芝。牧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温馨,后来,许灵均拒绝了父亲提出的送他去美国发展的机会,坚持留下来建设祖国的故事。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牧马人》亦保留了原著的大体框架,从许灵均的视角出发,重点展现了劳动对他精神品格的塑造以及劳动人民间那种淳朴、善良、互助的情感,淡化了原著那一份属于“伤痕文学”的哀愁,强化了爱国主义旋律。“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句反复在《牧马人》影片中出现的经典台词,生动地阐释了彼时人们革命的理想并非是面包牛奶,而是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凡俗生活。家庭世俗生活的温软甜蜜取代了革命的昂扬斗志,成为新的信仰。这种对世俗生活的信仰内在是新时期 “政治人” 向 “经济人”的转变,追求安全、自足、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而不是阶级队伍,被推向历史前台,以确立新的个体认同。不同于充斥着脱离现实生活的人物和情节,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样板戏电影”,《牧马人》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吐露人们经受苦难的心声,以写实的理念、真实的情感直面现实、抚慰重重伤痕。
(二)正视个体与社会的客观关系
谢晋导演常常谈起自己与好莱坞电影的密切关系,业内更是尊其为“半个好莱坞”导演。影片有着向观众传递正确价值观的责任。作为第三代导演中的“顶流”,谢晋导演熟练地将革命叙事和集体主义伦理与好莱坞叙事方法和镜语体系作了奇妙或者奇怪的搭配与杂交,进而成功地兼顾了好莱坞的英雄主义以及中国传统道德。伤痕文学受困于历史局限性,只是“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再者,“伤痕文学”的主创大多为活跃于十七年文学的作家,作为一种很深的历史“积淀”,作家对“主题”“题材”的迷恋以及对“思想立场”的敏感,对文学作品重大的社会意义的追求与固执坚守便在合理的想象与推理之中。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张贤亮的《灵与肉》在内容上大胆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人民群众带来沉重的伤害,但其创作原则仍在“十七年”的轨道上很自然地滑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依旧未能受到正确看待。
小说《灵与肉》出版后受到不少抨击,其矛头均指向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批评家们认为“作者抽象地谈论劳动,不加分析地颂扬这种劳动”[3],而对这种由于过往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劳动认可,实质上也是间接地肯定了血统论对许灵均的摧残,肯定了宿命的力量。与此同时,批评家们还强烈谴责许灵均与李秀芝的结合方式,“是一次在非人性的状况下的野蛮行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必然出现的婚配现象,结婚的双方事先没有任何了解,全凭一面而定”[4]。尽管围绕《灵与肉》展开的议题之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以今日的眼光回望那些曾针锋相对的论点,我们仍可发现《灵与肉》所体现出的“伤痕文学”缺点。张贤亮本人在相关采访中曾予以回应,自称是为了适应发表刊物的体量,大量删去了许灵均的心理描写,因而给了读者一种僵化死板的说教感,但其实许灵均的转变是在与人民群众的朝夕相处中逐渐进行的,并不能光归因于劳动本身。谢晋导演在影片《牧马人》中很好地发挥了人民群众对许灵均的精神教化作用,把个体的成长与蜕变融入人民群众的集体感化中。《牧马人》中,许灵均的牧场劳作生活被浓墨重彩地书写,牧场人民那种淳朴善良的性情得以充分彰显,许灵均在普通人民群众中重新找到“家”啦!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以及表情特写,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现了许灵均在农场的蜕变过程,劳动对他的塑造不再变得抽象,他那最终留在家乡的决定也不再被看作是为了迎合主流思想而刻意设定的结局。许灵均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建设家乡,是因为“我知道舍不得你的那些小学校里的孩子们,你舍不得老乡们,舍不得郭蹁子、董大爷,还有你舍不得它(中国)”。
虽然“伤痕文学”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政治惯性,但已经孕育着新的要素:正视个体与社会的客观关系,重视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提倡个体的转变来自“春风化雨”“日久天长”的缓慢改变,而非粗暴地归于一系列的硬性规定。
二、突围的叙事基调——性别身份的倒置与人性温情的增加
电影《牧马人》保留了小说《灵与肉》的大致叙事主题,主人公许灵均在淳朴牧民的关心照料下,在敕勒川度过了二十多年艰苦但幸福的时光。但在叙述基调上,不同于小说的低迷感伤,电影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浓浓温情。这些温情镜头的加入不仅能让许灵均坚守家乡的决定变得更加真实可感,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伤痕文学在性别创作领域的囹圄。“伤痕文学”创伤记忆的形象载体,往往是善良美丽的青春与底层女性,而有能力讲述这些记忆并由此成为历史主体的大写之“人”,基本是兼具知识者与老干部身份的男性。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尽管“伤痕文学”表面上书写和讴歌女性,但在这些性别化、自然化的女性表象背后,是男性知识者重构其历史主体性的力比多冲动。
(一)性别身份的倒置
“伤痕文学”中的女性诸如胡玉音、马缨花等民间女子,在知识者创伤记忆的书写中,同时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功能:她们既是历史创伤的承受者——受害者,也是救苦救难的抚慰者,还是受过文明熏陶的自然/原始之女的象征——自然人。胡玉音是南疆古镇的“芙蓉女”,而马缨花则是西北荒漠上的“绿化树”。革命年代的女性总是以健壮、乐观、向上的“铁姑娘”面貌出现,而“伤痕文学”中忧郁感伤、牺牲奉献、富有阴柔美的女性化形象,则是可视化模式的家国创伤记忆。这些不幸蒙难的弱女子亦是男性创作者对自己被冤屈经历的自我怜惜。况且,这种创伤记忆的性别书写方式本身也具有大众基础。
不同于小说中处处散发着母性光辉的李秀芝,电影中的李秀芝更偏向孩子气。小说中是这样描写两人的初次见面的:“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像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5]在小说的叙事中,李秀芝初次来到许灵均家中并没有多少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作为女主人的坦然。还未经许灵均应允,她已然把许灵均视为自己的夫君,缝缝补补地照料着这个辛酸的小家。李秀芝是这样的富有生气,使许灵均“突然想到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在许灵均眼里,李秀芝有着那匹曾经温暖过他心灵的棕色马的母性力量,仿佛她就是来拯救自己困苦生活的一位圣母,这是张贤亮小说惯用的“才子落难,佳人搭救”模式,小说中的许灵均在李秀芝母性般的温暖下感受到了幸福,以及以后发生的一个人脱土坯、栽白杨树、养家禽,李秀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主动的、富有创造力的母性形象。
(二)人性温情的增加
谢晋导演是一个十足的细节控,许多原著小说中的轻描淡写到了他的影片里变得浓墨重彩而绘声绘色。小说中鲜有许灵均受到的牧场人民照顾的直接描写,更多采用的是许灵均受到关怀后的心理状况反馈。“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而《牧马人》影片里却根据这句话,合理想象并增添了诸多牧民对许灵均的照顾情节。例如,郭大爷为许灵均的房子挂帘子挡风,郭大娘给许灵均做饭吃,安慰他“吃饱了,不想家”“人要往前看”。生产队全体成员提议给许灵均放三天婚假,并且众筹礼金助力许灵均与李秀芝建立起新的小家庭。许灵均放牧,李秀芝在家学写字,日记里娇嗔灵均“马都知道想家,人却不知道”。许灵均进城去北京,清清说:“爸爸是妈妈手里的风筝,无论飞得有多高,线都在妈妈手里”。这些充满生活气息与温情的话语举动,极大地丰富了影片内容,营造出温馨治愈的生活氛围,极大地扭转了原著《灵与肉》中过于重视发泄情感揭露苦痛的缺憾。
《灵与肉》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作者从一个小人物入手,采用个体生存叙事手法,深刻书写过往错误的大时代背景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创伤。但《灵与肉》也有着“伤痕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诸如人物形象过于扁平、缺乏细致情节而流于说教等。基于此,谢晋导演在拍摄其改编作品《牧马人》时有意淡化了原著的伤痛,增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抒发爱国主义赞歌。同时,打破“伤痕文学”惯有的“才子落难,佳人相救”的女性照顾者模式,进而转向了男性担当,实现了性别身份的倒置。虽然,以今日视角审视谢晋导演的创作,亦会发现其有着一定历史局限性,但与原著《灵与肉》相比,《牧马人》已经淡去了诸多说教而变得生动细腻了许多,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