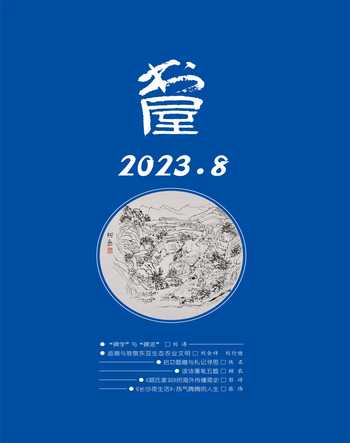《中印一家亲》自序
2023-08-21谭中
谭中
亲爱的读者们,我写这本书是经过一番犹豫的。世界各国名流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后写出自传或备忘录,使人们大开眼界,我这庸碌之辈似乎没有资格。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将要看到的文字像传记却称不上传记。那是什么呢?孔夫子两千多年前站在河旁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把自己活了九十年的人生比作长河,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我的“逝者如斯”的简单汇报。如果你们觉得有意思,那是因为它聚焦于“中印一家亲”这个重要课题。
1928年6月,我作为谭云山的种子来到人间(十个月以后才呱呱落地),父亲谭云山马上动身去了印度,到达印度时被当作中国文明的使者受到欢迎。1955年,我到达印度的情形也相类似。1967年,父亲退休。1971年,我担任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印度官方与民间把对谭云山中文水平的信任与了解中国的重任逐渐转移到我身上,我作为谭云山的长子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使得谭云山九十年前开创的“中印一家亲”道路没有因为他1983年去世而荒芜,我从父亲手中接过棒,成为在印度中国学领域的领跑队的成员之一。
我虽然在二十世纪末退休并定居美国,但从来没有退出由泰戈尔与谭云山开创的联合中、印两大文明实现“世界一家”理想的大业。谭云山入印九十周年使我平庸的“逝者如斯”有了意义,谭云山开创了“中印一家亲”道路,做出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他身心的每个细胞都发出了“中印一家亲”的异彩,可惜他没有留下自传或备忘录,他那“中印一家亲”的异彩随着他的逝世而永远消失了。这“中印一家亲”的异彩在我身上也有,我想要避免让它在我死后消失,所以应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构成了我写自己的“逝者如斯”的动机。
亲爱的读者们,请别误会。我不是说谭某父子两代象征了“中印一家亲”道路,我也不同意那種认为拓宽“中印一家亲”道路绕不开谭云山父子的说法。“中印一家亲”不是什么人的私有财产或专利,“中印一家亲”是历史发展规律,是时代的必然走向。谭氏父子只不过是“中印一家亲”道路上的先行者,单靠两个人四条腿是走不出康庄大道的。现在的问题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太少,应该动员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这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目的。
因为很少人提倡,“中印一家亲”这个概念在中国还不普遍。当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不是太好,使人们很难想到“中印一家亲”的方向上去。泰戈尔说,作为诗人,他的任务是要聆听生活中那些常人听不见的声音,把它们播送给常人。我写这本书正是希望对一种对“常人听不见的声音”做一点传播。父亲谭云山的家训加上我从梁启超、陈寅恪、向达、季羡林等大师的著作中得到的领悟,使我有了“中印一家亲”的理性知识。我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从亲身经历中得到“中印一家亲”的感性知识。这样,我写这本书就动力十足。
2017年11月,印度和平乡国际大学举行盛大的庆祝中国学院创办八十周年与谭云山入印九十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特别邀请我参加。参加这一盛会的有五十多位中国学者,许多都很年轻。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印民间交往已经形成较大气候。
2018年11月,与我六十五年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终身伴侣黄绮淑去世,中、印两国许多亲朋好友发来悼唁,交口称赞她不想自己、只顾别人的美德,使我这个摆脱不掉“我执”的老朽茅塞顿开,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离不开爱人绮淑的巨大投入。
印度友人希夫尚卡尔·梅农(曾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内阁的国家安全顾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受教于我们的德里大学中文班学生。他在悼唁中这样回忆我的爱人绮淑:“对我们大家来说,她不只是老师。她以身作则以及对我们的勉励对我们的影响如此之大。在我们成长的阶段,她经常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提醒我们重视生活要义,更使我们体会中国文化活生生的美丽。”
亲爱的读者们,印度友人(学生)寄来的这几句话——他内心深藏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回忆——使我既兴奋又惭愧。我在印度主要的业绩是教中文与介绍中国文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里大学中文班是我创办的,因为有点成绩使我也出了名。当时爱人绮淑帮忙参与其中,不,应该说是爱人绮淑和我的共同业绩!可是上面梅农所描写的我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我却是才刚刚知道。我心里想,当时如果没有爱人绮淑对学生梅农和其他人的那种感染力,我是否会在印度出名还得打个问号。那就是说,她实际上是我一生事业光明的电源。
这样看来,我的“逝者如斯”是我和爱人绮淑共同的“逝者如斯”,我没有把它藏之于己的权利,只有把它公之于世的义务。我的“逝者如斯”就非写不可了。
亲爱的读者们,我在书中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再加一些照片作证。照片是照相机的产品(不出于我的头脑),它既不隐瞒也不捏造,增加了事实的可信度,减少了文字的枯燥感。有了照片就有了故事的参与感与形象感。请你们翻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