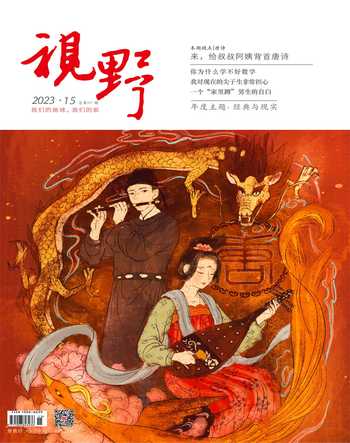来,给叔叔阿姨背首唐诗
2023-08-14黄晓丹
黄晓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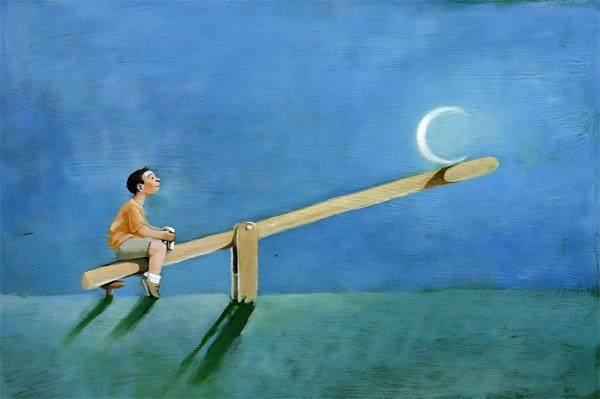
小朋友童年都有一个噩梦——给叔叔阿姨背一首唐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让人习以为常了,在我自己是个小朋友的时候,也经常被爸爸妈妈拉出来给叔叔阿姨表演背唐诗。但是你如果现在问我,这样做对小朋友好不好?我会说不好。
为什么不好?从我自己的记忆来说,当我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想要背唐诗,也不是对着任何人都愿意背唐诗。当众表演背唐诗这件事情,其实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哪怕背完之后大人会说这个小朋友真聪明。
在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就很明确地知道,一个想听我背唐诗的大人,并不想和我真正地交流。我之所以不得不背,只是因为年纪还小,没有办法拒绝大人的要求而已。
当我渐渐长大,我就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策略,把我会背的那些诗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表演用的,一部分属于我自己。对于表演用的那一部分,其实我关闭了对它的感觉,所以叫我背我就背,就好像在背乘法口诀表一样不带感情。而属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我就不让大人知道,以免他们让我表演。那些我小时候表演时背得最多的诗词,到现在我都对它们没有感觉。
我的师兄钟锦,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副教授,有一篇采访稿的名字叫做《他说太精妙的古诗词,不要让孩子过早接触》。为什么呢?他在里面讲到,小时候他的父亲会逼他背许多诗,虽然他到现在也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情感上很难产生共鸣。他还说,他整个小学都在背诗,背一首就会抄在本子上,虽然抄了四五本,但是用处并不大。
最后他援引我们的老师叶嘉莹先生的话说:“人的心灵大概也和肉体一样,是可以因日久摩擦而起茧子的!”
所以如果在孩子的感悟力还没有完全自主的时候向他们教授诗词,即使之后感悟力日趋成熟,孩子也会因为对作品太过熟悉而无法敏锐地体会其中的情感。我看了这个访谈之后就特别高兴,觉得“哎,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子,原来我们的童年经验都差不多呀”。
我和我这个师兄虽然都是从小就背古诗词,可是我们后来都有一个阶段,是重新自主地去阅读那些古诗词的选本,然后选出那些对我们自己来说有感觉的诗词。对我们来说,这一部分诗词才是打开古典文学大门的钥匙,并且这个过程是背着父母完成的。
后来为什么我们都选择了以古典文学为专业?我想是因为古典文学参与了我们的自我的建立过程,它让我们最初体验到“我是一个独特而自主的人”。这个道理就和有些人为什么选择计算机为专业一样,是因为计算机让他最初体验到自己是不同于父母的一个独特、自由的人。
表演
这里,我想分解表演背古诗词的过程,看看在這个过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真正互动又是怎么样的。
首先,背诵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而且与孩子们在学校里面进行的考试相比,这种背诵测试是突发的、任意的、公开的。不管这个孩子上一秒钟在吃什么饭或者玩什么游戏,只要大人忽然想到,就可以把他拉出来表演背诵。这当然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约翰·霍特写的《孩子为何失败》这本书里有一章就讲到测验的害处。作者说:
焦虑的孩子经常感到被测试,他们对失败惩罚丢脸的担心,严重削弱了他们感知和记忆的能力,逼得他们逃离学习材料。
在这位作者的另一本书《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中,他更详细地解释了测试的害处:
第一是说测试会给孩子压力,让他们去猜测大人要的内容,而不是自己感受到的内容;
第二是说不停地测试,向孩子传递了一种“我对你到底有没有掌握这个知识没有信心”的感受。
这两点说得当然对,但它并不是直接针对背诵测试而言的,我们怎样把这样的洞识聚焦在当众背唐诗这件事上呢?
我想可能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都默写过诗词,我们知道在默写过程中,有时记忆会忽然卡壳,有可能要先写出下句才想得起上句。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一首诗都回忆出来,我们还是一百分。
可是当众背诵的过程,特别是在一群没有耐心、随时都可能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的大人面前,一个停顿、一句话顺序的倒错都可能马上被指出、被提示、被更正,从而让背诵者感到挫败。
小朋友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到非常沮丧,变得结结巴巴,甚至逃走。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逃避办法,就是从此之后拒绝背诵一切古诗词,甚至为了避免当众背诵,干脆就不再学习古诗词。如果我们学习的某件东西,会使我们有当众出丑的可能,我们的学习热情一定就不会高。
作为大人,如果有人带着考考我的态度要求我背诵某一首诗词,我会感到不舒服;如果有人当众要求我背诵,我更会视之为挑衅。
既然大人是这样的感觉,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小朋友感觉不到呢?
功能
为什么当众背诵古诗词会败坏小朋友对于诗歌的兴趣?这要从诗歌的功能谈起。
诗歌是用来干什么的?在中国历史上对诗歌的功能有很多不同的学说,但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就是用于自我表达的诗歌更好,而用于表演的诗歌是比较差的。甚至在严肃的文学研究中,那些用于表演的诗歌都不太被提及,哪怕有时候提到也是作为反例。
所以在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有一个最基础的评判标准,就是你写这首诗到底是表达你的真情实感,还是用于应酬。
有些用于应酬的诗从技巧上看也很好,比如初唐的应制诗、明代的台阁体,但是所有的批评家都不会把它视为最经典的那一类诗歌,因为它没有表达个人的独特感受,或者说它不够真诚。这些批评家是说好了的吗?他们为什么都这么看呢?因为“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左传》中,就提出了“诗以言志”这句话;在大约公元前五世纪的《尚书·虞书·舜典》中,有更明确的表述,叫做“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几段重要的文论,都是在讲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产生的原因。
大致的意思就是,你心中有所感就会想把它表达出来,不表达出来你就不舒服。而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真情实感,就变成了诗。
如果你已经把内心的感受语言化变成诗了,但你觉得内在还有东西没有表达出来,就歌唱它,它就变成了歌,因此歌的源头也是内心的真情实感。
如果你唱了歌,但你觉得内在还有东西没有表达出来,那你就用你的身体来舞动,它就变成了舞蹈,因此舞蹈的源头也是内心的真情实感。
因为中国古人把所有这些艺术形式的源头都视为个人的真情实感,并认为不是作者先存在了一个想要去写一首诗、去唱一支歌、去创作一个舞蹈的念头,而是他们心中有藏不住的情感,这些情感自然流露出来,就成为了真诗。
所以在后来的文学批评中,不但有“言志诗”和“应酬诗”的高下之分,还有“真诗”和“假诗”的天壤之别。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陈子昂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为什么这首诗的地位这么高?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写应酬诗,虽然写得花里胡哨,看起来技巧很好,但是当陈子昂写出这首更真诚、更能表达自己个人体验的诗时,其他诗就都被比下去了。
感受
我讲这些和让小朋友当众背古诗有什么关系呢?
继续讲讲我自己的尴尬经历。在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吃喜酒或者吃人家的寿酒,吃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就会把我抓出來背古诗词。那时候他们特别喜欢让我背的几首诗词,比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就很尴尬了。因为这些酒席的氛围都是非常快乐的,这样快乐的氛围根本不适合这些诗词。
作为一个词的背诵者,如果我要忠实于这些词的真实体验感受,比如忠实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那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遗憾之感,就等于在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等于在说“别看我们今天欢聚在一起,可是谁知道这一次宴席之后,大家又会经历什么样的生离死别”。
如果一个小朋友在他的背诵中真的把这种感受传递出来,那他大概要被打了,因为他实在是太扫兴了,而且有可能会被视为“乌鸦嘴”。
如果他背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更是在结尾处把情绪一下子从高潮降落到很低的低谷,最后得出人生如梦、早生华发的感慨。也就是说,这是一首怀疑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诗词,这个意思小朋友不一定说得出来,可是这种感受小朋友是可以感觉到的。
这时他就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他忠实于自己从这首诗词中真正感受到的东西,那他的背诵就是不受欢迎的;而如果他选择满足大人们的期待,把诗词背诵得像大人们喜欢听的那种欢快的样子,他就得屏蔽自己对这首诗词的真正感受。
按照我们前面所说中国人对诗歌以及一切艺术形式的定义,当你屏蔽了对作品的真正感受时,这个作品的意义对你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似乎会带来一个悲剧,就是你当众表演背诵哪一首诗词,你就会失去那首诗词。我和我师兄的经历都佐证了这个定律!
有些家长可能要问,孩子们真的能够理解诗词中这些微妙的感受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我相信语言不仅仅传达了认知信息,还传达了情绪信息。
在中国的诗论和词论中,有一部分讲诗词作法,讲诗词的用韵和节奏。在这部分理论中讲得很清楚,说某些音节、某些韵脚就自然传递某种情感,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连用七个入声的叠词,传递了非常妻凉的情感,这种情感是靠声音而不是靠内容来传递的。
我们都知道写诗的时候,最好在声音和内容上都比较合拍。所以我怀疑在阅读诗歌,尤其是中国诗歌的时候,小朋友们可以在不完全了解诗歌内容的同时,仅仅从声音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情绪。而且事实上我们倡导学习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声音和形象的直观感受来增加对汉语的敏感性。所以如果你坚持认为小朋友不能懂得这些诗歌所传达的情感,那你也就没有必要来让他学习诗歌了。
再次回到让小朋友在公众场合表演背诵诗歌这一个主题上。
公众场合既然是一个场,它就有这个场自身的强大情绪。而小朋友为了符合这个气场对他的期待,就只能屏蔽自己对这首诗歌真正的情绪感受。这会使得他离自己的情绪很远,离诗歌的本质也很远。因此这样的方式对他的诗歌学习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诗歌教学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提升学生的修养,让他从表面上看起来像个能够引经据典的有文化的人,而是把诗歌作为一个媒介,让他学会更好地感受和表达自己的体验,同时理解他人的体验。
因此,当一个孩子能够当众背诵诗歌的时候,他和诗歌建立的关系未必是真诚可靠的。只有当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或者在他的心里暗暗藏下一首诗歌的时候,他才和诗歌建立了一种真正亲密、永恒的关系。如果你们观察到自己的孩子愿意阅读诗歌,但是不愿意当众背诵诗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这是他们在捍卫自己和诗歌之间的真诚的关系。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