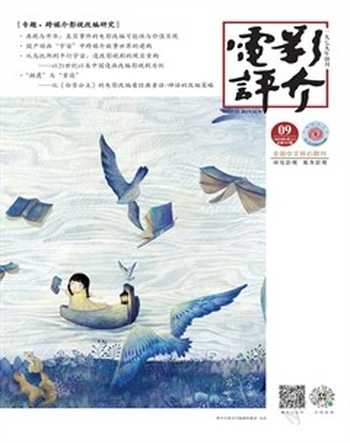从乌托邦到平行宇宙:漫改影视剧的现实重构
2023-08-09沙扬石翊之
沙扬 石翊之
漫改影视剧指基于漫画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漫画作品的主题、人物、故事、情境和叙事风格是影视再创作的根基。影视视听语言的审美范式是漫画作品改编的约束,也可能借鉴漫画的美学风格实现自身的发展升级。漫画所独有的静态图像审美符号系统,决定了其在创造艺术真实方面强大的夸张力和高度的凝练性,从而在对现实生活的解读与表达上别具深意,能引领读者接受某种程度上的现实重构。以“现实的渐近线”确立自身美学属性的电影和以戏剧冲突为核心驱动力的电视剧,目前虽然还无法百分百还原漫画里天马行空的视觉狂想,但仍探求在遵循本体属性的前提下,把独属漫画的对艺术真实的创造和对生活现实的表达进行二次塑造,从而达成新一轮的现实重构。
本文通过初步梳理2000年至今中国漫画改编的影视剧,着重分析和比较漫改影视剧的叙事时空如何对“现实世界”进行搬演、延展、突破、颠覆,并以“乌托邦”和“平行宇宙”两个概念为切入点,尝试探求中国漫改影视剧在现实重构层面的特征。
一、重构现实的漫长旅程:从现实生活到艺术真实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的摘要里写道:“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费尔巴哈在对比艺术和宗教时也提到艺术虽然“给了我们现实的假象,但并不能认为这假象就是现实本身”,而且艺术还“要求它所制造的影像能象真,能符合所表现的对象,能美丽”[1]。生活现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是艺术创作要解决的一对根本矛盾。重构现实即在此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并持续延展了其多样性。
漫改影视剧一方面须将漫画的幻境世界落地,让场景、设定、主人公的情感、困境等元素在艺术真实中找到落脚点;另一方面又须牢牢守护漫画主人公的美梦,不断为她(他)重建精神园地,使她(他)在不同的世界安家。20世纪50年代初,在冷战阴云中诞生的以超能力英雄漫画为改编蓝本的电视剧放大了漫画对超越人类身体极限和多元宇宙时空的幻想式救赎神话,为美国超级英雄类漫改影视剧奠定了生命力绵长且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传播通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级日剧《排球女将》《东京爱情故事》、风靡亚洲被多地改编的《花样男子》、引发社会热议的《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等根据日韩漫画改编的影视剧则从漫画原作中成功提取并杂糅了青春、纯爱、职场等叙事类型,为泡沫经济繁盛期的亚洲文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倒影。
国内漫画改编影视剧的发端不算晚。1949年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即改编自张乐平先生的同名漫画。该片和漫画原作均收获了广泛好评,流浪的“三毛”成为一代影史经典,为国内漫改电影确立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标杆;20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在深受日漫流行文化影响的基础上,拍摄了改编自中国香港本土漫画家马荣成作品的同名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中华英雄》。这类漫改影视剧不仅实现了武侠、奇幻、励志、喜剧等题材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担当了在新形态影视作品中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任,为中国漫改影视剧寻找自身属性、走向国际市场开辟了宝贵的阵地。
21世纪开始,中国大陆与中国港台地区联手推出漫改影视剧渐趋热潮。以当代校园为背景的《流星花园》《恶作剧之吻》成为青春偶像剧的标杆;以几米、朱德庸漫画改编的都市爱情剧《地下铁》《粉红女郎》也独树一帜、发人深省;还有围绕某一现实行业或技能展开的电影《头文字D》(以赛车手为讲述对象)、电视剧《中华小当家》(以厨师为讲述对象)、《网球王子》(以网球选手为讲述对象)也引发年轻人追捧。近十年来,以生活题材与现实话题为引领的国产漫改影视剧大放异彩,示范了崭新的创作路径。以《滚蛋吧!肿瘤君》《快把我哥带走》为代表的新近漫改电影展现了生活化、接地气的特征,影片的故事世界与变化中的现实世界保持着强烈的互文性。[2]
二、“乌托邦”的超现实想象:秩序解体与理想至上
柏拉图认为乌托邦(Utopia)源自人理想化的想象,意指“空想的国家”,可以承载灵魂栖息的家园。德裔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则深入地解释了乌托邦的意义:所谓乌托邦,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人们需要“乌托邦”去破坏既有与陈腐,去展示新生与将来,它的萌生点常常是非理性的向往與假想。值得一提的是,乌托邦必然是以突破集体潜意识、突破个人思维定势、突破原有的社会规范的个体的思维成果来启动的。[3]
国内漫改影视剧构建的故事世界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呼应了乌托邦的特点:美好的理想,秩序的突破。“乌托邦”是漫改影视剧进行现实重构最普遍的态势,漫改影视剧中的乌托邦图景,既是超越现实秩序的想象式筑建,也是面向未知未来的理想化寄寓。
(一)真实在场:奇观化景象筑建乌托邦式超验世界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乌托邦被用来描写试图实现某些理论的尝试,被用来表示某些美好的、但是极难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漫改影视剧中时常充斥着无法实现的客观情境,包括不符合常理的现象和不受自然约束的设定。漫改影视剧的世界里似乎不用全然遵循科学规律,疾驰而过的赛车与山路擦出剧烈的电光火石,百投百中的空心球,一只脚能踩碎一幢楼的庞然巨物,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物都带有“神奇”的色彩,相较现实有着奇观化的景观。同时,漫改影视剧与现实世界相左的是,这个世界里真正的“普通人”是稀少的、不被书写的,大多数漫画的主人公都携带异于常人的禀赋,或拥有某些隐秘的特殊技能,或拥有超越一般人的精气神和感知力。例如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漫画改编电影,包括《超人》《x战警》《蝙蝠侠》等,得益于漫画原作本身带有科幻色彩和未来主义的审美范式,在好莱坞成熟电影工业系统的加持之下,通过精湛的视觉特效手段将这种科幻未来感充分落地,包括鲜明的主人公造型、大量特殊的道具、光怪陆离的特效、赛博城市的景观建模等等,甚至原漫画并没有描述的部分在漫改影视剧中也得到了精妙的补充。国内漫改影视剧对于超现实世界观的塑造已比较成熟,2018年韩延执导的国产漫改电影《动物世界》以高水准的工业化制作和特效画面令观众耳目一新。该片打破了二维平面漫改常见的卡通化风格,给观众营造了沉浸式立体感的游戏化体验,尤其体现在主人公闯关的过程中:快速剪辑配合牌面转换的眼花缭乱,奇幻世界骤然下坠的失重感,主人公身后场景地动山摇的晕眩感。紧张和刺激贯穿电影始末,绚烂的场景、精密的特效、逼真的视听,让这个并不存在的奇幻世界充满说服力。
相比漫画作品,漫改影视剧超现实化的元素能够带给人强烈的“在场感”“沉浸感”,简言之,它能够塑造一个完成度更高的烏托邦。漫画中的超现实情境往往通过夸张的线条勾勒、丰富的色彩等绘画手段来呈现,或者以人像浮夸的反应、表情来侧面烘托,因而漫画世界里超现实的特效过分依赖于观众的“想象”和作品前期在叙事上的铺垫;而影视这门高度科技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艺术,能够依靠特有的视听语言和成熟的技术手段,弥合从二维到三维的媒介差异,把原本只能在脑中上演的“超能力”直接搬演到观众眼前,在观众的想象空间里挥毫泼墨,带来无比震撼的视听体验。至此,漫改影视剧创设了超现实的理想化奇观世界,着眼于破旧立新,彻底完成对现实的重构。
这样的书写延续了漫画的创造力、想象力、洞察力,依托数字技术呈现出“意念的自由释放”的间离世界,将现实陌生化为“超现实感”的景观[4],打破了现实世界的常规秩序并与现实割裂,构造出具象的乌托邦性质的超验世界。让观众体验片刻“不可能完成的理想”,沉浸在仿若绝对美好的“现实”中。
(二)美梦成真:大团圆叙事寄寓乌托邦式精神园地
漫改影视剧承袭了漫画艺术自诞生以来便有的讽刺、抒情、娱乐功能,漫改影视剧的情感底色通常鲜明而趋于极致,不吝于放大浓墨重彩的意志表达。
国内大量漫改影视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描绘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园地,着眼于价值观、感情观的书写。如果说影视的视听技术能够从物质方面完成乌托邦式的现实重构,那么叙事和价值观的重塑则能够让漫改影视剧在精神内核方面完成乌托邦的加强版书写,比如:歌颂勇敢、励志、团结、热血、有情人终成眷属、天赋才华不被辜负、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的理想化世界,用浪漫主义的方式解决现实主义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乌托邦必然是以突破集体潜意识、突破个人思维定势、突破原有的社会规范的个体的思维成果来启动的。[5]因而乌托邦式的精神投射不仅指向自由、平等,更指向对规则的突破,在漫改影视剧中表现为反秩序、创造力、反抗精神,最显著的表现方式即是“落魄天才逆袭”的叙事。
由刘伟强和麦兆辉联合导演的电影《头文字D》,改编自日本漫画家重野秀一的同名漫画集,讲述了周杰伦饰演的藤原拓海通过开车运豆腐,到成长为“飘移”神车手并打败一众赛车高手的故事。这部漫改电影作为典型的落魄天才逆袭的故事,将乌托邦式的精神意志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藤原拓海被塑造成一个幸运的天赋型选手,他并未接受系统的训练,而是通过每天运送豆腐,剑走偏锋地成长为拥有高超车技的车手,实力的练就过程是打破常规、出人意料的。他背后还有一个曾是秋名山飘移车神的父亲在保驾护航,可见他与赛车有一定的家族渊源,并不是一个与赛车毫不相关的真正的普通人。人物出场基调类似于明珠蒙尘的“天选之子”,尽管开局落魄,但他的逆袭是可被预见的。而后他的逆袭之路也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人物并没有强烈的“赢”的主观动机,弱化了“竞争”和“野心”这两个中性特质,于是,不把输赢放在心上的天才赢家又被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这是一个美好的、纯粹的、理想化的天才人物,他身上迸发着通向希望和未来的炽热力量,不切实际但引人向往,与乌托邦式美好虚幻的理想精神不谋而合;其次,藤原拓海打败的赛车高手纷纷大有来头:高桥凉介是深藏不露的超群赛车手,同时还是医学高材生。中里毅的座驾是价值不菲的GTR。他们大多为职业赛车手或拥有配置极高的座驾,而藤原拓海则是名不见经传的落魄草根,拓海无意间的胜利让高手们纷纷傻眼,正映射了一种反抗精神,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打破原有的比赛格局、强者壁垒,突破了高配置赛车精英才能赢得比赛的集体潜意识、突破了小人物不成器的思维定势,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式的敢于突破规则、摧毁秩序的精神力量。
乌托邦式精神在恋爱题材的漫改影视剧中也表现得很突出。2000年以来中国台湾地区涌现了一大批现象级偶像剧,绝大部分都改编自漫画,如《流星花园》《花样少年少女》《战神》《恶魔在身边》《公主小妹》等,在这些漫改影视剧中男女主人公通常会战胜身份、阶层、贫富、伦理的重重困难,最终携手相伴。剧中的爱情往往与无所畏惧的勇气捆绑,遵循着爱能战胜一切的简单逻辑。富人与穷人、优等生和后进生、(名义上的)哥哥与妹妹的结合,相比公主王子式“门当户对”顺理成章的童话叙事,既显现了浪漫美好的童话色彩,又隐含了一定的先锋性、革命性意义,带有醒目的乌托邦式精神质素。这些漫改偶像剧的可贵之处在于,让观众看到世界上至少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可以跨越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松动原本牢不可破的规则。
漫改影视剧缔造了乌托邦式的精神园地,让观众得以栖息其中并获得简单、安全、温暖的力量,让纯粹的感动直达心底,而这种精心设计的美好仅供应情绪、描绘理想,却没有分享通达的路径、生活的解法,导致其对现实意志精神的重构存在局限性。局限之一在于,回避或弱化现实困境的残酷性、悲剧性,不主动提出有参考价值的解决办法。横向比较亚洲各地区对日本漫画家神尾叶子漫画作品《花样男子》的改编剧集,同样讲述了男女主人公跨越阶级、贫富相爱的故事,中国大陆两版(《一起来看流星雨》《新流星花园》)选择有意弱化这种差距,而韩国版《花样男子》、泰国版《流星花园》则刻画了阶级壁垒,尤其泰国版大肆渲染F4的“权贵”“上流”,从演员的选择到服化道的描摹都较为精致时尚。但无论是选择性地忽略这种阶级前提,还是美化上流阶级、书写权贵想象,都会使得重构更像一种遮蔽;局限之二在于,进一步夸大了单一的情感力量。上述影视剧通常将胜利和美满寄希望于某一强大的精神动力,比如真爱战胜一切、热爱就能成功,容易带来唯心主义的嫌疑。《花样男子》的漫改剧蒙上了青春校园的精美光晕,俊男靓女爱得轰轰烈烈,反而使得校园霸凌、阶级差距等问题隐身。问题得到消弭的办法是:强者最终会被弱者“征服”,从而停止对弱者的伤害。这种逻辑的狭隘在于,对爱情寄予了虚高的期待和要求,既片面地忽视了爱情的瞬息万变、更无视了人性的复杂。
三、“平行宇宙”的类现实书写:秩序再造与多元价值
乌托邦的概念虽然极致,但在漫改影视剧中仍未形成一个独立于此时此刻的時空结构,其对现实的重构不妨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嵌融合式的。“平行宇宙”层出不穷的叙事打破了现实生活的“第四堵墙”,让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数量拥有几何级增长的合法性。
“平行宇宙”的概念由“可能世界”发展而来,也就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每种可能性导致了不同的后果”。[6]“平行宇宙”也罢,“多重时空”也罢,都是指某个或多个与我们身处其中的此地此刻,并行而客观独立的物质世界。在那个或多个并行而独立的世界里,重构的戏码也在并行发生着,且始终与变化中的现实世界保持着强烈的互文关系。漫画原作将一个个凝固瞬间展现出来的多重时空,在改编影视剧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些与此时此地共存的多重时空,对现实搬演而不照搬、延展而不依附、隐喻而不复刻,在遵守现实秩序的同时开拓了无限可能,以辩证的取舍完成对现实的重构,塑造了“既相似又不同”的“类现实”世界。故事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或者心理过程,如果在叙事中得到独立的表现,也可以视为漫改影视剧中平行宇宙叙事的一种变体。
相比上文中乌托邦指向的解构秩序、美满结局,在平行宇宙语境下无论是时空背景的移转、人的行为与关系、人做出的选择、发生的事件,都遵循着秩序和逻辑,这里的“秩序”既可以是现实的法则,也可以是故事世界中崭新的秩序。究其根本,平行宇宙应该顺应、完善秩序,而非颠覆、突破。在已知的秩序下,不放弃探寻出路,让观众在人物的抉择之间对现实的求索愈辨愈明。可以说,秩序性是国内平行宇宙式漫改叙事的底层逻辑。
(一)基于现实逻辑展开辩证性反思
平行宇宙式漫改影视剧故事的展开主动将自身置于有约束、有限度的规则之下,而不是在一片荒茫无度的旷野里随心所欲。平行宇宙的世界观始终遵循一种有度可依、无可遁逃的现实性底层逻辑。
改编自漫画家幽·灵姐妹同名漫画的电影《快把我哥带走》中,当妹妹时秒许下希望哥哥消失的愿望,并成功切换到另一种人生后,她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万事大吉无忧无虑,她的父母依然坚定地选择离婚。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无论许愿多少次人生重启,她都要与注定的现实困境会合。以平行宇宙的多重身份重审相似的现实困境,看似无论悲观到何种地步都无法避免被卷入人生的困境,但是平行宇宙的设计给予故事主人公全新的视角,帮助故事里和故事外的人看清真相。时秒在失去“妹妹”这一身份后,从原来一叶障目的生活中抽离,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荒诞不经的哥哥时分对自己的呵护和关爱,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沉浸在看似烦恼,实则幸福的“被保护者”的处境中,终于敢于向父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需求,也接受了父母必然要分开的事实。不违背现实的必然逻辑,不试图突破人物和背景的局限性,而是以转换视角的方式对现实进行辩证性反思,这是典型的平行宇宙漫改影视剧的内在秩序。
相比于用乌托邦为观众提供短暂的进入理想世界的通道,中国大部分漫改影视剧的平行宇宙设定旨在交给观众开启另一种活法的开关,引导观众换一个视角来直面现实生活,尊重利弊与共的现实境况,在困境之外寻求生机。相比于乌托邦的“遮蔽”式重构,中国大部分漫改影视剧的平行宇宙故事世界既不回避主流的社会运行规则、没有彻底解构秩序,也不忽视规则内部存在的结构性漏洞、滑向浮于表面的伪现实书写,而是扎根既有秩序加以反思,形成辩证性的现实重构。
(二)直面现实困境提供多元解法
平行宇宙式漫改影视剧以“漫画”为皮肉,现实为骨血,用漫画式绚烂多样的手段演绎了触及现实的生活真相,拥抱真实生活的鲜活琐碎,接受现实世界的矛盾和无常。平行宇宙的故事尝试着用多样的价值观和积极、开放的姿态寻找必然的现实问题的解法。
根据熊顿同名漫画改编、由韩延执导的漫改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中,癌症患者熊顿与病魔抗争的过程是通过浪漫喜剧的方式呈现的,并非以乐衬哀的反向抒情,而是将乐观积极的态度扎扎实实地倾注到了人物身上。电影在形式上参考了漫画的夸张属性来制造笑料,借鉴了漫画中人物拥有“Q版”第二人格的办法,启用“白日梦”“内心小剧场”等设定让演员可以从主线剧情中短暂抽离,以自我剖析式的独白、夸张化的表演来充分外化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充斥在主人公熊顿日常生活中的无数个梦境就像可以随时开启的任意门,穿过这一扇扇门即可来到平行宇宙,熊顿在数不清的平行宇宙里完成对现实的“吐槽”、发泄、延宕和解构,从平行宇宙喘息归来,她满载而归的勇气和乐观,又能够支撑她直面生活的一次次重锤。在熊顿第一次住院醒来前插入了一段诙谐的枪战戏,这是熊顿化身双枪女侠的梦境空间,给予人物点亮勇气的注脚,这是代表“勇敢”的平行宇宙;影片中间部分熊顿结识隔壁床的病友夏梦后,则用一段假想的清宫戏表现了熊顿的内心小剧场,在想象中熊顿跪服在夏梦塌前滑稽式地讨好,表达了熊顿被夏梦的气场震慑到的紧张和崇拜,透露了她想要主动与夏梦结交友谊的自我鼓励,这是代表“友善”的平行世界。每一段短暂的平行宇宙,都是熊顿内心一种积极的自我投射和现实演示,她用幽默、开放的姿态消解现实的难关、消化现实的痛感。“平行宇宙”是熊顿面对有时稍显残酷的现实,获得力量的来源和自我拯救的办法,是属于熊顿的人生哲学。
漫改影视剧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讨论着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内耗、抛弃现实的决绝之外,有没有可能存在其他的解决办法。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自己坦诚、对生活尽力。片中平行宇宙的意义不在于充当现实的无痛副本,而是当无常来临时,给人一个开启多重宇宙的机会,用一种最特别的方式活出自我。
或许可以把平行宇宙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千万种镜像,平行宇宙的故事世界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多元的解决构想,但有时也不得不面临现实两难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漫威漫画改编的电影中,《蜘蛛侠》系列最为特别,“蜘蛛侠”彼得·帕克作为漫威宇宙中少有的隐藏英雄身份的角色,尽管拥有飞天遁地的超能力,但仍然面临着学业、爱情等令同龄人困顿的难题。他落魄、贫困、不被赏识,活生生地演绎出超级英雄在平行宇宙中的B面人生,他艰难地生活在普通琐碎的生活和英雄救世的传奇缝隙之中,选择平凡的生活就要放下每一次路见不平的责任感;选择穿上战袍成为英雄,就要牺牲正常的人生和情感;接受一团乱麻的琐碎小事、接受心动女生的离去、接受在众人面前隐姓埋名的落差与落寞,平行宇宙中的故事和身份永远无法相交。《蜘蛛侠》第一部讨论的是当你被赋予力量时,你应该怎样使用它;第二部则讨论了一个更为极致的情境:当你被赋予责任时,你会选择承担并牺牲还是丢弃它,这是许多人同样面临着的现实困境。彼得·帕克在第二部中尝试选择丢弃被赋予的力量和责任,投向平凡生活的怀抱,他扔掉蜘蛛侠的服饰,获得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可是当危险来临时,他还是毅然决然变身蜘蛛侠,决心放弃平凡正常的生活,勇担责任。漫改影视剧主人公的难题和现实中的人们何其相似,在挣扎和摇摆中逐渐坚定心中所想,尽管艰难但仍然直面人生,做出最终的选择。
漫改影视剧通过放大现实的褶皱完成对现实的重构,缔造了一个现实加强版的平行宇宙,而它又通过聚焦普通人的现实困境,在极端情境中让迥异的价值观激烈碰撞,不避讳人的真实诉求、不局限于单一的价值理念,努力抚平一道道褶皱,不懈为真实的矛盾寻找可行性出路。
平行宇宙式漫改影视剧以漫画般的夸张诙谐、辛辣讽刺解构了现实社会里相对保守、固化的主流价值,不呼吁毫无思索的一往无前,也不鼓舞满腔热血的道德绑架,转而关注随着时代变化的人的具体矛盾,展示普通人挣扎向前的多种尝试。尽管没有示范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持续地探究和反思也拓宽了人们的认知边界,当人们回到现实生活时,仍然可以从漫改影视的种种构想中找到参考解法。
结语
2023年国内漫改影视剧持续发力。目前,改编自日本漫画家椿泉大热作品《月刊少女野崎君》的电视剧《开画!少女漫》,改编自本土漫画家庹小新古典玄幻漫画的同名剧集《狐妖小红娘》,改编自本土漫画家RC古风断案漫画《大理寺日志》的电视剧《大理寺少卿游》均已杀青。这几部待播漫改影视剧多由两种以上的类型元素同构,开启了漫改影视剧主体内容、审美形式、商业趣味融合的新境界。
漫改影视作品在影视艺术范畴内是一类特殊的存在,作为典型的“视图—影像”的跨媒介融合产物,不仅在技术层面拓宽了视觉建构的创作路径,也在内容层面促进了现实与想象的文化交互,因而漫改影视剧塑造的世界对现实生活总有更为复杂的解读、间离、再造。漫改影视剧对现实的重构,展现了“乌托邦”式突破的勇气和美好的理念,也提供了“平行宇宙”式和谐的秩序与务实的解法,大抵还存在更多重构的可能性。每一场从现实出发的艺术求索,亦不能忘却对影像本体的坚持与反思、对大众审美的观照与引领,以现实启发艺术,以艺术反哺现实。
参考文献:
[1][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下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01):683-687.
[2]徐智鹏.中国漫画改编电影的跨媒介叙事策略与文化认同研究[ J ].当代电影,2019(07):122-126.
[3]侯均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08):148-154.
[4]陈雪.数字技术之美:——漫改电影的现实书写、身体呈现与空间重构[ J ].南京師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1(01):102-107.
[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李步楼,尚伟,祁阿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15.
[6]江晓原,刘兵.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败给迷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