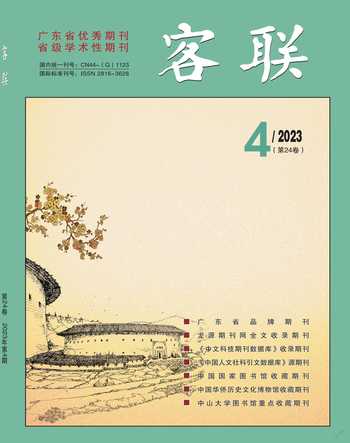劳动异化的当代表现形式
2023-08-07陈高敏
陈高敏
摘 要: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肆无忌惮,劳动异化的特征较为明显。随着时代的变迁,劳动异化的形式也有所改变。本文从白领的视角去探析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在当代的特殊形式及以此衍生的问题,并尝试找到适合个人使用的一些克服劳动异化的方法。
关键词:劳动异化;白领;克服异化
劳动异化并不是当今社会才有的现象,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不断进行变化。当今社会,劳动异化有了不同于往日的表现形式,而白领则在新的表现形式下,承受着与以往一样的负面影响。
一、劳动异化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劳动异化”的概念,意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却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使工人受其支配,因此,这种财富及财富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本身皆异化成为统治工人的、与工人敌对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劳动异化。
在经济和科技并不发达的过去,人的生活节奏缓慢而悠长,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对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现如今,物质更丰富、科技更发达、人类的知识储备更多,人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以越来越智能的科技去对抗自然的枷锁,理应拥有更多闲暇的时间。但事实上,不少人反而认为自己闲暇的时间更少了,慢不下来了,更不自由了。有人认为不自由的根源在于世界运转得太快,人只能跟着快,无法在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中慢下脚步来,也就无法“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恰恰表现出“异化”的特点,从客观上看,从前是一天24个小时,现在仍然是一天24个小时,即这个世界所参照的客观上的、物理上的时间并未变化,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那么变快的必然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人主观的“感觉”,或者说是体验。世界依然沿袭着自身的规律在运转,只是人类通过不断提高社會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让社会运行地“快”起来。人类创造出来的产品本应是为人类服务,让人拥有更多享受美好产品和服务的闲暇。但当前人类却服务于人类创造的本应为人类服务的“产品”,遭受到生产的反噬,这便是“异化”。
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异化都源于劳动异化,并通过“对象化”和“外化”的概念论述了劳动的辩证运动。首先劳动指向对象,劳动者通过劳动加工自然之物,使之成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劳动的必然过程。但是,随着对象化促成经济的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者和劳动本身也成为对象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外化”则是指劳动者将自己的内在思想、知识、能力实现在外在于他的劳动产品中,这也是劳动的必然过程。只是当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再属于劳动者本人,劳动者内在劳动能力外化成为商品即劳动力时,异化便同时发生了。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肆无忌惮,劳动异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当今社会,劳动保障制度更为健全,工人的休息时间、工资福利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劳动产品更为丰富,人类基础的衣食住行等需求也极大程度上予以解决;工作机会更为充裕,工人似乎可以更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工作……如此种种,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的矛盾似乎得以消弭,劳动异化似乎正在消失,但究其实质,劳动异化只是改变了其表现形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二、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之白领
白领是指受雇于企业的、接受薪酬的阶级人士。以白领为例,白领的劳动异化分别体现在劳动机会获得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和劳动结果的异化。
(一)劳动机会获得的异化
劳动机会获得的异化是白领进入职场所接触的第一个异化。当前,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少白领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各种苛刻的条件,以实现自身劳动的权利,造成了劳动异化。
正如我国目前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不少企业在白领求职时,在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有相关条款,但实际上,在应聘面试时,招聘人员往往会询问应聘人员对加班的看法,以及是否接受加班等内容。这个“加班”可能只是特殊情况下当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也可能是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也可能是周末免费加班是常态。能否接受“加班”成为应聘人员能获得这份工作机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甚至成为招聘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看起来应聘人员似乎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但当加班被美化为一种福报,且整体的工作环境皆是如此时,个体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劳动,否则将无法获取任何劳动机会。劳动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权利,而白领却需要为了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委身于“人”,恳求得到一个劳动的机会,劳动机会的获得与劳动者站在了对立面,形成了劳动异化。
劳动机会获得的异化,作为劳动异化的一个方面,本质的原因依然应归结于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着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劳动者要劳动,就必须有劳动对象——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实现和劳动对象的结合,以完成劳动。因此,本该劳动者自己所有的劳动机会成为了资本家的给予,使白领产生了劳动机会是被资本家给予劳动者的错觉。基于此,白领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等需要,只能通过提高学历、不断掌握新的工作技能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时以接受加班、接受非正常的企业文化等方式,不断降低自己的劳动幸福程度,使自己尽可能符合资本家设定的扭曲的工作条件,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和马克思在其所处时代描绘的工人为了生存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状况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给这种异化用协议、合同、谈判等方式为劳动异化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
劳动机会获得的异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卷”文化盛行。根据《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2021届高校毕业生为909万人,只有34%的大学生找到了工作。“僧多粥少”之下,各行各业都逐渐“内卷化”。比如“卷”学历,本科学历普及以后,大家就开始考研,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高达457万,同比增长达21.2%。对于已经工作的白领,还要面临“卷”岗位、“卷”时间,同样的薪酬待遇,白领之间需要争先恐后地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996”加班文化(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将“卷”时间现象展现的淋漓尽致。但事实上,内卷并没有真正提高工作质量,产生精益求精的效果,而是将精力花在了“内耗”上,虚耗了劳动者的精神。
(二)劳动过程的异化
劳动过程即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结合。白领的劳动过程,就是其作为劳动者,与公司给予的劳动对象进行结合,完成工作任务。劳动过程异化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答案:“‘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本身的异化、外化在劳动的过程中,工人同那个生产资料、生产管理相分离。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这样,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成了不依赖于他、转而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1]换而言之,由于白领劳动的对象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司的,因此,白领为这个劳动对象付出的体力、智力劳动最终得到的劳动结果属于公司,而不属于白领,白领只是为了工资才付出劳动力,公司只是明码标价购买白领的劳动力。此时,白领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异化了。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感觉到不舒畅。”[2]这是马克思对当时的工人在劳动中产生的痛苦的描述,但即使放到当今社会,仍切中要害、一语中的。因为工作是不快乐的,工作是对自己肉体的折磨,对自己精神的摧残,所以必须用自己通过出卖劳动力辛辛苦苦换取的钱财去换取快乐。同时,当代白领将工作的压抑转移到消费上,吃喝玩乐就是快乐的,能用钱换取的就是快乐,即消费等于快乐。“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会说:正因为劳动是不舒畅的,所以要发工资;正因为消费是舒畅的,所以要花钱。”[1]异化劳动带来的痛苦使得白领们寻求不痛苦的途径,资本家在白领生活的每个角落喷洒着“消费即快乐”的麻醉药,白领通过消费得到短暂的麻醉,麻醉使得白领感受不到痛苦,于是白领误以为这就是快乐。所以白领们不停被刺激去消费,不停被麻醉,当白领们对麻醉产生了耐药性时,就只能通过加大消费获得更大程度的麻醉,最终使白领无可避免地陷入消费主义中无法自拔。
这不过是劳动过程异化衍生的诸多怪相中的其中一个。劳动过程的异化使得白领在工作中找不到快乐,找不到作为人的本质,而误将动物的生存需求当做是快乐。这是一种人向动物的退化,这样发展造成的危害除了上文所说的消费主义盛行,还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主义的狂欢等等。对社会历史进程来说,劳动过程异化的危害可能在当前并不明显,但如不加以遏制,未来一定会发生阻碍社会进步的质变。
(三)劳动结果的异化
劳动结果的异化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就是劳动者通过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得到的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本人所产生的异化。当今社会,劳动者拿工资,资本家拿劳动产品,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劳动价值理论,工人的劳动是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组成,必要劳动是指保证工人能够生存下去的那部分劳动,也就是资本家给予工资的那部分劳动力;而剩余劳动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也是资本家竭力榨取的那部分劳动——很多时候,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远比工资多得多。从一开始资本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暴力的,他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非法占有,以至于在资本家站稳脚跟后通过建立法律制度、灌输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等等措施,将暴力占有逐步合法化。
在现实生活中,白领在工作开始前,一定拥有自己的想法;在工作过程中,一定也实现着白领的内在思想、知识、创造力等等劳动能力;其劳动结果,是其劳动能力外化在一个具体的产品上。但这个劳动产品不属于白领个人,而是属于公司,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工作积极性的降低,因为工作的目的是为他人,工作的结果是为他人所有,所以一些白领会抱有“给一分钱,出一分力”,我只要付出符合工资的劳动力即可的想法。而当每个劳动者都如此行动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进步将会停止。因为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进步,而人是通过在劳动的过程中释放自己的创造力来实现自己的进步的。一旦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开始躺平,社会也必将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又例如企业内的贪污腐败和职务侵占行为,如果从事销售工作的白领,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为公司签下了大单,但是自己拿到的提成仅仅只是这个大单收益的1%甚至不到更低,久而久之形成心里失衡,就开始收回扣要好处,通过各种方式去损害公司的利益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必将造成个人和社会的双重损失。
三、白领克服劳动异化之路径
我们意识到了劳动异化,甚至探寻到它的来龙去脉,那么接下来就要克服异化,回到正常的非异化的劳动中去。异化劳动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然发生的,其只存在于某一阶段,而当下的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正常的非异化的劳动中。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劳动异化到正常的非异化的劳动的完全飞跃。只是在还未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可尝试通过个人的努力,探索出某些克服劳动异化的方法,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进步。
从个人的角度看,当今的白领偏“佛系”,他们对工作机会的获得更多是“被动”的,即这个社会给我多少岗位、给我怎样的岗位,那么我就接受这么多岗位、接受这样的岗位,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岗位,而没有想过参与到改善供给中去。对此,白领应当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所实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白领作为人民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去为了建设这个国家出一份力。比如可以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去关注就业相关制度、措施等信息,并提供相应的意見和建议,并通过自己的想法、意见和建议,推动广大劳动者一同减轻劳动异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青年一代应当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而不是整天沉迷于个人的吃喝玩乐中。个人主义至上终归是虚空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离开了社会就是非人。关于提高政治参与度,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其他具体措施,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此外,如前文所述,劳动结果的异化可能导致企业产生贪污腐败和职务侵占行为,但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公司是“资本家”,那劳动者侵占公司的资源也是合理的,因为是公司的不合理压榨才导致劳动者的贪腐。可以肯定的是,侵占公司资源是错误的,是违法的行为。纵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暴力的,也不代表我们现在就要通过暴力推翻这一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在的“资本家”不是当初的资本家,不能简单的说公司就是资本家。本文只是尝试以白领的视角去探析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内涵,并希望能让更多普通人能够更容易理解这个理论,而不是走向“仇富”心理或“躺平”心态的两个极端。在这个克服劳动异化到达正常的劳动的过程中,我们工作或许不快乐,但是不要因此放弃自己,放弃让自己进步。劳动异化下的劳动也有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本质的可能,这是克服劳动异化带来的痛苦所能达到的。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时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白领在工作过程中释放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同时也在工作中提高技能、得到锻炼。工作不等同于劳动,劳动包含工作(在当今社会,工作是劳动的很大一部分),人们通过工作(并非特指进入职场,家庭主妇、个体户、农民、自由职业者进行的劳动都可以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去找到自己的坐标,去建立和这个社会的联系,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在一份工作中你感到不快乐,那么就要分析这个不快乐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及时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是相互促进、同时进行的,并不是单行线,这和个人提高政治参与度,主动改善大环境并不冲突,可以同时進行。
尽管离劳动异化的彻底消失依旧是长路漫漫,但白领依然可以从改善自身价值观入手,积极调整自身所处的劳资关系,联合其他劳动者一起争取自身合法权利,并通过参与国家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等方式,克服劳动异化给自身带来的损害,尽力消除劳动异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庆熊.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探究马克思揭示“异化劳动”的方法论[J].学术月刊,2010,42(09):31.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仰海峰.商品拜物教:从日常生活到形而上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02):13-17.
[4]王会平.异化劳动的超越与人的生存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2008(06):11-15.
[5]何云峰.论劳动幸福权[J].社会科学家,2018(12):8-14.
[6]李强,丁辉文.“新生代白领”进入中产阶层的体制机制障碍——某特大城市高科技园区白领阶层案例研究[J].河北学刊,2018,38(05):16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