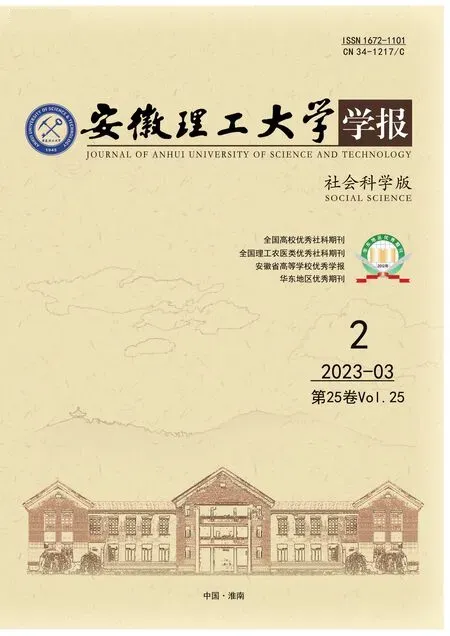埃莱娜·西苏“女性书写”理论的生成背景研究
2023-08-07王喆
王 喆
(安徽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601)
20世纪70年代左右,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哲学思想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创设了以身体为中心,兼具诗性与音乐性的“女性书写”理论,并逐步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作为“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中一种重要的理论表述”[1]185,“女性书写”理论“开创了女性主义对语言中欲望表达调查的新天地”[2]124。这种有别于先前的女性写作观不仅是一种写作理论与实践,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与认知方式。“女性书写”理论生发于当时法国社会中特殊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而所有的这些背景因素均促成了西苏本人对于性别差异、女性气质、女性语言及女性写作等议题的反理性、反规范性质的探究。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关于女性作家及其写作方式的新型理论的生成背景进行剖析,以更好地理解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
一、历史语境: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滋养
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扎根于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的历史沃土中。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角度来说,20世纪 70年代左右的法国女性主义,或法国新女性主义有着“单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影响”[3]。与传统英美女性主义理论家不同,法国女性主义的基本关注点在于“文学中‘女性气质’的生产”[4],其批评理论“本质上是心理分析的”[1]186。一直以来,高度异质、杂糅性被视为法国女性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多元的哲学、理论融合背景为法国女性主义传统涂抹上了一缕浓烈的思辨色彩。西方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女性主义创始论著《第二性》(TheSecondSex,1949)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就吸收了同时代的萨特(Jean-Paul Satre)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法国女性主义从多重理论思想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思想有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与二元对立思想、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于知识与性别的讨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解读、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及其经典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拉康(Jacques Lacan)对人类心智与语言的探究等。此外,德勒兹(Gilles Deleuze)、伽塔利(Félix Guattari)有关于身体与欲望的讨论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女性肉欲或身体的格外关注。
女性主义学者琼斯(Ann Rosalind Jones)较好地浓缩提炼过法国女性主义的四个变量或特征。首先是解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常致力于对法国主流男性作家,如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热奈(Jean Genet)等的经典文本、写作传统及文学史进行解构。其次是对沉默的挖掘。与传统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相比,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压抑”[1]186。与心理分析学家在具体案例治疗过程中重点关注病人话语中的离题、间断、迂回等看似无关紧要的语言表述类似,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擅长发掘女性作家在文本中流露出的被压抑的欲望或潜在的反父权制倾向等。她们集体抵制官方的话语语境,注重探索文本中内嵌的文化禁忌物(如同性恋等话题),尤为关注母女关系中“母亲”一方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而这正是西苏在“女性书写”理论中对母亲、分娩中的母体或母性进行全新阐发的缘由。再次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注重对文本中诸多印有女性气质的要素进行解码。如西苏在“女性书写”理论中主张感知文本中所透射的女性气质与反象征秩序因素(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修辞、结构、数字、神话模式所带有的移情作用等)。在分析具体的女性写作与文本特征时,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偏向于模仿或使用该作家的语言游戏,如双关、比喻等解读其中的女性气质,而非以简单的散文体方式进行复述。最后是她们注重挖掘作品中语法、词法、句法、比喻、结构模式与女性主义理论文本的亲缘关系。总体来看,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合力抨击父权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相比英美女性主义理论家,她们更着重于在哲学思辨层面上描述男女性别差异所在。以西苏为首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致力于抵制对菲勒斯的盲目崇拜,进而颠覆弗洛伊德提出的有关女性作为被压迫者角色的观点。如专属于女性性属、女性肉体的愉悦感,或“享欲”(jouissance)概念正是西苏“女性书写”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3位杰出代表西苏、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与伊莉格蕾(Luce Irigaray)拥有多元化的职业、学术背景。她们或为女性作家、专职心理分析师,或是学院派中具备一定资历的文学、哲学教授,且都有海外流散经历。因此,在个人特质方面,3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较为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思想、日常的辩证法思维方式等。她们坚信人类、上帝或享有特权的艺术作品的最终命运都是走向死亡,并致力于从阅读、写作中汲取某种颠覆性的政治力量。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促使她们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与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如家庭相联。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多借用心理分析学中的“无意识”“力比多”等核心概念,试图对男女两性欲望进行区分,进而探索专属于女性的力比多、幻觉、欲望等。英美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弗洛伊德一贯持不屑与排斥态度,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却截然相反。
对于女性作家作品,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极其重视其中的女性语言与身体的关联,她们的讨论焦点在于辨析女性受压迫地位的本质或是男女性别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大多聚焦于“文本、语言学、语义学或心理分析的理论”[2]195,甚至于她们所创作的理论文本本身也是高度实验性质的,是女性主义理论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的混杂产物,其宗旨在于挑战英美女性主义中较为传统的文本书写或文学创作形式。在“女性书写”理论的完整建构过程中,西苏特别强调性别中的文本再现、写作的具体方式及书写过程。如在《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1975)等诸多有关“女性书写”理论的经典文本阐发中,西苏尝试采用现代、非线性的写作方式,以诗化哲学的行文风格成功创设了一种专属于女性的语言表述与书写方式。
二、多元文化语境:解构主义与心理分析的哲学背景
总的来说,西苏的女性主义著述“塑造了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哲学的前言性问题”[5]1。她曾坦言自己身处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并明晰解释自身对于哲学知识、辩证分析法有着较充足储备与选择性的使用:“我与哲学是有关系的,但是是对话性质的”[6]150。“女性书写”理论生发于二战之后的法国学界,成长于现象学、存在主义、左派社会现实主义思想发展的全盛时期。因此,对西苏而言,“女性书写”理论的生成背景早已超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或思潮的狭窄范畴,是“一种生活、言谈与观察世界的方式”[6]xxii。
尽管西苏在欧美学界被习惯定义为女性主义理论家,但她的大多数学术理念却是反向生发于西方经典作家作品,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坡(Edgar Allan Poe)、乔伊斯(James Joyce)等所创作的多元风格的文学文本;或是借鉴了德国浪漫主义学者,如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卡夫卡(Franz Kafka)等的文学创作思想。“女性书写”理论中异常鲜明的哲学特质派生于克尔惇凯尔(Søren Kierkegaard)、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德里达等男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在西苏的相关理论著述中,读者可以明显觉察出她对于古希腊神话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概念的多处援引。此外,法国诗人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独特的诗歌写作风格与诗歌创作理论也部分影响了“女性书写”理论的诗意文风。对于殖民地中被殖民者的持久关注也促使西苏将女性主义视野敏锐延展至第三世界国家作家作品,如巴西女性作家李斯佩克特(Clarice Lispector)、南非已故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人的文学作品。
总体上看,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成长于法国当代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现代语言学、符号学肥沃土壤中,而后壮大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与拉康的现代心理分析理念,因此可被视为几位男性哲学家思想理念的部分杂糅。但是,西苏仅是某种程度上借鉴了他们的理论表述,并非拿来主义,她最终力图展示给读者的是这些男性哲学家一贯的父权制偏见。在弗洛伊德及拉康的心理分析学中,女性通常只是某种隐形的存在,或是一种缺失物(the lack)。与男性相比,身为“第二性”的她们更是一种甘愿保持缄默的性别存在。而西苏“女性书写”理论的价值与贡献,就在于对女性的这种身份缺失与沉默地位进行了修正与改写。
(一)解构主义的根基
很大程度上,西苏的阅读、写作过程及其“女性书写”理论的生发背景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与拉康的现代心理分析理念。西苏曾明确表示,“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将一直会是我们时代中最伟大的道德批判警示姿态”[7]xviii。德里达所要批判的是二元对立范畴之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是一元论主导下的逻各斯世界(the Logos)。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家“果断地谴责二分的现实及其他的单位,二元对立”[8]。基于此点,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作用对象或类似的理论目标,即对固有、常态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极大影响了西苏对于男女性别间二元对立的哲学阐发,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西苏的理论文本被评论家明确界定为“对解构主义的贡献和对诸如男人/女人、女性/男性、女性气质/男性气质过时二分法的重新思考”[9]9。最终,在部分吸纳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辩证法的质疑,西苏的理论体现了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的转变”[9]xiv。
在《突围:向外向外:攻击/出走/突袭》(“Sorties:Out and Out:Attacks/Ways Out/Forays”,1975),以下简称《突围》)的开篇,西苏列出了后结构主义中如“主动/被动……理性/经验……男性/女性……言说/写作、话语/书写”[10]63等诸多二元对立物的存在。在这些贯穿于西方多个世纪表征系统(representation)的二元对立范畴内,或经由西苏定义的“对子”(couples)[10]64中,前者总是占统治或特权地位,而后者一贯居于支配、被贬损地位,两者间等级森严。在西苏眼中,性别差异的建构正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一直以来,男性被视为主动、活跃的主体;女性倒退为被动、消极的客体,她们常与西方哲学思想中的被动性(passitivity)相联。西苏性别差异思想的着力点就在于颠倒这种对立物之间内嵌的主次、先后关系,她致力于解构西方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中异常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而探索女性性征与语言的本质关系。
德里达所创设的表示无限过程的“延异”与“书写”“礼物”“专有”等术语均在某种程度上启发、影响着西苏“女性书写”理论的完整生成。德里达认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柏拉图起,真理、存在、本质等总是与言语或“活的声音”相联,书写或文字退居次要、不在场的位次。德里达所要批判、解构的正是这样一种重语言、轻书写的结构,他认为书写应替代言说,并取代言说固有的特权地位。语言的意指系统在潜在意义上是一个无止境的、拖延性的过程。在德里达眼中,书写行为就如同延异产生的整个过程。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逻各斯意义从来就不是完全在场的,它总是被延后。所谓全部思想与语言系统的存在基础,即某种“终极真理”或“超验所指”将不复存在。对西苏而言,以女性身体、无意识、力比多冲动为中心的“女性书写”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可以超越逻各斯中心论的表述。在“女性书写”理论中,“在场”或一成不变的父权专制被解构,无限的差异、延搁随之浮现。正如解构主义思想,“女性书写”理论是一种对无上权威和霸权的抵制。对于德里达和西苏而言,“书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德里达高度评价西苏为“法国现存的最伟大的作家与诗人般的思想家”[5]9,并部分赞同西苏的女性主义思想,特别是西苏对于性别差异思想的解构主义式阐释,如他曾在讲稿中明确提及“性别差异是可以被诠释、被破译、被解码的”[11]121。西苏在1962年初识德里达,之后两人便保持着一种较为亲密友好的关系。在相关访谈录中,西苏更是坦言自身与德里达思想的同缘性,甚至于彼此之间有着一种最为奇怪的“相当多的亲近关系”[11]80。西苏与德里达曾合著过文本《面纱》(Veils,1998),随后,她还专门创作了《作为年轻犹太裔圣徒的雅克·德里达》(PortraitofJacquesDerridaAsaYoungJewishSaint,2001),细描德里达与她本人都经历过的海外阿尔及利亚、犹太生活背景。
尽管学术探索之路与方向存有惊人的相似性,但由于学术兴趣存在相异性,二者的学术观点偶尔也会“分道扬镳”。如在论述“死亡”这一议题时,两位理论家的观点就存有较鲜明的差别。在“女性书写”理论中,西苏认为死亡意指已经发生了的过去时,她坦然接受死亡的现实;而德里达则判定死亡即将发生于未来,个体皆是被置于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中。西苏对自己与德里达的关系曾作过颇为形象的描述,“有时分开、有时又走到一起”[11]81。而在性别身份层面,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更是一直以来视德里达为自身的“他者”。
(二)心理分析学的底色
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之外,弗洛伊德的传统心理分析学及之后拉康的现代心理分析学被公认为西苏“女性书写”理论的另一个直接源头。西苏明确承认自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思想影响很大,“我们对于无意识的探讨皆归于弗洛伊德”[12]。在相关访谈录中,她曾颇为亲切地写道:“我的叔叔弗洛伊德”[13]。弗洛伊德认为,最初状态下人类的性征是多形态、可变的,而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认为要在相关诗意书写中展现个体,尤其是女性个体性征的多元、灵活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极为清晰。
然而,西苏与传统心理分析学的关系始终是“有争议性质的”。西苏在《突围》中对弗洛伊德有关性别差异议题的论述进行了批评。弗洛伊德认为,解剖学层面的女性生理特征决定了其在性别二元对立状态中处于常态低等地位;而西苏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弗洛伊德设定的有关性别差异的唯一生理区分标准——阴茎的有无。总体来看,弗洛伊德有关性别差异的描述中充斥着男性欲望的体验,女性性征仅是男性性征的参照物。如在弗洛伊德看来,女性存在崇拜阳具或“阴茎嫉妒”(penis envy)心理。在这种标准下,男女性别差异在视觉上的直观呈现只会致使其沦为“一种偷窥者的理论”[10]82。在西苏的女性主义视阈中,弗洛伊德对阴茎的无上崇拜仅是一种带有强烈歧视色彩的性别差异观念,男性在这种性别对立状态中尽享特权。因此,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向女性发出了异常明确的反叛呼召:“不要呆在心理分析的封闭中。环顾四周,然后开辟新路”[15]429。在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中,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一贯被定义为非女性主义的,男性、父权的弗洛伊德强调的是对女性气质甚至是对男性性征中潜在的某些女性气质的压制,他意欲把女性流放、发配至某个“黑暗的大陆”[15]422,而西苏则指明这一隐喻仅是弗洛伊德设立的一种诡计,其目的在于掩盖女性的性征与她们潜在的母亲身份。对此隐喻,西苏加以大胆挪用,并号召女性勇敢探寻女性气质的领地、专属于女性的性愉悦体验或身体的享欲。在“女性书写”理论中,这种黑色常被西苏定义为中性色彩,甚至带有相当褒义色彩。如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写道“我们是黑色的,我们是美丽的”[15]416。
对于弗洛伊德的阉割焦虑、俄狄浦斯情结等经典心理分析学概念,西苏同样加以质疑或批评。她认为,不同于男性,女性总是一位乐于奉献的给予者,“对于砍头或阉割的恐惧,她们毫不关注”[15]425。西苏坚信其性别差异思想,认为“女性书写”理论势必会为男女两性作家带来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诸如“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字眼最终将毫无实质意义,“性别”将是持续流动、易变的。此外,弗洛伊德对梦境的解析、对死亡本能的论述,也极大影响了西苏后期对于“女性书写”理论的完整阐发。
新弗洛伊德学派代表人物拉康的的现代心理分析学观念对西苏“女性书写”理论影响也很大。20世纪60年代,拉康从结构语言学角度延伸拓展了弗洛伊德的传统心理分析学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内涵,由此提出了现代心理分析学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即镜子、想象与象征(Real/Imaginary/Symbolic),分别对应着弗洛伊德建构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在镜子阶段,孩童在镜相中发现了作为自我、主体对立面的“他者”;随后,在想象阶段,母亲与孩童融为一体,差异和缺失并不存在;然而,在象征秩序中,孩童对母亲的占有欲望与性亲近的想法却被代表着父亲法律、父亲名字的菲勒斯所压抑,他们遭遇到了阉割威胁,无意识随之浮现。
在拉康眼中,性别身份建构于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且以差异和缺失为根基。在象征秩序中,他者演变为真理的源泉。然而这种所谓“真理”的真实性却有待怀疑,其或仅是一种对菲勒斯力量的曲解。由于他者的缺失,在象征界中对于意义的找寻注定徒劳无功。拉康颠覆了索绪尔的符号学与语言学理论,他指出,在语言之内,主体向意义移动,然而意义的取得却是以对未被言说的事物(如对无意识的压制)为代价的。这种压制将是持续的,被压制的无意识最终只能通过语言介质完成对意义或身份的消解。在拉康的现代心理分析思想体系中,文本即是某种欲望的话语。在“女性书写”理论中,西苏尝试运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给予拉康的性别差异理论批判性评价。她认为,象征秩序中的二元对立关系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改变,语言系统中父权的中心地位可以通过女性作家新型的书写方式,或专属于女性的语言加以扭转改变。西苏创造性地挪用了拉康的心理分析话语,并对其所提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女性主义修正。
此外,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中有关女性的“享欲”概念生发于拉康的心理分析学思想。在拉康看来,“享欲”是力比多力量在某一时刻的积攒或凝聚,它从想象阶段爆发,随后涌动至象征阶段。在此基础上,“享欲”可被理解为个体性力的突然释放,其结果扰乱了象征秩序中的连贯性。拉康曾特别指出,“身体的享欲……是超越菲勒斯的”[16]。西苏成功借用了拉康对于“享欲”的概述,转而用以描述专属于女性身体的性愉悦。在“女性书写”理论中,这种专属于女性及其身体的享欲同时印有“流动、弥散、持久的观念”[17]。
三、政治语境的催化
“西苏的作品与教育方法皆带有1968年五月事件与环境的影响印记。”[6]xvi除强大的历史背景与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外,“女性书写”理论还根植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与颠覆性质的政治语境中,如发生于1968年5月的以学生为主体力量的巴黎政治运动“五月风暴”与近乎同时期发生的第二次法国女性解放运动浪潮。在分析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的生成背景时,莫伊(Toril Moi)就谈及到这一时段法国社会中所发生的宏大的历史事件,如“五月风暴”。在当时,“它几乎推翻了所谓西方民主中更具有压制性的一种民主”[2]9。五月风暴”中的女性学生对该政治运动中部分男性同胞的父权主义偏见或资产阶级思想深感失望,她们联合左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属于自身的政治运动团体,如“政治与心理分析”(Psych et Po)、先锋派后结构主义理论团体“太凯尔”(Tel Quel)、“革命女性主义者”(Féministes révolutionnaires)等。在政治语境层面,这些法国女性革命运动团体坚信当代女性作家写作的终极任务之一在于对象征秩序的颠覆,如对文本中句法的重组、革命性质的文字游戏,或是对“能指”(the signifier)等语言学概念的解构和戏谑。
20世纪早期,依托西方社会中女性争取选举权的历史背景以及随之浮现的具有解放、进步性质的“新女性”形象,英国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自己的屋子》(ARoomofOne’sOwn,1929)中对女性写作境遇进行了深刻反思。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此时,尽管现代女性已在某些方面,如选举权、就业领域等取得了较明显进步,但性别歧视现象仍无法得以根除。因此,鉴于当时甚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性别环境,西苏对于当代女性作家及其写作状态的反思更为激进,更具有革命性。
在“五月风暴”运动时期,西苏积极参与相关政治集会与示威活动。在教育实践开展方面,她创建了颇为激进、具有实验性质的巴黎第八大学万森纳分校(Paris VIII---Vincennes),以抵制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压制性、阶级性的教育结构体制。1974年,西苏在巴黎八大成立了欧洲大陆首个专门研究女性问题的博士点“女性学研究中心”(The Centre de recherches en études féminines)。之后,她又联合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热内(Jean Genet)等法国男性学者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实验性杂志《诗歌》(Poetique)。作为当时法国学界中的极度活跃分子之一,西苏与“女性”杂志社创始人福特(Antoinette Fouque)、实验性质的太阳剧场(Thétre du Soleil)创始人莫须金(Ariane Mnouchkine)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由此卷入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法国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浪潮。西苏与众多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女权主义革命者并肩作战,最终成为20世纪70年代法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受1968年及之后法国社会政治气氛的影响,西苏持续号召女性对传统教育培训结构进行变革,以实现女性性别身份的真正解放。其中,她所关注的核心话题即是“对于她(和他)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关系的变革”[6]58,这正紧密呼应着以身体为中心而向外发散的“女性书写”理论。反之,该理论“在社会意义上具有着颠覆的潜能”[18]。
四、结束语
西苏在以心理学与语言学为中心的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的沃土中开创了一种存在于写作与性别差异中的崭新思维模式,创建了法国女性主义中关于女性写作议题的“女性书写”理论。“女性书写”理论的生成得益于多元的文化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于女性写作的鲜明的性别政治可被定义为当时法国学界中盛行的某些理论思潮,如德里达解构主义与拉康现代心理分析学的综合杂糅产物。因此,除去其女性主义理论家的鲜明标签,西苏在西方学界又常被视为一位极其思辨的哲学家。由于“不在传统的哲学界限里思考或阅读”[5]9,她在学术理论层面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多维度研究视角。另外,作为女性主义解放运动的忠实践行者,西苏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中激进活跃的政治革命生涯也部分影响了其先锋派特质“女性书写”理论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