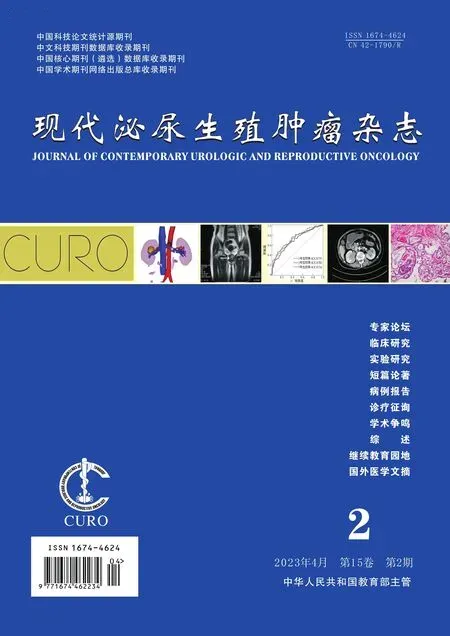脐尿管癌的诊疗研究进展
2023-08-06王祖恒刘喆程文
王祖恒 刘喆 程文
脐尿管癌(urachal carcinoma, UrC)是一种较为罕见的侵袭性膀胱肿瘤,好发于男性,临床表现较为隐匿,常以泌尿系统症状为临床表现,与膀胱尿路上皮肿瘤难以鉴别。诊断主要依靠CT和MRI,以评估局部浸润和淋巴结转移状态,并判断是否存在远处转移。膀胱镜检查可定位肿瘤,并进行活检。病理学是诊断UrC的金标准。外科手术是治疗的首选方案。国内外关于UrC的研究主要为个案报告及回顾性研究,缺乏前瞻性,目前尚未对UrC的发病机制和诊断治疗标准达成共识。本文主要对UrC的诊断治疗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
一、病因及流行病学
在胎儿期,脐尿管是连接胎儿膀胱和脐的管状结构,是胎儿的重要排泄器官,负责清除膀胱内含氮产物。在胚胎期的第4~5个月,脐尿管管腔闭合逐渐退化为纤维肌性的韧带,称为脐正中韧带。脐尿管属于腹膜外结构,位于腹横筋膜与腹膜之间的疏松结缔组织内(Retzius间隙),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残存部分脐尿管,以管状或囊状结构与膀胱相通。脐尿管管腔闭合失败可导致各种异常,包括恶性转化为UrC。
UrC最初由Hue和Jacquin于1863年发现,是一种罕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每年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一,约占膀胱肿瘤的0.35%~0.7%[1],其中,腺癌为UrC最常见的类型,占膀胱腺癌的10%~30%[2]。UrC在男性和女性患者中发病率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显示男女比例高达3∶1[3],国外研究显示男女比例为1.4~1.6∶1[4]。UrC平均发病年龄50~60岁,比膀胱肿瘤发病年龄早约10年[5]。
由于UrC发病率低,UrC的病因研究尚不完全清楚。在残存的脐尿管中,三分之一的脐尿管上皮被柱状细胞所取代,但未发现脐尿管残体和膀胱内部之间的通道。有学者认为,脐尿管管腔直径小,并且存在阻塞管腔的上皮分泌物,即使脐尿管重新开放,尿液回流到脐尿管残体的可能性仍然不大[6]。因此,与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不同,尿液中存在致癌物的假说无法解释UrC的发生。UrC的组织学类型(最常见为腺癌)、免疫组化及基因改变等均与结直肠癌相似。有学者据此提出两种假说,一种是UrC源于胚胎发育过程中泄殖腔内含物或肠道残留;另一种则是来源于化生[2]。Yu等[7]发现,UrC患者中一半以上有吸烟史,但目前的研究中相关数据较少,吸烟致UrC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临床表现、诊断、病理及分期
1.临床表现:UrC的临床表现与是否侵犯周围组织及肿瘤在脐尿管中的位置关系密切。UrC早期局限于脐尿管内时,患者通常无症状,侵犯周围组织时才会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侵犯膀胱内壁时会出现无痛性血尿;侵犯腹壁时会导致下腹部肿块及疼痛。此外,UrC的症状还与肿瘤的位置有关,肿瘤位于脐尿管上段表现为脐部流出血性或黏液性液体;肿瘤位于中段表现为腹部肿块;肿瘤位于下段或靠近膀胱顶部则常出现血尿。血尿是最常见的症状,约70%~90%的UrC患者始发症状为肉眼血尿,此外,约20%的患者出现黏液尿,20%的患者下腹可触及肿块[2-3]。5%~15%的患者初始症状为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约15%的患者无任何上述症状,因体检发现就诊[3]。缺乏特异性和早期症状不明显而延误临床诊断是该病预后不良的原因之一,部分患者在诊断为UrC时已发生转移。
2.诊断:Johnson等[6]于1985年最早提出了UrC的诊断标准,2016年Paner等[8]进行了改进,诊断标准为:①肿瘤位于膀胱顶壁或前壁;②肿瘤生长于膀胱壁;③膀胱前壁及顶壁无非典型肠上皮化生、膀胱炎、腺性膀胱炎;④膀胱无尿路上皮肿瘤;⑤排除其它来源的原发性腺癌。对位于膀胱外的肿瘤,诊断标准为:①肿瘤位于膀胱顶壁或脐尿管中;②病理标本发现肿瘤与尿路残体相连,同时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膀胱镜检及病理学结果明确诊断。
影像学为UrC重要的辅助诊断方法。超声为筛查手段,典型表现为膀胱前方不规则低回声肿块,其内血流信号呈斑片状[9]。CT和MRI有助于评估局部浸润和淋巴结情况,并可发现有无远处转移。50%~70%的UrC患者影像学检查可以发现局部钙化灶,此为UrC的特征性表现。胸部平片可用以判断肺部(最常见转移部位)转移情况[10]。由于腺癌对氟代脱氧葡萄糖(fludeoxyglucose, FDG)摄取率低,18F-FDG PET/CT诊断UrC的阳性率为80%[11],延迟利尿后18F-FDG PET/CT对诊断淋巴结转移有重要意义,阴性预测值为100%[12]。
诊断性腹腔镜检查有助于发现腹膜转移情况,并准确评估转移灶的范围及是否可切除。大多数病例中,膀胱镜检可帮助定位肿瘤,并对肿块进行活检。UrC膀胱镜下主要表现为膀胱顶壁或前壁的息肉样或溃疡性病变。国内研究报道,约20%的UrC患者尿液脱落细胞学检查呈阳性[13];梅奥医学中心统计发现,约38%的患者尿液细胞学检查呈阳性[14]。荧光原位杂交诊断UrC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远高于尿脱落细胞学,分别为71.43%和94.61%[15]。
UrC患者部分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如CEA、CA19-9、CA724和CA125等。CEA和CA19-9常用于诊断胃肠道和胰腺癌,CA125和CA724常用于诊断卵巢癌[10]。上述肿瘤标志物对于UrC的诊断缺乏特异性,但可用于预测治疗效果和复发情况[4]。其中,CEA可作为UrC治疗监测和随访的最有价值的肿瘤标志物,而术后CEA和CA125升高则高度提示UrC复发可能。Siefker-Radtke[16]发现约59%的UrC患者血清CEA水平升高,部分患者肺转移后血清CEA显著升高。与欧美患者相比,亚洲患者肿瘤标志物升高更常见,韩国的一项多中心研究发现,有94.6%和89.7%的UrC患者分别伴有CA19-9和CEA水平升高[7]。
3.病理:大多数UrC位于膀胱顶壁,部分可同时存在于膀胱顶壁与前壁。肉眼观,肿瘤平均大小约为4~5 cm,以外生型及无柄型多见[17]。镜下观,UrC主要为腺癌(约90%),大多数(约65%)腺癌可产生黏液,肿瘤细胞漂浮其中(胶体癌);单纯肉瘤和移行细胞癌各占约8%,约2%为高度未分化肿瘤,鳞癌也可见于个别案例[18]。
UrC与膀胱尿路上皮癌的生物学行为特征有所差异。大多数膀胱尿路上皮癌病理表现为非侵袭性乳头状尿路上皮癌,并不侵犯肌层,而大多数脐尿管腺癌主要累及固有肌层和膀胱周围组织,与膀胱尿路上皮分界明显。膀胱尿路上皮通常完整,无乳头状尿路上皮癌或原位尿路上皮癌[17]。UrC常见转移方式包括血行转移、淋巴道播散和膀胱内播散。局部转移部位包括盆腔淋巴结、腹膜或大网膜。远处转移以肺和纵膈淋巴结最为常见,其他常见转移部位包括骨、肠、脑和肝等[19]。
UrC免疫组化检查CK7、CK20、CDX-2、HMW、villin常呈阳性。其中,CK7、CK20、CDX-2为膀胱腺癌共同特征。多中心研究发现,90.1%的UrC患者EGFR和p53表达升高,而56.2%和64.0%的研究人群中检测到KRAS突变和CK-20表达升高[7]。这些免疫表型缺乏特异性,与原发性膀胱腺癌和结直肠腺癌等难以鉴别。
4.分期:目前,UrC分期方法有Sheldon分期、Mayo分期和TNM分期3种。20世纪80年代,Sheldon最早提出了UrC分期系统:Ⅰ期,肿瘤局限于脐尿管黏膜层;Ⅱ期,肿瘤突破脐尿管黏膜层但局限于脐尿管;Ⅲ期,突破脐尿管,累计周围脏器(ⅢA期,侵犯膀胱;ⅢB期,侵犯腹壁;ⅢC期,侵犯腹膜;ⅢD期,侵犯腹腔其他脏器);Ⅳ期,累及局部淋巴结或远处转移(ⅣA期,局部淋巴结转移;ⅣB期,远处转移)[20]。2006年,梅奥临床医学院Ashley等[14]对Sheldon分期进行了简化,称为Mayo分期:Ⅰ期,肿瘤局限于脐尿管或膀胱内;Ⅱ期,肿瘤超出脐尿管肌层和/或膀胱肌层;Ⅲ期,肿瘤浸润区域淋巴结;Ⅳ期,肿瘤浸润非区域淋巴结或其他远处部位。肿瘤TNM分期:Ⅰ期,肿瘤侵袭脐尿管上皮下结缔组织;Ⅱ期,肿瘤侵犯脐尿管或膀胱肌层(ⅡA期,肿瘤侵犯膀胱深肌层;ⅡB期,肿瘤侵犯膀胱浅肌层);Ⅲ期,侵犯膀胱周围软组织、前列腺、子宫或阴道;Ⅳ期,侵犯腹壁并转移到淋巴结或其他远处部位[18]。
三、治疗
对于UrC的治疗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治疗方案,手术治疗、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均有报道。其中,手术切除仍然是治疗的主要手段,包括膀胱部分切除术或根治性切除术。研究显示,膀胱部分切除术与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患者术后长期存活率无明显差异,但行膀胱部分切除术患者的UrC复发率高于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患者[19]。膀胱部分切除术患者术后并发症更少,生活质量更高,因此,膀胱部分切除术为目前临床上最常用术式。对于是否需要进行双侧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目前尚未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淋巴结清扫术可以切除隐匿转移的淋巴结,从而使患者5年生存率提高25%[19]。也有研究表明,淋巴结清扫对于UrC预后无显著影响,但由于影像学对于淋巴结转移的诊断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较高,因此淋巴结清扫对于分期有重要意义[5,19]。
目前,对于UrC患者是否需要辅助化疗仍存在争议[14]。研究表明,对于复发性和转移性UrC,化疗可使患者生存获益[5]。对于复发率高、阳性切缘、淋巴结转移、腹膜累及或未切除脐部的患者,建议化疗4~6个周期[5,21]。目前,UrC仍无标准辅助化疗方案,最常用的化疗药物是顺铂和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 5-FU)。Szarvas等[22]发现顺铂和5-FU联合比单独使用有更高的应答率,且此方案与其他化疗方案比较[23]反应率最高,肿瘤进展率最低(分别为43%和14%)。
Lee等[24]对17例UrC患者进行了基因测序,发现APC、COL5A1、KIF26B、LRP1B、SMAD4和TP53等6个基因与UrC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些基因改变也见于膀胱癌与结直肠癌,提示UrC与膀胱癌和结直肠癌具有相似的遗传变异。因此,有研究认为大肠癌的标准化疗方案对UrC患者也有效,相关研究显示mFOLFOX-6(亚叶酸、氟尿嘧啶、奥沙利铂)方案对UrC有效[25]。
有研究表明,UrC对于放疗的反应率约为30%~40%[21]。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切缘阳性、腹膜浸润、高等级肿瘤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应行辅助放疗[21]。
过去的几年中,分子生物学技术、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的发展为UrC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Reis等[26]在70例UrC患者中检测到73个致病突变和4个基因扩增,其中错义突变是最常见的突变类型,其次是截断突变和无义突变,最常见的基因改变是TP53突变。Lee等[24]发现KRAS、MYC和生长因子受体参与了UrC发生,表明它们在UrC的靶向治疗中具有潜在价值,其中KRAS、FGFR和EGFR均与MAPK信号通路有关,这意味着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抑制剂或FGFR抑制剂可能是治疗UrC的一种策略。例如,EGFR拷贝数增加提示抗EGFR药物(如西妥昔单抗、帕尼妥单抗)可能有效,MYC扩增提示MYC抑制剂可能有效。因此,在UrC的治疗中,应考虑对这些类型的基因改变进行临床试验。Mäkelä 等[27]使用1 160种药物对UrC细胞进行体外药物筛选,发现UrC细胞对靶向抑制MAPK信号通路中MEK和mTOR位点的药物敏感。UrC的分子改变谱与传统的尿路上皮癌明显不同,而更类似于原发性膀胱腺癌和结直肠腺癌。原发性脐尿管肿瘤存在TP53(最常见)、KRAS、NRAS、BRAF、APC、NF1和/或Smad4突变,但通常无TERT启动子和PIK3CA突变——两者在尿路上皮癌中很常见;此外,在原发性UrC中,有报道显示存在FGFR基因家族(FGFR1、FGFR2和FGFR 3)和/或EGFR扩增[28]。Nagy等[11]发现10%和15%的UrC患者分别出现APC和PTEN突变,两者皆参与了大肠癌的发生。这些研究提示,在制定UrC的诊断及治疗策略时,临床医师可以从大肠癌的治疗方案中汲取经验。
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L1)的表达率在UrC中较膀胱肿瘤(14%~28%)低[29]。Maurer等[30]在UrC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中均未发现PD-L1表达,Reis等[26]发现,约16%的病例中发现肿瘤细胞表达PD-L1,Kardos等[31]观察到MSH6突变患者使用抗PD-L1抗体阿替利珠单抗后病情保持稳定。
四、预后
与膀胱尿路上皮癌和腺癌中的非UrC相比,UrC预后更好,其总的5年生存率为45%~49%,肿瘤特异性生存期的中位值约为48个月,而尿路上皮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约为27个月[19]。
影响UrC患者预后的因素包括肿瘤分期、术后切缘阳性、肿瘤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和手术类型,其中手术切缘是最重要的预后预测因子,而肿瘤大小和组织学类型等对预后影响不大[19,21]。Ashley等[14]在多变量模型中发现了2个UrC独立的生存预测因子:肿瘤分级和切缘情况。研究表明,患者的生存时间与肿瘤分期密切相关,Ⅰ、Ⅱ期患者平均生存时间是10.8年,如果患者累及局部淋巴结或扩散至周围脏器(Ⅲ、Ⅳ期),则预期寿命显著下降[10]。其中,Sheldon分期系统较Mayo分期和TNM分期对于预后更有意义[5]。目前研究发现,上述的各种肿瘤标志物、免疫组化和遗传改变均与预后无显著相关性[5]。但有研究认为,CK7阳性是UrC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3]。
五、总结
UrC早期症状不明显,缺乏典型临床表现,漏诊、误诊使UrC诊断晚于一般的膀胱尿路上皮癌,且由于UrC的罕见性,对其相关诊疗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改善UrC的预后极为重要。目前关于UrC的多数研究,其肿瘤样本数量较少,并且来自癌症的不同阶段。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的样本对于研究UrC特异性突变有重大意义。此外,个性化治疗可能是UrC更合适的选择。免疫治疗对UrC可能有潜在的效用,但需要更多的相关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