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亲密爱人”下手
2023-08-04吴雪
吴雪

《致命爱人》作者简·蒙克顿·史密斯(Jane Monckton Smith)教授是一名犯罪模式学家,专门研究凶杀、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等案件。
英国北方一座美丽的小镇上,文森特正紧攥着一把长而锋利的刀,站在一幢平淡无奇的办公大楼的停车场前。看到妻子唐娜走出来,还没等到她打开车门,文森特便向她捅出了第一刀。一下,两下,三下……这个动作直到唐娜死亡时依然没有停止。
文森特捅了唐娜38刀,然后打电话报警自首。这是《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一书里提到的一起凶杀案,这类发生在现任或前任配偶、伴侣间的凶杀案件,被称为“亲密伴侣谋杀”。
杀妻碎尸的许国利,杀害香港名媛蔡某的邝氏家族,再往前,杀妻藏尸冰柜的朱晓东、将孕妇妻子推下悬崖的俞某冬,都是登上新闻的一个个“文森特”。
很多人担心媒体对亲密谋杀的密集报道,会引发模仿犯罪效应。但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分析了十年间的数据,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在出现一起轰动事件后,媒体在一段时间内会倾向于优先报道同类型的事件。
这也从侧面反映,“亲密关系犯罪”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往不断发生,未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6 月 28 日,山西垣曲县一男子杀害妻子和 3 个月大的儿子,并将岳母砍伤,或因彩礼纠纷;隔天,“男子杀害妻子欲藏尸冰柜案”一审宣判,凶手高某一审被判死刑;7月10日,长沙一男子在某企业门口杀害妻子,行凶原因疑似男子出轨后多次起诉离婚被驳回产生怨恨。
那么,原本最亲密的爱人,为何成为了枕边最危险的凶手?是一时的激情还是长久的谋划?而她/他们为什么不离开,是什么限制着她/他们的自由,让她们无法逃离?
消失的总是“她”
婚姻之外,同居、恋爱等或长或短的亲密关系,都有可能成为滋生暴力的隐秘角落。社会新闻中从来不缺少案例。
2020年8月4日,云南勐海县警方通报,应届女大学生失联案件取得新进展。女生男友洪某与另外两名男性合谋,将女生诱骗至勐海县郊外的山林中杀害并埋尸。结局是悲惨的,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她本应该在8月1日参加江苏省的自学考试。
在亲密关系暴力事件中,女性似乎更容易受到伤害。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2020年7月,南京女大学生被男友诱骗到云南杀害。
根据《柳叶刀》2013年发布的一项全球系统性研究,约七分之一的谋杀案是由死者的伴侣或前任伴侣所犯,且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受害者数量是男性的6~10倍。到了2019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全世界共有87000名女性被蓄意杀害,其中30000名是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所谋杀。
而涉及青少年的此类案件,女性受害者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0%,近四成男性凶手是她们的前任恋爱对象。这些数字反映了记录在案的凶杀,实际数值显然要高得多。
作为跨域医学与法学的“双料”学者,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重庆市公安局特邀犯罪心理学暨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向静认为,对于伴侣关系中的谋杀,受害者和施暴者的性别比例是一种普遍趋势,但并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性别本身,伴侣谋杀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如权力关系、控制欲望、家庭暴力、性别角色等。
数据画像显示,男性凶手有13%—58%处于失业状态,情感障碍患病比率较高约17%,39%的凶手在童年目睹过家长之间的暴力。凶手可能在实施犯罪前有“迷恋”表现,比如,跟踪、持续打电话、发消息,幻想自己除了杀死她别无选择。
相比之下,杀害男性伴侣的女性,多数曾遭受过对方的虐待,受教育水平较低,意味着可以求助的资源更少。女性往往会在遭受过多年虐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穷尽所有求助资源而不得,以及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杀死男性伴侣。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2023年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姚某某因不堪丈夫长期暴力,在绝望无助、心生怨恨的情况下,持宿舍内的螺纹钢管猛击其头部数下,又拿来菜刀砍切其颈部,致其当场死亡。法院认定其故意杀人“情节较轻”,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向静告诉《新民周刊》,每个案件都有独特之处,一些常见的心理特征可能与谋杀行为相关。比如,情感操纵、家庭暴力和虐待倾向,凶手可能试图通过暴力来控制伴侣或解决嫉妒心理,或因缺乏对他人感受的关注与连结,表现得冷酷无情,进而更容易实施谋杀。
谋杀后的自杀,也是亲密伴侣谋杀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几乎有一半凶手会在谋杀伴侣后试图自杀,特别是男性凶手。这类凶手可能因伴侣身患绝症等原因终结其性命,也可能是强迫另一半与自己一同自杀或殉情。
长期暴力和情感操纵也会导致受害者自杀,加害者很难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大量死亡仅仅被记录为灾难、意外、自杀或其他自然原因。事实上,那些“看不见的凶杀”,并没有被更加慎重地调查。
一场有预谋的犯罪
现实情况往往是复杂的。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在读博士张蔚,因为专注于犯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为了知乎等热门网络平台热门的答主,他曾经接触过这样一则案例:2010年,深圳有对同居近20年的情侣,在一场与往日无异的争吵中矛盾升级,男方拿起厨房的菜刀,砍向另一半。三刀落在脖子,一刀落在头上,女子当场身亡。
复盘这一案件,当事男子曾经有过婚姻经历,又遇上生意失败,被害者与他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两人具有特别的感情基础,只是在日常琐碎中累积了负面情绪,在外因触发下失控。结合另一个杀妻案,当事男子一整天遭遇大雨、迟到、工作不顺,在临睡前,看到老婆手机上一条露骨的消息,两人爆发激烈争吵后,一失手,把她打死了。


杀妻碎尸的许国利在媒体面前陈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时,神情镇定。
有超过80%的凶手,有过预先构思计划。他们可能由于经济纠纷、情感纠纷等长期矛盾累积而预谋实施凶杀。
不可否认,亲密伴侣谋杀一部分是基于“激情犯罪”。但有超过80%的凶手,有过预先构思计划。他们可能由于经济纠纷、情感纠纷等长期矛盾累积而预谋实施凶杀。比如,杭州来女士失踪案、香港名媛蔡某凤碎尸案。“激情犯罪更强调瞬间情绪爆发和冲动控制失常,与情绪调解困难、个人攻击性倾向和解决问题不成熟应对机制有关。亲密伴侣谋杀则是长期关系问题累积的结果。”向静分析道。
在《致命爱人》一书中,史密斯通过研究四百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提出了八个阶段历程的 “凶杀时间轴”。这一概念也挑战了“激情犯罪”为此类案件辩解的叙事。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分会前任委员吴国宏认为,操纵者对受害者的恶意、不满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在心头盘算得失,最终计划妥当,才走上这条路。
以“网红拉姆案”为例,被害人拉姆被前夫唐路泼上汽油并点火致其烧伤,半个月后因医治无效死亡。案发前,唐路用孩子当筹码,威胁拉姆说“不复婚我就杀了他”,被迫复婚后,唐路的行为变本加厉,他一拳砸在拉姆姐姐卓玛脸上,造成她左眶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

左图:被前夫烧伤后死亡的网红拉姆。右图:拉姆前夫唐路受审。
于是,拉姆下定了决心离婚,不识字的她去县城找人写了离婚诉讼书,以失去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为代价,换取了自由。但这时候,唐路权力感的丧失,让他开始相信必须毁掉拉姆才能重新夺回控制权,这也是诱发操纵者在后来阶段里走向杀人的临界点。
和唐路一样,大部分操纵者都会对谋杀作出计划,有人会盘算杀人的方式和手段,有人会精确计划如何实施,还有人不仅会策划杀人还策划如何逃脱,通常他们还会借助网络完善杀人计划,比如,购买一整套杀人工具,书籍、刀具甚至可能用到的物品。
发生在2016年的上海杀妻藏尸案,凶手朱晓东在争吵中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杨俪萍,并把她的尸体藏于冰柜中长达105天。事发两个月前,朱晓东就购买了《死亡解剖台》《死亡哲学》等书籍,其中他的藏尸手法也与书中所描述的案例多有雷同。
香港名媛蔡某凤碎尸案现场证据也揭示,房间内的墙壁上,精心挂好了帆布,为的就是防止杀人时血液溅到墙上留下证据,用来行凶的地点也地处偏僻,久不住人,异常安静。
在几乎所有亲密谋杀案中,操控者行凶前后均有或多或少的反常表现。在决心杀死唐娜前的一段时间里,文森特不再观看一部名叫《科里》的电视剧——这是文森特保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在另一起案件中,凶手下定决心杀人前,移动了家里的沙发,而这个沙发20年都没有被移动过位置。
杀妻碎尸的许国利,在镜头面前神色泰然地讲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笃定“她肯定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她出不去的”;跟来女士的家人讲,“找不着就不用找了,出去玩几天,可能就回来了”。有媒体报道,被捕前一天,碰到同小区的居民,丈夫还骑车笑着打招呼。“许国利面对妻子的离奇失踪过于镇定自若,是其反侦查行为的表现,也让其疑点上升。”向静分析,“此外,从心理动力学的观点来看,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和纠纷可能触發个体内心的冲突,许国利可能试图通过暴力或谋杀来解决或逃避内心冲突。”
根据公开媒体报道,许国利炒股欠下百万元贷款,向来女士借钱遭拒绝,还被破口大骂,他自称日子过得憋屈,被逼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现实原因上看,许国利是为经济利益杀妻,而从心理学角度上,他将自己内在的自尊受损、焦虑、愤怒不安等统统痛苦归因于伴侣,并将其视为外部威胁,报着侥幸心理妄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掉眼前的问题,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向静说。
嫉妒、暴力与性别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往往伴随着“过度杀戮”和“持久性暴力”。
在这类案件中,行凶的过程是充满着愤怒的,“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受害者大多在临死前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操纵和虐待。吴国宏认为,再计划周密的犯罪,在最后行凶那一刻,仍旧需要动物性的冷酷凶残,在精神分析层面,“泛性”本能中包含生与死两个方面,前者与生殖、繁衍相连,后者就与攻击、杀戮相关。
而在很多时候,孩子也被视为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他们要么是被当成“附带伤害”被杀害,要么被故意安排目睹自己母亲的死亡,以此留下长久的、不可抹去的伤害。
7月10日,长沙街头杀妻案中,受害者张莉因发现丈夫重婚提出离婚,在离婚官司开庭前两天,张莉还未下班,17岁的女儿前往张莉公司拿钥匙,没想到,丈夫贺敏也尾随其后,找到下楼出来的张莉,当着女儿的面,从身后直接杀死了她。警方调查取证发现,贺敏曾对张莉有家暴历史。
那么,为什么亲密犯罪中总伴随着性侵、暴力、虐待。吴国宏认为,“男子气”是一种基于生理性别建构的社会性别文化,世俗层面,要求男性强硬,不被鼓励展示脆弱,追求成就和成功,鼓励同性之间的竞争,拒绝“女里女气”。
性别社会学研究者王向贤在2011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即使在普遍认同“性别平等”的地区,仍然有39%的女性遭受来自伴侣的暴力。超过半数的男性受访者认为“男人应该强硬,必要时用暴力维护尊严”“男人不应该打女人,除非女人挑战了男人的声望”。
男性婚姻期待中,还包含了一种“性”方面随时可以得到满足的预设。比如,很多人会把亲密关系对象“异化”为某种工具——从传宗接代、性欲发泄、装点人生门面,甚至经济图謀,在他们的认知世界里,两性平等、尊重的交流与审视,可能压根不存在。
在这些僵化的角色认知中,男性需要在亲密关系中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一旦这种预设受阻,男性可能被定义为社会中的“失败者”,伴随着理想的男性角色土崩瓦解,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最终作出杀害伴侣的行为。“仿佛自己终于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终于亲手毁掉一个人让其他真实或想象中的同性对手彻底落空,也终于‘男人了一把。”吴国宏补充道。
此外,过度或反复出现的嫉妒,也是一种警告的信号,它反映出一种行为的模式、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持续的威胁,嫉妒使操纵和摆布变得情有可原,嫉妒法则以及激情犯罪的神话赋予操纵者权柄,是因为它们给了实为操纵的情形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忠诚法则往往紧跟在嫉妒法则之后,并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操纵闭环,其他的控制则在其中得以培育萌发。

即使在普遍认同“性别平等”的地区,仍然有39%的女性遭受来自伴侣的暴力。
不过,吴国宏也表示,这些都是宏观泛化的分析,具体而言,亲密犯罪的男性往往存在人格扭曲和偏差,在司法流程中都会接受所谓“是否”具有行为责任能力的考量,但“肯定”的结论背后,有很多并没有公之于众的专业评价和报告,这些人一般会有偏执、反社会人格的特征,很多甚至达到心理疾病的程度。
还有一部分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可能基于被害妄想、嫉妒妄想、命令性幻听等病理性精神症状而作案,且作案时也可有预谋与反侦查行为。电影《消失的她》男主角何非就是偏向于自恋型人格障碍合并反社会人格的人。当女主角李木子锁在囚笼里,表示呼吸困难时,何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没有任何触动和波澜,更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
“剥夺理论”下的人质困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张三”,也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幽暗的一面。
犯罪心理学者武伯欣强调,亲密关系交往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即使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也藏着点点的“蛛丝马迹”。比如了解伴侣对待争吵和冲突的方法,当双方正确地认识到亲密关系当中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哪些,就可以站在这一点上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但是,现实的困境仍然存在。对婚姻关系中的受害者来说,逃离的过程艰险万分。三年前的8月,河南商丘的刘女士遭到了结婚以来的第三次家暴,丈夫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二楼。情急之下,她选择跳楼逃生,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双下肢瘫痪。经历了长达九个月的恢复,她提起离婚诉讼,而后在网络上曝光,终于逃出婚姻囚笼。
有观点指出,操纵欲强的人会试图把受害者困在一段关系中,让她们难以离开,类似于人质困境。因为情感操纵通常是由施暴者的恐惧所驱动的,同时由受害者的恐惧所维持。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受害者会逐渐形成一种“长期的恐惧”,这是人们的生存本能。
人们通常会用“煤气灯效应”来形容被操纵的受害者因为无法信任自己的认知和直觉而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并变得无法反抗的现象。一方面,习惯性的恐惧让受害者下意识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长期的情感控制令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
向静认为,心理学上的“剥夺理论”也提供了一种解释。在伴侣关系中,受害者可能遭受了面临人际交往、自尊和掌控感的剥夺,面临着离开的各种风险和困难,包括经济依赖、住房问题、情感社会支持缺失乏以及对未来的担忧,特别是如果还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使得离开变得更加困难,让受害者感到束缚和无法自拔。
“受害者在婚姻中可能面临一个困境:如果他们相信操纵者会改变或停止操纵行为,他们可能选择继续忍受操纵,以维持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一些受害人认为自己是因为‘爱而无法离开。操纵者善于威逼利诱,常声称‘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甚至以伤害自己或自杀作威胁,激发受害者的担忧、关心与内疚。”向静说。

电视剧《不完美受害者》中遭受家暴的米芒。
操纵之网还包括了与其他人明里暗里的共谋。在美国佛州女子洁丝敏的案例中,她的婚姻是包办的,和姻亲住在一起。她没有朋友,没有联系人,谁都不认识,被公婆及大家庭限制,她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粗活,洁丝敏感到被困住了,她不认为自己有离开的可能,逃跑无济于事,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
显然,亲密关系犯罪中的心理和情感操控增加了法律监管的难度。而亲密谋杀之前的暴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法律的支持,还存在证据收集困难的问题。
向静认为,许多案件发生在私密场所或限制自由的环境,导致受害者难以获取证据或报告犯罪。受害者在暴力发生后,会经历较长的思考期,没能在第一时间验伤,导致证据很快灭失。
其次,受害者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如恐惧、羞耻、经济依赖或感情上的压力而不愿意报告犯罪。他们可能担心社会的质疑和指责,或者担心报告后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在社会文化的偏见里,对于亲密关系的暴力或性侵可能存在误解或鼓励沉默,这些困境,也给法律监管带来挑战,限制了受害者获取帮助的渠道。
2023年1月1日,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扩大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适用于妇女在分手或离婚后遭受纠缠、骚扰、泄露或传播个人隐私的情况,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以来,家庭暴力逐步从一个私领域走出来了。
此外,受害者也应增强自救意识,寻求妇联、司法机关的支持,以及留存好通话录音、聊天记录、伤情诊断证明等证据十分必要。还有一点,受害者一定要有这个想法:遇到暴力不是我的错,自己的任何不足都不能成为暴力的理由,都不能把伤害正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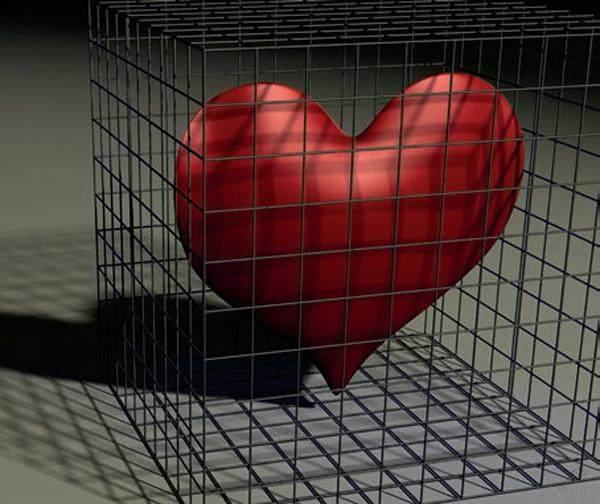
受害者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如恐惧、羞耻、经济依赖或感情上的压力而不愿意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