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梓森:“追光逐芯”的一生
2023-0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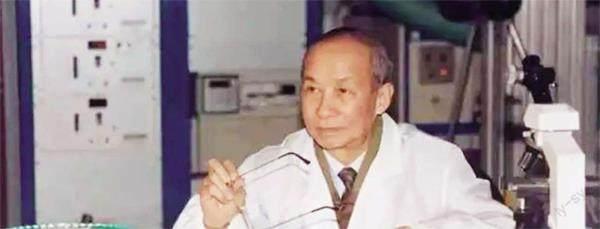
赵梓森是武汉邮科院的开拓者,是“中国光纤之父”,是“中国光谷”的倡导者。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光纤通信从武汉邮科院获得国家项目立项起步,1982年连接武汉三镇的“八二工程”作为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里程碑,逐步实现产业集群发展和腾飞,是他开启了中国光通信大国之路、强国之梦。赵梓森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科技进步追求和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光通信事业孜孜不倦追求的一生。
大学毕业后,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工作,由于教室和课程已经排满,他暂时被安排到实验室工作,很快就因为勤动手、善思考、肯钻研的特点让领导刮目相看。教课之余,赵梓森开始深入研究和反复推敲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基本课程,这为他后来投身大科研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一直坚信:“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大建设,你只要有本事,就一定有事业可为,有大事可做。”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1972年,邮电部将“大气激光通信项目”交给武汉邮电学院,1971年以前,这个项目都是由北京的大研究院承担,但因为缺少关键仪器——平行光管(没有平行光管,光学天线不能校正焦点)而进展缓慢。因为赵梓森爱搞科研,名声在外,他被委以重任,成为项目负责人。
赵梓森另辟蹊径,“土法上马”,他把天线搬到屋顶,利用太阳光作为参考光源代替平行光管校准了光路,几天后就有了进展。通过这个项目,改善了激光器、校准了光学天线、增加了光放大器,还设计出脉冲调相通信系统代替PCM通信机。一年后,通信距离已经从最初的八米跃升到十公里(发端是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武汉六渡桥水塔顶,收端是青山水运工程学院,晚上用灯作信号对光,传输距离达十公里),取得重大进展。
1966年,美籍华人高锟在英国BTRL上发表的论文提出玻璃丝的损耗低达20dB/km,可用于通信,为此美国康宁玻璃公司花了3000万美元研制出3根长30米、损耗为20dB/km的光纤,认为光纤将会引起一场通信技术的革命。
在完成“大气激光通信项目”后,赵梓森听说美国在研究“光纤通信”——利用玻璃丝进行通信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解决雨雪天气通信失灵的新办法可能找到了。赵梓森提出要发展“光纤通信”科研项目,但绝大多数人反对,包括一些领导和专家。他们当时都不理解:“玻璃丝怎么能通信?赵梓森你不要胡搞,要花几千万元,你负得了责吗?”
赵梓森坚持认为,技术路线是科研成败的关键,在他的坚持和个别领导的支持下,他领着几个人设立了光纤通信这个可有可无的小项目,做前沿试探性研究,连正规的实验室都没有,项目组就在实验楼厕所边的清洗室内做化学试验。在遴选国家科研项目时,邮科院与中国最早研发光纤通信的大研究所进行背靠背答辩,最终武汉邮科院的方案胜出,直到今天,在光通信领域,实践证明赵梓森提出并主导的石英光纤通信技术路线依然是正确的。
光纤通信步入正轨后,赵梓森开始负责邮电部“八二工程”,即要在1982年建设中国第一条实用化的光纤通信线路,让老百姓能够打通电话。在那段岁月里,赵梓森和同事废寝忘食、随时待命,终于研制、设计、安装、开通了我国第一条光缆市话通信工程。20世纪90年代又带队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长架空光缆工程——“京汉广工程”,长度达3000公里。
1995年,赵梓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即首批提出加快武汉光电子产业发展,将武汉建设成全国性光电子产业基地的倡议。
“美国有硅谷,中国也应该有个光谷”(由黄德修、许其桢等首先提出),2000年5月7日,赵梓森、杨叔子、黄德修等26位院士和专家在《关于加快技术创新,发展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建议》上签名,吁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武汉)”。同年5月31日,他被“中国光谷”聘为首席科学家,2001年2月28日,在他的倡导推动下,科技部正式批准在武汉建立国家光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命名为“中国光谷(武汉)”。
从2001年立项到2007年,仅六年时间,“中国光谷”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基地之一。2018年,他所在的武汉邮科院的光纤通信实验,让一根光纤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如今,“中国光谷(武汉)”是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和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之一,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光纤光缆和光纤通信系统设备市场份额占全世界一半以上。
尽管短短几年内,“中国光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纤通信产业基地,但赵梓森心里很清楚,在高端光器件方面,中国与美日最顶尖的公司还有差距。
2005年前后,光迅科技给赵梓森汇报工作时提出,在高端光模块的研发上,由于短缺光芯片而遇到困难。赵梓森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在光芯片这个领域,请公司早日布局,并且加大科研投入。不能算小賬,要算大账。未来10年或20年往后看,这个领域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赵梓森详细地解释道:“光迅科技作为光电子器件的国家队,高端的光芯片不能依赖进口,一定要自己搞,不能在将来被外国技术卡了脖子。”
那时候,中国的芯片领域还没有受到外国的限制,可以从外国进口,如果企业自身投入研究和开发光芯片,可以说是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站在短期利益的角度来看,让企业做出这样的战略布局是很不容易的。按照他的建议和指导,光迅科技很快调整了战略布局,加大了对光芯片的科研投入。时至今日,光迅科技每年的国产光芯片产量已经破亿。每年产品销售收入超80亿元,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已经解决了许多国外对我们的“卡脖子”问题。如果没有赵梓森当年的提醒,后果很严重。
1980年,赵梓森推动并创立了武汉邮科院硕士点,将科学研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前沿知识、先进理念等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源泉,为后续发展培养火种。退休后,作为邮科院的科技顾问,他经常给学生、员工作报告,每年的新员工培训、OFC论坛分享是他30多年来的坚守,他用退而不休的方式,用他那充满激情、具有穿透力的上海普通话,培育和浇灌着未来事业的种子。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武汉邮科院先后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追光人和一批批高层次人才,他们正带领着高水平的科技团队,一起为民族的光纤通信事业持续发展不懈努力。在赵梓森的推动和关怀下,邮科院先后成立了“国家光纤通信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培养了大批光通信人才,服务于三大运营商、烽火、光迅、长飞、亨通等著名公司。
除了知识上的传承,赵梓森教给后辈的还有家国情怀、无私奉献,回想起来让我们深受感动。赵梓森在指导学生和年轻人的时候,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们以后能够留在邮科院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找工作不要光为了钱,多为国家想想,多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以国家的光纤通信事业为重。”在他的指引下,无数学生和后辈都留在了邮科院生根发芽,在邮科院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光棒精神,一代代邮科人把他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薪火传承下来,共同推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通信事业砥砺前行。
关于创新,赵梓森如是说:“创新往往是发生在那些对某事物有极其浓厚兴趣的人身上,一旦迷恋,便废寝忘食,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赵梓森用其一生忘我地投入到我国光纤通信的创新事业中,战胜困难,超越自我,升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