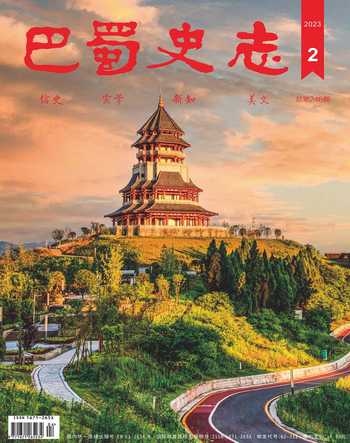王火:当代“谈迁”的另一面(下)
2023-07-29田闻一
此情可待成追忆
1983年,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有幸认识王火老师,崇拜他的人品学问,同他走得很近,哪怕过后转到了新闻战线,直至今天也是。他认为我是作家型记者,对作为后辈的我,很是关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像一个花园中负责的园丁,培育并注视着我这棵幼苗的成长、开花、结果。
我们彼此注视,相守相望。
1987年,我在中国作协主办的半月刊《新观察》第19期发表了《当代“谈迁”——记作家王火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全方位记述王火写作150万余字的三部曲,总题为《战争和人》背后的由来、艰难艰辛、曲折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不长,影响巨大,风靡一时,转载也多,直到现在。其间,他接到几家刊物寄给他的答记者问。他从来不知这些刊物,当然也谈不上答记者问。刊物中有关答记者问,是对我的那篇文章的抄袭。他给我看,我们都一笑置之,苦笑了之,这样的事多了,也很好地宣传了王火老师。
2007年,王火老师30余万字的长篇封笔小说《东方阴影》出版。同年7月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曲尽其妙》一文,对他这部封笔书作了评论。他认为我最能体察、表现他这部长篇小说的内核和精髓。我的这两篇文章,虽是草灰蛇线,但应该说,对王火老师在24年间的努力、突破,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绩、贡献,至少作了一个粗线条的总结和勾勒。为此,他表示赞许,我感到欣慰。
王火老师告诉我,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时,他的老师,著名的战地记者萧乾,把记者分为三类:一是记者采访时,表面上并没有怎样记、没有怎么用心,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却相当详实具体生动,富有冲击力,事半功倍;另外一种记者,虽然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很勤奋、很用心,做什么事情都是孜孜不倦;还有一种记者,相当努力,相当用心,相当勤奋,但结果总是事倍功半。他夸奖我是第一种记者。其实我知道,这是他对后学后进的我的鼓励、勉励和爱护。
我在业余时间,最初写作出版两本书,引起他高度重视,给我写了两封信,都发表在《四川日报》上。在此,不妨摘录一些——
闻一同志:
酷暑天,感谢惠赠大作《成都残梦》为我消夏。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可读性强,内容吸引人,有悬念,读来津津有味。读完全书20余万字,颇像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我在街上书店、报亭及书摊上看到《成都残梦》畅销。目前,正宗文艺书印数都少,《成都残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34000册(这是第一版的印数),真不容易。您的艺术品位是高的,却大众化,我很赞赏。我们很需要有畅销书作家,您颇有成功的条件。
曾读過您写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未遂政变》。那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真实题材,写的是蒋介石麾下将校军官团拟发动政变的一个真实完整的故事。为写那书,您曾利用休假,自费去东北采访当事人。书出版后,反应很好,也是畅销。《成都残梦》沿袭了《未遂政变》的写法,文字上更老练出色,有新闻记者犀利的鸟瞰透视力,也有小说作家细腻描写和让人物丰满于情节过程之中的技巧……
我不是说大作已经完美无缺,但成就是主要的。您工作繁忙,业余创作条件艰辛,锲而不舍使我感动,您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愿您接受我的祝贺!
王火
1992年8月
过后,他将这两封信,以总题《致田闻一的两封信》收入2017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的《王火文集》第9卷中。
王火人品很好,是于今难能可贵的君子、“真君子”——这点,是认识他的人的共识。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应源于他的家庭出身,源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教养,同时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他父亲王开疆,就不说了。当时,他们家住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等。王火儿时很调皮,但父亲从来不打他。他最怕父亲找他谈话,一谈话父亲就要从思想上挖根子。父亲教育方法很特别,不要求他读书成绩最好、拿第一,但人品一定要好;万事都讲一个“好”字,功课做得好一点,待人好一点,体育好一点……虽然他父亲在他16岁时牺牲,但对他影响很深。
这样家庭教育出来的子女没有差的,不仅王火好,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如此。他的哥哥一辈子隐姓埋名,是我国卓有成就、卓有贡献的兵器工业专家,年前去世;他的妹妹,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一家,有口皆碑。
王火的父亲在他十多岁时,同他母亲李荪离婚,之后又娶了两个妻子,第一个北师大毕业,对王火很好,可惜早逝;第二个蛮不讲理,在王火父亲牺牲后,争霸财产,将王火赶出家门,王火不得已去投奔生母李荪,那时,王火刚16岁……这些,在他的《战争和人》三部曲中,都有生动形象的展现、描写。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因此成就了王火。
如今,人生大局已定。
第二次入蜀,在成都生活了35年的王火不再走了,也不愿走。在王火看来,时年88岁的妻子凌起凤,2011年7月1日在成都病逝,虽然她离去已11年,但那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的飘逝;在感情上、意念中,他始终觉得起凤没有离开他,没有离开这个家。既然起凤没有离开这个家,他也不会离开。
我曾经问过他,您在上海出生,后来在许多地方都生活过:南京、香港、重庆、北京、临沂、成都……您觉得,您最有感情,印象最深的是哪里?他略为思索后,坦率地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和南京,毕竟我在上海出生,在南京有珍贵的记忆。但成都是我居住最长的城市,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交了很多本地朋友,感情很好。四川,尤其成都,是座兼容并蓄的城市,很养人。四川人待人热情,性格活泼,幽默风趣。四川藏龙卧虎。我爱人去世后,在上海的几个妹妹怕我孤单,多次邀请我回上海居住,我都拒绝了。我已离不开成都了。一方面是成都舒服,还有很多朋友,比如马(识途)老、李致。另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她——他指了指挂在对面墙上的妻子的照片,我要在这里陪她。
毫无疑问,凌老师的去世,对王火打击很大,让他很是伤心、伤感,加上这些年年龄日增,他的身体急剧衰弱,随时要住一段时间的院。他其实很不喜欢住院。
我们本来就是“君子相交淡如水”。他不喜欢有人打扰。我平时尽量不去打扰他,只是逢年过节,或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候,打个电话向他问好。每次电话通了,电话中总是传出王火老师那口好听的、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显得年轻、清晰的带有江浙味的普通话。他总会抢先问:“闻一,你好吗?我很想念你……”让我感动。
在我看来,作家成功的人多,比如: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和徐志摩等,还有国外王老师或崇拜、或喜欢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高尔基,法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但是,在家庭生活方面,能有王火老师这样成功的,殊为难得。
时至今日,王火老师的视力很差,已完全不能读书看报了。年前,他把一生中珍藏的海量的书,包括珍藏的手稿,悉数捐献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相当重视,专门派了几部大卡车来成都运回去保存。
2021年底,我要去海南长住一段时间。出发之前,专门去看望了王火老师,给他带了一本我写的刚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大西皇帝张献忠》,这本书多年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过,当时书名叫《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得了巴金文学奖。
送王老师这本书,不过是个心意,料想他是不会看的。这么厚一本书,30余万字,字小,一般人看来也费劲。不意开春我回成都后去看他,言谈间,王老师居然把我这本书看完了,看得很细致,多有肯定和鼓励,让我十分感动。从这些地方,再次看出王老师对人的真诚,对后学的支持鼓励,还有期望之殷。
他的10卷本《王火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写给我的两封信,收入其间第9卷中。这对我自然有不同的意义和感情,因此,我将第9卷在手中多摸挲了一会儿。我知道,向来送我书很大方的王老师,之所以没有把这第9卷送我,是因为他已经无书可送。他要送我这第9卷,就得去买,而且光买第9卷还不行,得买每本厚得砖头似的10卷本。况且,他写给我的两封信,发表在《四川日报》的当期报纸,我是收集起来了的。
不意,半个月后,王火老师的女儿王凌打电话给我说:爸爸要送你的第9卷本到了,请你来拿,爸爸住院去了……王火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意的人。
2019年11月末,成都在宏大的世纪城举办第一届天府书展、书市。
我也应邀参加。我发现世纪城大门外的高墙上,挂着一些大都是成都地区的招牌人物相片。时年95岁的王火老师和已然105岁仍在创作、堪称世界作家之最的马(老)识途,高悬上方,位列首席。墙上的他们,对大批络绎而入者颔首微笑。我很高兴,当即用手机拍了王火老师的照片,用微信发给了王凌。
下午回家,在手机上看到王凌传来的王火老师留言:“闻一!”仍然是那口熟悉亲切的带有江浙味的普通话,他不知怎么得知了,在这届书市上,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他们作为重点书出版的我的川军系列书4本,而且反响很好,销得很好。留言中,王火老师对我一如既往的赞赏、鼓励。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太留意,只是思想上电光石火般闪现出这样一些细节,这样一些画面——
18岁到江津的王火,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凌铁庵最喜欢、喜爱的年轻人、准女婿。
凌铁庵原名凌昭。1885年出生于安徽定远一榜眼府邸,是著名清代爱国将领聂士成的外孙婿。他本是武人出身,爱国将领,当过安徽革命军第五师师长。过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服膺于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后受孙中山指示,回国参加了诸多斗争。后来在东北,遭受“东北王”张作霖嫉恨、暗害,张作霖派人将凌铁庵炸伤,致使凌铁庵双目失明。
双目失明的凌铁庵最喜欢王火念书、读报给他听。
一次,凌铁庵问王火,你有多高?王火说一米七六。凌铁庵说,我看不见你,你能不能让我摸摸?王火走上去让凌铁庵摸了。
王火相貌俊朗、身肢修长,四肢匀称。
凌铁庵说:“好了。我清楚你了,倜儻!”凌铁庵又说:“我听人说你倜傥,果然倜傥。”一般而言,在“倜傥”之前,是要加上风流二字,叫“风流倜傥”。凌铁庵虽然双目失明,却看得很准,王火只有倜傥没有风流,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1949年春天,凌起凤随父亲去台湾前夕,与王火在南京见最后一面。凌起凤调皮地叫王火,“溥老!”她突然宣布:“我要在这里同你私订终生了。你愿意吗?”王火闻言心如鹿撞,喜不自禁,立即回应:“我愿意。我要终生爱你!永远同你相亲相爱!”
凌起凤用她那双美丽的丹凤眼,很专注地凝睇了他一会,专门问:“是永远吗?”
“永远!”王火回答得斩钉截铁。
“好!”凌起凤说:“我不会轻易说爱谁。一旦说了,哪怕雷霆万钧,必然生死相许、相随。我这人,就像秋瑾‘身不在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我会信守终生的。”凌起凤大有其父基因,有种侠肝义胆的刚烈。
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凌老师曾经对我谈起过,她从台湾回大陆时的矛盾痛苦:“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女。何况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和我所处的时间最长,感情最深。明知我这一去,我们父女就是生离死别。可是我的老父亲离不得,又心疼他的女婿王洪溥,他还是鼓励我回大陆去与王洪溥完婚,白头偕老……”听凌老师说到这些,让我感慨莫名。
我完全可以想象,凌老师去后,在漫长的十年间,在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落叶敲窗的夜晚,王老师都没有睡,都在思念凌老师。他或是坐在书房里的书桌前,与挂在对面墙上的爱妻照片面面相对,相互凝睇。照片上是凌起凤老师的老年照。虽满头鹤发,但仍然美丽、端庄大方,风采依旧。照片上的她,用那双美丽的丹凤眼注视着他,凝睇着他,似乎在叮嘱他:不要熬夜。天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注意身体……事无巨细。而每当这个时候,王火老师都有些恍惚,觉得起凤不是离他而去了,而是到英国小女儿王亮家小住一段时间去了。王亮留学英国有年。学有所成,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生活幸福……
我想,我该结束这篇文章了。王火老师喜欢唐诗,那就用白居易的名诗《长恨歌》中的最后几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恨)绵绵无尽期。”来结尾吧,我将原诗中最后一句中的“此恨”改为“此爱”。因为他和凌起凤一生中只有爱,没有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