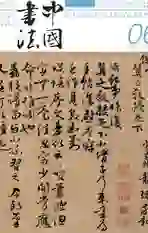挥运之理:书法的形构经验与美学意义
2023-07-25詹冬华李鸿川
詹冬华 李鸿川
关键词:挥运之理 书法形式 美学意义
自汉以降,古代书论及批评中就不乏有关书法的种种喻象描绘,或风雷云水,或飞鸟虫蛇,或龙虎凤鸾,等等,其中尤以动物为多,也有部分植物与自然现象,所描绘的基本上是各种动态的物象。这些『喻象描绘』带有诗性想象的成分,如果与书法的笔墨形态对号入座,往往会方枘圆凿,难以索解。实际上,古人所描绘的动态意象主要不是书写之后的图像结果,而是包括『空中挥运』与『纸面动作』等在内的多维度、全方位的动作体系以及由此生成的气韵动势效果。也就是说,古人观念中的书法不仅仅是静态的笔墨图像,还是一次完整的书写行为。古人的喻象言说,实际上是对无数次书写行为的经验总结与美学描绘。
『空中挥运』与『纸面动作』。书法的挥运动作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纸面动作』,二是『空中挥运』。对于『纸面动作』,前人之述颇为丰赡,如孙过庭的『起伏衄挫』,米芾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董其昌的『自倒自起,自收自束』,等等。明清书家对书写动作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如解缙《春雨杂述·书学详说》谓:『若夫用笔,毫厘锋颖之间,顿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扬之,藏而出之,垂而缩之,往而复之,逆而顺之,下而上之,袭而掩之,盘旋之,踊跃之,沥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扫,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挥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坠之,架虚抢之,穷深掣之,收而纵之,蛰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莹,鼓之舞之使之奇。』[1]
实际上,解缙所列述的不仅仅是『纸面动作』,还包括『空中挥运』。『空中挥运』是书写动力产生的初始阶段,『纸面动作』是书法形态的关键成因,空中取势,纸面赋形。书写一旦开始,『空中挥运』与『纸面动作』便互为因果地交替进行。每当笔锋着纸,『空中挥运』便遁于『空际』,『纸面动作』所留下的笔迹则显于目前。一个独立的字乃至一幅作品的起始必然由空中开始,而后落于纸面,接着再次回到空中,又再次回落,如此反复,在一虚一实的交替中完成书写过程。这时『空中挥运』不只承担着时间先后交替的过渡,还同时肩负着极为微妙的空间性动作与创作意图。无论是传统书斋的小字还是榜书乃至明清立轴大字的书写皆不例外,即便书写过程中存在蘸墨或者有意地接笔行为也仍可看作是『空中挥运』的一环,它起到换气和调节作品章法节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统领书写动作的是书家的创作意识,即古人所谓的『意在笔前』。如果说落于纸面的动作在书写工具材质和书写法度的种种约束下逐渐偏离书家本意,那么『空中挥运』便是架起书家之『意』与书写之『迹』的桥梁。如此,那些曾经被认为隐匿不定的『笔意』便能找到一个更为明确的依托,而书法的精妙处也会有迹可循。由此,仅就每个笔画的孤立描摹或许还远远不够,这充其量只能算作合乎规范的『描画』,如一些初学者,所写字形笔画几近原作,而在细节和神韵上却判若云泥,究其原因往往是对原作的书写方式与挥运路径不够熟悉,导致书写连贯性不足。这种点画之间毫无关联的堆砌并不能完整反映『书写』这一特性,相反,将点画之间、字之间乃至行之间有效组织建构起来的『空中挥运』才是书法气韵与动势生成的重要环节。『空中挥运』的实质是生命『节奏』的表达,这种虚空中的动作形态是一种过渡。当然,它的存在必须配以『纸面动作』才有意义。
『挥运』与书法的形式构成。从『挥运』的角度来考察书法的形式,则要着眼于笔墨图像生成前与生成时的运动状态,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势、力、形。『空中挥运』取势,『纸面动作』发力,两者配合生成线条与字形。三者之中,势具有主导作用。蔡邕《九势》云:『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2]清代周星莲亦谓:『作字之法,先使腕灵笔活,凌空取势,沉着痛快,淋漓酣畅,纯任自然,不可思议。』[3]但书作的字势、笔势表现得较为含蓄,『势』犹如字的血脉经络,虽不可视,却隐约可感,观者需要通过点画的姿态与映带关系、字内部件的相对位置以及字间行间的空间关系才能体会『势』的存在,因此,『势』表现为动态的空间关系。书法用笔对『力』颇为重视,董其昌说:『善用笔者清劲,不善用笔者浓浊』[4]。『清劲』表示用笔爽利遒劲,『浓浊』则是拖沓无力,笔墨堆积。这种『力』的宣发主要靠『纸面动作』完成,运笔时要充分利用毛笔的弹性,时时顶得住笔,即行即驻。『势』具备『力量』与『方向』两个属性,同时也是『力』的蓄积阶段,所以,『势』对于『力』具有重要的生发与规导作用。而『形』又由『力』生,由此,『势』最终暗藏于『形』中。在实际书写中,『形』的生成往往取决于『势』的运用。朱履贞《书学捷要》谓:『书之大要,可一言而尽之。曰:笔方势圆。方者,折法也,点画波撇起止处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圆者,用笔盘旋空中,作势是也,圆出臂腕,字之筋也。故书之精能,谓之遒媚,盖不方则不遒,不圆则不媚也。』[5]此论囊括了『空中挥运』与『纸面动作』的基本要领。『盘旋空中』起到取势的作用,势对应着『动』,其路径以『圆』为主;『纸面动作』形成点画形态,笔画转折处以『方』居多,落成后趋于『静』。『空中挥运』不受笔纸间摩擦的束缚,故能较为灵活的施展手臂与手腕的『弧线运动』;而笔锋一旦着纸,这种动作就必须克服摩擦及墨汁胶质带来的阻涩感,再加之汉字点画结字的严密纵横,进一步限制了臂腕的自然弧线运动,这样一来,必须配合手指更为细腻的『小动作』,才能完成点画的精准书写。
需要进一步详明的是,因所书点画、书体以及书家的差异,『空中挥运』方式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挥运的速度、节奏以及幅度三个方面。笪重光在《书筏》中总结了不同笔画对应的起始形态和运笔动作的差异:『横画之发笔仰,竖画之发笔俯,撇之发笔重,捺之發笔轻,折之发笔顿,裹之发笔圆,点之发笔挫,钩之发笔利,一呼之发笔露,一应之发笔藏,分布之发笔宽,结构之发笔紧。』[6]这些『发笔』之处正是『空中挥运』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在冯承素摹本《兰亭序》诸多字的起笔处找到线索。如『亦由今之视昔』中的『今』字撇画的起笔处,有一定曲折的『虚尖』;又如其中『之』字挑画的入笔方向显然和第一笔的『点画』相呼应。从这些字的起笔形态可以想见,王羲之运笔的摆动速度相对缓慢从容。因为是行书作品,没有字间显性的连带,其间凌空取势受手部惯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整幅作品在节奏上比较舒缓,运笔的提按动作居多,绞转较少。相比之下,颜真卿的《祭侄稿》却透露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呈现出独特的『空中挥运』模式。从全篇首字『维』的起笔可看出,颜真卿当时下笔之猛烈迅疾。孙过庭《书谱》有言:『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7]『维』字给整幅作品定调,决定了这篇稿书的生成速度是『迅疾』的。同时我们可以从第六行的『亡』『侄』『赠』等字看出他处理字间连带关系的爽利与直率,由于下笔力度大,速度急,故『挥运』惯性很足,虽然也牺牲了某些笔画的细节,比如『标』『承』『知』等字的收笔处略显粗简残破,但它并不影响整体的艺术感染力,反而在情绪的流露方面形成视觉与动感的张力,营造了一种郁勃、悲怆的情感氛围。
『挥运之理』的美学意义。古人论书常用拟象比况的方式,将自然万物的生命状态同书法的形态互参互证,虽然设想绮丽,丰富鲜活,但难以理性逻辑演绎,变成可以传递的实践经验。究其原因,是因为后人只能见到前人的墨迹图像,却无法亲见当时挥运的情形。当前人的书论评语与墨迹同时呈现于后人面前时,就很容易被视作同一时空语境下的产物并等同视之。换言之,后人是依照前人的言语提示,从可见的『迹』追寻不可见的『所以迹』,但结果无异于刻舟求剑。如果转换一下思路,将书论批评中的『喻象描绘』与书家的挥运过程关联起来,可能就豁然开朗了。明代书画家徐渭对此中真意早有所悟:『余玩古人书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剑器、若担夫争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观雷太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点画字形,乃是运笔。知此则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惟壁坼路、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是点画形象,然非妙于手运,亦无从臻此。手之运笔是形,书之点画是影,故手有惊蛇入草之形,而后书有惊蛇入草之影;手有飞鸟出林之形,而后书有飞鸟出林之影……故笔死物也,手之支节亦死物也,所运者全在气,而气之精而熟者为神……以精神运死物,则死物始活,故徒托散缓之气者,书近死矣。』[8]徐渭所谈的『古人书旨』实际上就是『挥运之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古人所做的『喻象描绘』多为动态,实际上就是对运笔过程的形象化传达。运笔是『形』,所产生的点画是『影』,有此动态之形,方有此动态之影。再进一步,运笔者是人,依凭的是『气』,掌控并统领『气』的是『神』与『意』。气有体,却无形,它既与书家的神、意相通,又与天地宇宙的大化流行同轨合拍。如此一来,书法就不仅仅是可以观看的线条字形,而且还是其背后律动的挥运过程。